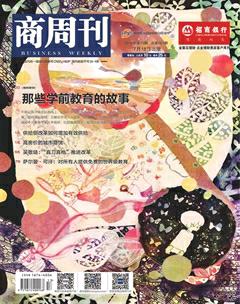雜文家的生存與死亡
多年前翻閱過一本閑書《兄弟文豪》,說的是魯迅和周作人的恩怨糾葛——情仇大概還說不上。骨肉手足本應相親相愛,殊不知雙雙成名后卻怒目相向,以致分道揚鑣。按照郭沫若的說法,“五四”期間最偉大的成就就是誕生了周氏兄弟。后來又讀到一些文章和資料,其中涉及魯迅與作人之間情趣愛好價值取向生活態度之異,但是被談論最多的,并不是兩兄弟的為人,還是他們的文章。
魯迅與周作人都是雜文大家,但兩位的雜文卻是風格迥異。魯迅的雜文是“匕首和投槍,要鋒利而切實”,“在風沙撲面,狼虎成群的時候”,“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對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但是周作人的雜文,卻一洗簡單粗率之風,更加地從容舒緩、飄逸灑脫。
其實,雜文并不是一般人腦子里固有的概念,并非一定要血脈賁張、劍拔弩張、一針見血、斗狠逞兇。雜文固然要有戰斗性,但論理說事卻要曲徑通幽處、潤物細無聲,且辭章與義理皆備,寓邏輯與思想于嬉笑怒罵或漫不經心的起承轉合之中。
可見,雜文實際上是很難寫好的。
但是寫好雜文并不是個純粹的學識、文采、智力、勤奮問題,它跟所有文體一樣,需要合適的土壤和環境,需要照應時代的呼喚。無論是雜文的極盛時期即民國初中期,還是首提雜文概念的南朝文藝理論家劉勰所處時代,抑或是優秀雜文百花齊放的春秋戰國時期,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當時的社會正處于新舊交替、各種思潮交流碰撞、文藝與思想的表達相對自由開放、大一統一元化的傳統意識形態相對式微,甚至迎來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唯有這樣的時代,才容得下雜文這種銳利的社會柳葉刀,去刮骨療傷、針砭時弊、指點江山。
那么,在當今我們這個時代,還需不需要雜文,還有雜文和雜文家嗎?
6月26日下午,56歲的知名雜文家朱鐵志先生自殺辭世的消息在網絡迅速傳播,眾多文化界人士表示震驚和哀痛。晚間人民網發布消息證實了這一消息。
朱鐵志先生1982年畢業后被分配到《紅旗》雜志社工作。1988年《紅旗》休刊,后來一本名為《求是》的雜志問世,朱鐵志在該刊從事政治理論編輯工作長達30多年。聞此噩耗后,我在朋友圈“大不敬”地發表了幾句感想,其中之一是說,這幾十年來,嚴格意義上的雜文已經不存在了,又遑論雜文家。
應該說,我這句話并不屬于價值判斷,而只是一個技術性的事實判斷。十幾年前就有過“時評勃興、雜文式微”的說法。而時評和雜文的不同,不僅僅在于文體上的表現手法各異,文章內容也有很大差異。簡而言之,在寫作方式上,現在要求“有話好好說”,不需要曲徑通幽、指桑罵槐、聲東擊西;而在內容上,傳統媒體都要求所評事件必須要有“正規”的由頭,甚至一定要有見報新聞出處。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時評的興盛和雜文的式微,都是不可避免的。如今好像時評也衰敗了,但主要還是就傳統媒體而言,網絡尤其是移動互聯網上的時評可謂汗牛充棟,且涉及題材稍寬泛于傳統媒體,看上去頗有些氣象。網上的雜文也是大量存在的,但緣于眾所周知之故,網絡雜文仍然是難成氣候。
生存還是死亡,對當下風毛麟角的雜文家來說,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正直且誠實的朱鐵志先生做出了自己的選擇,我們在痛惜之余,是不是也應該嚴肅地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如今都在說轉型。而在此之前,許多雜文都轉型寫時評了,但是寫得頗為痛苦。朱鐵志生前也在積極轉型,然而緣于其身份特殊等方面原因,轉型更加艱難。我看到他今年2月在自己分管的求是網上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對一個頭頂“著名雜文家”桂冠的老文人而言,撰寫那樣的理論文章,于他可能是太為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