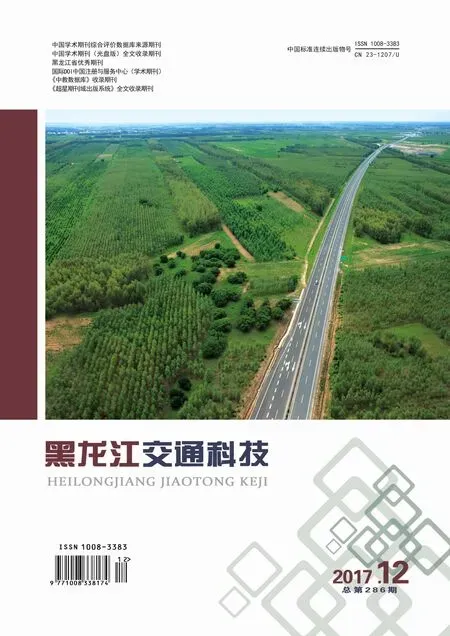高速公路CFG樁—網復合地基沉降控制效果研究
沈 遼
(江蘇中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江蘇 無錫 214072)
1 地基沉降測試數據分析
1.1 工程概況
江蘇省境內某高速公路DK171+432~DK171+583標段穿越高壓縮性軟土,結合現場原位測試和室內土工試驗測試獲取該區軟土層基本物理力學參數詳表1所示。

表1 土層基本物理力學參數
結合表1軟土層參數,DK171+432~DK171+583標段采用CFG樁—網復合地基進行處治。其中:CFG樁強度為C20,樁徑為0.5 m,樁間距為1.5 m,樁長10.6 m;墊層為0.5 m厚繼配碎石,內鋪設單層土工格柵,格柵極每延米限抗拉強度為90 kN。
1.2 測試數據分析
為研究高速公路軟土地基施工期沉降特性,在路基中線埋設沉降觀測板,借助測量儀器對路基填筑期沉降進行觀測。開始時間為2016年5月1日,監測頻率為2次/d。
由圖1的地基沉降隨填筑高度及時間變化曲線圖可知:填土高度增加,相應地基上部荷載變大,地基固結因上部附加應力增加而持續發展,是地基沉降的主要原因;地基沉降隨時間發展并不是按恒定速率發展,呈現明顯的三階段特征:(1)快速發展。填筑初期階段,沉降隨填筑荷載增加快速發展,沉降速率約為2 mm/d;(2)緩慢發展。地基固結隨附加應力發展速率較為復雜,但是整體呈現前期固結較快后期緩慢的規律,對應于地基沉降亦呈現出該現象,當沉降發展到一定階段后開始趨于緩慢發展,沉降速率為1 mm/d;(3)趨于穩定。當固結達到一定程度,地基沉降隨時間發展基本不再增加,該階段沉降趨于穩定,沉降速率幾乎為零。驗證高壓縮性軟土采用樁—網復合地基后,地基沉降在建設期基本完成,處治效果較好。

圖1 沉降—填土高度—時間變化曲線
2 樁設計參數對地基沉降影響
大量工程實踐證明,樁間距及樁徑與地基處治效果密切相關,而不同的地質條件影響的程度亦存在差異。基于此,借助有限元分析軟件ABAQUS建立三維數值模型,對相同條件下不同樁徑、不同樁間距等工況下地基的沉降特性進行對比分析。
模型中上部路堤尺寸參考圖1,地基橫向寬取50 m,豎向埋深取50 m;模型沿線路縱向方向取50 m。模型網格采用結構化網格劃分技術劃分,單元類型采用C3D8R六面體縮減積分單元。模型底邊采用固定邊界,縱向方向面采用法向約束,橫向兩側地基限制側向位移,其它區域采用自由約束。整個模型僅考慮重力場作用,地下水采用水土合算簡化處理。建立后的模型詳見圖3。

圖2 建立后的數值模型圖
由圖4可知:相同條件下,改變樁徑對地基沉降影響相對較小,樁徑為0.5 m、0.8 m和1.0 m對應最終穩定時的地基沉降分別為27.2 mm、30.42 mm和32.06 mm,增加樁基對應沉降減少幅值比約為1 mm/0.1 m;與增加樁徑地基沉降改善較小相比,改變樁間距與沉降發展更為密切。相同條件下,樁間距為1.5 m、2.0 m和2.5 m對應的計算40 d內最大地基沉降值依次約為32.06 mm、44.31 mm和52.43 mm。且從計算收斂趨勢來看,40 d內計算顯示樁間距為2.0 m和2.5 m條件下地基沉降仍呈發展趨勢。由此可見,增大樁間距使復合地基整體剛度下降,地基變形控制相對較差,因此在高壓縮性軟土區域更應合理的設計樁的間距。

圖3 改變樁參數沉降隨時間變化曲線圖
3 結 論
(1)由現場測試可知,地基沉降隨填土高度增加逐漸變大,且呈快速發展、緩慢發展和趨于穩定三階段特征;高壓縮性軟土地基采用樁—網復合地基處治后,沉降在建設期基本完成(處于穩定狀態),最終穩定時沉降值約為35 mm。
(2)由計算結果可知,改變樁徑對地基沉降影響相對較小,增加樁基對應沉降減少幅值比約為1 mm/0.1 m;改變樁間距與沉降發展更為密切,樁間距為1.5 m、2.0 m和2.5 m對應的計算40 d內最大地基沉降值依次約為32.06 mm、44.31 mm和52.43 mm,且樁間距為2.0 m和2.5 m時地基沉降收斂趨勢較差。
[1] 趙俊明,劉松玉,石名磊. 交通荷載作用下低路堤動力特性試驗研究[J]. 東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07,(5):921-925.
[2] 劉怡林,黃茂松,杜佐龍,等.公路路基地基承載力的離心模型試驗與分析[J].巖土力學,2010,(11): 3499-3504.
[3] 廖濟柙.滲透排水技術在平原區低路基高速公路中的應用研究[J].公路交通科技(應用技術版),2010,(12):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