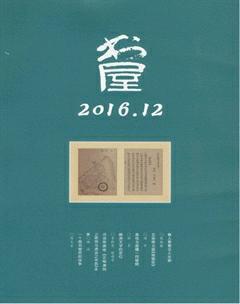“清晨來到樹下讀書”
黃發有
一
藏書票之所以可愛,除了在方寸之間擁有深厚的人文積淀之外,它形象地記錄和表現了讀書人的習慣與愛好。這些薄薄的舊紙片,對于不感興趣的人而言,就是一堆垃圾。可對于那些臭味相投的人而言,那真是掘之不盡的寶藏。在把玩藏書票時,經常會看到樹下讀書的圖案。我個人在學生時代,晴天的清晨特別喜歡跑到樹蔭下讀書,當和煦的陽光從樹葉的縫隙里漏下來,被陣陣微風攪動成一地碎金時,心情總是特別愉悅,記憶力也往往有超常發揮。記得當年有一首歌曲風靡一時,那就是谷建芬作曲、高楓作詞的《校園的早晨》,歌曲唱道:“沿著校園熟悉的小路/清晨來到樹下讀書/初升的太陽照在臉上/也照著身旁這棵小樹/親愛的伙伴親愛的小樹/和我共享陽光雨露/讓我們記住這美好時光/直到長成參天大樹……”
在我收藏的藏書票中,有十幾張都以樹下讀書為主體圖案,我個人最喜歡的是其中兩張:一張貼在一本1931年由紐約的Modern Library出版的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亨利·亞當斯的教育》)上,票主為Geogina G.Kerr和Reg.N.,為共用藏書票,設計者在底部緞帶右側的隱蔽處留下了花押PR.。主體圖案為一個靠著大樹的男子正在專注地讀書,背景圖案為附近的建筑和遠處的山巒。另一張貼在一本1961年由美國伊利諾伊州的RICHARD D.IRWIN,INC.出版的Cases in Industrial Management(《工業管理實例》)上,票主為H.Russs Zimmerman。在圖案中,一個男子放松地坐在地上,靠著一棵枝葉繁茂的參天大樹,他光著腳丫,正在心無旁騖地讀書。
在樹下讀書,是從古至今許多讀書人的共同愛好,既可以領受自然的無私饋贈,又可以體會閱讀的快意,何樂而不為呢?“閱世長松下,讀書秋樹根。”清代詩人鄭鉽《題陳南麓都諫匡山讀書圖》有這樣的詩句:“松下軒窗坐,巖間卷帙開。”坐在窗外的松樹下,在石頭上打開書卷認真閱讀,這真有天人合一的意味。明朝的畫家吳偉有一幅絹本、設色的《樹下讀書圖》,畫面表現的是傳統的隱逸與耕讀題材,一位中年士人耕牧之余在樹下休息,展卷讀書,自得其樂。兩度出入宮廷的吳偉,通過表現遠離官場的閑適生活,曲折地表達了對當時腐敗的政治和艱險的仕途的不滿。
我頗為喜歡的作家孫犁有一篇《野味讀書》,其中有言:“解放戰爭時期,我在河間工作,每逢集日,在大街的盡頭,有一片小樹林,賣舊紙的小販,把推著的獨輪車停靠在一棵大柳樹上,坐在地上吸煙。紙堆里有些破舊書。有一次,我買到兩本《孽海花》,是原版書,只花很少錢。也坐在樹下讀起來,直到現在,還感到其味無窮。”這段文字讓我聯想到在山東大學執教的歲月,校園里有一片著名的小樹林,里面擺著一些石凳和石桌,當時教授都沒有獨立的辦公室,我經常坐在石凳上,和學生一起討論問題,不止一次和學生爭到面紅耳赤。盡管雨天時挨過淋,冷天時受過凍,也曾中過“天屎”的“頭彩”,但今日回想起來,卻依然覺得美好。
在樹下讀書,并非只有日常的詩意,同樣可以體驗蕩氣回腸的激情。海明威在散文《非洲的青山》第二部《記憶中的追獵》中寫道:“悶熱的天氣中,我躺在涼風陣陣的樹蔭下讀著書,不用為寫作而費神,想到我們四點鐘時就要進行新一輪的獵殺,心里就十分高興。”遺憾的是,像海明威這樣在戰場邊緣和非洲的深山老林里讀書的境界,于我而言難以企及,只能是內心里一種遙遠的向往。
二
在藏書票的方寸世界里,除了與書有關的方方面面,也關注凡間乃至神話里的愛恨歌哭。在我收藏的藏書票中,有一張的主題為皮拉姆斯和提斯柏(Pyramus and Thisbe)。書票的作者為保加利亞年輕的藏書票大師Hristo Kerin,他生于1966年,獲得過2004年阿根廷國際藏書票競賽特獎、意大利Bodio Lomnago國際藏書票競賽特獎等眾多獎項。這張書票為銅版蝕刻作品,還使用了版畫中的飛塵技法,作品印制在壓制有作者特殊印記的紙上,有作者親筆簽名,為編號限量版(71/75),畫芯尺寸為12x9cm。
希臘神話中收入了皮拉姆斯和提斯柏的故事,但其最初源頭是一則古巴比倫的神話傳說。皮拉姆斯是古巴比倫最英俊的美男子,提斯柏是最美艷的少女,他們是鄰居。不幸的是,由于兩家家長不斷發生沖突,因而禁止這兩位心心相印的戀人相見。在萬般無奈之中,他們只能緊靠著隔墻,通過傾聽戀人的聲音來排遣相思之苦。愛神阿佛洛狄忒被他們的深情所打動,于是暗中相助,使得兩家之間的隔墻裂開了一條小縫。這對戀人借助小小的縫隙,可以低聲細語,相互傾訴。到了夜晚降臨,他們就只好把深情一吻,留在冰冷的墻壁上。后來,兩人約定到城外林子里一株白色的桑樹下見面,這兒臨近亞述王尼諾的陵墓。先到約會地點的提斯柏沒有看到皮拉姆斯,在尋找皮拉姆斯的過程中,驚動了草叢中的一頭巨獅。當被驚擾的獅子張著血盆大口撲過來時,提斯柏只好丟掉面紗,在驚慌失措中逃走。當皮拉姆斯趕到時,沒有看到戀人的身影,只見地上到處都是獅子的腳印,還有一條被撕碎的紗巾,紗巾上沾滿了獅子捕食的獵物殘留下來的血跡。皮拉姆斯誤以為提斯柏已經葬身獅腹,悲痛欲絕,便拔出防身的匕首,在桑樹下自殺而亡。當提斯柏再次回到約會地點時,看到愛人已死,不愿獨活,也自殺殉情。他們的鮮血流到了白桑樹下,白色的桑葚也隨之變成了紫紅色。后來在西方的多種語言中,將Pyramus和Thisbe都用作“為愛而死的人、殉情者”的同義詞。
在Hristo Kerin制作的藏書票中,作者選取了提斯柏決定追隨皮拉姆斯的瞬間,她緊靠著已經氣絕的戀人,表情堅定而絕望,目光空洞,將手中的匕首指向自己的身體;背景中有月光里的桑樹葉子,還有獅子的圖案。經過飛塵技法的處理,整幅畫面層次鮮明,黑、白、灰的過渡自然,充滿了視覺沖擊力。
在世界文學傳統中,皮拉姆斯和提斯柏的傳說激活了眾多文學大師的想象力。古羅馬詩人奧維德在其代表作《變形記》中完整地記述了這個故事。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中有一場戲中戲,上演的正是皮拉姆斯和提斯柏的殉情故事。1562年,阿瑟·布魯克發表《羅密歐與朱麗葉之悲劇故事》;1594年,莎士比亞創作了《羅密歐與朱麗葉》。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故事原型,也可追溯到皮拉姆斯和提斯柏的傳說。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大詩人塔索也據此創作了著名詩篇《阿敏塔》(Aminta),但丁的《神曲》也多處提到這個傳說,皮拉姆斯和提斯柏的傳說在歐洲敘事文學中影響深遠。在某種意義上,這個傳說如同一把鑰匙,開啟了一扇扇門扉,吸引了一批批作家和藝術家,編織形形色色的“殉情的羅曼史”。
三
我自小是一個書癡,讀小學時父親給我的為數不多的零花錢,我都自作主張用來買書。讀初中時開始寄宿,家里面給我的伙食費,有不少也被我從牙縫里摳出來,還是用來買書。上大學以后,更是變本加厲,買書的數量在同班同學中遙遙領先。我本科主修經濟學,卻不務正業,對文學情有獨鐘。那時買的全是新書,因為對舊書毫無興趣,一是覺得舊書太丑太臟,蓬頭垢面,齜牙咧嘴,氣味難聞;二是喜歡追逐時興的信息,對過時的學問不感興趣。在杭州街頭一些古舊書店和學校圖書館的書架上,偶爾也會翻閱一些舊書,漸漸留意到藏書票這種東西。記得在學校圖書館的一些舊書上,透過標注借還日期的白紙條,能夠影影綽綽地看到底下的藏書票。當時覺得好奇,有幾回忍不住撕開那白紙條,但看到的藏書票已經面目全非,只是隱隱看到“之江文理學院”的字樣。去過幾回杭州古舊書店,記得在書的封二上看到過很多民國時期的藏書票,每本書的標價一般是幾毛錢,最貴的也不會超過五元。遺憾的是,我當時對藏書票的態度僅僅是看看而已。當然,荷包空虛還是個大問題,那時學校食堂的一份大排加青菜只要四毛五分錢。
博士畢業以后,到山東大學執教,閑暇喜歡逛書店。在中山公園的舊書市場和英雄山文化市場,陸陸續續淘到一些有趣的舊書,其中有一些老文化人的藏書和一些帶著民國藏書票的館藏書。隨后幾年,趁著去北京開會的間隙,在琉璃廠舊書市場買過一些舊書,有一小部分民國圖書和外文舊書也黏貼著藏書票。總體而言,北京舊書店的老板大都比較懂行,帶藏書票的舊書都賣得很貴,難得有撿漏的機會。
2009年秋天,我到哈佛大學從事一年的訪問研究。在哈佛各式各樣的圖書館里,我看到的每本書幾乎都有藏書票。這一段時間,我真正開始對藏書票產生濃厚興趣。大致而言,哈佛大學的藏書票有三種功能:一是標明藏書的場館。始建于1638年的哈佛大學圖書館有九十多個分館,每個分館都有專用的系列藏書票。二是標明圖書或購書基金的捐贈者的姓名。哈佛大學的辦學基金大都來自捐贈,校友的捐贈更是其中的基石,大量的圖書也依靠實物形式或基金形式的捐助。通過藏書票的形式,哈佛大學圖書館在延續一種感恩的傳統。凡是來自校友的捐贈,藏書票上都會注明校友的年級。三是紀念為哈佛做出過卓越貢獻的教授,最為常見的是紀念在1869年至1909年之間擔任校長的查爾斯·威廉·艾略特的藏書票。雖然是一張張薄紙,但這些藏書票讓哈佛讀者明白了每本書的來源,而且在方寸之間涵育一種獨特的校園文化。
哈佛圖書館員工做事的細致,真是讓人感動。譬如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有詞學大師龍榆生(名沐勛)捐贈的《朱疆村先生手書詞稿》,書內除了貼有燕京圖書館的通用藏書票外,還貼了兩張紙條。一張白紙上標著:“FROM PROF.M.S.LUNG”;另一張裁剪成梯形的牛皮紙上寫得更詳細,除了用英文手寫捐贈者的姓名、身份(中國上海暨南大學教授)、捐贈時間(1935年3月2日)外,還專門用中文手寫“龍沐勛教授”。更讓我吃驚的是一本《客家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的書,這是一本作者贈書。由于我是客家人,而且一直關注客家研究,才會從書庫里調出這本書。從借閱記錄來看,我是第一個借閱者。作者舒龍是一個客家文史研究者,我在贛州參加世界客屬懇親大會時見過他。令人意外的是,燕京圖書館居然專門為這本書制作了一張藏書票,略微有點傾斜地貼在封二,上面打印著“Gift of Shu Long”(舒龍的禮物)。在中國的舊書市場看多了被棄若敝屣的作者贈書后,哈佛圖書館對作者贈書的珍惜,真是讓我肅然起敬。
在哈佛訪學的那段時間,除了掃描或拍攝哈佛一些有特色的藏書票外,我開始留意美國舊書店里的圖書,居然淘到了幾十種帶著藏書票的舊書。版畫藏書票起源于德國,目前可考的最早的“刺猬銜花”藏書票,其制作年代約為1450年。早期的藏書票主要在皇家、貴族、教會圈子里流通。從十九世紀開始,律師、醫生、建筑師等高收入階層加入藏書票收藏者的行列。到了十九世紀后期,隨著普通人群涉足藏書票收藏領域,藏書票才逐漸成為一種具有極高文化內涵的流行藝術。而藏書票傳入中國,已經是二十世紀初期,魯迅倡導的版畫運動助推了藏書票的發展。
說實話,我個人對于純粹為了收藏的藏書票并不是太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貼在舊書上的藏書票,尤其是民國大學的藏書票和讀書人專用的藏書票。當然,作為一種微型版畫的藏書票,自身就有獨特的藝術價值。尤其是藏書票中的一些經典之作,其美感和文化價值都有超越時空的魅力。就我個人趣味而言,如果說藏書票有畫龍點睛的妙處,那么,離開了整條飛舞的蒼龍,孤零零的眼珠也就失去了靈透的光芒。那些貼在舊書上的藏書票,猶如黑夜里的一束束燈光,陪伴著我們回到歲月深處;猶如一座座路標,引領我們去追尋一所大學、一個知識分子、一本書所走過的獨特旅程;猶如塵垢里的珍珠,散發出一種無法為時光所掩埋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