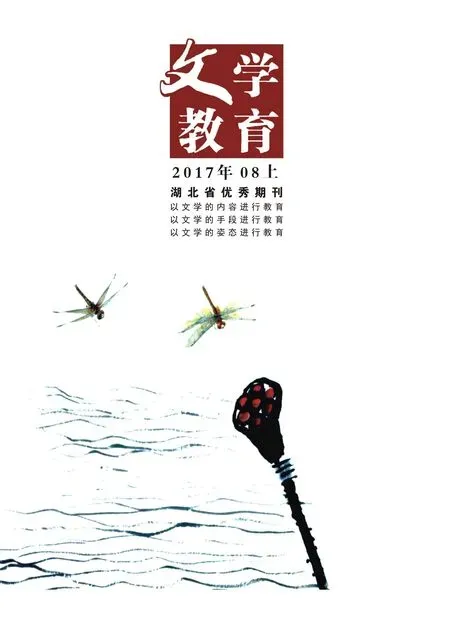《對純真的愛》中的戰爭創傷書寫
涂媛媛
《對純真的愛》中的戰爭創傷書寫
涂媛媛
小說《對純真的愛》是德國作家威廉·格納齊諾一部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作為戰后成長起來的一代,格納齊諾沒有急于追問父輩應對二戰所承擔的罪責,而是將他們作為戰爭的受害者,描寫戰爭如何摧毀了他們的信念﹑理想和希望,導致他們在戰后因這種心理創傷而無法正常生活。小說不僅書寫了戰爭親歷者的直接創傷,還書寫了戰爭對戰后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所造成的間接創傷。作品中所描繪的雙重創傷既是對戰爭的控訴,又是對戰爭的反思。
戰爭 受害者 直接創傷 間接創傷
“創傷”既是個病理學術語,也是個心理學和精神分析學術語。站在精神分析的角度,弗洛伊德指出:“創傷”是由于某個事件來得太過突然或極端,以致于人的內心無法適應和接受,從而導致心靈所受到的一種永久性的擾亂。[1]217
二戰給多數歐洲人,尤其是德國人,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心靈創傷。納粹歷史在德國人的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對這段時期的體驗或討論成為了德國的集體意識。對于那些親歷過二戰的德國人來說,納粹歷史成為了他們生平的一部分。由于那段時期的生活經歷與納粹歷史的相互關聯,他們被冠上了“納粹追隨者”的稱謂。[2]79與前一代人對自己在二戰期間的經歷保持沉默或極力回避的態度相比,戰后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則經歷了從六十年代的“討伐父輩”,急于想與“父輩決裂”以劃清自己與納粹的界限,到逐漸意識到父輩其實也是戰爭犧牲品的心理歷程。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一些作家開始在文學作品中書寫戰爭給普通百姓帶來的創傷。作為戰后成長起來的一代,1943年出生的威廉·格納齊諾沒有在作品中追問父輩應為戰爭所承擔的罪責,而是將他們作為戰爭的受害者,著力書寫戰爭給他們所造成的心理創傷,以及這種創傷對下一代人,即戰后成長起來的一代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格納齊諾的戰爭創傷敘事較為集中地表現在其1990年發表的小說《對純真的愛》。小說刻畫了心理異常的一家人:自我封閉的父母和總想逃離的孩子。文中沒有明確的時間背景,但偶爾出現的“戰爭時期”﹑“二戰前”等字眼卻為解讀格納齊諾在文本中的戰爭創傷書寫提供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線索。小說描繪了“我”的父母在戰后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揭示了戰爭給他們留下的創傷:失去信念;無法適應現實的狀態;與家庭和周圍環境的不和諧。并揭示了父輩們的這種創傷心理給“我”的童年及成年所帶來的間接創傷。
一.游離現實的父親
“家”理應是個溫暖的港灣,是人們情感生活中一個寧靜的角落。然而“家”對于小說《對純真的愛中》的主人公來說是個“缺失”。這種缺失源于父母受創傷的心理。戰爭的殘酷摧毀了主人公的父母曾經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沉痛的絕望感﹑恐懼感和被愚弄感使他們失去了對身邊一切的信任。對現實的厭惡和恐懼﹑內心的失望情緒和幻滅感使他們不愿面對現實生活,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自我封閉。
父親是個失業的機械工人,靠著一些外來的裝配訂單賺錢養家糊口。他花了大部分時間執著于自己的機器發明。這是種什么樣的機器,連他的妻子和孩子們都一無所知。由于父親的收入不夠用,每當月末來臨時,全家便會籠罩在沉默和壓抑之中。然而家庭的這種經濟窘況并非是由于當時社會經濟的衰退,而是緣于父親無法適應現實,不切實際地沉浸于自己的創造發明的游離狀態。當周圍的人都在忙于開蔬菜水果店﹑彩票站﹑土豆批發店賺錢的時候,父親卻不愿參與到這普遍的經濟繁榮中去。周圍的鄰居們漸漸變得富裕,他們買了成套家具﹑汽車和電視,開始夏天出去度假。這一切卻遭到父親了的蔑視。小說中,父親無法適應現實的生活狀態給家庭帶來的困境與當時社會經濟的繁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父親的這種游離現實的狀態緣起于戰爭對其心靈和生活的摧殘,緣起于他理想的幻滅和對未來的迷惘。當無法面對自己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時,父親選擇了逃避,寧愿活在自己的工作世界里。沉浸于工作中成為了父親自我封閉的方式。他完全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抱著一種孩童般天真無邪的幻想,期待著自己在工作中取得成就。兩幅父親珍藏的照片是他幻想世界的縮影。這兩張照片是父親年輕時利用外出工作時在攝影工作室所拍攝的。照片上的父親衣著講究,看起來完全像個功成名就的紳士。父親用照片給自己編織了一個美麗的夢,將這種假象當作是生活中某個值得紀念的瞬間保留下來。他將照片上虛假的完美視為未來生活的預兆,無法分辨“成功”和“扮演的成功”之間的區別。[3]81
父親固執地堅守著自己其實早已失敗的生活規劃,甚至在自己靠發明機器致富的夢想破滅后,還將失敗歸罪于自己的妻子,并最終將自己那黑暗或半明半暗的地下室當成了一個自我幽禁的場所。
二.陷入絕望的母親
當父親不敢面對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而將自己封閉在天真的夢想世界中時,母親卻因看到了她那夢想與現實之間的反差而陷入了深深的絕望之中。母親也曾對幸福生活充滿了憧憬。晚上時,母親喜歡把一個雞蛋握在手里。每當她心情好時,就會把一個檸檬扔在半空,然后像抓只小球一樣抓住它。母親的這些舉止行為表達了她內心對圓滿和充實懷有一種烏托邦式的向往。[4]79然而戰爭使她對現實生活中所有事物感到失望。人們可以將這種失望稱為是貫穿于整個人生的恐懼感,每日不斷更新,因而說不出具體的原因。
母親對現實生活的失望和恐懼使她不敢再展望未來,從此只能在自閉中茍活。母親將自己夢想的破滅完全歸咎于自己的丈夫,將丈夫視為自己生活失敗的根源。然而軟弱的她不敢違背丈夫的任何意愿,只能在內心將自己的婚姻看作是一個失策。關上百葉窗后陰暗的臥室成為了母親“自我關押”的場所。[3]14在主人公的回憶中,母親總是獨自帶著自己的問題躺在臥室里。偶爾她出來上廁所時,“我”總想趕緊看她一眼,但是她也急急忙忙,不讓自己被人看見。一家人居住在一套小房子里,但是“我”卻經常見不到母親。當全家人都聚集在一起吃晚飯時,才短暫地有了“家庭生活的影子”,那時“我”才“終于有機會看見母親”。[3]15
母親因對現實失望而躲進臥室,將自己關押在一個陰暗幽閉的場所,或偶爾沉浸在一個自我幻想的美好世界里;而父親則是不想面對現實而躲進了自己天真規劃的工作世界中。他們似乎相信,回歸到某種純真狀態,個人和社會的問題就會不復存在了,這也正是這部小說名字“對純真的愛”所表達的涵義。
由于心理創傷,對現實采取回避和退卻的態度是父母人生悲劇的起因。自我封閉使父母完全陷入了內心的孤寂,由此所引發的兩人之間溝通和交流的缺失同樣也是造成他們婚姻悲劇的原因。當母親將自己關閉在臥室里時,父親白天在偏遠的地方工作,晚上則坐在電視機前,直到節目結束。而作為父母,他們絲毫不關心自己的孩子。對于孩子“我”為逃避家中的沉悶而做出的一系列叛逆行為,他們雖不理解,但也不阻止。他們不強迫也不期待“我”做什么,對“我”不聞不問,甚至都不和“我”說話。小說栩栩如生地刻畫了一對由于遭受戰爭創傷,在孤獨中徘徊,在絕望中失落,將自己與家庭和外部世界隔離的“畸形的父母”。他們的孤獨和自我封閉也造成了整個家庭人際關系的毀滅。
三.孩童時渴望逃離的“我”
小說不僅書寫了戰爭親歷者所遭受的直接創傷,還描寫了“我”——戰后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因戰爭所遭受的間接創傷。作為孩童的“我”,在這個飽受創傷的家庭里感受到的只有寒冷和孤獨。這里不僅是物質生活的地獄,也是感情生活的沙漠。“我”覺得自己以及自己的父母從未有過生活在一個家中的感覺,因為每踏入住處,里面充滿的不是家庭的溫暖和親情,而是“死一般的寂靜”。[3]14在“我”看來,家的概念只淪為居住的場所,而非是親情﹑感情和血緣的維系。
“我”內心渴望改變當前境況的心愿如此強烈,以致于“我”想背叛自己的家庭。“我”希望有另外的父母﹑另外的兄弟姐妹﹑另外的房間﹑另外的往事。然而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被更換掉,因而“我”企圖將自己變成另外的人。在孩童玩伴——兩個美國孩子的家中,“我”感受到小伙伴們過著富裕的生活,有著開明的父母是多么幸福和自由。于是“我”也想要做個美國人。“我”在申辦的兒童讀者證上為自己取了一個美國名字,把這個讀者證看作是自己另一種生活的證明。“我”感到非常幸福,甚至一度相信,自己已經向成為美國人邁進了一小步。然而這種渴望轉變的心態和行為只是遭到了家人的“嘲笑”。他們都認為“我”瘋了,卻沒有一個人關心“我”之所以這么做的原因。失去親情的“家”淪為了束縛自由﹑壓抑人性的牢籠。“離開”成為了“我”內心最深切的渴望。離開意味著擺脫家庭所帶來的孤獨感和束縛感,擺脫當前生活所造成的壓抑感。[5]7“4我”喜歡去火車站看著遠去的火車,心里明白自己的這種喜好并不是因為像當時的年輕人一樣希望做個火車司機。“我”只是喜歡那些慢慢變小的鐵軌和慢慢在天空中彌散開來的青煙,渴望像它們一樣遠離和消失。
“我”擺脫現實束縛的渴望與父母的自我封閉形成了對立。“我”與父母的生活方式漸行漸遠。與母親總呆在陰暗的臥室﹑父親喜歡陰暗的地下室形成對比,明亮通風的樓梯間成為了“我”的另一片天地。當“我”實在無法忍受家里的寂靜時,便打開房門往樓梯間偷聽。雖然樓梯間也像家一樣寂靜,但“我”還是會站在打開的門邊上,因為“我”喜歡那透過門縫刮進的一絲涼風吹拂著臉的感覺。樓梯間成為了“我”通往自由﹑進入外面世界的過道。此處的涼風是一種“誘惑力”,吸引著“我”逃離家庭,也為成年后“我”的漫游埋下了伏筆。在街上閑逛,在漫游中觀察和反省是成年的“我”消除對現實的恐慌和擺脫內心孤獨的方式。
“我”不僅渴望逃離家庭,還渴望打破家中死一般的寂靜,向往著一種富有朝氣和生命力的生活。“我”常常期望能夠放飛一只握在手中的小鳥。這里的“小鳥”是溫暖和生命力的象征,“放飛小鳥”象征則著主人公內心向往自由的渴望。然而這種渴望始終只是個烏托邦,因為“我”常常仰望天空,甚至偶爾會張開右手,然而卻從未有小鳥飛來過。
四.成年后無法擺脫陰影的“我”
在“我”的回憶里,與父母﹑兄弟姐妹相處時感到的只有孤獨和冷漠。家庭成員之間始終缺少應有的相互關愛和相互理解。孩童時不幸的家庭生活不僅給童年的“我”造成了傷害,還給成年后的“我”留下了始終無法愈合的心靈創傷。忘記孩童時家庭生活所帶來的傷害,是開始正常家庭生活的前提。[6]50然而,不幸的童年所造成的陰影總在“我”的心頭揮之不去。當前的心境與情緒總能將“我”帶入對童年生活和已逝父母的回憶中。在小說中,“我”對當前生活的反思總是與對過去的回憶交織在一起。“回憶將過去和現在直接聯系在一起,往事以一種意義融合的方式被植入到了現在。”[4]80一方面,人類在童年階段所造成的創傷性記憶會或隱或顯地影響著日后生活的體驗。成年是童年的延續,童年記憶會被主體反復書寫或言說。小說中不斷呈現的童年回憶正是在書寫著童年陰影對“我”當前生活造成的影響。另一方面,這些回憶也在表明父母的人生觀已在潛移默化中深深影響了“我”的人生觀,甚至決定了“我”對世界的情感態度。父母對待外部世界時的內心矛盾實則已成為“我”永久潛在的內心矛盾的一部分。[4]86在小說中,讀者可以發現,逝去父母的形象依舊在“我”對身上繼續存活——“似乎我活著,就是為了繼承父親的孤獨和母親的驚慌失措。”[3]8
小說中,童年經歷雖已成為過去,貌似慢慢消逝,但其實仍深藏在“我”的意識深處,會時常隨著周圍景物帶來的各種感知,伴隨著記憶的回旋而涌現出來,重新帶給“我”傷痛。正如小說中“我”對法國當代女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的評價:杜拉斯自以為成功地擺脫了自己的母親,卻沒有意識到“為這種擺脫所要付出的代價便是,她一生都得書寫自己瘋狂母親的故事。她所獲得的自由,將會因這種內心的強迫而失去一半”。[3]103父母所帶來的這種始終揮之不去﹑無法擺脫的陰影尤其表現在:“我”對待婚姻生活充滿了恐懼和不信任感。“我”也曾幻想自己以后能擁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能夠看著妻子在家中找東西或打掃房間,看著孩子滿地爬,擺弄玩具的樣子。然而此時,父母熟悉的身影總會擠進到所虛構的畫面前,使“我”明白:為什么在真實的家庭背后只能有一個虛構的家庭。不幸的家庭生活加劇了“我”當下的孤獨狀態。
此外,在童年生活的影響下,成年后的“我”在面對社會現實時,常常有著與之父母相類似的心態。書寫父母實際上就是在書寫自己。如果說,成年后的“我”對自己生存世界的探尋是一種橫向的視角,那么對父母生活狀況的回憶和反思則是對這種視向的一個縱向補充。[7]22向往自由幸福的生活,然而在感到無力實現時,又想在殘酷的現實面前退縮和躲避始終是“我”矛盾的心理。
五.結語
與一般的二戰創傷小說不同,《對純真的愛》書寫的不是德軍對猶太人﹑或是入侵者對被侵略者所造成的創傷,而是將普通百姓作為戰爭的受害者,書寫他們因信念﹑理想和希望被戰爭摧毀后所造成的無法愈合的心理創傷。小說通過顛倒時空順序的自由聯想和回憶,既描寫了“我”的父輩——戰爭親歷者的心理創傷,又描寫了戰爭對“我”——戰后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的間接傷害。作品中所描繪的雙重創傷既是對戰爭的控訴,又是對戰爭的反思。
[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M].高覺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217
[2]Michael Kohlstruck: Zwischen Erinnerungen und Geschichte.Der Nationalismus und die jungen Deutschen. Berlin:Metropol Verlag,1997:79.
[3]Wilhelm Genazino.Die Liebe zur Einfalt[M].Reinbek bei Hamburg:Rotwohlt Verlag GmbH,1990.
[4]Jonas Fansa. Unterweg im Monolog.Poetologische Konzeptionen in der Prosa Wilhelm Genazinos [M]. Würzburg:Verlag K4nigshausen&Neumann GmbH,2008.
[5]Anja Hirsch.Zwischen Lust und Angst.Erzhlen im Zeichen des Verschwindens [C].//Heinz Ludwig Arnold (Hrsg.): Text und Kritik. München: Richard Boorberg Verlag,2004:74.
[6]Susanne Mittag.Im INSTITUT FR MNEMOSYNE oder Grundkurs in der Kunst des Erinnerns.Aspekte der Erinnerung in den Romanen Wilhelm Genazinos[C]. //Winfried Giesen (Hrsg.):Wilhelm Genazino.Begleitheft zur Ausstellung 11.Januar–25.Februar 2006.Frankfurt:Druckerei Imbescheidt,2006:50.
[7]Claudia Stockinger.Das Leben ein(Angestellten-)Roman[C].//Heinz Ludwig Arnold(Hrsg.):Text und Kritik. München:Richard Boorberg Verlag,2004: 22.
(作者介紹:涂媛媛,華東理工大學外語學院德語系講師,博士,研究方向:德語語言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