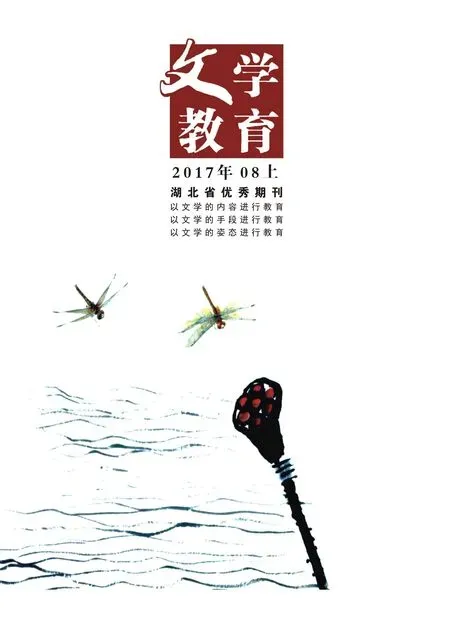程頤被貶涪陵原因初探
冉桂芬
程頤被貶涪陵原因初探
冉桂芬
程頤被貶涪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長期以來,人們往往夸大程頤和蘇軾之間的矛盾,把程頤被貶涪陵的關鍵原因歸咎到蘇軾身上,這顯然是不對的。在筆者看來,程頤被貶涪陵是因為多方因素、一步步層積疊加的結果。其中,失勢于高太后是被貶涪陵的起點,不受宋哲宗待見是根源,與蘇軾爭寵失利是催化劑,被其學生和族侄出賣陷害是直接原因。
程頤 被貶涪陵 原因
程頤,1033~1107,字正叔,人稱伊川先生,北宋洛陽人,為程顥(程顥,1032~1085,字伯淳,人稱明道先生,宋代理學家、教育家)之胞弟,北宋理學家、教育家。世稱程顥、程頤兄弟“二程”。在仕途上,程顥曾官京兆府都縣及江寧府上元縣主簿、澤州晉城令,神宗初,任御史;程頤歷官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除秘書省校書郎,授崇政殿說書。
1097年(紹圣四年)二月,已經在洛陽講學十年的程頤被視為“元祐黨人”,“以黨論放歸田里”,并詔毀其出身以來文字。同年十一月被遣送涪州編管,即送交涪陵地方官管制。本文擬就程頤被貶涪陵原因進行一番梳理。
程頤被貶涪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長期以來,人們往往夸大程頤和蘇軾之間的矛盾,把程頤被貶涪陵的關鍵原因歸咎到蘇軾身上,這顯然是不對的。在筆者看來,程頤被貶涪陵是因為多方因素、一步步層積疊加的結果。
一.程頤之得勢
程頤在政治上的得勢,是因為他在政治上主張保守,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北宋后,確立了“重文輕武”、“守內虛外”、強化皇權、不抑兼并等基本國策,很快就導致了冗官冗費、積貧積弱、邊事不治、土地集中、貧富懸殊等嚴重的社會危機。為扭轉局面,1069年,宋神宗即位后,啟用王安石,施行了大刀闊斧的變法措施,從而引發了“變法與不變法”以及“如何變法”的大討論。由于未能將那場大討論有效控制在有序范圍內,加上“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慣性思維,使得北宋歷史開始進入起伏跌宕的“黨爭”時期。從某種程度上講,程頤是北宋黨爭的犧牲品之一。
1086年,宋神宗死后,年僅十歲的小皇帝哲宗繼位,定年號元祐,由他的祖母(神宗之母)高太后垂簾聽政。高太后原本就不同意兒子——宋神宗的所作所為,聽政后,立即啟用舊黨,排斥新黨,廢除王安石新法。這時程顥已死,程頤經王巖叟和新任宰相司馬光等人薦舉,被高太后以宋哲宗的名義加以重用,于元祐元年二月“丙午,以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為校書郎,用王巖叟薦也”;三月辛巳,“以校書郎程頤為崇政殿說書,從司馬光言也”;五月“戊辰,詔孫覺、顧臨、程頤同國子監長貳修立太學條制”;八月癸卯,“以崇政殿說書程頤兼權判登聞鼓院”。至此,程頤以“布衣”之身,達到了他仕途的頂峰。他所擔任的“崇政殿說書”崗位,主要工作就是為皇帝講讀經書。崇政殿說書雖然官階不高,但可以接近龍顏,程頤驟然間成了能夠影響天子的顯赫人物。程頤很重視這一職位,他在經筵宣講理學,自覺地擔當起從理論上否定王學的任務,成為舊黨中十分重要的政治人物。
二.程頤被貶涪陵原因
1.失勢于高太后是程頤被貶涪陵的起點。
程頤之得充崇政殿說書,得益于王巖叟、司馬光等高太后信賴之人的舉薦,但程頤意欲在朝中復遵古禮,較為古板,對高太后獨專朝政、不守禮制多有微詞。據《資治通鑒》載,有一次,“頤赴講,上瘡疹不坐已累日,退詣宰相問曰:‘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圣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為寒心。’”程頤與宰相司馬光的這段對話,既對高太后在宋哲宗生病后“獨坐”朝堂表示了抗議,又對身為宰相的司馬光對皇帝已經“累日”“不御殿”漠不關心、默認高太后“獨坐”朝廷理政行為的指斥,實際上已經把自己的伯樂司馬光和實際最高當權者高太后都得罪了。以至于“翼日,呂公著等以頤言奏,遂詣問疾,上不悅,故黜之。丁亥,孔文仲、左正言丁騭進對,太皇太后宣諭曰:‘一心為國,勿為朋比。’”可見,高太后對程頤很是不悅。
元祐元年(1086年)9月,劉摯上書指責程頤同國子監長制定的“太學條制”“高闊以慕古,新奇以變常,非徒無補而又有害”,“乞罷修學制所,止責學官正、錄以上,將見行條制去留修定”。程頤雖然“亦自辨理”,“然朝廷訖不行”。12月,程頤的學生朱光庭上書指責蘇軾所撰“學士院試館職策題”是在貶低宋仁宗和宋神宗。高太后看到朱光庭的上書后,“詔軾特放罪”,好在“軾聞而自辨,詔追回放罪指揮”,并引得呂陶也上書為蘇軾辯護。元祐二年春正月壬戌,“王覿言:‘硃光庭訐蘇軾策問,呂陶力辨。臣謂軾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耳。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此大患也。’太皇太后深然之。時議者以光庭因軾與其師程頤有隙而發,而陶與軾皆蜀人,遂起洛、蜀二黨之說”。
“自蘇軾以策題事為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與程頤善”。此后,“軾、頤既交惡,其黨迭相攻”。在這種情況下,當右司諫賈易“獨建言,請并逐二人。又言呂陶黨助軾兄弟,而文彥博實主之。語侵彥博及范純仁”的時候,“太皇太后欲峻責易”。可見,高太后對程頤已經極度不滿了。加上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又說:“頤人品纖污,天資險巧,元無鄉曲之行,常在公卿之門。臣居京師近二年,頤未嘗過門。臣比除臺諫官,頤即來訪,先談賈易之賢,又曰:‘呂陶補司諫,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曰:‘何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今陶設為司諫,明叔辭去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陛下以清明安靜為治于上,而頤乃鼓騰利口,間亂群臣,使之相爭斗于下。伏望論正頤罪,放還田里,以示典刑。”
元祐二年八月,“程頤罷經筵,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退出了宋朝的政治核心圈。
2.不受宋哲宗待見是程頤被貶涪陵的根源。
程頤對自己的學問很自負。他一生研究古禮,在擔任崇政殿說書后,一心想效仿王安石變法,從皇帝開始來一場自上而下的復遵古禮運動。他曾向高太后和宋哲宗上過三道劄子,核心是要求朝廷上下、尤其是皇帝遵從古禮,以期“歲月積久”“養成圣德”。其中,他在第二道劄子中“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應宮人、內臣,并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樸;及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在第三道劄子中更是要求在他講課的時候坐著講而要皇帝站著聽,他說:“竊見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于禮為悖。乞今后特令坐講,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臣以為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為重!”
史載,“頤每以師道自居,其侍講,色甚莊,言多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有之。’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憑欄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帝不悅。”
宋哲宗曾斥責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程頤執拗如此,甚至都讓賞識他的司馬光也出言批判其過分,認為“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為此等人也。”(《寓簡》)如此一來,程頤和其它的官員也合不來,甚至令有些人厭惡了。所以,朱熹《伊川年譜》說程頤在經筵“拘禮自守,不少假借,議論褒貶,無所顧忌。由是服其學歸其門者甚盛,而不合者亦眾,遂有洛、蜀、朔三黨之號”。所以,宋哲宗在程頤離開朝廷政治中心后,始終未再真正啟用過程頤。
3.與蘇軾爭寵失利是程頤被貶涪陵的催化劑。
程頤和蘇軾皆屬于司馬光舊黨序列,他們都反對王安石變法,又都在司馬光任宰相,廢除王安石新法時,得到高太后、司馬光的重用。1086年(元祐元年)三月辛未,以“起居舍人蘇軾為中書舍人”;九月丁卯,“以中書舍人蘇軾為翰林學士”。這樣,蘇軾和程頤幾乎同時成為當時皇帝宋哲宗的老師,進入了皇帝近臣之列。
程頤方正嚴謹,動遵禮法;東坡則曠達瀟灑,不受拘束。“程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每加玩侮。方司馬光之卒也,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光,頤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坐客有難之者曰:‘孔子言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蘇軾曰:‘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眾皆大笑,遂成嫌隙。”在司馬光去世之前,蘇軾與司馬光、蘇軾與程頤之間雖有不同見解,但都還能和諧共處,相安無事。但司馬光死后,他們之間的分歧便立即公開化。群龍無首的舊黨保守派一分為三,其中司馬光最親近的部分官員、尤其是山西籍官員組成朔黨,以程頤為首的官員組成洛黨,以蘇軾為代表的一群官員則成為蜀黨。
在筆者看來,程頤和蘇軾之間分歧的本質在于爭寵,在于他們兩人都想爭奪在朝堂上的話語權,爭奪對皇帝的控制權。
如前所述,在洛、蜀黨爭中,出局的是程頤,得寵的是蘇軾。在古板偏執的程頤和豁達豪放的蘇軾之間,無論是掌控朝政的高太后,還是年幼的宋哲宗,都選擇了蘇軾。但程頤被謫貶出朝后,程門弟子始終咬住蘇軾不松口,一有機會就參奏他,“當軸者恨之,趙挺之、王覿攻之尤甚。軾知不見容,請外”。于是有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己卯,“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罷為龍圖閣學士、知杭州”。
高太后死后,宋哲宗親政,再次啟用王安石維新派人士(啟用新黨)打擊舊黨,蘇軾和程頤都是被打擊的對象。紹圣四年(1097年)十一月,程頤被遣送涪州編管的時候,蘇軾已于紹圣四年(1097年)閏二月被流放儋耳(海南島),并于七月抵達儋耳,不可能是導致程頤被貶涪陵的主力因素。但這里必須指出,與蘇軾結怨是程頤的學說在當時未能得到更大范圍傳播的重要原因。
元祐五年(1090)程頤之父程珦捐館于西京國子監公舍,程頤丁憂在家。元祐七年(1092)程頤服喪期滿,三省建言宜授館職,當年3月,“以程頤為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眾,而蘇軾在翰林,士亦多附之者。二人互相非毀,頤竟罷去。至是頤服闋,三省言宜除館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皇太后從其言,故頤不復召”。蘇轍的一句話,使程頤失去了一次復出的機會。當年4月,范祖禹指出“程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與相知二十馀年,然后舉之。頤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迂疏則固有之,人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圣明”,并建議啟用蘇軾等人后,5月,“丙戌,詔程頤許辭免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差,管句崇福宮。初,頤表請歸田里,言:‘道大則難容,節孤者易躓。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高毀甚,史冊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眾口!’又曰:‘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恥以茍祿位,孟子所謂是為壟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及崇福命下,頤即承領敕牒,但稱疾不拜。假滿百日,亟尋醫,訖不就職”,直至被貶涪陵。
4.被其學生和族侄出賣陷害是直接原因。
程頤被貶涪陵的直接原因是其族子公孫和學生邢恕落井下石。據《續資治通鑒》卷85記載,1097年(紹圣四年)“初,章惇、蔡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者。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又責呂大防、劉摯、梁燾、范祖禹、劉安世等過嶺,意猶未慊,仍用黃履疏、高士英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宋元學案》卷三《劉李諸儒學案》引《伊洛淵源錄》說:“謝良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伊川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原注: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為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伊川曰:‘然。邢七亦有書到頤,云屢于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為言官,卻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后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于此也。’”朱熹(朱文公)撰《伊川先生年譜》也說,“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紹圣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足見,程頤本人對其族子程公孫和弟子邢恕在其被貶涪州之事中所發揮的作用,也是心知肚明的。
注:本文所引資料皆出自《宋史》和《資治通鑒》。
(作者單位:重慶市涪陵第五中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