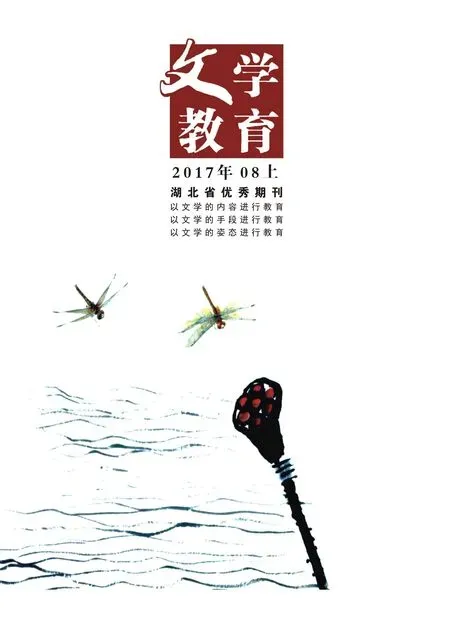以《因為女人》為例淺談當代女性的精神困惑
原雨
以《因為女人》為例淺談當代女性的精神困惑
原雨
本文通過分析閻真《因為女人》中女主人公柳依依一生的愛情經歷,揭示其命運悲劇的深層原因,探求當代女性精神困惑的原因及出路。
《因為女人》 女性 精神困惑
閻真是當代作家中寫困境的高手。繼他的《曾在天涯》、《滄浪之水》的描寫男性知識分子的困境之后,《因為女人》這部作品,又鮮明的表現出在當代自由與欲望社會背景下,女性在物質與情感生存方面所面臨的嚴峻困境。在這部小說中,閻真表面上描寫了一個堅信愛情至上的純情女大學生柳依依,歷經各種情感磨練,十幾年間揮霍青春,淪為他人情婦,最終成為怨婦的情感故事。實際上小說以男性視角直面當代女性在男權社會下用青春和身體換取金錢的生存現實,深刻地指出了當代女性的精神困惑。
小說開篇便寫道“生理事實在最大程度上決定了女性的文化和心理狀態,而不是相反”,因此在小說中,作者塑造的女性形象柳依依柔軟脆弱,在一次次的被男人傷害后,仍選擇在男人的懷抱下生活。身體和愛情的價值對于柳依依這樣的女性而言凌駕于生活的一切之上,是她們身為女性生存的第一理由。起初當薛經理拿金錢誘惑她的時候,她果斷拒絕了,因為在她心里還保有著崇高的理想主義愛情,所以當她遇見研究生夏偉凱時,她認定這就是愛情,是她一輩子的依靠,她義無反顧的付出了自己的所有。然而這兩個人對待愛情的態度完全不同,這也正反映兩性之間對于愛情和婚姻的不同。柳依依幻想純潔浪漫、天長地久的愛情,而夏偉凱則是以性為目的的。波伏娃曾說:“對男人來說女人所表現在他們眼中的只是一個性感動物,她就是‘性’,其他什么都沒有。”[1]事實上,不僅夏偉凱如此,此后柳依依接觸的每一個男人都是這樣。這正是當代女性被性對象化的悲哀所在。就當柳依依沉迷于甜蜜的愛情時,卻發現夏偉凱有關系未斷的前女友,有偶遇的籃球寶貝,這樣的“花花公子”顯然打碎了柳依依對愛情的信仰。,對于一個女人來講,愛情和婚姻,其實就是人生歸宿和精神皈依的終極問題,柳依依的悲劇命運正根源于此。
浪漫熱烈的“愛情”在物質和欲望的時代一下子就會顯露出它的虛幻與蒼白,女性到底要追求的心目中理想主義愛情,還是愛情背后的永久的經濟依靠,是很值得拷問的。這樣的精神困惑當然也是柳依依所面臨的。當柳依依崇尚的愛情信仰被摧毀后,她曾試圖解構神圣的愛情,試圖想要反抗令她失望悲傷的生活,但是她沒有像張潔《方舟》里荊華、梁倩、柳泉一樣自立自強成為女強人,她還是選擇依靠男人。因此她的種種努力,最后都會歸于失敗。柳依依對郭博士的逃離,對賈先生的拒絕,與阿裴的一夜情,真實地反映了她想反抗又無力反抗,在男權社會之下迷茫不知所措的心態。但是當一個真正強大的男人來到她的生活中時,她還是無法拒絕。秦一星要求柳依依做他的情人時,她曾痛苦地掙扎過,因為這既不是她的愛情準則,也不是世俗的道德所不允許的。但是最終她接受了秦一星,因為她既需要男人又需要金錢。情感的孤獨和無止境的欲望追求本是人性的共同弱點,在《因為女人》中,在閻真男性作家的筆下,在女性對于欲望貪婪的這種淋漓盡致的冷靜描述中,令人強烈而真實地感受到部分女性的精神沉淪已經到達了觸目驚心的地步。當代社會中,無數已經發生和還在發生著的這樣的女性悲劇告訴我們:如果一個女人把愛情作為唯一的追求和依托,把自己生活的全部希望都依附在一個男人哪怕是真心相愛的男人身上,而主動放棄尋求和爭取自身獨立的政治與經濟地位,那就勢必沒有好的結局。柳依依的結局注定是淪陷,是悲劇。
當先天的年輕美貌被時光侵蝕,年老色衰的柳依依就只能又一次陷入到情感的迷茫之中,最終她還是離不開的還是婚姻。婚姻的美滿是以感情為基礎的,她將就的嫁給了一直追求自己的農村小伙宋旭升——既沒有夏偉凱的陽光帥氣也沒有秦一星成熟闊氣。所以結婚不是柳依依的情感出路,婚后的柳依依對宋旭升就是愛不起來,宋旭升顯然也感受到了這一點。在他時來運轉,他也選擇背叛家庭,背叛柳依依。柳依依從做別人的情人,到自己丈夫找情人的怨婦,已經將青春和愛情消耗殆盡。她對無味的人生茫然了,她失去了生活的目標。她最后感嘆,在這樣的生活中她無路可走,這個世界沒有信仰的容身之所。親情和愛情是作者為柳依依找到的出路,可是沒有獨立精神的柳依依又怎會走出男人的怪圈?
閻真曾說“柳依依的命運不是一個灰色和殘酷的極端,她只是我所理解的平均數。”[2]當代社會中,的確有不少自立自強的女性,但也有不少女性正如柳依依一樣為了金錢,為了欲望,不惜犧牲自己的精神和靈魂,拋棄自己的信仰取悅男性。然而女性如此卑微的為男性改變真的可以解決精神困惑,獲得幸福嗎?要想改變女性的精神困惑關鍵是女性本身的變化,女性本身要有自由獨立的靈魂,形成自我獨特的魅力。還要有更高的生活智慧。其次也要改變社會文化,男性與女性要共同觀照,共同對整個社會文化進行反思。要用強有力的道德懲戒來約束男權社會的不良風氣,致力于構建男女和諧的兩性文化。
[1](法)波娃著;桑竹影,南姍譯.[M]第二性:女人.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 1986.12.
[2]余中華,閻真.“我表現的是我所理解的生活的平均數”—閻真訪談錄.[J].小說評論,2008(4).
(作者介紹:原雨,西北民族大學文學院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