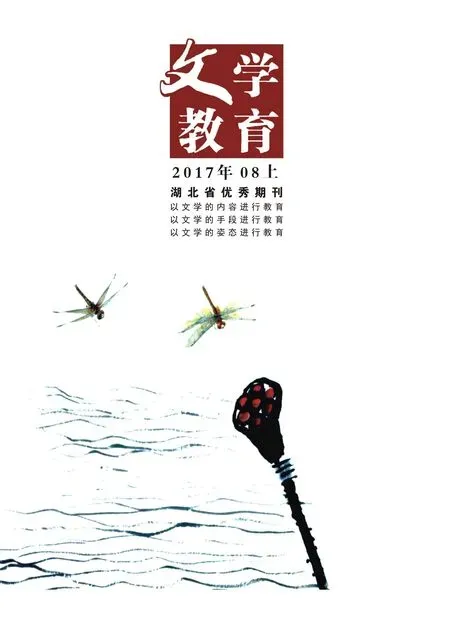新媒體時代下網(wǎng)絡文學影視改編熱潮芻議
宋夏
新媒體時代下網(wǎng)絡文學影視改編熱潮芻議
宋夏
隨著人類生產(chǎn)方式的變革、生活方式的更新,文學隨之漸漸走向多元化,在大眾媒體蓬勃發(fā)展的今天出現(xiàn)了圖像化的趨勢。網(wǎng)絡文學作為依托新媒體發(fā)展的大眾文學的一部分,更與影視圖像有著密不可分的天然聯(lián)系。反觀網(wǎng)絡文學的影視改編熱潮之下,對文學的創(chuàng)作、影視的發(fā)展究竟有何利弊,這一點對于文學自身及其社會影響都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新媒體 網(wǎng)絡文學 影視改編 文學圖像化 文化消費 文學性
中國網(wǎng)絡文學的誕生源自北美華人網(wǎng)絡文學。20世紀80年代美國將網(wǎng)絡對公眾開放,90年代形成浪潮之時,在美華人留學生籌辦了《中國新聞摘要》(1989),轉發(fā)各大通訊社有關中國的消息。1991年,全球第一家中文電子周刊《華夏文摘》創(chuàng)辦發(fā)行,更是在當時的華人之間廣為流傳。[1]在短短的二十幾年間,網(wǎng)絡文學更是借助網(wǎng)絡這一強大的媒體工具得以發(fā)展,超越了原先作為載體的形式,同時使得許多網(wǎng)絡文學作品本身帶有網(wǎng)絡語言的特色,勢頭強勁。而在近幾年中,眾多網(wǎng)絡小說不斷被改編為影視作品,其中不乏有些廣受好評,甚至成為“現(xiàn)象級”的精品受到追捧。這一熱潮的出現(xiàn)有著深刻的社會根因,需要引起學界的重視和探討。
一.網(wǎng)絡文學影視改編熱潮之“象”
網(wǎng)絡文學影視改編的歷史,可追溯至1998年痞子蔡的《第一次親密接觸》在網(wǎng)絡中大受歡迎。痞子蔡在當時與并稱“網(wǎng)絡文學的三駕馬車”的李尋歡、邢育森、寧財神都是具有高學歷的作家,代表了網(wǎng)絡文學初興時期與傳統(tǒng)作家同等的修養(yǎng)與水準。這部小說在2004年被改編為電視劇,第一次以直觀圖像化形式展現(xiàn)在觀眾面前。[2]此后,又有幾部小說被改編,在各大地方衛(wèi)視上映。新世紀的初期也成為網(wǎng)絡文學影視改編的初期。
2010年之前,國產(chǎn)電視劇中有20多部也是由網(wǎng)絡小說改編而成,在改編數(shù)量上有了上升。例如軍事傳奇題材的《亮劍》(2005),抗日英雄的個人傳記,寧財神的《武林外傳》(電視劇版2005年,電影版2011年),市井搞笑,港式無厘頭的特點。六六的《雙面膠》(2007)、《王貴與安娜》(2009)、《蝸居》(2009)等。這幾部都屬于家庭倫理題材,展現(xiàn)了戀愛婚姻、婆媳關系等現(xiàn)實世界中平凡普通人的生活瑣事,受到觀眾的好評。同時,還有一些充滿爭議的作品,比如青春戀愛題材的《會有天使替我愛你》,將表現(xiàn)少女愛情幻想的這類網(wǎng)絡小說搬上電視銀幕,引發(fā)了多方面的熱議,既有社會各界關于表現(xiàn)內(nèi)容的批評,也有原小說讀者對于改編的不滿。
而從2010年開始的15年來,無疑可稱為網(wǎng)絡文學影視改編的黃金發(fā)展時期。在網(wǎng)絡小說風靡的基礎上,取材于各類小說,選材新穎獨到,改編經(jīng)驗的積累,使得不少作品獲得了觀眾及評論界的認可與稱贊。各類題材的網(wǎng)絡小說不斷地被改編為電視、電影作品,其中更有的作品達到了家喻戶曉、全民跟風模仿的地步。如2010年的《美人心計》、《佳期如夢》、《杜拉拉升職記》(電影版,電視劇版2012年)、《泡沫之夏》,電影《山楂樹之戀》,2011年的《甄嬛傳》、《步步驚心》、《傾世皇妃》、《裸婚時代》,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2012年的《小兒難養(yǎng)》,2013年的《盛夏晚晴天》,《風中奇緣》、《杉杉來了》、《何以笙簫默》(電視劇版,電影版2015年),電影《致青春》,2014年的《匆匆那年》(電影及電視劇版),2015年的包括《錦繡緣之華麗冒險》、《云中歌》、《古劍奇譚》、《盜墓筆記》、《花千骨》、《瑯琊榜》、《他來了,請閉眼》、《羋月傳》,電影《九層妖塔》、《尋龍訣》、《左耳》、《第三種愛情》,以及16年出品的《如果蝸牛有愛情》。其中有很多電視劇在收視率上獨占鰲頭,比如《甄嬛傳》,劇中人物對話的宮廷文雅風格甚至在網(wǎng)絡上受到追捧模仿,形成盛及一時的“甄嬛體”以及相聲笑話中獨具反轉效果的“說人話”,獨具風味。
由此觀之,網(wǎng)絡文學影視改編還有繼續(xù)升溫的可能,題材類型大體也可分為七類:家庭倫理型、青春戀愛型、宮斗宅斗型、玄幻仙俠型、懸疑驚悚型、穿越架空型、歷史架空型。這七種類型大多是普通觀眾都可接受、喜聞樂見的類型,既有貼合現(xiàn)實的,也有滿足幻想的,無論是起初作為網(wǎng)絡小說,還是之后改編為影視劇作品,都有很廣的受眾范圍。
二.網(wǎng)絡文學影視改編熱潮之“因”
縱觀網(wǎng)絡文學的改編熱,這種潮流的出現(xiàn)是有幾點原因的。
第一點是市場經(jīng)濟與受眾基礎。當今社會,在市場經(jīng)濟的大環(huán)境中,能夠被編劇導演選中改編為影視劇的網(wǎng)絡文學作品,大多是具有十分廣泛的受眾群的。現(xiàn)今的影視劇的制作,最終的目的都是取得收視率上的勝利。所以導演在選材時,首先選擇能夠吸引大多數(shù)人的注意、符合大多數(shù)人觀影需要的題材。隨著自媒體時代的到來,網(wǎng)絡在人們的生活中發(fā)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電子圖書、網(wǎng)絡小說的流行,也成為無法忽視的現(xiàn)象。那么,影視劇除了獨立創(chuàng)作劇本,或者取材于經(jīng)典文學作品的翻拍,亦或選擇傳統(tǒng)文學的書目,在文化消費的環(huán)境中則遠不如網(wǎng)絡當紅小說更具吸引力、更有商業(yè)價值。
第二點是網(wǎng)絡媒體為網(wǎng)絡文學作品數(shù)量的急劇增長提供了有力條件。網(wǎng)絡小說的流行,使得擁有高人氣的作家同樣擁有了高收入。據(jù)統(tǒng)計,僅2012年,網(wǎng)絡作家唐家三少(張威)、我吃西紅柿(朱洪志)、天蠶土豆(李虎)就分別以3300萬元、2100萬元和1800萬元的版稅收入(包括在線、無線點擊閱讀獲益,授權簡繁體紙質出版物收益,授權影視改編和游戲改編的收益)等,榮登中國網(wǎng)絡作家富豪榜前三甲。[3]知名網(wǎng)絡作家的高收入與網(wǎng)絡便捷的自媒體傳播方式,使得一些具有文學夢的人開始躍躍欲試,嘗試網(wǎng)絡文學的創(chuàng)作。在滿足自我實現(xiàn)的需要、精神層面的尊重與愛的需要,追求榮譽地位的需要的同時,滿足生理層面追求財富,“為稻粱謀”的需要。網(wǎng)絡媒體門檻低,使得許多人都有條件開始網(wǎng)絡文學的創(chuàng)作。同時,網(wǎng)絡方便快捷,雙向互傳的特點,使得網(wǎng)絡小說在創(chuàng)作的同時可以及時與讀者進行意見交流,有的作家甚至因為大多數(shù)讀者的意愿去設計某段情節(jié)或者人物的經(jīng)歷、結局,從而受到讀者的熱捧和歡迎。
第三,網(wǎng)絡文學自身的特點。網(wǎng)絡文學從其誕生之時開始就具有文化快餐的性質,在生活節(jié)奏大大加快的現(xiàn)代社會具有很大的市場需要。網(wǎng)絡小說大多情節(jié)跌宕起伏,故事性強,同時善于在人們不了解不熟知的虛空環(huán)境中創(chuàng)造一種相對理想的故事,滿足人們的幻想。創(chuàng)作是作家的白日夢,讀者就是與作家一同做夢的人,使讀者在想象空間空間中與作家一同馳騁徜徉。正是網(wǎng)絡文學與生俱來與大眾契合的這一方面,使得面向大眾的影視劇找到了可取的素材。有的影視改編作品善于對網(wǎng)絡小說“源文本”的藝術品位和審美意蘊進行提升與重構。[4]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在商業(yè)和藝術上取得雙贏的電視劇《甄嬛傳》。相對于原作小說《后宮·甄嬛傳》(流瀲紫著),它的故事情節(jié)更具統(tǒng)一性,敘事結構更完善,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對廣大受眾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網(wǎng)絡文學影視改編之“思”
網(wǎng)絡文學借助網(wǎng)絡這一媒體進行傳播,在此階段與傳統(tǒng)文學的不同之處大多還在于媒介。當被改編為影視作品時,就由文字符號轉變成了視覺圖像。但是,“圖像作為一種符號本是對現(xiàn)實存在的表征,但在當今社會,圖像完成了對真實的殖民,即圖像已經(jīng)由表征轉變?yōu)榇嬖冢F(xiàn)實卻轉變?yōu)閳D像的表征。”[5]人們追求圖像帶來的感官刺激,追求新鮮好玩的東西,喪失了反思與批判,喪失了對于事物精神內(nèi)涵的思考,這種流于淺層的觀念,使得人們不再關注真正有價值的存在,一味地娛樂,“娛樂至死”。在網(wǎng)絡文學與影視劇盛行的現(xiàn)代社會,人們錯誤地將圖像符號與現(xiàn)實世界的關系進行了倒置。圖像“顛覆了文學幾千年來構建的精英文化意識而在電子媒介時代獲得了文化消費霸權。”精英文學不再是文壇的主宰,不再是人類靈魂的主宰,精英文學走下神壇,“文學的邊緣化”成為學界擔憂的問題。正如德勒茲所說,圖像化生存的邏輯“顛覆了本體論,廢黜了基礎,取消了開端和終結。”網(wǎng)絡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中不乏精品佳作,也不乏有觀眾在觀影看劇之后重回文學作品。但這樣的回歸,無法代替?zhèn)鹘y(tǒng)文學的力量和作用。人們在關注影視劇、網(wǎng)絡小說的同時,不應該忘記“詩意地棲居”。
網(wǎng)文影視改編的熱潮在一方面體現(xiàn)了新媒體對于文學的創(chuàng)作、傳播與接受的巨大的解放作用,但從另一面來看,暗表了文學性的遮蔽,因為技術媒介的操控性和圖像性扼殺了充滿無限可能性的文學意義的自動生成。從這個角度來講,次熱潮背后的意蘊關乎文學的未來與生命。對于文學的發(fā)展前景,筆者雖未悲觀地認為“文學已死”,但是,文學的本真精神,真正具有文學內(nèi)核和價值的東西,值得我們所有人去堅守和承傳。
[1]錢建軍.第X次浪潮——華文網(wǎng)絡文學[J].華僑大學學報,1999(12)
[2]歐陽友權.網(wǎng)絡文學:挑戰(zhàn)傳統(tǒng)與更新觀念[J].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1 (2)
[3]馬季.規(guī)模持續(xù)增長,期待原創(chuàng)發(fā)力——2012年網(wǎng)絡文學綜述 [J].文藝爭鳴,2013(2)
[4]鮑遠福,王長城.語圖敘事的互動與縫合——新世紀以來中文網(wǎng)絡文學的影視改編現(xiàn)象透視 [J].魯東大學學報.2015 (7)
[5]曾慶香.圖像化生存:從跡象到擬像、從表征到存在[J].新聞傳播與研究,2012(5)
(作者介紹:宋夏,杭州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文藝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