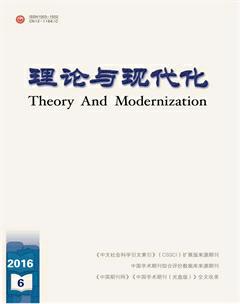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反思、溯源與問題
摘 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央為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常態、破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瓶頸性難題、引領中國巨輪在現代化事業下半程“行穩致遠”的重大戰略舉措。其政策措施和發展進程可以在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和社會有機體理論中得到說明和支撐。從現實與理論的雙重邏輯來看,供給側改革的難點在于:在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動力轉換的同時,還必須兼顧刺激經濟增長、擴大內需、保障就業、改善民生等目標;不僅要在經濟領域做文章,而且必須以此為契機協調經濟、社會、自然三大系統的關系。因此,供給側改革的實踐必須在兩端著力,確立短期和長期兩大目標,正確認識和處理改革過程中的八對核心關系。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常態;社會再生產理論;社會有機體理論
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6)06-0037-06
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首次提出將“供給側改革”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突破點,明確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這是中央為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常態、破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瓶頸性難題、引領中國巨輪在現代化事業下半程“行穩致遠”的重大戰略舉措,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此后,供給側改革成為理論界乃至全社會關注的焦點。
一、當前學界對供給側改革的研究及反思
圍繞什么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意義等問題,學界開展了熱烈的討論,形成許多共識。首先,研究者普遍認為,供給側改革重點在經濟結構調整,與需求側管理具有較大的不同。供給管理注重以中長期和高質量制度供給統領生產的創新模式,而需求管理則注重有效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運用短期和靈活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出口和消費。其次,研究者普遍認為,盡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受到西方經濟學中供給學派的影響,同英國撒切爾政府和美國里根政府時代的經濟政策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在發展環境、政策目標和實施手段等諸多方面還是存在明顯差別。比如胡鞍鋼等指出:“里根經濟學”提出時,美國的主要指標都是發達經濟體的典型標志,而當前我國仍處于城鎮化和產業轉型的加速期;“里根經濟學”的政策目標首先是抑制通貨膨脹,而我國的首要目標是解決結構性產能過剩;“里根經濟學”的政策手段突出表現為減稅和放松管制,而我國則力圖通過改善供給結構的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1]。林毅夫也指出:西方供給學派徹底否定產業政策,而我國的供給側改革的關鍵就在于穩定的宏觀政策和精準的產業政策。因而并非是對供給管理理論的簡單復制,而是著眼于中國發展實際提出的新戰略[2]。最后,對于供給側改革的意義,學界普遍認為,無論從我國改革本身的歷史邏輯還是從發展的實際要求出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都體現了黨對國情世情的科學判斷和準確把握。供給側改革既是未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頭戲”、“主戰場”,也是“攻堅區”、“深水區”,將對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起到“一錘定音”的關鍵作用。
不過,對于供給側改革的具體內涵和工作重點,不同學者有著不同的解讀。有的學者認為供給側改革的重點是通過優化供給側環境,建立高效的制度供給和開放的市場空間,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發微觀主體創新創業能力[1]。有的學者則強調加強政府監管、制定產業政策、積極運用政策性工具以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技術更新換代、區域空間協作、行業政策協同[3]。有的學者主張供給側改革的重點在于壓縮過剩產能、清理僵尸企業,消化房地產庫存,化解金融風險[4]。也有的學者認為我國經濟下滑的主因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單純壓縮產能并不能帶動經濟增長,因此主要經濟政策仍應以反周期性措施為主,特別是強化有效投資,再擇機進行供給結構調整[5]。
綜合學界的爭論,我們認為,當前,以資源、環境為代價、以基建投資、土地增值和廉價勞動力為主要發展要素的傳統模式已顯露出疲態。在新常態之下,調整發展思路、轉換發展動力已是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從經濟運行的情況來看,我國目前存在供需錯配、市場機制運行不暢、創新能力和轉換能力不足、產業結構有待完善等客觀的結構性問題,也存在資本邊際效率下降、出口不振等周期性問題;而從經濟、社會、自然三大系統的總體狀況來看,“投資產能過剩、要素供給約束、環境污染加劇、社會矛盾增加”[3]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控制。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在兩端著力,確立短期和長期兩大目標。
所謂兩端著力指的是針對經濟的結構性問題,重點推進要素端和生產端的改革。要素端改革就是要促進土地、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等全要素的科學配置,提升要素使用效率,使各要素在健全的市場機制中自由流動;生產端改革則是指破除農業、工業、現代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體制障礙,淘汰落后產能、降低稅費負擔,打破行業壟斷、激發私營經濟活力,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兩端著力的中心點是創新,以技術創新為先導,以體制創新為重點,帶動兩端的共同發展,充分發揮創新對要素配置和產業轉型的乘數效應,加快形成有利于創新發展的現代市場體制、產權制度、政府監管體系和投融資體制,推動發展方式由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創新驅動轉變。
所謂確立兩大階段目標是指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有中短期任務,也有長期戰略。從短期來看,供給側改革要重點突出“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戰術任務,優化經濟結構,扭轉周期性下滑趨勢,保持經濟基本面的良性運行;而從長期來看,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突破口,解決經濟結構不合理、貧富差距過大、環境破壞加劇等長期以來困擾我國發展的瓶頸性難題,促進經濟增長、成果共享與生態改善的正向交互作用,全面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溯源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然與我國過去側重的需求側管理不同,那么,其理論基礎是什么?學界有不同看法。有的學者認為是新制度經濟學,有的學者認為是我國的“本土流派”——新供給經濟理論[6]。我們認為,無論是著眼于要素端與生產端改革,還是以創新驅動經濟增長,無論是中短期內有效供給水平的提升,還是長期的經濟、社會、自然三大系統的綜合調整,都可以在馬克思主義中找到豐富的理論支撐。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和社會有機體理論可以為我們理解供給側改革的政策措施、發展進程和目標取向提供重要的視角和資源。
(一)社會再生產理論與供給結構改革
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是一種以供給結構為核心、探尋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動態均衡的學說。馬克思雖然沒有直接使用“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這樣的概念,然而,他在《資本論》中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分析,揭示出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平衡條件以及可能出現的矛盾。首先,馬克思認為,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從根本上說,包括價值總量的平衡和宏觀結構的平衡。這兩種平衡互為前提、互相影響,共同構成社會經濟協調運行的前提條件。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宏觀結構又包括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其中,供給結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經濟宏觀結構的樞紐,它關系到各種生產要素的投向,關系到社會產品的多少和社會總供給的形式,影響和決定著需求結構。因此,當供給結構出現內在矛盾時,將導致社會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失衡,進而引起宏觀結構與價值總量的失衡,最終使經濟發展陷入困境。其次,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價值總量和宏觀結構的失衡具體表現為兩大部類生產的失衡。馬克思將社會總產品劃分為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兩種形態,前者即第Ⅰ部類,后者為第Ⅱ部類。只有兩大部類的生產保持合理的比例、正常的交換和健康的結構,才能順利實現社會商品總和(W =C +V +M) 的各個組成部分的價值補償和物質補償,保證社會再生產平穩運行。反過來講,如果第Ⅰ部類的生產結束后不能有效提供第Ⅱ部類生產所需的生產資料,或者第Ⅱ部類的生產結束后不能有效供給第Ⅰ部類的生產所需的消費資料,擴大再生產的鏈條就會中斷。最后,馬克思認為供給和需求的平衡是通過價格的變動來實現的,因此要重視與貨幣相關的政策手段對供需平衡所起的調節作用。同時,馬克思還指出必須將國際競爭納入供需平衡的考量之中。由此出發,可以看到,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受到貨幣政策、信貸收支平衡、財政收支平衡、國際收支平衡等因素的影響,金融體系、國際市場以及政府宏觀調控在經濟運行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雖然馬克思社會再生產理論主要關注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但提供了一種從實體經濟,特別是物質資料的供給與需求、生產與消費的角度關注宏觀經濟結構平衡條件的特殊視角。由此出發,我們不僅可以取得對我國現階段存在的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的一種合理解釋,而且能夠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踐指明方向。首先,當前我國經濟存在的總量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結構失衡引起的,屬于結構性的總量失衡[7]。在供給和需求兩端突出表現為“供給不足與供給過剩并存”、“需求下降與需求外移并存”[8]。其中,供給側結構性問題尤為突出,具體表現為產能過剩、創新能力薄弱、市場機制不完善等等,其結果是造成經濟發展所需的有效供給不足。因此,按照馬克思關于總量平衡和結構平衡的原理,必須對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進行調整,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關鍵支點,增加有效供給水平,推動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重新實現動態平衡。其次,當前我國兩大部類生產中存在的失衡現象,實質上就是國民經濟各個部門比例和要素配置出現問題。一方面,我國三大產業結構需要調整,現代服務業、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和綠色環保產業等尚需做大做強。另一方面,兩大部類之間的要素配置存在結構失衡。生產資料領域面臨生產成本上升、企業稅負過重、勞動力供給不足、資本邊際率下降等問題;生產資料領域則面臨供需錯配、市場機制不暢、融資平臺欠缺等問題。因此,按照馬克思兩大部類平衡的原理,應著重從生產端和要素端進行結構調整。一方面,要從生產端發力,調整產業政策,加減乘除并舉;大力推進新興產業、壟斷行業和服務業領域改革;淘汰落后產能,加快制造強國建設;以創新驅動產業轉型升級。另一方面,要從要素端發力,推動稅制改革,有效減輕企業課稅負擔;建立健康的市場機制和創新環境;推動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完善金融體系,增強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最后,按照馬克思對貨幣調節作用和世界市場的研究,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必須充分重視貨幣政策、信貸手段和財政手段的作用,同時增強抵御國際風險的能力。一方面,要維護穩健和適度的貨幣環境,防范各類金融風險;綜合運用各種貨幣、財政和信貸政策機制和杠桿工具,盤活存量、優化增量,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另一方面,要加速掌握核心科技,樹立自主品牌,培育高端制造業,增強全球資源配置能力。
(二)社會有機體理論與三大系統協調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長期目標是實現經濟、社會、自然三大系統的協調,這不僅符合我國可持續發展的現實需要,也在馬克思的社會有機體理論中得到說明和支撐。社會有機體理論是一種以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為基礎、以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雙重關系為出發點、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目標的社會發展理論。馬克思認為,社會有機體是由多種要素構成的相互聯系、 相互依存的有機統一整體;它具有一定結構,按照一定次序建立起來,并且處于不斷運動和進化的過程之中;它的發展既是自然歷史過程,也是人類有意識參與的結果。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所說的“社會”指的是由人類的實踐活動所結成的整體系統,相較于現代社會學語境中的“社會”,屬于廣義的概念。它實際上包括了現代社會學意義上的三大系統:以物質生產為核心的經濟系統、以公共關系和公共服務為核心的社會系統(狹義的)和自然系統(與人直接相關的)。這三大系統在馬克思那里表達為兩種互相影響的關系,即人與自然界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并以物質生產活動為軸心。進一步講,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社會有機體的突出特點是整體性、層次性和運動性,并且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最終指向。整體性指的是社會的諸屬性、要素和環節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特性,共同構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層次性指的是社會作為活的機體,不是由各種要素的機械組合,而是按照一定次序建立的緊密聯系的有機整體。運動性指的是社會有機體不是僵死不變的靜態物,而是一個永遠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活的機體。其各個組成部分互相影響,牽一發而動全身。正如馬克思所說:“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機體”[9] 102。以人為本指的是社會有機體的發展目標不在于單純物質財富的積累,而在于人的全面自由發展,要不斷為這一目標創造條件。
馬克思的上述觀點如果轉換為現代社會學的語言,那就是經濟、社會(狹義)、自然三大系統具有整體性和共生性。三大系統之間既可能產生正向交互機制,也可能產生負向交互機制。其中任何一個系統出現問題,都將影響其他系統的健康運行。比如,當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無法通過合理的機制為全體民眾所共享時,不僅會導致社會系統的結構錯位和潛在風險,而且會誘發通過掠奪自然的方式來轉移矛盾,造成三大系統的全面脫節和整體惡化[10]。我們以往的發展中所暴露的問題的主要根源就在于當物質財富不斷積累時,卻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會公平和生態保護的重要性,在成果共享以促進社會成員的全面發展上做得不到位。因此,按照馬克思的社會有機體理論,要真正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以此作為我國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支點,僅僅關注經濟領域是不夠的,最終必須落腳到對經濟、社會、自然三方關系的調整,促進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漸進共享,在三大系統共生性基礎上形成經濟增長、社會福利、生態財富的耦合關系。其中,促進經濟增長是手段,積累生態財富是重要載體,提升和共享社會福利是落腳點。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央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切中當前中國改革發展的現實需要,而且是對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的繼承與發展。而我們所強調的兩端著力與兩大目標都能在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和社會有機體理論中找到科學支撐。那么,關鍵問題在于如何實現由理論向實踐的過渡,如何切實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
三、正確處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核心關系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常態以來,改革任務日趨繁重,各類矛盾問題急需解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肩負著引領中國經濟轉型的重任,必然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其難點在于在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動力轉換的同時,還必須兼顧刺激經濟增長、擴大內需、保障就業、改善民生等目標;不僅要在經濟領域做文章,而且必須以此為契機協調經濟、社會、自然三大系統的關系。要做到以上要求,就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改革過程中的八對核心關系。
第一,要兼顧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管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總的調子是,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按照馬克思社會再生產理論,供給側與需求側是經濟發展的“一體兩面”。供給側改革主要有土地、資本、勞動力、創新“四大要素”;需求側管理則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十二五”以來,我國經濟增速顯著下降,其原因主要是供給結構與市場需求脫節造成的“供給失靈”,但需求側也同樣存在問題,如投資比重過高、儲蓄率居高不下、內需不振、出口疲軟等等。有鑒于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能脫離需求側的現實情況;相反,通過提高有效供給水平,可以帶動需求側的升級。因此,必須將供給側的長期改革和需求側的短期措施結合起來,特別是利用中國城鎮化的戰略機遇,實現供需兩側的雙轉型,重點是通過創新實現供給端改革對需求端管理的引領作用,扭轉當前供需錯配的局面,推動形成“供需平衡”的理想狀態。
第二,要綜合運用結構調整措施與反周期性措施。我國經濟的此輪陣痛,既是長期以來結構性問題顯現的結果,也受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所采取的4萬億元反周期措施的影響。要解決體制機制的問題,培育高質量制度供給和創新能力,需要足夠的定力和相當的時間,而且對經濟增長可能造成短期沖擊,導致經濟下行周期的延長。相對應的,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組合,以需求管理為核心的反周期性措施具有見效時間短、效果顯著等特點,但副作用較大,有時候甚至會延誤經濟結構調整的戰略機遇期。因此,合理的做法是兩種措施結合起來,以推動體制機制結構性改革為重點,配合以穩增長、反周期的措施。特別是要持續推進重大基礎設施的長期投資,因為基礎類投資雖然從短期內看屬于需求側措施,卻對供給側有著深遠影響。通過投資來補齊短板,可以有效破除經濟發展瓶頸約束。不過,與此同時,要約束政府重復投資和低效投資等行為,降低債務風險。
第三,要打破要素驅動慣性,實現向創新驅動的轉變。以往我們的發展過于依賴“投資驅動”和“要素驅動”,在經濟、社會、生態各領域均造成了一定的消極影響。此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重點通過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多種方式,實現向創新驅動的轉變。具體措施包括:(1)營造創業、創新、創智的良好環境,提高與創新相關的教育支出密度、研發支出密度、基礎設施密度、人力資本投資密度,發揮我國資本積累與人才積累的雙重優勢[1];(2)依托“雙創”和“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等行動計劃,大力培育自主創新能力,開發新型金融支持方式,助力大眾創業、萬眾創新;(3)加快技術、產品、業態等領域的創新步伐,推動我國整體產業水平由低端向研發設計、品牌經營、營銷網絡的高端延伸,帶動有效供給能力的跨越式發展。
第四,要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放松政府管制、釋放民間活力,即通過優化制度供給,建構開放的制度環境,發揮市場機制決定性作用,最終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強微觀經濟活力,促進要素的自由流動與合理配置,提高供給體系的整體質量和效率。這就要求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完善準入與競爭機制、基礎設施、市場培育、系統整合與商業運作等五大環節,推進資源品價格改革;同時堅持簡政放權和放管結合,清理政府權力邊界,制定負面清單,減少行政審批事項,形成公平、高效、規范、透明的服務型制度體系。不過,簡政放權并不意味著放任自流,政府在供給側改革中需發揮主導作用,通過穩定的宏觀政策、精準的產業政策、靈活的微觀政策、嚴格的監管政策和托底的社會政策保障國民經濟的穩中有進,為供給側改革保駕護航、贏得時間。
第五,實現行政手段為主向市場手段為主的轉變。結構性改革需要科學合理的政策工具。我國上一輪產能過剩治理主要是通過限制投資或“關停并轉”等行政手段加以實施,在當時取得一定成效[11]。但此次產能過剩的強度更大,涉及的問題更加復雜,單純運用行政手段必然造成嚴重的副作用。因此,必須探索兼并重組、市場出清、破產清算等市場化的“有序退出”的科學路徑。同時,要運用好金融、稅收、財政三大市場化工具,加快財稅體制和分配機制改革,建立現代金融體系,加強對融資性擔保機構的監管和引導,開發“金融超市”及適應中小微企業特點的金融產品[8],積極防范金融風險。
第六,正確處理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關系。供給側改革既要放大國有資本正向功能,又要為民營經濟“松綁減負”。一方面,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發揮國企改革在供給側結構調整中的引領作用,打通國有資本進退機制,大力推進國有企業向重點行業、關鍵領域和優勢方向的集中,全面增強國有經濟市場競爭、配置資源和抵抗風險的能力。另一方面,加快推進壟斷行業改革,鼓勵民營企業進入更多領域,進一步消除制度性壁壘,激發民營經濟創新能力。
第七,兼顧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我國的供給側改革既要利用國際市場的資源與機遇,也要防范來自國際市場的各種風險。關鍵在于,通過掌握核心科技,樹立自主品牌、提升產品質量等措施,培育新的競爭優勢,實現“彎道超車”;推動出口產品結構升級,推動裝備制造等出口主導產業的更新換代,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物流鏈、價值鏈,放大供給側改革的乘數效應。尤其是要鼓勵大中型企業通過跨國并購、上市、參股、重組聯合等方式“走出去”,增強國際競爭力。
最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終目標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協調三大系統。一方面,要通過供給側改革,擯棄單純積累物質財富的傳統思路,轉而通過創新實現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消耗的脫鉤,推動生態財富累加同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另一方面,經濟增長和生態財富的增加必須最終轉換為社會普遍福利水平的提升,通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社會福利制度建設,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速相匹配、公共服務水平同經濟發展水平相匹配,使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一言以蔽之,要以供給側改革為契機,全面落實五大發展理念,促使經濟系統的良性增長、自然系統的生態盈余和社會系統的和諧共生,實現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
參考文獻:
[1]胡鞍鋼,周紹杰,任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應和引領中國經濟新常態[J].清華大學學報,2016(2).
[2]林毅夫.供給側改革的短期沖擊與問題研究[J].河南社會科學,2016(1).
[3]馮志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J].經濟問題,2016(2).
[4]劉堯飛,沈杰.經濟轉型背景下供給側改革分析[J].理論月刊,2016(4).
[5]姚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的幾個重點問題[J].河南社會科學,2016(1).
[6]許夢博,李世斌.基于馬克思社會再生產理論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分析[J].當代經濟研究,2016(4).
[7]倪國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視域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研究[J].蘭州學刊,2016(7).
[8]盛朝迅,陳蕾,王頌吉.重點領域改革節點研判:供給側與需求側[J].改革,2016(1).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蘭洋.綠色發展理念的哲學基礎與多維審視[J].學習與實踐,2016(5).
[11]盧峰.如何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J].河南社會科學,2016(1).
Abstract: The 2015 Central Economic Working Conference proposed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which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major strategic innovation that adapts to and leads China's New Normal Status. According to Marx' theory of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heory of social organism,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must keep balance between long-term economic restructuring with short-term economic growth, and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systems correctl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above requirements,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eight core relationships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
Keyword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China's New Normal Status; Marx' theory of social reproduction; Marx' theory of social organism
責任編輯:翟 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