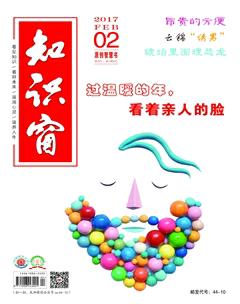橫濱的風景瑪麗
姓羅名強
敢于直面不堪回首的歷史,需要莫大的勇氣,對一個人是如此,對一個國家也是如此。貧窮苦難的瑪麗驕傲地活出了尊嚴,她用自己的方式活著。
瑪麗像是行走的雕像,時時刻刻在提醒我們還有這樣一段歷史,這不僅是日本的悲劇,而且是關于戰(zhàn)爭最大的反思。
1
那是1945年,日本戰(zhàn)敗,整個國家破敗不堪,滿目瘡痍的鋼筋骨架,遍地的血肉模糊。美軍隨即進駐,給絕望的日本人帶來了更大的恐慌。在蕭條失落的戰(zhàn)后環(huán)境中,很多人一夜之間失去了工作,包括24歲的瑪麗。
戰(zhàn)爭中,日軍在亞洲各地的暴行,顯然也成為日本人對占領軍想象的最重要參照。因此,擔憂婦女遭暴行凌辱被列為第一的國民恐慌,當局冠冕堂皇地聲明:為了維護民族的純潔性和百年后的未來,作阻擋狂瀾的防波堤,作戰(zhàn)后社會秩序的地下支柱。用一部分女性的肉體去換來絕大部分婦女的安全。于是,一則招聘涉外俱樂部女性事務員的廣告迅速面市。失業(yè)者們蜂擁而上,瑪麗也成為其中之一。
年輕的瑪麗容貌艷麗,會彈鋼琴,寫得一手好字,還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沒人知道她的真名,也沒人知道她來自哪里,但是她會很禮貌地打招呼。那時候,大家都叫她 “皇后陛下”,在當時的風塵花町名噪一時。
夜幕降臨,華燈初上的時候,被喚為“皇后陛下”的瑪麗便昂著胸膛,穿著復古的裙裝,打扮得像貴族小姐一樣,自信且優(yōu)雅地走在街上,用最溫柔的聲音和路人道一聲:“晚上好!”
于生活之苦難者,或自怨自艾,悲嘆人生;或精神自瀆,成瘋成魔。但瑪麗不一樣,在她身上,活出了尊嚴。就是這樣,如夏花一般燦爛,哪怕卑微到塵埃里。
如同那最不起眼的菖蒲,無人眷顧,也有自己的春天,這個貴如皇后的女子,也迎來了自己的愛情——瑪麗和一位美國軍官熱戀了。
是的,瑪麗相信愛情,無關身份,兩顆心的碰撞,跟身份有什么關系呢?陪他吃晚餐,一起聽海風的聲音。他送給她一枚翡翠戒指,作為定情信物。或許,她終于可以擺脫這些苦難了。
2
命運再一次與瑪麗開了個玩笑。
1951年,美國軍隊被召回,相戀的美國軍官要離開日本,回到自己的國家。不過,美國軍官說過,他會回來找她。
那天,瑪麗去送行,穿著純白蕾絲裙,戴著純白蕾絲手套,給自己清秀的臉上粉刷上純白,那是愛情的純潔。郵輪起航,瑪麗跟著郵輪奔跑。郵輪已經(jīng)走遠,瑪麗開始站在那里唱歌,那個場景那么的悲傷。
瑪麗之所以這樣打扮,是想在潮漲潮落、人來人往中,愛人能在人群中一眼認出她……
3
從此,瑪麗站在橫濱,一朵等愛的玫瑰,站成了城市的風景。
于是,白色的裙子、白色的妝面、白色的頭發(fā),蒼白的,是過往春天褪色的顏色。瑪麗將自己浸泡在舊時光的液體中,不肯離場。
瑪麗的身份如同莫大的恥辱,讓周邊的人避之不及或嗤之以鼻。但她不慍不怒,微笑著前行。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是在等著心里的那個他。
一天,一月,一年,十年……愛人依舊沒有歸來。看到年老色衰的瑪麗打扮得像幽靈一樣每日出現(xiàn)在街頭,很多人會害怕、會嫌棄,對她的曾經(jīng),大家雖緘默不言,但都充滿了鄙夷。
橫濱的大部分地方都將瑪麗拒之門外。比如說她常去的理發(fā)店,還沒進門,就有其他客人抱怨她的到來,并對理發(fā)店老板說:“如果她還來這里做頭發(fā)的話,我們就不來了。”老板很無奈,只好告訴瑪麗,讓她今后不要再來了。而瑪麗鞠了個躬,有些失望地說:“真的不可以了嗎?”
在得到肯定的答復后,沒有埋怨,也沒有抗議,瑪麗只是遺憾地說:“那好吧。”然后默默地離開了。
瑪麗佝僂著、拖著箱子緩慢前行的背影,孤獨的味道比妝面還濃。
等不來的愛,還有周邊一切的鄙夷,足以讓人恐懼。
4
世界并不像想象般絕望,有侮辱她的人,自然也有善待她的人。
無家可歸的瑪麗,累了就在一家旅社的大堂里休息,那里有一把屬于她的破椅子,一個商務老板送給她的,上面用中文寫著:“我愛你。”很長一段時間,她就睡在這間大廈的過道里,睡在這把椅子上,腳放在她的包上。
瑪麗時常去咖啡廳喝咖啡,但客人們對她充滿敵意,并對老板說:“請別讓她進來,我擔心哪天用到她喝過的杯子。”老板不忍心趕走可憐的瑪麗,就專門給她買了一個杯子。于是,瑪麗每次去點餐,就會禮貌地說:“請用我的杯子給我裝一杯咖啡。”
其實,瑪麗很清楚在大家心目中的自己是怎樣的存在。有一次,她常去的化妝店老板看著她孤獨的背影,想請她喝杯咖啡。而瑪麗卻說:“你是誰呀,我不認識你,快走開。”生怕讓人看到他們同行。
雖然貧窮,但是瑪麗仍然是愛體面的,從不接受施舍。她還善待自己身邊的人,給他們捎上一張明信片,或是寄一份小禮物,哪怕只是一條毛巾。
5
唾棄也罷,嬉笑也罷,忘記也罷,瑪麗以優(yōu)雅的姿勢活在這個對她而言有著重要意義的城市。1991年,70歲的瑪麗沒有等回愛人,卻遇見了元次郎,他是一名酒吧歌手。元次郎年輕的時候,他的母親和瑪麗一樣,而他卻因為覺得丟臉侮辱了母親,當母親逝世后,方才后悔莫及。當看到瑪麗時,愧疚轉化成了一個兒子對母親深沉的愛。他和瑪麗之間的感情是一種無法形容的羈絆,他們每周都會一起吃一頓飯,聊聊天、談談心。元次郎的每次演出都有一個瑪麗的專屬位置。
在這涼薄的世界,他們成了彼此最深的依靠。盡管都經(jīng)歷過苦痛,他們一樣人淡如菊,他們說話很輕,他們的神態(tài)很輕,他們的眼淚很輕,盡管瑪麗的腳步很沉,元次郎的歌聲很沉。
1995年,在一場紛紛揚揚的大雪過后,74歲的瑪麗消失了。在離開的前一晚,她給元次郎寫了一封信:如果再給我三十年,我會努力成為一個好老太太,我還有很多很多夢想……
在失蹤之后,曾經(jīng)投以異樣眼光的人們卻開始懷念她、找尋她、紀念她。才發(fā)現(xiàn),那個昔日的瑪麗女皇,已經(jīng)長在了橫濱的肌膚里,無法忘卻了。
習以為常時,存在是那樣的可有可無;習以為常時,離去是那樣的悵然若失。
2001年,元次郎探望了在故鄉(xiāng)養(yǎng)老院里的瑪麗,坐在臺下的瑪麗仔細聽著,時不時地點點頭。這時候的瑪麗,卸了妝,是一位年邁且慈祥的老太太,她用回了自己的真名,西岡雪子……
元次郎在臺上艱難地給她唱日文版的《My Way》:
“我愛過、笑過、哭過,滿足過、失落過,我毫不羞愧,因為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活著。
明天我將離開世界,與你們一一告別。這些年我過得很完整,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活著。”
2005年,就在元次郎去世的第二年,瑪麗也離開了這個無情或者多情的世界。到最后,她也沒有等到那個美國軍官。
轟轟烈烈的歷史終歸于沉寂,心靈的純凈是一種不屑于施舍金錢的傲慢,還是一種對于真情永不言悔的執(zhí)著,抑或是一種不受羈絆的自由。想起瑪麗,卻不是孤單和可憐,而是波瀾壯闊的海和天空中閃耀的星光,她面帶微笑,仿佛從未受傷過,在人世間飽受歧視和冷遇的她,把傷害輕輕推開,活在一個卑微的時代,卻是最優(yōu)雅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