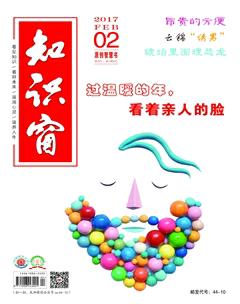夜行
李卓
衣錦夜行,聽起來是很好的詞語。
好友列表中有一個叫喬木的人,我給她一個單獨的分組,名為“行”。長久以來,我一直羨慕著她,更確切地說,是羨慕她的生活。
很早的時候,喬木就開始了她的第一次旅行,麗江、大理、廈門這些文藝小城都留有她的足跡。而今年四月,她突然發(fā)來消息說:“我在尼泊爾。”面對這五個字,我像是患了失語癥般久久沒能言語,隨后想想便也釋然了。她一直都是這樣的一個人,想到哪兒去,便省吃儉用攢一筆錢,然后一個人、一個背包,一顆不愿停歇的心,說走就走了。
在尼泊爾,異國他鄉(xiāng),她在去一個地圖上面找不到的小鎮(zhèn)時迷了路。后來,她搭乘陌生人的破舊小皮卡,在蒼涼荒蕪的異國月色中一路前行。回國后,那段經(jīng)歷被她記錄下來。我總是富有感情,設身處地去感念她的思想,去體會平淡薄涼的文字中蘊藏了多大的震撼力。
而后,我想自己去旅行,在漫長旅途中找尋一些特殊經(jīng)歷。我無限向往有些孤寂、有些安靜的環(huán)境。衣錦夜行,雙腳摩挲大地,聆聽寂靜之音,似是一個孤寂的朝圣者。
在天津,我有一段這樣的旅程。我一個人,腳踩著復古的青磚甬道,走在漸漸沉睡的城市中央。街道不太寬,星星也隱去了,只剩路燈照射路面,一段明亮,一段黑暗。
和友人去津門故里的當天,古樸的懷舊被繁華的商業(yè)所掩蓋,雖是青磚灰瓦,青石鋪路,但就是淡了感覺。和友人相視無奈,不禁失望,于是便約定待到晚上再來。
我因一點小事耽誤,忙完之后卻不見友人蹤影。住的賓館離津門路不遠,但那標志性的“天津之眼”卻沒了蹤影。我不知道這是哪兒,哪一條路可以通向賓館。
我迷路了。
但我心里一點兒也不慌張,眼前泛起夜晚的霧氣,耳邊不時地響起行人步履匆匆的腳步聲。我先沿著街道往東走一段,然后感覺不對,又返回往西走一段,心中沒有焦躁而是無比寧靜。幸而,在街道口看見幾輛出租車。
我取下背包抱在胸前,坐上了副駕駛的座位。司機三十歲左右,臉上刻畫著生活的滄桑,眼中流露出沒什么激情的眼神。
他忽然說:“你一個小孩兒,這么晚還在外面做什么?”我搪塞說去看夜景,此后無話。看著手表,已經(jīng)凌晨一點了,街道上車很少,司機開得很快,流螢般的風流包裹著我的全身。
在一個路口停了車,他說:“二十一塊八,零頭抹去,給二十就行了。從這個巷口往里走一會兒就到。”我看著他笑了笑,低聲說了謝謝。
離開的時候,我忍不住回頭看去,一輛孤獨的小車向無盡的長道駛?cè)ァN彝蝗桓杏X生活也這般沒有盡頭,所能做的便是不停地向前走。從路口一直往里走了很久,路過無數(shù)的霓虹招牌,這些五顏六色,在潮濕的夜里,起了皺。
這是凌晨一點半鐘的天津,一個與我不平行的世界。
這座城市于我是陌生的,我只是一個獨行在這里的異鄉(xiāng)人。我沒有在這坐過地鐵,沒去過文化中心、天塔、世紀鐘,所熟悉的也只是從海上吹來的裹著濕氣的風,以及天上那片沒有星星的夜空。
如今星星被藏在霓虹后面,那些閃亮的像眼睛般一眨一眨的都是昨日的星光了。
我最初來這座城市的時候是2009年,而今再次到來已是2016年。七年歲月流逝,什么痕跡也沒留下,所能做的只是勉懷。
在一個路口的轉(zhuǎn)彎處,亮著昏黃的白熾燈,一位老人坐在燈下的小扎椅上,盯著吞吐白氣的蒸籠——是賣狗不理包子的。老人看見我走來,立馬站了起來,咧了咧僵硬的嘴角,而看到我沒有停留后,又坐了回去,眼睛里有一瞬間的暗淡。
想了想,我又折回去要了一籠,雖然清楚味道不地道。
光芒隨著我離去的腳步漸行漸遠,回過頭去,老人將那盞昏黃的吊燈高高地舉過頭頂。我手中拿著溫熱的飯盒,它的溫度像一股濃濃的熱流般涌向某個不斷躁動的地方。
想起喬木,在異國小鎮(zhèn)迷路搭乘便車時,她在想著什么,是否也像我一般有種與溫暖相擁而眠的沖動。
經(jīng)年往事,她逃掉晚自習,跑到圖書館的天塔上大喊:“我想去遠方……”
她在麗江的一米陽光里駐唱和人拼酒聊天。
我永遠也無法擁有她的生活,而在此刻,我想我能理解她的心情。我想我也找尋到了。
這段路被我緩緩地走了近半個小時。
原來每個人對“遠”的定義是不相同的,計程車司機告訴我的很近,可能是用車程丈量的,而我卻先入為主地用腳步來定義他的那個“近”。
我走過天津的這條街,路過黑暗,也路過光亮。
好聽的兒化音、北方胡同、賣包子的老人,以及為我舉起的那一盞燈。
我行走在天津,這個孤寂、安靜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