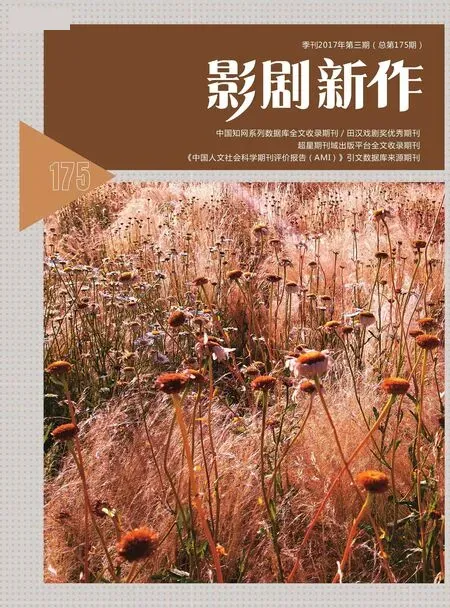一夢悠悠四百載
--評鄉音版《臨川四夢》
韓貴東
一夢悠悠四百載
--評鄉音版《臨川四夢》
韓貴東
夢中有情,情訴于夢,于《臨川四夢》而言,其作品本身的象征意義早已遠超四夢中夢境內容的表達.明萬歷十九年至二十六年的朝綱政要,悉數被湯顯祖揮灑潑墨于四夢之中,湯顯祖一生歷經嘉靖、隆慶、萬歷三個時期,將其對人生的價值與意義,時代的感慨與夢囈,借助于明傳奇的形式表達出來,既是對現實的某種意識認同,又是其對理想抱負,出世亦或是入世的某種思考."因情成夢,因夢成戲",鄉音版的《臨川四夢》正是主創人員對于湯顯祖玉茗堂四夢的再創與書寫.
一、文本的現代化
"發乎情,止乎禮義."四夢之中的情感傾訴實則要借助于唱詞的文本表達,文本的情感渲染自然要求情由"快樂原則"向"現實原則"轉變抑或是遞進.從唱詞文本的"古樸"到"現代化"過程的轉變,亦可以看出鄉音版《臨川四夢》的巧妙之處,諸如在戲中"爺們""情不知從何所起,便一往情深,可以動人還可以動鬼嘞"等戲劇唱詞文本的變異與表達,都能夠在接受美學視域中給觀眾極強的觀戲體驗,甚至于在唱詞出現的一剎那立馬入戲,并由此漸進性的關照到湯顯祖進行創作的時代風貌與特征.唱詞文本的現代化不僅僅是停留在大量現代性詞語的運用,還表現在劇中對于觀眾耳熟能詳的湯顯祖式辭藻的共鳴,例如"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四夢之一《還魂記》第十回即是此文本的出處,而"斷井頹垣"一詞也正因為此戲被觀眾所熟悉,其唱詞文本華麗但不耽溺,優雅卻也不落俗套.這本身便是對《臨川四夢》的一種二度創作,既把原有文本進行了遵照性的采用,又在不斷的改編過程中融入時代性的特質.
二、影像的表意化
《春秋公羊傳注疏》第十六卷中曾言及到"饑者歌其食, 勞者歌其事",傳統的文字、繪畫、歌謠等形式將世俗世界的五彩斑斕強有力地記錄下來,因此作為一部大型的舞臺戲劇,自然要對其舞臺的影像配合進行一定的權衡.大型現代舞臺劇在擺脫了傳統戲臺式舞臺的限制之后更加擅長通過舞臺的層次布景、燈光運用、道具等多種聲、光、電元素進行戲劇創作.因此從影像視角對鄉音版《臨川四夢》進行管窺,不難看出其突破與改制的力度.舞美設計中選擇將充滿了明朝式韻味的道具與舞臺的空間進行有機的結合,既將湯顯祖創作時的場景進行再現與還原,又把前、中、后不同現代舞臺的空間進行了適當填補,在情愫表達中自然而又流暢地完成舞臺演出.舞美的完備與現代化燈光的運用本就是相諧一致的,作為一部大型現代舞臺劇沿用了影視化的影像表意手法,將多種舞臺燈光進行處理.熾熱的紅色、憂郁的藍色、濃烈的黃色等光線實際上既能淺表化地表達內容又能夠細致性地展現人物的命運.尤其是在《南柯記》中淳于棼進入蟻國后,舞臺先是運用紅色的燈光,又在背景舞臺上選擇藍色的光線,紅色原本的喜慶與祥和在此處很自然地通過影像反差,表達了淳于棼悲劇性的人物命運.甚至于通過對基耶斯羅夫斯基《紅》《白》《藍》三部曲的對比關照,我們不難發現鄉音版《臨川四夢》的舞臺燈光充滿了表意的符號,自由、平等、博愛不也正是湯顯祖所處的時代創作土壤所缺乏的嗎!因此從影像表達的視域來看,《臨川四夢》既強化了內容表達,也兼顧了其舞臺劇創的影像形式,簡潔而又富有詩意.
三、舞臺調度的新式化
無論是中國本土化的戲劇舞臺,還是西方現代化的舞臺表演,都要注重舞臺形式上的場面調度."擺在合適的位置"于場面調度的定義而言,絕不僅僅是一句簡單直白的準則,更應該是導演爛熟于心的金科玉律.從世界三大表演體系"梅蘭芳體系""布萊希特體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來看,準確地說鄉音版的《臨川四夢》是一種借鑒式的融合.基于現代舞臺戲劇理念的要求下,《臨川四夢》注意舞臺調度充沛的同時又盡可能地做減法,力求簡單而又溫情的視聽享受.中國傳統戲曲本身作為一種表意化極強的表演形式,在場面調度的人物情感渲染中自然要先把故事講清楚,鄉音版《臨川四夢》的場面調度可以看出導演童薇薇的用心之處.作為一位足跡遍布歐亞、執導過上百場舞臺戲劇的導演,其導演風格在差異性中又能看到其共性,無論是《岳家小將》《長劍魂》《新十五貫》,還是越劇《紅樓夢》等作品,對于童薇薇而言,實則更多是在不同地域性的文化視域中尋找舞臺創作的答案,毫無疑問場面調度手法的擅長是一個舞臺戲劇導演的立足之本.鄉音版《臨川四夢》中演員的調度自然而又富有神韻,諸如淳于棼、杜麗娘的走邊串場,在交代清楚人物的行為,展現人物關系,甚至點送戲劇沖突等方面均能夠有所指代意義的再現舞臺人物的形象.甚至于在觀看《還魂記》中杜麗娘、柳夢梅情感變化的戲份時,被兩位主人公站位的距離感勾起了些許憤然的共鳴.舞臺演員的調度需要符合相應的舞臺站位支點,從前至后的舞臺層次要把握相應的調度原則,既不能使主演過于突出以致曲高和寡,也不能讓配角搶戲主次不分.
四、劇情結構的典型化
《格薩爾》人物研究者吳偉將人物分為類型化、典型化與個性化三種,實際上作為典型化的人物也要依托于典型化的情節.鄉音版的《臨川四夢》在劇情設置中取舍有度,更能夠反觀出編劇曹路生老師對于四夢的某種認識,比如戲劇《紫釵記》節選了《怨撒金錢》《醉俠閑評》《曉窗圓夢》等回目進行舞臺戲劇的演繹.抓住了典型化的情節進行創作,實際上對于受到大量舞臺時間與空間限制的戲劇而言,能夠節選典型的劇目進行創作本身是需要很強的戲劇創作功力的,曹路生老師既要照顧到折子戲的內容敘事,又要在此基礎上表現舞臺敘事的魅力,因此選擇性地對故事進行挪用是必然的.這使得對《臨川四夢》原本故事不是很清楚的觀眾也能夠在第一時間把握住故事發展的關鍵線索,從而了解四夢的故事原委.劇中不僅僅是故事抓到了典型化的章節,其結構也在敘事當中將湯顯祖作為劇中主要角色進行貫穿,敘事手法的創新使得鄉音版的觀眾能夠更加明了地體會湯顯祖進行戲劇創作的個人情感以及時代背景.四夢當中黃衫客、胡判官、契玄禪師、呂洞賓作為每一出戲的敘述者使得整部戲在劇作結構中把握住了"穿針引線"的敘事原則,線性而又有層次地進行故事講述,整部節選的戲劇中序尾與開頭一張一合的編排,使得觀戲的余韻良久.
誠然,戲劇舞臺的表現仍然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戲劇本身作為一種現場性的舞臺藝術形式,不單純是傳情達意,更要彰顯時代的風貌與特質,鄉音版《臨川四夢》在情節的節選上把控了重點,但也正是因為整齊劃一的編排與選擇,使得許多觀眾認為戲劇故事的講述未起高潮便戛然而止,大有不足以寬慰之狀.
戲劇本身的發展要能夠與時代的思想發生碰撞,因此鄉音版《臨川四夢》注重了對時代精神的吸收與接納,以戲劇創作的規律進行本土化的改編,在個體性特征尚存的基礎上實現對現代大型舞臺藝術的塑造.毋庸置疑,藝術創作的土壤既是來源于生活,更是高于生活.
韓貴東:南昌大學
責任編輯:謝菁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