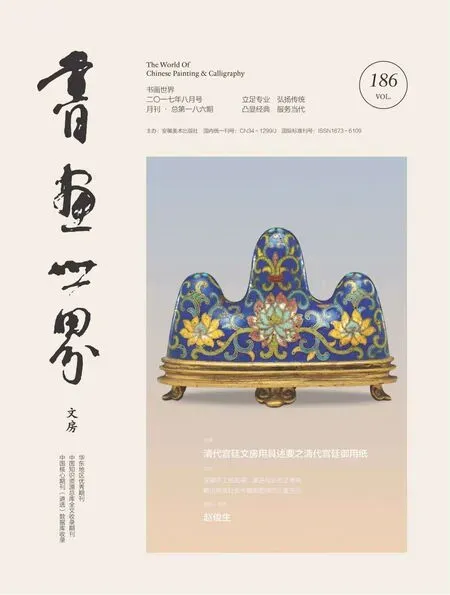白蕉書法探究
文_劉軍
廣東農工商職業技術學院
白蕉書法探究
文_劉軍
廣東農工商職業技術學院
清末民初碑派書風雖占據書壇的主流地位,白蕉卻依然堅守著帖學之道,以“二王”書法為依歸,其書風則主要體現在“古、淡、雅”三字上,保持著純粹的帖學思想。
“二王”書法;白蕉;碑派書風
白蕉是民國書家中最典型的帖學代表人物,清末民初碑派書風雖占據書壇的主流地位,白蕉與其他人不同,卻更加深入地研究了“二王”及魏晉尺牘,在系統內進行革新,追溯至魏晉書風,糾正帖學末流弊端。他靠獨立高潔的品格和高超的書法水平,在追求形式美的同時,回歸純樸,汲取魏晉書風之精髓,將魏晉文士的高妙意趣化入尋常瑣事且恰到好處,其神態直逼“二王”。白蕉取法晉人的第一條路徑是由唐人溯源晉人,這是一條捷徑。其早年學書初學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銘》,與此同時對褚遂良、陸柬之等人法書也頗為用心。師法“二王”,首要師其筆法,唐人對晉人的筆法保存可信度較高,白蕉走此捷徑,不失為一上策。除了學習唐人,白蕉涉獵廣泛,同時對五代楊凝式,宋代米芾,明代董其昌、王寵等人法書皆有鉆研,真可謂汲取百家之長。
一、白蕉書法分期
白蕉早期以歐、虞為階梯初探“二王”筆法,中期則直接師法右軍得其神韻,從其晚期成熟書風來看,為其所用者更多的是王獻之一路。他依靠著自己對“二王”書風獨到的理解及不懈的追求,取得了成功。其書學經歷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一)初成面目,師法歐虞
1940年左右,初成面目:歐陽詢的楷書從隋碑而來,虞世南是智永弟子,但歐虞楷書從用筆到結體都不無相似之處。而白蕉其他行書,則似乎虞體的成分多些。歐體中宮緊,而虞體中宮寬;歐體多相背之勢,虞體多相向之勢。虞世南楷書雖為山陰嫡傳,然而隸意明顯,似過于王羲之、智永,白蕉結字多取相向之勢,沒有采用虞世南那種平緩右伸的橫畫和捺畫。
(二)步武右軍,鳳翥龍蟠
1950年左右,風格漸變:以白蕉寫給姚鹓雛詩札為代表作品,個人風格已基本成熟,此時的書風尤得王羲之神韻,且氣息醇正。白蕉學王羲之,當然是無帖不學,而所得最多的是《得示帖》《孔侍中帖》和《喪亂帖》。白蕉曾自稱:“學《喪亂帖》四十年如一日,又據說放大王羲之雜帖張之壁間,日夕觀摩,得其神采。”王羲之用筆以裹鋒為主,線條瘦硬;折多于轉,更見鋒棱瘦骨。在這一時期白蕉的行草,筆法精到,氣息醇正,點畫圓轉潤朗,舒展大方,結體疏密有致,勻稱妥帖,外觀柔美,內現力度,潤而不肥,枯而不燥,穩險得體,險不怪誕,通篇洋溢著濃郁的書卷氣息。
(三)自由瀟散,不滯于物
1955年后,書法大成:尤以1963年書就的《蘭題雜存長卷》為代表,用筆精美,瀟灑錯落,氣息高遠。此時的書風更加自由瀟散,相比之下書貌特征更加接近于王獻之。王羲之和王獻之每個人的書風都呈現多面性,都存有“質”“研”特征的書貌,但是羲、獻兩人書法存有較大差異這也是毋庸置疑的。以一千多年以來對于“妍”一路書風的繼承來看,我們應該承認王獻之在“妍”上略勝其父一籌。王獻之創造了書法藝術新型的審美風尚,對后世影響深遠,宋代的薛紹彭書法和明代的王寵書法就是其中較為典型的例子。薛紹彭書法最大的特點是溫雅清潤,在效法魏晉的同時,更加注重其神韻的培育,尤其用心于王獻之字的形態,并取得了明顯的效果。明代的王寵書法最突出的特點是瀟散簡淡,他對于王獻之的學習似乎已經成為公論。同樣取法王獻之的駿爽、流便之感,到了王寵這里就變為典雅古淡,其實這是對王獻之精髓的時代性把握。白蕉的書法和薛紹彭、王寵是一脈相承的,可謂將王獻之一路書法再次推向巔峰。白蕉書法的發展歷程可歸為“楷書——行書——行草——草書”,這是以年齡為依據進行劃分的。與王獻之一樣,白蕉的草書作品傳世最多,也最為世人所稱道,其書無論字字獨立還是豪放暢達,都很好地繼承了王獻之書法的衣缽。以杜萌若先生解讀的王獻之行草書章法為例,將白蕉書法的形式做一比較。第一種為字際穿插:這一種形式一般出現在草書之中,打破常規的單字或者字的組合,造成一種空間沖突,給讀者在視覺上帶來強烈沖擊力。第二種是行間顧盼:這一種情況主要說明的是行與行之間的呼應關系,有時候鄰行的字可能伸展到另外一行,雖然字字互不牽扯,但是相鄰兩行的字勢出現呼應之態。
二、白蕉書法特征
白蕉書法別具一格,最突出的特征是獨得晉韻,富有獨特的美學內涵,可以用古、淡、雅三字來詮釋白蕉的獨特之處。東晉名士一般追尋瀟灑高逸的境界,生活在民國時期的白蕉亦有相同性情,他的言談舉止不拘一格,正是在有意地尋覓魏晉士人的瀟灑境界,更有赤腳參加朋友聚會等行為。他的這些舉止在當時看來實為高人風致。白蕉擁有溫文爾雅的外表,這正是典型謙謙君子之風。君子外表之下卻掩藏不住那副桀驁不馴的傲骨,今天看來也正是他狂狷脫俗的氣質,才成就其書法獨特的內涵。
(一)白蕉書法之“古”
對于其“古”的寓意,我們大致可以理解是師出古法,主要是指宗法“二王”、遵循古法。白蕉選擇帖學,但不像同時代的書家那樣選擇董、趙等人,而是直接宗法“二王”。對于遵守古法,很多書家剛接觸書法,為了起點更高一些,標榜“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的口號而選擇了“二王”。但是更重要的是下一步要能守住古法,也就是能踏踏實實地深入“二王”書法精髓之中。事實證明絕大多數書家根本沒有完成遵守古法的使命,而白蕉是一個踏實深入“二王”傳統深處的書家。他的字的每一個簡單筆畫必是下筆有由,這正是其遵守古法的結果。
(二)白蕉書法之“淡”
“淡”則主要是指白蕉書法的簡淡這一內涵,簡淡的審美內涵是一種由表及里的顯現。這一內涵需要對比才能夠更加明確。就像羲、獻父子之間的“質”“妍”之辯一樣,白蕉的簡淡可以和沈尹默的書法做一比較。沈尹默于漢魏諸碑用功極深,其一下筆就能讓人感受到漢魏時期的厚重氣象,給人一種莊嚴、沉重之感。相比之下,白蕉書法擺脫了篆隸之氣,其筆力就顯得柔弱了許多,筆力的柔弱勢必帶來柔和、雅致、溫潤之感,這就使得白蕉書法整體呈現出“淡”的特征。導致其書法出現“淡”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白蕉的字結體簡單,不像常見的行草書那樣有過多的纏繞,而是簡簡單單幾筆,甚至減少牽絲的數量,從而更進一步迎合了其書法簡淡的審美內涵。
(三)白蕉書法之“雅”
“雅”是人們對白蕉書法比較公允的評價,因為晉人之韻就包含古雅、典雅之意,白蕉獨得晉人韻,其書貌呈現“雅”態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沈尹默重視的是法度,程式化的束縛多一些,像馬公愚、鄧散木等人則更為刻意,其實他們已遠離“二王”的精神內核,毫無疑問白蕉是同時代的佼佼者。白蕉學王獻之,悟得了其風流倜儻與瀟灑自由的真諦。白蕉在章法布局方面將其“雅”展現得淋漓盡致。同樣和沈尹默的行書進行比較,沈氏的手札也顯風度翩翩,但是其程式化過于嚴重,就使得其略顯俗態。然而白蕉的字革除了多余的枷鎖,以行云流水之勢給人帶來雅的感觸。前面所提到的古、淡、雅融合在一起,就使得白蕉的書法展現了一種大美之風。白蕉的字在用筆取法上依傍古人,在結體上簡潔明了,在章法上疏密有致,如行云流水。這就使得其書法從細節到整篇給人以舒暢的感覺,這種感覺不僅僅停留在視覺上,而是由表及里深入讀者的內心。這是白蕉豐厚學養和精湛藝術技能的最佳詮釋。
綜觀白蕉的書法特點:結體瀟散灑脫,收放自如;點畫簡潔凝練,質樸清新;章法疏密有致,不落痕跡。白蕉追求內心絕對的靜止,這是一種清澈見底、溫潤如玉的天然氣質,這也正是藝術家所追求的目標。通觀白蕉的書法作品,一派天真,他在用筆上簡化了起筆和收筆的頓挫,是為儒者風范;在結構上出現隨機性的結構脫離,收放自如,全無匠氣。在白蕉的作品中看不到炫目的書法技巧,他寫的是一種寵辱不驚的氣度與心境。他專心于尺牘,把握住了“二王”書法的精髓,筆法間架可學,而氣質神韻不可學,所以白蕉高出同時代書家,也是學習“二王”最成功的范例。
三、白蕉碑帖觀
白蕉的藝術體悟極其敏銳,他的藝術觀是客觀的、辯證的。他給予碑帖的態度是:碑與帖同等重要。學書要學習碑與帖中的精華部分,初學者以碑入手為佳。對于爭論已久的碑派興盛的緣由,白蕉評價中肯,認其原因有二。《碑與帖》中這樣說道:“清代的學術考據特別發達,當時尤其是古文字學更為進步,因此從古碑、碣、鐘鼎文字中發現新義,其價值正足以彌補正史經傳某些不足之處。”考據學的發展帶動“碑學”的興起,此為其一。其二,《云間言藝錄》中有言:“學帖大弊,在務為側媚。側媚成習,所以書道式微也。我國書法衰于董趙,壞于館閣,所謂忸怩局促,無地自容。”正是因為白蕉精熟于帖,深知“帖學”弊病,所以白蕉倡言學書者初習碑刻尤佳。
在碑與帖的關系上,白蕉認為:“碑與帖,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碑沉著、端厚而重點畫,帖穩秀、清潔而重使轉。碑宏肆,帖瀟散。宏肆務去粗獷,瀟散務去側媚。書法宏肆而瀟散,乃見神采。”筆者認為白蕉怒斥包慎伯、康長素的真正目的不是批判碑刻低劣不能學,而是批判包、康扭曲阮氏重碑卻無抑帖的本意,推波助瀾引領“碑學”狂潮,致使“帖學”筆法一度缺失,為書法帶來空前的損失;同時指責康氏不分碑刻好壞,肆意宣揚己見,引學書者誤入歧途。《碑與帖》文中有此言證:“長素把造像最惡劣者,像齊碑、雋修羅、隋碑阿史那都贊為妙絕,龍門二十品中,又深貶優填王一種,都是偏僻之論。”從中可以看出白蕉對于碑帖之觀念。那么其保持如此純粹帖派的動機又是什么呢?首先,白蕉是一位真正的文人書法家,厚重樸茂的碑派書法風格與其格格不入。從白蕉的言談舉止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魏晉風度的韻律,單是其長相也散發著其溫文爾雅的氣息,更不用談及灑脫的處世原則。一個真正的文人書家最重要的是擁有高格調的書風,典雅的“二王”書風正是白蕉的不二選擇,我們很難想象白蕉粗獷碑派書風的面目。其次,很重要的一點是白蕉能夠不畏時代,堅持自己的追求。碑學時代的力量是巨大的,自康有為以來全國上下無不深受其影響,但是身處碑帖交接時代的白蕉并沒有改變自己純粹的“二王”帖學觀念。
四、結論
白蕉以自己獨特的見解學習經典“二王”帖學,并打通了帖學史,成就卓著。沙孟海《白蕉題蘭雜稿卷跋》云:“白蕉先生題蘭雜稿長卷,行草相間,寢饋山陰,深見功夫。造次顛沛,馳不失范。三百年來能為此者寥寥數人。”此乃對白蕉最好的詮釋。在近代碑學昌盛的情況下,白蕉仍然堅持自己的藝術觀點,潛心研究帖學,深入挖掘帖學的精髓,糾正董趙末流的弊端,繼承其中最優秀的傳統,并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用自己的成就推動了帖學的發展,為近現代帖學的復興做出了最具實際意義的貢獻,使人們能夠重新認識到“二王”書法和帖學的意義及價值,其意義極其深遠。
[1]康有為.廣藝舟雙楫. 姜義華 ,張榮華,編校.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2]白蕉.海上代表書法家系列作品集:白蕉[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6.
[3]白蕉.白蕉論藝[M].金丹,選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0.
[4]曹軍.白蕉書法管窺:兼評其在近現代書法史上應有的地位[D].南京:南京藝術學院,2008.
[5]張明偉.云間白蕉:三百年來一復翁[D].濟南:山東大學,2014.
約稿、責編:史春霖、徐琳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