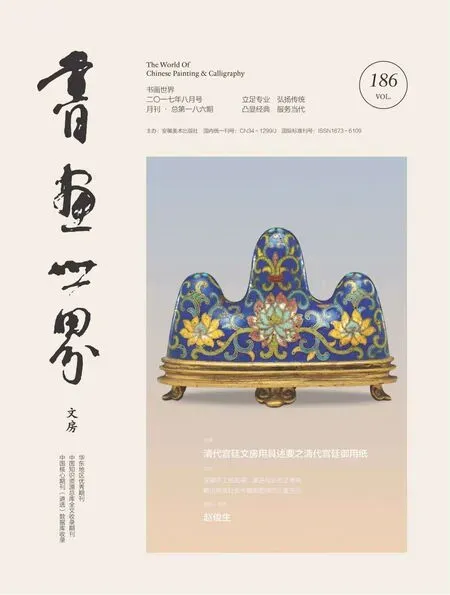黃賓虹篆書的繪畫意趣
文_商振馳
中石化濟南輸油管理處
黃賓虹篆書的繪畫意趣
文_商振馳
中石化濟南輸油管理處
黃賓虹的篆書吸收了碑版的斑駁之美、璽印的斷續之美和殘簡斷素中視覺的不確定性等因素,個人的情緒更為強烈。這些他在繪畫中最追求的理想,使他的篆書打上了深深的繪畫審美烙印。
繪畫意趣;美術化;畫在書先;內部控制
黃賓虹曾對學生石谷風說:“我的書法勝于繪畫。”作為一個對自己有著清醒認識的老人,他向來謙遜,如果不是有著十分的把握,是不會對自己做這樣的評價的。早在民國時期,很多學者對黃賓虹的篆書就給予了很高評價,盡管他的篆書知音稀少,但他那富有繪畫意趣的創作,猶如一座高峰,令人仰止。
清代早期的篆書雖然開啟了學習遠古碑刻的風氣,但由于館閣書風的影響,總體上比較拘謹,在表達主觀情緒方面顯得保守。民國時期的書法審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構,包世臣、康有為的大力提倡,鐘鼎彝文、碑版造像、敦煌遺書、殘簡斷素、磚文銘刻、璽印文字這些以前不被重視的資料得以被重新審視,大大地突破了唐代以來書法的取法傳統,使得書法較早地進入了現代視覺文化的系統,為書法的美術化、視覺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黃賓虹作為一位著名金石學家,身居風尚中心,對此有著深切的體會。他的篆書吸收了碑版的斑駁之美、璽印的斷續之美和殘簡斷素中視覺的不確定性等因素,更加易于傾注、表達個人的情緒,因而感染力更為強烈。同時上述因素也正是他在繪畫中孜孜以求的理想,不可避免地,他的篆書從源頭上就打上了深深的繪畫審美烙印。
黃賓虹在《畫語錄》中經常說:“書畫本無二,書畫同源而異體。”但是他在書法起源上的觀點卻和他上述的說法有細微的差異。他認為書法起源于原始的刻畫花紋或者是圖案形象。他在給弟子劉作籌的信中說:甲骨殷契及鐘鼎古文中,圖騰一類,有字有畫,畫在書先,為最近考古家所公認。在四川時,得“巴蜀王”大圓印,黃賓虹考證為東周時物,尤貴其文為“書畫未分之證”。作為畫家,黃賓虹如此關注、強調圖文未分時“畫在書先”的古物遺證,其實在這書與畫的源頭上,他已經找到了它們之所以相同的內核。
1929年黃賓虹發表了《虛與實》一文,在文中他說:筆法之妙,純在中鋒,順逆兼用,是為得之。此皆言用筆之實處也。至于虛處,前人謂分行間白,鄧石如有以黑當白之說,歐人稱不齊弧三角為美術,尤貴多觀書法,自能得之。這段論述暗合了西方的格式塔心理學(完形心理學)的觀點,是黃賓虹繪畫筆法的主要理論依據,同時也是黃賓虹篆書創作的理論依據。黃賓虹的篆書,尤其是晚年作品,都有意識地運用了這種方法。1951年黃賓虹創作《繁花散木》聯,其中“參”“匠”兩個字,似乎是在寫的過程中有意識地對筆法和力度進行控制,讓筆觸始終不過分接觸紙面,墨和紙之間保持著似落非落、似著非著的接觸方式,營造出一種斑駁陸離的藝術效果。
自然的美只能在自然和藝術中才能得見,但藝術中的自然美不同于自然中的自然美,是一種很難得的境界。一般層次的藝術皆是出于對自然的模仿,只有天才的藝術家才能從對自然的模仿中走出,進入藝術的高境界,黃賓虹無疑是后者。他的繪畫體現了中國藝術中難以企及的天人合一的精神。書法雖然不對自然進行直接模仿,但自然的境界也是書法藝術追求的目標。作為一位杰出的山水畫家,黃賓虹不僅十分重視書法用筆,而且也十分注重把在繪畫當中體會到的用筆感覺融入書法中去。據邱振中先生的說法,書法線條內部控制的難度要比繪畫線條大得多,它需要瞬間轉換的內容也復雜得多。黃賓虹把繪畫線條訓練的修養運用到篆書創作中,所以,他晚年的一些作品“看似毫不經意,但筆鋒一觸紙,便密實而凝重,即使是最細微的筆觸,也像是鐵畫銀鉤,不可移易。這是中國繪畫中理想的,但卻很少有人能夠達到的一種境界”(邱振中語)。如1953年黃賓虹創作的《心腸肌骨》聯,線條如屈鐵墜石,有如從紙上生出一般,不可移易,望之令人生敬。他曾舉古人文獻說明:“易曰:‘可觀莫如樹。’”這是因為,樹的姿態是自然的、變化的,樹的每一個局部都符合他的審美理想——“不齊之弧三角”。這樣的思維也同樣存在于他的篆書創作中,如1952年創作《駒影龍文》聯,“精”的米旁六點,像極了他經常運用于畫面上的泥里拔釘點,感覺就是樹石之間的點法。
作為杰出的山水畫家,黃賓虹提出了“七墨法”。在中國繪畫史上,他被譽為墨法的集大成者。他山水畫用墨的特點之一就是純熟地運用宿墨,把山水畫的墨法推向了新高度。古代書家中重視墨法的傳統由來已久,蘇軾善濃墨,董其昌喜淡墨,王鐸用漲墨,黃賓虹篆書突破了濃墨、淡墨之限,濃、淡、干、濕、焦各種因素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有力地增強了藝術的表現力。各種墨法不僅是表達作品內涵的輔助手段,而且是作品的必要組成部分。他那看似漫不經心的用墨方法,其實是長期試驗、千錘百煉的結果,當我們面對原作的時候,或許更能感受黃賓虹作品的魅力。因為有著豐富的墨韻,黃賓虹篆書才更顯示出其“干裂秋風、潤含春雨”的獨特審美境界。這種境界,不是也蘊含著很深的山水畫意蘊嗎?在其1953年的《和風平頂》聯中,這種感受是顯而易見的。
黃賓虹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天崩地裂的變革時期。他不僅是這個時代的經歷者,還是積極的參與者。他從積極參與轉變為以藝術的方式對這個時代進行觀照,在這個過程中他經歷過掙扎與彷徨,但對藝術的執著與熱愛始終沒變。在長達90年的漫長生命歷程中,他的方法之一貫、理路之清晰,世所罕見。他書法觀是在長期繪畫創作過程中不斷激蕩形成的,是交互作用的結果。在如此的背景之下,他的篆書含有很深的繪畫意蘊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了。
約稿、責編:史春霖、金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