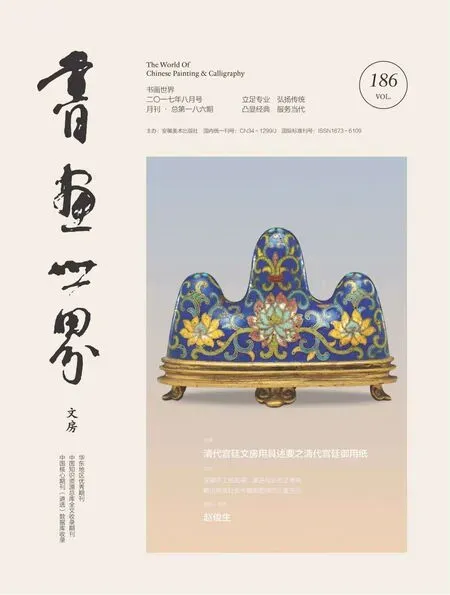由傳統看當代書法的當代性
——由陳忠康書法展說開去
文_陳凱
安徽省阜陽市潁東區書法家協會主席
由傳統看當代書法的當代性
——由陳忠康書法展說開去
文_陳凱
安徽省阜陽市潁東區書法家協會主席
傳統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一條流動的河。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看待傳統的角度是不一樣的。角度的不同,也會使傳統表現出不一樣的味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傳統在每個時代都具有“當代性”特質。在當今時代,我們也在以不同以往的角度解讀著傳統,從而使傳統在當代表現出新的高度。本文以陳忠康的書法實踐為例來闡述書法的傳統和當代性的問題,指出當代性與傳統性并不相悖,從本質上說是一致的。
書法;傳統;當代性
顯然,當代藝術的概念并不是以時間來界定的。應該說,它的概念是模糊的,手段是隨意性的。它不僅沒有一個屬于自身的固定風格類型,也不存在一個為世人共知的美學主張。它的視域是開闊的,思想是開放的,觀念是超前的,思考方式是全新的。但同時也不可否認,當代藝術的概念必不可少地包含了時間的界定性,假如以此為標準,當今的藝術創作都具有一定的當代性。這個界定性當然也包括中國傳統書法在內。
當今的中國書壇存在著一些觀念截然不同的流派,或者說,由于觀念的不同,存在著無論從理論支撐,還是從創作方法,甚至是從視覺效果、藝術感受來講都大相徑庭的書法流派。比如以胡抗美、劉洪彪、張旭光、陳忠康、陳海良、楊濤等為代表的傳統書派,以曾翔、邵巖、邱振中、李強等為代表的現代書派,以王鏞、沃興華、白砥等為代表的“丑書”派。其實,無論傳統書派、現代書派還是“丑書”派,它們的代表書家并不是僅僅存在于一個書派中的,很多書家在不同的流派中都有涉獵,且都有不俗表現。比如曾翔,他不僅傳統功底深厚,而且在現代書法創作領域和所謂的“丑書”領域都有很高的成就,并且是一個極具爭議的人物,近段時間在網絡和朋友圈流傳頗廣的“吼書”便是其藝術實踐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比如楊濤,不僅在傳統大草、隸書、篆書上有著不俗的表現,而且在所謂的“丑書”領域也是重要的代表人物。再比如白砥,他在早些年就以深厚的傳統功底活躍于書壇,而在近些年的書法實踐中因審美異于常人面目被世人目之為“丑書”。還有王鏞,推崇者目之為大師泰斗,而貶之者則視之為洪水猛獸。
避開傳統派書法不談,現代書法和“丑書”都毋庸置疑地受到西方當代藝術的影響,這個影響當然不能僅僅從中國書法的純粹傳統性中解讀,而更多的是從西方當代藝術理論中汲取營養,從而得到靈感,并從觀念上解構傳統中國書法,使中國書法的傳統性得以顛覆,最終使中國書法在結體、章法、字法、筆法等諸多方面得以拓展和豐富,中國書法的表現形式在西風東漸的過程中變得多樣而前衛。
現代書法由于基本脫離了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且摒棄了漢字作為載體的傳統書法基本規定性,從而游離于書法藝術和抽象藝術之間,很難得到中國本土文化的完全認可。而“丑書”也由于審美取向的偏狹性而很難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可(其實“丑書”同樣源于中國書法之傳統)。前段時間,一些報刊對所謂“丑書”的口誅筆伐,便是例證。
然而,作為中國傳統藝術表現形式之一的中國書法,假如不以西方當代藝術理論來解讀和指導,而是完全遵循中國書法發展的內在規律,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滋養和當今時代快速發展的影響下,以純粹的傳統書法理論解讀、指導,那么中國傳統書法是否具備當代性呢?是否符合當代藝術的規定性呢?答案是肯定的。
筆者有幸參觀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的“中國藝術研究院著名藝術家系列精品展之陳忠康精品展”,對此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
陳忠康先生以自己不斷入古出新的書法實踐,詮釋了中國傳統書法的當代轉換。他的這種轉換,不是機械照搬古人的法帖,做古人忠實的奴隸而不敢越雷池一步,也不是信筆為體、聚墨成形,置傳統經典于不顧,而是一種敬畏經典、深入古帖、充分了解傳統后的任情恣性和心性的自然流露。
陳忠康以其不懈的努力與艱苦的探索,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經驗并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闡釋體系,為當代書法帖學的深入及傳統書法創作開辟了一條獨特的道路。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著名書法理論家邱振中先生評其為 “當代書法創作中一個典型的個案”,并期望其“在中國書法史的序列里,再上幾個臺階”。這次展覽為我們展示了這種可能性。作為當代帖學的重要代表人物,陳忠康在當代書壇有著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在于其對中國書法傳統的深入挖掘,最難能可貴的是他以超乎尋常的毅力和異乎常人的稟賦,不斷地詮釋著經典,不斷地和古人對話,和古人較勁。
當然,如果說,僅僅是臨摹古人、重復古人,陳忠康便不能成為陳忠康。陳忠康的意義在于他在充分了解古人的基礎上找到了表現自己、表現時代的最佳切入點,正如他在展覽自述中所言:“我把自己定位為一個堅定而刻苦的學古派……學書三十余年,一路過來,摸爬滾打,須臾未嘗離開古帖,不同時期總在與形形色色的古人對話。面對一個個人物和他們的作品,從不喜歡到喜歡,很多時候需要調整自己的精神狀態,打破很多自我局限的框架。這個歷程,對自己既是實踐能力、認知水平的提高過程,也是不斷磨礪心性的過程。開悟需要這種漸修。所謂‘字如其人’,書法的進步與人生的修煉是互為一體的兩個側面。”也正是他這種“須臾未嘗離開古帖”的做法,才使得他在同時代眾多的書家中脫穎而出,成為真正繼承中國傳統書法衣缽的當代書家代表人物之一。
陳忠康說,中國其他藝術形式如繪畫等講求“中得心源,外師造化”,而書法則講求“中得心源,外師古人”,從古人、古代經典中探得消息,是書法區別于其他藝術形式的重要特征。
陳忠康對中國書法史和當代書法創作現狀的深刻了解,使他能精準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和奮斗的目標。他說,只有從縱向上了解了歷史和橫向上了解了當前的創作現狀,才能更好地定位自己、發展自己。
一個時代的書法高度取決于這個時代對傳統經典認識和挖掘的深度,一個人書法水平的高低同樣取決于他對傳統的認知和把握。這一點,在中國書法史上已經被無數次證明。比如歷代書法大家對書法經典的理解和研悟,雖然都不太一樣,但都達到了一定的高度,所以才能成為大家。陳忠康的書法以“二王”為根基,對“二王”筆法有著獨到的理解和精熟的把握。他經常說,“二王”經典的每一個細節都是意味無窮的。能體味到每個細節的意味無窮,不僅需要深邃的洞察力,更需要對經典的無限敬畏。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所以,他的書法才有了耐人品咂的意味。
陳忠康的書法雖然不能說代表了當今書法創作的最高成就,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傳統帖學的當代轉換。他的書法以傳統帖學為根基,在楷書、隸書、行書、草書、篆書等幾大書體上都有著不俗的表現。曾經在微信圈里看到一組其以傳統經典為范本的模仿之作,其傳統功力和驚人的模仿能力,的確令人驚詫、艷羨和神往!這種能力體現了他對經典認知和把握的能力。
著名書法評論家姜壽田在《當代中青年書法家批評》中有這樣的評價:陳忠康的帖學實踐無疑屬于學院化經典解經模式。從其創作可以看出陳忠康是一個忠實的古典主義者。對他而言,并不存在什么主義與觀念的預設,他也沒有什么雄心要為帖學注入什么自己的東西。在這方面,張羽翔有著很大的不同。張羽翔始終謀求帖學的存與立,在破中接近元典——這種努力后期走向異化。陳忠康則是老老實實地膜拜古人、膜拜經典。而事實證明,當代帖學要彌合傳統帖學的斷裂確確實實需要像陳忠康這樣對傳統深入精研的人物。“圓熟的時代歷史經常被遺忘,直到面臨危機才重新發掘。”從這個意義上講,陳忠康的“入古”是有積極意義的。
“陳忠康書法是圍繞著‘二王’展開的。他所極力謀求解決的問題是逼近和探源‘二王’筆法,因而對‘二王’筆法的細心體察研悟,便構成他書法創作的核心。在他的筆下,‘二王’筆法的絞轉、搭鋒、中側鋒轉換皆有著高難度的體現,而氣息的醇正也使其作品頗具古意。”
當然,陳忠康的書法并不是只在“二王”法帖中求得信息,除了“二王”,他還在唐宋明清諸名家中汲取營養。他的觸覺是全面的,視野是開闊的,從而使得他的書法顯得更加豐富,韻味更加悠長。
怎樣從傳統的角度看書法的當代性?傳統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它是一條流動的河,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看待傳統的角度是不一樣的。角度的不一樣,也會使傳統表現出不一樣的姿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傳統在每個時代都具有“當代性”特質。在當今時代,我們也在以不同以往的角度來解讀著傳統,從而使傳統在當代表現出全新的高度。以陳忠康為例,他的書法實踐從傳統中來,又異于傳統,是傳統之河中一條一直往前、奔騰不息的溪流。他的書法藝術是傳統的,又是現代的,同樣也不可否認地具有“當代性”。
我們在繼承著傳統,發展著傳統,同時又在創造著傳統。也就是說,今天被稱為“具有當代性”的書法實踐,在若干年后又被我們的后人稱為傳統。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從這個角度來講,當代書法也好,傳統書法也好,古典書法也罷,其實都是書法發展長河中的一個過程而已。我們也只有把當代書法做好,推向更高的高度,才能成為后人眼中的傳統,這是作為當代人的一種歷史責任和擔當。
我們不能以偏、奇、怪來定義中國書法的當代性,也不能以表面化的視覺形式來說明書法在當代的發展和高度,更不能脫離中國本土文化來談論書法。書法是中國獨有的一門藝術形式,是在傳統文化滋養中形成的,離開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滋養,書法便失去了它所具有的文化價值和藝術價值,變成無根之木、徒有虛名了。
那么,以陳忠康為代表的傳統書法派有沒有當代性呢?這就回到了本文的主旨。
書法是中國獨有的一門藝術形式,是在中國特定的文化生態中形成的。以西方藝術理論來解讀中國傳統書法的做法雖無大錯,但總歸是有隔閡的,并且這個隔閡是與生俱來的。在這樣的隔閡中看待中國書法,就如同霧里看花、水中望月,最終也不能看得真切明白。在當今知識全球化和書法國際化的大背景下,也只有保證了書法的本土化和純粹化,才能使其不失去自身存在的價值。任何一門藝術形式都有其內在的發展規律,人的主觀能動性雖不可否認,但如果違背了事物發展的規定性,注定會被歷史所遺棄。20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現的所謂現代書法,由于過于脫離書法藝術生存的土壤,過于急功近利,所以一開始便顯得先天不足,沒有多長時間便銷聲匿跡了。
書法的創新和變化,是隨著時代發展而發展的,這是一個亙古不變的規律。與傳統書齋里以展示和手頭把玩為主要欣賞方式不同的是,在以展覽為主要展示方式的當代社會,書法從章法形式和視覺效果也在發生著不同以往的變化。這是時代進步的必然結果,也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作為當代書法家,我們必須適應時代要求,并引領時代潮流。
另外,實用性的終結,也為傳統書法在當代的發展帶來契機。這些都是書法當代性的一種體現。書法藝術自漢代以來,歷代的發展都離不開實用這一主題。所以,傳統書法的發展和創新,無不是包含著實用這一目的性。雖然有時候這一目的并不十分明顯,比如在草書領域內的創新等。時至今日,隨著科技的高度發展,信息化社會已經來到,人們在享受科技帶來的便利的同時,傳統藝術門類,特別是書法,就面臨著實用性消隱的問題。在這一問題上,當代的書法家們應該說是獲得了更大的發揮和創新的空間,也為書法的當代發展找到了一個絕佳的契機。另外一點,就是隨著考古發掘的不斷推進,一些古人不可能見到的書法資料源源不斷地被發現,民間收藏的興盛,也使一些過去不能見到或不被重視的書法珍品得以重見天日。
大道至簡。說到底,其實最大的當代性,就是在深刻理解并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深刻領會書法的本質和發展規律,以精熟的傳統技法為前提,以深厚的學養為保障,融入時代特征,參合一己之意,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有一定的發展和創新,既有個人才情的發揮,又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反映時代發展變化,這才是書法真正的當代性。并且當代性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并且會被賦予不一樣的實質內容和精神內涵。
[1]胡抗美.中國書法藝術當代性論稿[M].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12.
[2]姜壽田.當代中青年書法家批評[M].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9.
[3]方愛龍.割裂傳統而強調書法的當代性值得檢討[J].美術觀察,2007(10).
[4]曾來德,陳羲明,管峻,李嘯,楊旻.書法的當代性[J].中國書畫,2008(09).
[5]王瑞蕓.西方當代藝術審美性十六講[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
[6]姜壽田.當代中青年書法家批評[M].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9.
約稿、責編:金前文、史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