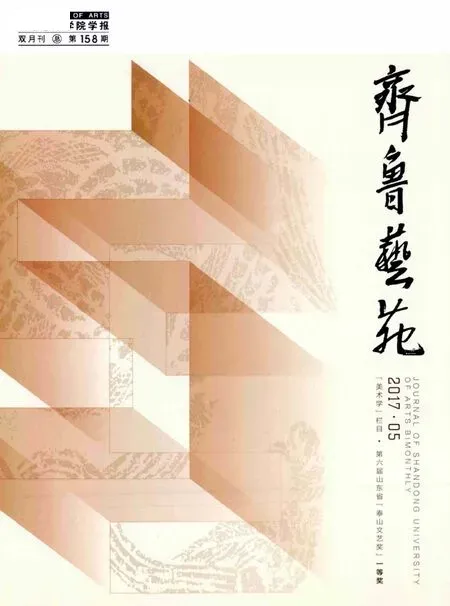儒家文化及樂舞觀對海陽秧歌的影響
潘 晶
(山東藝術學院舞蹈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山東地區是中華民族和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早在舊石器時代,這里就有古人類生息繁衍。山東亦是先秦時期齊國、魯國所在地,號稱“齊魯禮儀之邦”。齊魯文化是一種以古代齊國和魯國為代表的地域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成為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其精神作為中華民族的靈魂,至今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齊魯文化發軔于東夷文化。早在四五十萬年以前,東夷人的直系祖先沂源猿人面對群山樹海,勇敢地開始了從原始森林走向文明的艱難跋涉。“從原始社會至夏商時期,齊魯的東夷人逐漸形成了兩個文化中心。在泰山以北,以今之淄博為中心,是爽鳩氏、季荝、有逢伯陵和季蒲姑氏等活動的地域。泰山以南,以今之曲阜為中心,是少昊、蚩尤、顓頊、后羿、奄國等部落和方國的居地,同時又是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聯系緊密、便于交融的地區,因而有及其豐富的文化積淀。距今6000年左右,齊魯的原始居民進入新石器時代,他們被統稱為‘夷’或‘東夷’。”[1](P2)
隨著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分工的發展以及對夏商文化的廣泛吸收,東夷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聯系逐漸加強。西周建立后,通過分封建立了許多諸侯國,其中以齊、魯兩大諸侯國為主。齊國和魯國分別繼承了東夷文化和夏、商、周三代的先進文化,但由于兩國建國方略的差異和人文環境、地理條件的不同,此后的六七百年中,兩國各自沿著自己的軌道向前發展,逐漸形成了兩個既有共同點而又風格迥異的文化傳統——齊文化和魯文化。戰國時期,兩種文化體系開始逐漸融合,形成齊魯文化。
齊文化具有“重實效、崇功利、舉賢才、尚法治、揚兵學、倡開放的文化品格”[2](P4),其精神主旨是“因時變化,與時俱進”,其思想代表是強調“與時移物,應物變化”的黃老學派。魯文化“講究道德名節,注重研究傳統文化和闡發宗法倫理觀念”[3](P4),其精神主旨是“固守傳統,強調原則性”,其思想代表是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儒家、墨家學派。齊文化和魯文化的結合,共同締造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源頭——齊魯文化,這使得山東的古代文化既重視人文價值理想,又重視現實國計民生;既注重道德禮儀的建設,又注重行政法規的完善;既保有厚重的傳統,又能兼容并包。齊魯文化所蘊涵的“自強不息、愛國主義、厚德載物、勤勞勇敢、求真務實”的文化精神,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資源和理論基礎。
一、講禮之風范
儒家文化重視“禮”,這是種極為森嚴的儀式形式,且形式大于內容,體現在在樂舞中就是講究排場和氣勢,如西周時期的“八佾舞”。“佾”是古代舞蹈陣容的衡量單位,一佾八人,最高級別給天子享用的舞蹈是“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場面浩大,講究排場。古代的禮儀樂舞均講究祭拜的先后,如祭祀時,需先焚香叩拜,而后祭品呈上,再行叩拜,如此幾進幾出,彰顯對神靈的敬仰。因此,在儒家思想的制控下,華夏成為了禮儀之邦,一個講“禮”的國度。講,可視為講究,禮,可視為禮數,這些禮數也影響著山東秧歌的發展。
孔子作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十分重視樂舞的教育作用,強調樂舞為政治服務,還把規范人的倫理道德觀念的“禮”與樂緊密結合在一起。《論語·八佾》中記載,孔子因為大夫身份的魯國季氏僭越,擅自觀賞了只有天子才有資格欣賞的“八佾舞”而大聲抗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左傳》中記錄了周人對“禮”的認識:“經國家,定社稷,徐敏人”,其目的是:“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可見周人對“禮”體現出一種追求穩定的保守傾向,對此,孔子是極力維護的[4](P25)。孔子認為禮與樂的配合是統治百姓的有效措施,只強調規范性極強的禮,會造成不“和”,而樂可以“和民聲”,但樂也要依靠規范性極強的“禮”來節制。
山東被稱為“禮儀之邦”,將社會政治、倫理道德相結合,“敬天尊祖”也滲透到了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舞蹈。無論是上層社會還是底層百姓都自覺信奉。山東三大秧歌之一的海陽秧歌,受儒家傳統文化及樂舞思想的影響,對禮儀十分注重、講究。海陽秧歌中重要的禮儀就屬“拜進”,又稱“三進三出”,是在祭神、祭祖的“三叩九拜”的基礎上演化而來。大年初一,秧歌拜祭本家祖宗,后到各村串演,過程中要向東道村家廟、祠堂祭拜,而祭神的活動也離不開秧歌隊,也要行大禮。古時,參拜的禮數更為周全,也更為繁瑣,講究“進門一二三,出門三二一;一回三番九個禮,九回翻番八十一禮[5](P34)”。從進門到出門,過門就拜,鼓樂喧聲之中,眾目睽睽之下,秧歌隊有秩序、畢恭畢敬地表演一整套規范的動作,十分虔誠地完成對祖宗和神靈的祭拜過程。據說參拜儀式能持續兩個小時之久,其莊重、虔誠之心,熱烈程度可想而知。如今的“三進三出”比過去的“三拜九叩”在形式上簡化了不少,但其本質卻是相同的。“三進三出”是歷代秧歌隊必行的禮節,也從側面反映出齊魯人重儒尚禮的秉性。兩支秧歌隊若迎面相遇,不能繞行不能回避,而要行參拜之禮,如若這“三進三出”之禮做得不好,就等于說秧歌隊不尊重他人,不懂規矩,就會被人恥笑。正是因為極為重視禮儀,民風古樸,使得海陽秧歌在表演上套路規范、動作整齊。海陽秧歌講究禮儀,也彰顯出山東人重禮尚義的品質,所以說海陽秧歌明顯帶有儒家傳統文化及樂舞思想的印跡。
二、善美之體現
中國古代對舞蹈理論的研究始于春秋戰國時代,人們也將這一時期視為中國文化的軸心時期,而有關的樂舞思想也發軔于此。中國古代樂舞不分家,有樂必有舞,有舞必有樂,樂之為用,全在聲容兼備,有聲而無容,不能稱之為樂。先秦諸子百家中對樂舞理論有著比較深刻見解的首推儒家,而孔子作為儒家的創始人,雖然在樂舞理論方面沒有留下系統的著作,但是他總結了前人對樂舞的見解,在一些基本認識上,為儒家的樂舞思想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儒家提出的“美善統一”的思想,要求舞蹈的美必須與善相結合,唯此才能盡善盡美。孔子認為《韶樂》是盡美盡善之作,聞之“三月不知肉味”,而《大武》是歌頌武力取天下的樂舞,盡美卻未盡善。唐朝孔穎達對《禮記·樂記》做疏證時指出:“樂之善惡,初從民心而興,后及合成為樂。樂又下感于人。善樂感人,則人化之為善;惡樂感人,則隨之為惡。”[6](P26)這又將樂舞對社會生活、對人的作用闡發得明白曉暢。
依據傳統的排列方式,海陽秧歌隊中走在最前面的是“執事”,緊隨其后的是“樂隊”,“舞隊”則走在秧歌隊的最后面。這三大部分分工明確,各司其職,且配合相當默契。執事與樂隊都是為舞隊而服務的,分別負責秧歌隊的禮儀事務和奏樂、營造氛圍。舞隊作為秧歌隊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角色眾多且極具個性特色。無論是錮漏與王大娘、丑婆與傻小子帶有情節性的雙人舞,還是扇女、小嫚的集體表演,都是在樂大夫的統一指揮下,即興表演,變換隊形,無不體現著對美的一種追求。說到海陽秧歌的禮儀莊重、陣勢龐大、規范嚴謹的美,不得不提春秋時期的齊國,這里曾經誕生了被孔子評價為“盡善盡美”“聞之三月不知肉味”的《韶》樂,其氣勢恢宏,規模龐大,藝術感染力強,體現出一種恢宏壯觀之美,這對后世齊魯樂舞的發展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也體現在海陽秧歌的表演形式中。
優秀的舞蹈作品總能體現特有的民族審美習慣,倡導特定的時代審美追求。除了外在表演形式的美,海陽秧歌的美還體現著其內在的思想性。海陽秧歌的思想內容積極向上,崇尚對美好的追求,對生活的熱愛,倡導人們去追求真、善、美。古時它是祭神、祭祖的儀式,今日它成為廣大民眾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際交流的重要方式,在歷史的每個階段它都譜寫了不朽的篇章。抗日時期它是宣傳抗日、激勵斗志的重要手段,如今它已然成為海陽市的文化品牌,也成為了招商引資的一種重要途徑。
三、真情之流露
儒家樂舞思想的代表著作《樂記》中指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7](P26)作者以人心感物而動來探討樂的本質,認為樂舞是人們思想感情的表現,但并非所有的人類精神活動都是藝術。當人們的思想感情需要表達時,同時又通過特定的形式外化出來時,那才是藝術。如果只是發出自然的聲響,并不能算是“樂”,自然之“聲”禽獸亦可以發出。這樣的表述清晰明了,正印證了“內容決定形式,形式依附于內容,但形式又反作用于內容”的觀點。
孔子認為,樂舞是人們思想情感方面的表現,可以通過樂舞觀察一個國家的政治面貌和民俗風情。樂舞不僅是人們思想感情的外化形態,它對人們的情感也具有反作用,因而孔子認為樂舞是移風易俗最有效的工具,也是教化民眾的有效工具。明代的樂律學家、舞蹈家、歷算家朱載堉在繼承儒家樂舞思想的基礎上,提出“論舞學不可廢”,把舞蹈看作一門藝術,看作人文科學的研究對象,他認為:“蓋樂心內發,感物而動,不知手足自運,歡之至也。此舞之所由起也”。他站在“天人合一”的角度強調:“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此之謂也。”強調人與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和諧的關系,并以此強調舞蹈所起的中介作用和各種功能,充分肯定樂與舞各自獨立的藝術品格與相互難以取代的重要作用。
海陽秧歌中的錮漏與王大娘兩個角色,是從秧歌劇中演化而來的一對情景舞蹈演員,表演時也是成雙成對,不離不棄。他們是海陽秧歌中藝術風格最為突出的一對人物,有著優美的舞蹈動作和豐富的表現手法。二人眼神相互交流、互相挑逗,“你進我退,你攔我去,你去我追,你撲我引”[8](P108),盡情對舞,動感極強。錮漏與王大娘的傳說有多個版本,有說王大娘是玉皇大帝的小女兒,名叫旱魃,因眷戀人世不歸天庭,危害人間,后被土地神所化的錮漏匠利用情誼將其收服;也有說王大娘是千年狐仙所化,玉皇大帝命土地神化作錮漏將其收服,但土地神最終愛上了這個美麗的狐仙,與王大娘一起演繹了一場終破牢籠的愛情故事。無論是旱魃還是狐仙,無論天兵天將還是土地神,也無論錮漏與王大娘的結局如何,他們都是民間藝人將自己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傾心附之的妖、仙、人化為一體的特殊人物,是人們借以抒發情懷,給自己以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和信心,同時也體現了對封建社會制度抑制人們情感的鞭撻和痛斥。
呂文斌在《膠州秧歌的特征與形成》一文中談到膠州秧歌的審美時指出:“社會一方面要求男演員扮演的女角色要用女性動作的優美姿態滿足審美要求,另一方面社會又用儒家的觀念,要求扮演的女性角色表現出溫順賢惠、含而不露的品德。受這種社會審美心理的影響和約束,在秧歌表演中,男演員扮演女性角色也是在兩重心理下完成的,一重是他們為能借助自娛性的秧歌形式,盡力去表達自己生活中不能表達的內心情感而感到歡娛的心情,另一重又受儒教和社會審美標準的束縛,在動作上表現出既激動又沉穩的含蓄美的特征。秧歌中扭、擰、抻、韌的風格特點,就充分表現出了掙脫不了那個時代的婦女們被壓抑的內心激情,這一切可以歸納成一個‘曲’字。這個‘曲’,不只表現在女性角色代表的現實生活中的婦女們,
同樣也體現在那個時代的男人身上。這種兩重心理的藝術體現,形成了膠州秧歌女性動作既有北方婦女舒展奔放,又有內在含蓄、含而不露的風格特點,令人感到別有風情,韻味無窮。”
無論是海陽秧歌中為爭取自由的錮漏與王大娘,還是借助自娛性的秧歌形式表達內心情感的膠州秧歌,他們都是人們內心情感的一種寄托,一種表達。人們借助秧歌這一形式宣泄著內心的情感,秧歌又依托著人們的情感得以保存和傳承。
綜上所述,秧歌作為一種身體符號,代表了農耕時代民眾的思想,體現著最樸素的民眾情懷。百姓在一年當中最適宜的時候,舉行最能表達他們心愿的活動——秧歌,他們在一起歡歌笑語、載歌載舞,用這樣一種獨特的形式來犒勞辛苦了一年的自己。海陽秧歌在中國民間舞蹈尤其是秧歌類舞蹈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它歷史悠久、形式多樣、保存相對完好、普及范圍廣,與其它地區的秧歌(東北秧歌、河北秧歌、陜北秧歌等)有著鮮明的差異,風格亦有顯著不同。漲陽秧歌經歷了幾百年的發展和流變,印證了不同時期民眾的精神生活,同時也承載著多元社會文化內涵。它生長在素有“孔孟之鄉”的齊魯大地上,受傳統儒家文化思想及樂舞觀的影響,帶有鮮明的民間祭祀性質,也體現著中國傳統文化所蘊含的勤奮務實、勇于拼搏、自強不息、團結奮進的民族精神。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進步,充滿韻味的膠州秧歌、古樸粗獷的海陽秧歌以其自身獨特的魅力,越來越多的受到廣大民眾的喜愛。
[1][2][3]孟祥才,胡新生.齊魯思想文化史—從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
[4][6][7]馮雙白,茅慧.中國舞蹈史及作品鑒賞[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5][8]于蔚泉.海陽秧歌[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