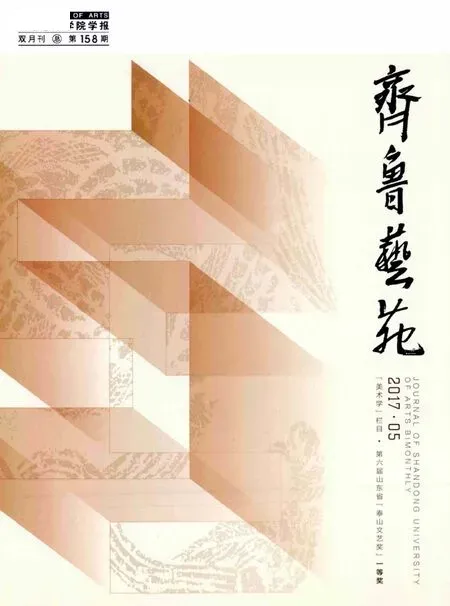商業之殤:國統區話劇“市儈主義”批判之反思
沈后慶
(廣西藝術學院影視與傳媒學院,廣西 南寧 530022)
中國話劇史往往把四十年代上海和大后方話劇的發展看作是中國現代話劇發展的黃金階段,這不僅指戲劇文本的創作獲得極大的豐富成果,更是指戲劇演出,尤其是商業演出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當然也隱含了與之相伴的戲劇批評的眾聲喧嘩。作為戰時的陪都,重慶集中了大量的戲劇人才,成為抗戰期間的戲劇重鎮,這從中國話劇批評史上諸如戲劇民族形式問題、歷史劇問題、建立新現實主義體系問題,以及關于《野玫瑰》《清明前后》與《芳草天涯》等的論爭幾乎都發生在這里可以得到佐證。此外,大后方戲劇一時繁盛,批評家們對于職業演劇下的商演模式出現的不健康傾向,諸如“市儈主義”“噱頭主義”“打游擊”等,也進行了嚴厲批評。
一
從具體過程和內容看,國統區話劇“市儈主義”的批判,主要有以下三個階段:
一、發聲階段。大致從1937年7月到1941年10月,這個階段主要針對開始出現的“噱頭”等不良演劇臺風提出批評。
1937年抗戰爆發后,作為第一支來渝的外省救亡戲劇團體,上海影人劇團一行34人在陳白塵、沈浮、孟君謀率領下來到了重慶。盡管演出的劇目與抗戰有關,如《盧溝橋之戰》《放下你的鞭子》《流民三千萬》《漢奸》等演出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但還是有批評家針對上海影人劇團的演出說:“我們不要把他們當做‘明星’看待,他們也不要這樣看待自己。觀眾與演員都應該以絕對嚴肅的態度互相看待。”[1]文章批評上海影人劇團演員王獻齋扮演的日本兵,剛出場未講話,觀眾就哄堂大笑的情況,從中可看出批評家對這種以裝扮吸引觀眾的“噱頭”表示了不滿。
隨著諸如熊佛西率領的平民教育促進會抗戰劇團、陳鯉庭等組成的上海業余劇人協會等專業水準的劇團來到重慶,重慶演劇掀起了一個小小的高潮,但隨著演劇隊伍的擴大,戲劇演出中不良的現象隨之出現,1939年2月16日,由姜公偉召集的“如何建立戲劇演出體系”座談會上,到會的熊佛西、洪深、鄭伯奇等人就提高導演的地位和權力以及揚棄過分夸張的演技兩個問題達成了比較一致的意見。其實這兩個問題是緊密相關的,演出中導演地位和權力的加強就意味著對演員舞臺演出的控制,這也說明當時重慶舞臺存在著的不良傾向。而次年,即1940年1月在《戲劇崗位》每月座談中,發表了葉(仲寅)《關于噱頭》一文。文章中說,有些團體的排練,演員過于隨意,“甚而往往一出戲只經過一二次排練就搬上舞臺,演員連劇詞都記不得,全靠提示的人演雙簧。一些自作聰明的演員沒有辦法,就只好亂用‘噱頭’應付觀眾”。文章語重心長地提出:“這種戲將來會漸漸變成文明戲,那時話劇只有任其滅亡。”[2]同年,杜宣也對當時劇壇把“噱頭”作為“創作方法的中心”給以了批判,并以實際的事例表明應該堅決反對那些“‘寄慘痛于哄’的唯‘噱頭’的傾向”[3]。
對“市儈主義”的批評一開始就采用了集體批評的方式,此時座談會成為最好的選擇。1940年2月21日,繼1月間出版的《戲劇崗位》批評演劇的“噱頭主義”之后,中華全國文協在重慶舉行第一次戲劇座談會。會上對于演出中的“噱頭主義”“生意眼”等不良傾向進行了批判,到會的有胡風、臧云遠、鳳子、黃芝岡、海尼、萬籟天、辛漢文、光未然、葛一虹、王泊生、章泯、張西曼等,座談會并且涉及到戲劇改編問題。從參加座談人員主體看來,左派人士無疑成為對“市儈主義”批判的中堅力量,而從1941年7月開始,《新華日報》逐漸成為左派人士戲劇批評的平臺,其中林實的《一年來重慶話劇種種》[4]和舒非的《如何挽救大后方演劇運動的低潮》兩文就提到了后方演劇人“生意眼”的問題[5]。1941年10月10日,為紀念第四屆戲劇節,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在一園大戲院舉行紀念大會,到會的有張道藩、黃少谷、鄭用之、陽翰笙等數百人。會上,陽翰笙講話說,戲劇界迎合觀眾低級趣味傾向抬頭應引起注意。同日《新華日報》發表《后方的戲劇運動者要怎樣跟功利的,買賣的傾向斗爭?》一文,文中指出“戲劇運動”與“戲劇買賣”的區別,認為“戲劇運動是文化運動的一環,是新的文化園地的拓殖者,是新的進步的文化勢力的撫育與推進者”,“但戲劇買賣卻止于是商品的買賣,作這種買賣的實利主義者,只知利用一切已成的價值,對于一切尚未獲得市場價值的新嘗試,新事物均不感興趣”。作者為此要求現階段的演劇者們“不賣弄‘名家’、‘明星’、‘生意眼’,……不抄襲,賣弄一切已成的噱頭”[6]。一切跡象表明,對戲劇演出不良傾向的批判逐漸成為當時戲劇批評界關注的重點。
二、深化階段。從1941年10到1945年5月,主要針對四次霧季公演不良傾向的批判,是從文本到舞臺的全面批評。
1942年2月6日,《戲劇崗位》社邀請戲劇界人士召開座談會,到會的有史東山、賀孟斧、陳鯉庭、陳白塵、孫師毅、王瑞霖、張駿祥、楊村彬、黃芝岡、蘇丹、安娥、徐昌霖、周峰等30余人,陽翰笙主持。到會者對當前戲劇的演出,是凌亂或是蓬勃爭論激烈,大家認為劇本必須要有積極意義,內容與藝術都要有擇其佳者;演出要嚴肅認真,不可草率;要愛護演員,不要叫他們同時演兩三個戲;舞臺工作要統一協調;劇評不僅注意舞臺,必須注意教育觀眾,評論要具體、深入、客觀。2月13日《新華日報》刊登了座談會記錄要點。
劇評家劉念渠在評論1941年10月至1942年5月的重慶霧季公演時,以演出影響較大的28出戲劇為例,認為直接、間接反映抗戰的占到二分之一。而演劇上取得新成就的演出有:“《北京人》、《閨怨》、《屈原》、《表》,給觀眾予統一的印象。”問題較多的是以“留渝劇人”為名義的演出,他們沒有任何物質設備,全靠找到關系。他還批評了幾個演出:“意識歪曲的《野玫瑰》、庸俗的《天網》、勉強抗戰的《遙望》。”而“這正表現了某些(戲劇)工作者不夠警覺,在無所謂中流為盲目演出”。在論及這一期間表演和舞臺工作新成就時,他認為表演上糾正了形式主義,布景設計除寫實而外開始向風格化探索,克服過去一個時期競相新奇的傾向,理解到設計必須從劇本內容著手,成為創作中的有機一部分。而回顧這一期間的演出,有待克服的弱點有:一,演出的無計劃性;二,凡參加演出榜上有名的應各盡其責,一些導演團與顧問團人員沒有幾個是盡到責任的,而是被人當做金字招牌打出去支撐門面;三,草率的演出,有的導演只排排位置,指點一下聲音高低就把戲推向舞臺,有的演員一人兼在三處演戲、排戲[7]。作者在肯定公演成績之外,對諸如“留渝劇人”的演出團體,諸如《野玫瑰》《天網》《遙望》戲劇文本以及導、表演員存在的不足與缺點給予了批判,現在看來有些認識,如對《野玫瑰》的態度不免極端,但總體而言,對當時劇壇存在問題的批判還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從1943到1944年,隨著霧季公演的逐漸升溫,對戲劇演出不良傾向的批評逐漸走向一個高潮。梅令宜就認為過去兩個霧季的“演劇惡性市儈化傾向的發展并不顯著”,對職業劇團為了生存顧及票房給予一定的理解,但從最早的以“留渝劇人公演”名義,后來成為“打游擊”的演出形式,“到了現在(民國三十二年夏天以后),我們卻真的看到了演劇市儈化的抬頭”,甚至“另一城市的演劇正走上一個市儈化的高潮”。作者認為幕后最大的推手是資本的流入,不良商人把金錢投入到戲劇演出上去,不考慮戲劇藝術的純潔與藝術價值,贏利的最大化成為他們的終極目標,加之“偏偏有一伙演劇工作者愿意跟他們‘合伙’”,在此情形之下,戲劇就逐漸走上商業至上的道路,如果對“市儈主義”不加以打擊,就會重蹈昔日文明戲的“覆轍”。[8]
批評家白苧更是針對章罌認為當我們的劇運遇到困難之時,“前面有人筑起一道墻,我們也就只好歪一點拐到旁邊的小路去”[9]言論,表示“堅決地反對”,他認為梅令宜《另一個危機——略論戲劇界的“市儈主義”》一文,“那總是公平的論斷,正義的應援,也是我們戲劇工作者充滿了血淚的痛心史!我們不怕‘家丑外揚’,卻怕別人‘指鹿為馬’!”[10]同日,章罌對白苧的言論加以回應,認為在當前情況下,不合作沒有出路,在不給戲劇“開倒車”的前提下,這種合作“能擴大我們工作的范圍,讓劇運能繼續生存”,而戲劇工作者只要抱著嚴肅的態度與人合作與盲目地跟從別人是不同的,當“康莊大道”走不通之時,“非得在小路上迂回前進不可”[11]。同日編發的《編者附言》認為,二者基本的出發點還是為了當前劇運的發展,一個為劇壇亂象疾呼,一個提出在當前情況下劇運工作者應采取的具體策略,雖然有所異議,但并沒有原則上的分歧,這種觀點還是有一定的道理。
隨著對“市儈主義”批評的逐漸深入,如何在譴責之余對劇運進行建設,成為批評家們聚焦的首要問題,代表性的文章有夏衍的《論正規化》一文。在《論正規化》一文中,作者認為戲劇工作者已經從“業余”逐漸走向職業化,這是話劇運動的“轉型期”,在此期間,應注意兩點:一、每位導演、演員、舞臺工作者要著重技藝的提高,要達到起碼的技術水平。夏衍提出,重慶當時有三個“職業劇團”,即使在霧季,也不是每個劇團都有經常性的演出,讓大批戲劇工作者窩工、坐茶館,為什么不用來提高業務水平、藝術水平的工作呢?以此為將來正規化劇院作準備。二、建立一個有紀律、有責任感的職業演員乃至舞臺工作者的做人態度、工作態度。要摒棄“自由主義”“平均主義”和“臺上見”的工作作風。夏衍說:劇壇應有“明星”,社會和劇壇不要吝于對他們的褒揚,這個名稱并不可怕,有明星架子真的可怕,尤其是沒有明星成就先有明星架子更是可怕。在生活待遇上,每個人的工作“值”多少,是他“取”酬的標準。干好干壞報酬一樣多,則是獎勵不進步和偷懶[12]。此外,戲劇家焦菊隱則認為:“在職業化的演劇活動以外,普遍地扶持業余演出,是很重要的工作。”[13]隨后,批評家白苧也從業余演劇的角度回應、贊同和補充了焦菊隱的觀點[14]。
1944年2月15日第六屆戲劇節紀念大會由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在文化會堂舉行。《新華日報》為紀念戲劇節發表社論,題為《抗戰戲劇到人民中間去——祝1944年戲劇節》,提醒戲劇工作者警惕“脫離人民,游離抗戰現實,趨向于卑俗娛樂和高蹈自喜的傾向”[15]。16日《新華日報》出版的戲劇節紀念特刊,刊登了郭沫若、夏衍、焦菊隱、史東山、梅令宜等人的文章,嚴肅、認真地討論了戲劇界的狀況,這又是一次帶有意識形態性的“集體批評”。
整個霧季公演期間,每年都有幾十臺話劇搬上舞臺,四個霧季共演出100多出話劇,后來被話劇史家稱之為中國話劇史上的黃金時代。這個黃金時代不僅是因為演出多,更主要是從文本創作和舞臺表現都顯示出較高的藝術水準,但這并不表示沒有質量低下的創作和演出,上述對霧季公演期間出現的“市儈主義”的風氣的批判就說明了這一點。但應當看到,特別在對戲劇文本的甄別上,由于過于強調戲劇文本反映抗戰現實的主旨意義,有時不免矯枉過正,而且當時國共兩黨對戲劇陣線的爭奪,也會出現非學理的批評思維,這都是我們在看待當時批評言論時所應該注意的。
三、反思階段。從1945年以來到1949年,主要是針對“打游擊”演劇風氣的批判。
第四次霧季公演之后,由于政治局勢并不明朗,加之各個劇團生存空間越來越小,客觀上造成了“市儈主義”的進一步蔓延,這時,很多劇團以“打游擊”的形式進行戲劇演出活動。“打游擊”的演劇形式由來已久,1941年皖南事變后,國共合作名存實亡,參加“中”字號的我黨演劇人和進步演職人員紛紛撤離或辭職,另組民間劇團“中華劇藝社”,由應云衛任社長,理事有孟君謀、陳鯉庭、陳白塵等。國民黨為了排擠進步力量,搶占舞臺,用“留渝劇人”的名義組織“游擊演出”,所謂“游擊演出”就是由個人出面以高價拉攏演員零時拼湊一臺戲演出,不屬于任何單位。我黨針對這種情況也組織了“游擊演出”,叫做“以游制游”,這類演出共組織3次,首先是賀孟斧出面組織演出了沈浮編導的《重慶二十四小時》,其次是顧而已組織上演的世界名劇《閨怨》,還有周峰出面組織的俄國名劇《大雷雨》。可見,最早的“打游擊”是國共兩黨為爭奪戲劇陣營,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都曾經使用過的演出形式。只是到了霧季公演之后演變成戲劇掮客等組織的贏利至上的戲劇演出。這種戲劇演出因為人員主要靠臨時拼湊,演劇人員水平參差不齊,加之缺乏有效的管理、排練、監督,演出水平可想而知。
《新華日報》以“重慶劇壇一片混亂”為正標題,以“沒有演員的新劇團占領劇場,認真演戲的團體別再想演戲”為副標題,對抗戰勝利后的大后方劇壇的亂象給予概括。消息最后說:“霧季已經完了,可是還有八個十個劇團‘搶’院子。瞧樣子,大約下半年沒有特殊背景的劇團就不用想演戲了。”[16]這種“打游擊”性質的演出自然不會被富有責任感的戲劇家們所容忍。1945年3月22日,宋之的、于伶、夏衍、鄭君里在城內陽翰笙家中聚會,漫談如何制止目前話劇界游擊成風事宜。大家深切感到,如果不把目前這種惡劣不堪的壞風氣制止,30年來話劇運動的成果,將被某些“特殊人物”支持的游擊演出所毀掉。之后,張駿祥和王瑞麟分別于3月29日、3月10日去陽翰笙處,談及游擊演出破壞話劇運動的情況。
當然,對于“打游擊”之風的蔓延,戲劇批評家們并沒有一味地加以批判,他們也對此進行了反思。如1945年《國民公報》星期增刊從4月29日起連載《論現階段演劇諸問題》一文,認為“自33年(1944年)霧季開始后,在舞臺上很少見精彩的演技,甚或某些曾有過很好成績的演員,反而顯出了若干程度的退步”[17](P176-177)。但文章沒有停留于一味的批判,而是在批判的同時還論及了捐稅、票價、審查、劇本創作、劇團收入與開支、劇團管理、向演劇隊學習諸問題,對演員的表演停滯不前的原因做了探討并給以建議:在演出者方面,必須注意到演員的精力,愛護演員的前途。與其讓他們馬馬虎虎地演三五個戲,不如讓他們好好地創造一兩個人物。在導演方面,對于已有相當成就的演員,應當做到真正的合作,避免由過分信任而產生放任自流;演員方面,尤其珍重自己的藝術及前途發展的工作,學習與生活有合理的支配,在刻苦的生活中專心工作,加緊學習。這里作者對當時演員演技退步的原因沒有一味從演員身上找原因,而是綜合考慮了導演在演員演技發展所起的作用,并且從關心演員前途的大局出發,一方面認為演員自己要自珍自愛,加強業務學習,一方面對戲劇管理者提出要求,即要關心演員的生活,這種批評就比之一般對“市儈主義”歪風一味譴責讓人信服,也更具有實際的意義。
戲劇家焦菊隱也針對日益嚴重的“打游擊”現象,給出了自己的建議:“一,要有計劃地推動業余演出,擴大戲劇運動的活動領域;二,要有計劃地而且普遍地‘打游擊’,用游擊的方法,來游擊‘游擊’。”[18]可見,作者在反思中認為對待當時“打游擊”現象泛濫,切實的措施是采取適當的方法來加以斗爭,而不能一味被動地加以批判。
從上面諸位批評家的言論可以看出,對“市儈主義”歪風的批評有個從舞臺演劇現象的一般批評的發聲階段,到文本、舞臺、管理等全面批判的深入階段,再到分析原因、給出對策的反思階段的過程。
二
綜合上述三個階段的批評實踐來看,對“市儈主義”的批判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特點:
其一,開始時間早,并且與整個大后方戲劇發展相伴隨。
從上文中可知,雖然重慶直到1937年才有話劇的商演,但隨著中國政局的發展,大批劇人開始涌向大后方,作為中心的重慶迎來了越來越多的戲劇團體。重慶等大后方戲劇的發展是在職業演劇發展之后興盛起來的,可以說從一開始大后方的演劇就帶有濃厚的商業氣息,商業化演劇形式必然帶來諸多弊端,因為眾多淘金的戲劇團體層次不一,水平各異,為了爭奪市場,不免泥沙俱下,這早已被富有責任感的批評家所注意。從整個大后方現代戲劇發展來看,對“市儈主義”歪風的批判從發聲到深化再到反思,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其二,以左派報刊雜志為批評載體,以左派為批評力量的主體,以“集體批評”為主要批評方式。
重慶戲劇發展的中堅力量是左派人士,對戲劇發展過程出現不良傾向的批評也以左派人士為主,與之相對應的是對“市儈主義”批判的載體主要是當時中共在重慶唯一的機關報紙《新華日報》和帶有明顯左派色彩的《戲劇時代》《戲劇月報》等專業戲劇刊物。如由中央青年社編輯,文風書局出版發行的大型戲劇刊物《戲劇時代》于1943年11月11日創刊(共出6期,1944年10月10日終刊),從編委洪深、吳祖光、馬彥祥、焦菊隱、劉念渠的身份看,就帶有濃厚的左派性質。而且批評的方式也采取了左派人士慣用的座談會等“集體批評”的方式。
其三,對“市儈主義”的批評與對國民黨的斗爭相伴,即要求當局降低上演稅,提高劇人的待遇。
“集體批評”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話語霸權的威力,這與當時國共兩黨對戲劇文化陣地的爭奪有關。中國現代史上,國共有幾次聯合的情況。作為當時占據主導地位的政黨,國民黨一向對文化藝術領域實行管制。早在1927年5月30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駐滬辦事處編審組藝術股對包括戲劇在內的藝術內類實行審查制度,一切有關革命的劇本及詞匯均須審查,方能上演,否則一律取消。重慶在1938年10月1日就成立了類似性質的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戲劇演出和出版都歸其管轄。
更為重要的是,國民政府對戲劇演出征收過重的賦稅,自然引起劇人們的不滿。1943年4月8日,在重慶戲劇供應社宴請重慶劇作家的宴會上,大家召開了一次聯誼會的小會,繼1942年12月4日張駿祥在電影戲劇界座談會上提出上演稅問題,大家進一步探討了保障上演稅問題,并在推遲出版的《戲劇月報》三月號上,向全社會發出“不要餓死劇作家”的宣言,宣布了決議上演稅暫行辦法:重慶、昆明、西安三大城市,首演劇作家的劇本,報酬不少于500元,上演稅最低應占全部票款收入(除去捐稅)的3%。當時眾多作家都簽了名。在同一期《戲劇月報》上還發表了“保障上演稅運動特輯”,分別刊有于伶《感慨與期待》、張駿祥《上演稅與狄翁·波乞靠》、老舍《不要餓死劇作家》、夏衍《被艷羨的另一面》四篇文章。其中老舍說:“寫劇本也要花費光陰,耗費心血,也要喝茶吃飯……有人要演我的戲,便是看重了它,也就應當給我上演稅,天理人情,才兩無缺欠。”[19]夏衍則說:“‘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現’,這并不單單適用于一匹馬”[20],它對于劇作家也同樣適合。由于物價上漲,作家生活艱難,文藝界人士生活倍加艱苦,貧困者日眾,《新華日報》為此發表社論,要求“提高稿費,保障劇作稅,設法改善作家生活”[21]。
1944年2月15日第六屆戲劇節紀念大會由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在文化會堂舉行。羅學濂主持大會,馬彥祥發言,要求減低戲劇演出的捐稅。其中除了對當時劇壇“市儈主義”進行批判之外,史東山《今日戲劇的命運》、夏衍《我們要在困難中行進》兩文明確反對當局把戲劇娛樂化,且加以重稅的做法。同日,戲劇家馬彥祥在《中央日報》上也發表題為《為演劇征捐呼吁》,對當局征收戲劇50%的“娛樂稅”表示不滿。可以說,抗戰后期,上海和大后方劇壇越演越烈的商業化、庸俗化傾向,國民黨政治高壓下過重的稅收是一個重要誘因。
客觀而言,因為語境不同,重慶等大后方在戲劇生存空間上較之當時的延安、上海小了許多。延安劇人的待遇自不待言,就同時期上海而言,有人就說,“大家說最近的電影演員待遇好極了,其實演話劇的此番打入龍門,石揮居然能拿到六百〇一元的月薪,也不算錯的了”[22]。可見,在當時商業演劇繁盛的上海,職業演員的生活還是無憂的。而在由上海《雜志》社于1944年1月11日召開的舞臺藝術座談上,大家在討論“演員們的生活”之時,普遍感到收入并不高,不過演員韓非則說,“演員的待遇雖然不能算好,但是社會上一般小職員的待遇還不如我們呢!所以我們雖然比上不足,卻比下有余”。演員沈浩、蘭心、韋偉等對此問題也都一致用了“滿足”[23]一詞。
反觀當時大后方劇壇,當時劇人窮死、病死的消息充斥著大報小報。1941年2月5日,洪深與夫人常青真及患晚期肺結核的女兒在賴家橋家中服毒自殺。郭沫若等帶醫生迅速趕去搶救,洪深才脫離險境。洪深在遺書中稱:“一切都無辦法,政治、事業、家庭、衣食住種種,如此艱難,不如且歸去,我也管不盡許多了。”周恩來得訊后指示:“著人予以資助。”[24](P62)中華劇藝社前臺主任沈碩甫貧困交加,死前的襯衣襯褲爛得沒法補,連墓地也是當時的朋友劉盛亞捐獻出來的。還有著名導演賀孟斧、中華劇藝社業務主任沈碩甫、優秀演員施超、江村都是在貧困、饑寒和重病中死去。其中1943年4月3日,沈碩甫死后入殮之時發現內衣內褲也不完整,墓地系四川作家劉盛亞所捐。而詩人兼演員江村,本應約去成都演出《北京人》,后因故未演,一氣之下肺病惡化,終因貧困交加,不幸于1944年5月23日病死的,其墓地是成都劇人之友、記者車輻捐助的。某劇作家謂:“江村之死,痛心之至,以他生前未亂打游擊,而且為游擊者所累也。”郭沫若為墓碑題詞,文曰:“劇人江村之墓。”[25](P155)1945年5月10日,著名導演賀孟斧去世,身后蕭條,連治喪費用都成問題,墓地也是劉盛亞所捐。中國現代戲劇開拓者之一朱雙云,病逝于四川北碚,也是“身后蕭條,無百元之儲”。[26]
有人以上海影劇壇演員阮玲玉、艾霞、英茵自殺和英子的肺病為例子,說明上海演員生活不容樂觀[27]。上述演員皆為女性,作為受害者,確實也反映了當時藝人生存的不易,但客觀說,她們不全是因為窮困或死或病,這與重慶等地劇人因為窮困而亡的情況還是有著很大區別。
收入低,劇場少,生活上的困頓帶來精神上的苦悶,劇人的生存壓力越來越大,戲劇生存的空間越來越小。由夏衍、宋之的、于伶取材于當時劇人的生活,合編的五幕七場劇《戲劇春秋》于1943年11月14日在銀社公演(導演鄭君里)。12月30日,《新華日報》發表克立的文章《用他們自己的艱辛與血淚,已經引起了觀眾們的共鳴——從<戲劇春秋>的演出看當今的劇人們》,文章道出戲劇工作者生活的辛酸和精神上的苦悶,并在觀眾中獲得共鳴。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對戲劇等文化的管制更是變本加厲,加之美國電影的沖擊,話劇界舉步維艱。對于不景氣的劇壇,熊佛西認為“主要的原因還是由于政治不清明,而影響到人民經濟生活的破產”,“藝術畢竟是繁榮安定的社會產物”,在多數人還在為生活著想的時候,“劇運的低潮是必然的現象,而毫不足驚奇”。而阻礙戲劇藝術發展與前進的“惡魔”是什么呢?作者主要從三方面談起:“(一)劇本何以脫離現實”,作者認為“生活不安定,言論不自由”是“惡魔”之一,“因為一般劇作家生活的貧困,他們在寫作的時候不能不考慮作品的銷路與演出時賣座問題;銷路好,賣座盛,他們則可多收入一點版稅或上演稅,以換取他們的溫飽”。而沒有寫出反映時代、反映人們大眾“心聲”的作品,關鍵在于政治高壓之下沒有言說的自由。此外,在“(二)導演何以傾向噱頭”“(三)演技何以華而不實”中既對導表演中存在的不足給以批判,同時也認為“生活不安定,言論不自由”是造成不足的“惡魔”[28]。作者從文本到舞臺,對于戲劇從業者給予了理解與同情,不但顯示了作者的人文關懷,作為身處其中的劇人,其觀點也令人信服。
結語
40年代上海戲劇畸形繁榮下出現的商業至上行為也遭到批評家的譴責,但客觀而言,上海的通俗化演劇是市民戲劇審美的表現,對商業至上的批評針對的是客觀出現的媚俗現象,多是從戲劇本體出發的理性發聲。不同于上海對商業至上的批判,重慶戲劇作為國共兩黨爭奪文化藝術陣地的重要陣營,戲劇批評意識形態的痕跡很重,對“市儈主義”的批判總是與國民黨對戲劇的高壓相伴,故而此次批評的主體是左翼人士,而作為意識形態陣地爭奪下的戲劇,也更多附加了社會學的因素。另外,聯系當時身處國統區的劇人的生活語境,諸如“市儈主義” “打游擊”等惡習的形成還是有一定的客觀原因,那就是為生計而被迫滑入商業泥沼的可能。生存環境逼迫加上商業利益的誘惑,演出過程中出現不注重藝術品位、盲目迎合觀眾的傾向在所難免,這也是我們看待當時劇人走上“市儈主義”之路所應該反思的。
[1]姜公偉.從“全民文化”談到影人劇團的演出[N].國民公報,1937-11-7(3).
[2]葉.關于噱頭[J].戲劇崗位,1940,1(4):141.
[3]杜宣.關于劇作上唯“噱頭”的傾向[J].戲劇春秋,1940,1(1):3-4.
[4]林實.一年來重慶話劇種種[N].新華日報,1941-7-12(4).
[5]舒非.如何挽救大后方演劇運動的低潮[N].新華日報,1941-7-17(4).
[6]后方的戲劇運動者要怎樣跟功利的,買賣的傾向斗爭(演劇之友座談報告)[N].新華日報,1941-10-10(5).
[7]劉念渠.重慶抗戰劇運第五年巡禮[J].戲劇月報,1943,1(1):64-77.
[8]梅令宜.另一個危機——略論戲劇界的“市儈主義”[N].新華日報,1943-10-21(4).
[9]章罌.劇季的過去和現在[N].新華日報,1943-10-23(4).
[10]白苧.寧肯碰壁,不走小路——“態度嚴肅”并不等于“藝術成功”[N].新華日報,1943-11-1(4).
[11]章罌.走向目標的道路:敬復白苧先生[N].新華日報,1943-11-1(4).
[12]夏衍.論正規化[J].戲劇時代,1943,1(1):10-15.
[13]焦菊隱.我們要扶持業余演出[N].新華日報,1943-12-29(4).
[14]白苧.論扶持業余演劇[N].新華日報,1944-1-24(4).
[15]抗戰戲劇到人民中間去——祝1944年戲劇節[N].新華日報,1944-2-15(4).
[16]重慶劇壇一片混亂:沒有演員的新劇團占領劇場,認真演戲的團體別再想演戲[N].新華日報,1945-5-8(3).
[17][24][25]石曼.重慶抗戰劇壇紀事[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5.
[18]焦菊隱.游擊“游擊”[N].新華日報,1945-8-12(4).
[19]老舍.不要餓死劇作家[J].戲劇月報,1943,1(3):3.
[20]夏衍.被艷羨的另一面[J].戲劇月報,1943,1(3):7.
[21]為抗建文化著想[N].新華日報,1943-8-15(4).
[22]伊麗.兩個分野:一部分專拍電影,一部分專演話劇[J].萬象,1942,3:18.
[23]舞臺藝術座談[J].雜志,1944,12(5):12.
[26]李元龍.哀朱雙云[J].萬象,1942,5:19.
[27]芳君.劇運與劇人的生活[J].女聲,1943,2(3):6.
[28]熊佛西.談目前劇運的低潮[N].大公報(戲劇與電影),1946-1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