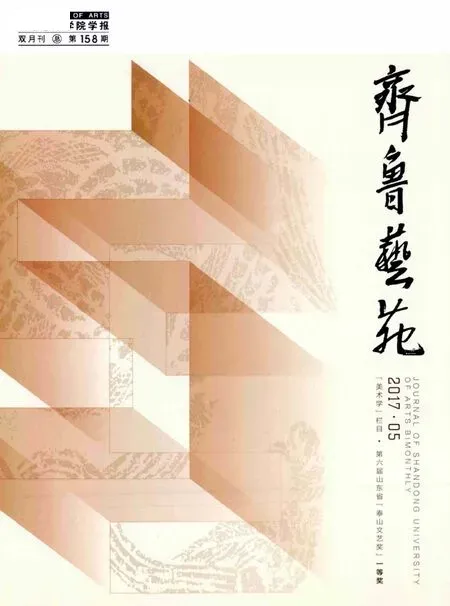萬比洛夫對契訶夫戲劇的繼承與發展
于利平
(山東藝術學院戲劇影視學院,山東 濟南 250300)
萬比洛夫(1937—1972)在蘇聯戲劇史上無疑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作家,從1962年開始發表作品到1972年不幸葬身于貝加爾湖,在這短暫的十年當中,萬比洛夫創作出4部多幕劇、3部獨幕劇和1部戲劇小品。果戈里、奧斯特洛夫斯基等俄羅斯傳統戲劇大師都對萬比洛夫的作品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后者的作品受契訶夫創作風格的浸染尤甚。萬比洛夫繼承契訶夫創作風格的同時,也做出了自身的改變和發展,其中一個最為顯著的特征就是,在追求作品抒情性和象征性的同時,萬比洛夫并不排斥舞臺戲劇性的呈現,從而形成了自身獨特的藝術特征。
一、萬比洛夫對契訶夫戲劇的繼承
萬比洛夫對契訶夫多幕劇藝術風格的繼承,主要反映在作品內容和主題意蘊兩個層面。首先在作品內容上,萬比洛夫繼承了契訶夫多幕劇的重要特征——抒情性和象征性。由時空環境、人物關系和舞臺事件所構織呈現出的戲劇性情境是西方現實主義傳統戲劇的核心要素,契訶夫早期獨幕劇中也常出現充斥著起伏波折的沖突場景。然而在他的晚期多幕劇作品中,作者摒棄了早期屬于傳統主流戲劇的創作方法,具有沖突特征的戲劇性情境被靜態的抒情性情境所取代。
無論創作目的還是審美效果,戲劇性情境和抒情性情境都截然不同:“戲劇性情境一般以逼真性、刺激性為目標,使觀眾仿佛置身于緊張的場面之中。而抒情性情境應該適當克服真實場面中的劇烈的直接沖動,把情感化為淡淡的情思,并和外在的景物合為一體。”[1](P63)由此可見,戲劇性情境作品以讓觀眾“信以為真”,并以此為心理基礎進而產生強烈的“內模仿”為目的,而抒情性情境作品則控制情感,其場上任務并非為了展示緊張激烈的故事情節,而是要表現事件對人物的心理影響,以抒情和象征手法刻畫人物形象。
因此,我們在契訶夫的多幕劇中能看到諸如“失家園”“遭背叛”“被拋棄”等舞臺事件,卻很難找到由因果關聯的事件串聯而成的情節線索;我們無法找到人物臺詞之間的邏輯關系,大多數對白都是所答非所問,或者是心不在焉的敷衍。但是在其多幕劇中,我們隨處能看到“湖水”“海鷗”“櫻桃園”“非洲地圖”等象征性意象,能看到特里波列夫、尼娜、特里果林、阿爾卡基娜、沃伊尼茨基、加耶夫等象征性人物,以及“特里波列夫打死一只海鷗”“契布蒂金失手打碎磁掛鐘”“娜達莎巡視房間,不允許有光亮”“費爾斯被遺棄在家中”等等情節象征。象征手法的運用,以具體形象表現抽象意義,大大拓展了契訶夫多幕劇的內容意指,令其作品意味深長。
同時,我們也發現契訶夫多幕劇中的人物在面對困境時不抗爭,不戰斗,而只是發出對生活的感慨:尼娜在被特里果林拋棄,過著卑微生活的時候,并沒有忘記藝術理想。她領悟到在藝術創作中要有耐心,要有責任感,要有信心。她感嘆著自己的精神力量越來越堅強了;阿斯特羅夫雖然對現狀不滿,感覺庸俗的生活正在吞噬他的生命,但是也一直在憧憬未來,想象著一千年后人們的生活,希望能為人類的幸福做出貢獻;三姊妹面對娜達莎的逼迫,只是向往著莫斯科的生活……這些憧憬和感慨沖淡了劇中人的痛苦,讓他們的精神暫時擺脫了當下的困境,生成為一種超然物外的境界。契訶夫多幕劇中的人物多富于言辭和思想,而缺乏改變現狀的執行力和行動力。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懦弱,而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則在于他們痛苦的根源不是現實中那些具體的人和事,而是生活和環境本身。人與生活(環境)之間的矛盾,才是作者所要真正表現的主題。
由此我們發現,契訶夫在其多幕劇中刻意回避了舞臺事件外部行動的呈現,而代之以抒情性和象征性的描寫,從而令其作品超越了具體事件甚至具體時空的藩籬,契訶夫多幕劇中人物命運的逆轉、變化不再由具體的他人或事件決定,人們所面臨的不是能夠解決的具體問題,而是無法解決的人與存在之間的永恒矛盾,這使得其作品具有了現代性和多義性特征。當今,契訶夫多幕劇依然活躍在世界各國的舞臺,而劇中那些令人沉思的人物,他們的憂傷,他們的痛苦,也依然深深打動著今天的觀眾。
契訶夫的話劇作品影響了后世一大批劇作家和導演,萬比洛夫作為本民族的繼承者,更是深得其作品抒情性和象征性之要義。這一點在其《窗子朝著田野的房子》《六月的離別》《長子》《打野鴨》《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等作品中皆有所體現。
《六月的離別》講述的是一個關于選擇的故事。地質學專業大學生柯列索夫愛上了校長的女兒塔妮婭,校長列普尼柯夫以拿不到畢業證為要挾,要求柯列索夫離開他的女兒。柯列索夫一時軟弱,對索尼婭提出了分手。畢業之際,索尼婭趕來與柯列索夫告別,兩個年輕人再度心生波瀾。校長找到柯列索夫私談,再次以讀研究生為條件,讓他放棄戀人,選擇前程。柯列索夫對索尼婭坦言他曾經為了畢業證產生過動搖,滿心失望的索尼婭離開了他。失去愛情的柯列索夫幡然悔悟,當眾撕掉了畢業證書。
熟悉契訶夫的讀者可以從這個劇的很多地方看出契訶夫對萬比洛夫的影響。劇中的教授是一個擅于玩弄權術的偽知識分子,用教授妻子列普尼柯娃的話說:“……你并不是個學者,問題就在這兒。你是個行政干部和半瓶子醋的學者。這是為了你的威信裝裝門面的。”[2](P41)列普尼柯娃對列普尼柯夫的評價很容易讓人聯想起《萬尼亞舅舅》中那個“整整講了二十五年的廢話”[3](P486)的浪費紙張的謝列勃里雅科夫教授。可惜列普尼柯娃意識到這一點時半生已過,為時太晚。她痛心地對丈夫說:“如果你是個學者,我也就心安理得了。得了,別再談這個了。別擔心,你什么危險都不會有,我明白這一切已為時過晚了……”[4](P41)列普尼柯娃和她的教授丈夫的關系,同《萬尼亞舅舅》中的沃伊尼茨基和謝列勃里雅科夫教授之間也很類似,列普尼柯娃和沃伊尼茨基兩人的痛苦是那么相似:奉獻者最大的悲哀,莫過于在付出一切之后才發現上當受騙,曾經的美好愿望和萬般辛苦全部付諸東流。
由此可見,《六月的離別》受《萬尼亞舅舅》很大的影響,繼契訶夫之后,萬比洛夫再一次無情痛斥了知識分子中的沽名釣譽之徒。然而深究此劇,我們會發現契訶夫對萬比洛夫的影響并非僅止于此:《六月的離別》中的象征性意象和象征性情節,以及整體上呈現出的抒情風格,才真正體現出萬比洛夫對契訶夫多幕劇藝術風格的繼承。
第二幕中,布金和弗羅洛夫這對情敵因為瑪莎要去花園深處決斗,槍響之后兩人安然無恙地走出來——他們沒有向對方開槍,只是打死了一只喜鵲。這只“喜鵲”與契訶夫筆下的“海鷗”何其相似,它們都象征著生活中那些被毀掉的無辜受害者;而卓洛圖耶夫被判入刑,出獄后一心想要證明金錢可以摧毀道德最終卻失敗的故事,則是一條副線,作為劇中的象征性情節呼應著柯列索夫遭受靈魂考驗的主線,兩者共同呈現出作者所要表達的主題。
《六月的離別》整體上具有一種濃郁的抒情風格,作品雖然講述的是年輕人的愛情遭遇考驗的故事,同時也有三角戀愛關系和“復仇”情節,但是卻并不過多將筆墨擲于事件的發生和發展,而是著力表現人物受到事件沖擊后的心理反應和性格轉變。正如我們以上所看到的,無論是“決斗”還是“復仇”,萬比洛夫都將這些情節置于“暗場”處理或者由人物語言交代完成,場上觀眾所看到的,往往是劇中人對人生的嗟嘆、惆悵和無奈,或者是人們對愛情和未來的熱情贊美和一往無前。而貫穿始終的歌聲和散文化風格的開場和結局,更是增添了全劇的抒情色彩。
萬比洛夫話劇的象征性和抒情性,同時也體現在《窗子朝著田野的房子》等其他作品中。《窗子朝著田野的房子》是一部獨幕劇,劇中只有兩個人。農莊奶牛場的場長阿斯塔芙耶娃和小學教師特列齊雅柯夫一直默默喜歡對方,可是特列齊雅柯夫下鄉教書的期限已滿,就要離開村莊返回城市了。特列齊雅柯夫走遍全村跟大家告別,最后來到了阿斯塔芙耶娃的家。故事就從這里開始了。阿斯塔芙耶娃一直不安地等待著特列齊雅柯夫,當她從窗戶上看到他終于到來時,趕緊鎮定下來,佯裝熨衣。他在跟她告別之后沒有勇氣表白,準備離開。她卻以窗外的歌聲為借口,不放他走。性格有些呆板的他不明就里,只是急著去趕車,后來愛情終于戰勝了羞怯,他敞開心扉,道出愛慕之情,最終決定留了下來。
全劇沒有緊張激烈的故事情節,只有兩個年輕人由于羞怯而產生的內心沖突。臺詞活潑幽默,具有豐富的潛臺詞。其中的“窗戶”,象征著兩人克服羞澀,相互打開的心靈之窗。整部作品貫穿著歌聲,窗外的歌聲與窗內兩人的心思相互應和,頗具濃郁的詩意和浪漫色彩。
可以說,抒情性在萬比洛夫的作品中隨處可見,抒情性與象征性相伴而生,無論是《六月的離別》中的喜鵲、《打野鴨》中的野鴨和花圈,還是《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中花園里的柵欄,都被作者賦予了一定的象征意味。契訶夫和萬比洛夫的作品都具有一定的抒情性和象征性,這只是兩者之間外在的相似之處,讓我們確定萬比洛夫繼承了契訶夫戲劇精神的是兩位作者對抒情和象征手法運用的深層原因。眾所周知,契訶夫多幕劇以表現人物內心和精神世界為根本目的,因此抒情和象征都是為刻畫人物形象所運用的手段和方法。而萬比洛夫的戲劇作品正是以抒情和象征來表現人物內心世界,在此意義上,我們認為萬比洛夫的作品在抒情性和象征性上繼承了契訶夫多幕劇的風格特征。
其次,在作品的主題上,萬比洛夫繼承了契訶夫多幕劇的深層主題意蘊——人與生活(環境)的沖突。人與生活的沖突是契訶夫多幕劇的主旨,也是契訶夫在生命盡頭給未來留下的最后的“天鵝之歌”,是其作品具有現代性的重要表征。萬比洛夫的《打野鴨》等作品也因為對這一主題的復現而超越了同時代作品對社會、道德、價值觀層面的表現,成為典范之作。
《打野鴨》的戲劇結構不同于萬比洛夫其他的作品,它以“給活人送花圈”這一奇異事件開場,利用舞臺暗轉,貫穿了主人公奇洛夫的六段回憶。通過回憶我們了解到青年工程師奇洛夫充滿謊言的荒誕人生。他在單位無心工作,鼓動同事欺騙領導。他的父親臨終前寄來信件,要見他最后一面。他冷酷地嘲笑這些信件,并不理會父親的請求。他的妻子加林娜善良聰慧,曾與他真心相愛,然而奇洛夫并不珍惜,他背叛妻子找了情人薇拉,繼而又勾引了少女伊林娜。
奇洛夫在三個女人之間來回周旋,謊言充斥著他的生活。無論親情還是愛情,他都報以無所謂的態度。用他的話說:“我對一切,世上的一切,都麻木不仁,我不知道我該怎么辦,不知道……難道我真是沒有心肝?……是的,是的,我什么都沒有……”[5](P259)沒有趕上見父親最后一面,他后悔莫及,得知噩耗后馬上訂機票要趕去參加葬禮。然而當他在咖啡館見到伊林娜時,又決定跟她一起吃飯,明天再走。
加林娜最終無法忍受被欺騙的生活,決定要離開奇洛夫,當得知妻子真的要走時,他情緒激動,極力挽留,他向加林娜真誠懺悔,承諾帶她去打野鴨——那是他最向往的生活,同時也能看出他發自內心的懺悔。然而一切都無法挽回,加林娜還是走了。在他發現一直在聽他傾訴的不是妻子而是伊林娜時,他又很快不以為然地接受現狀,油嘴滑舌地贊美起伊林娜來。
奇洛夫以局外人的態度,用欺騙和謊言構織起自己的人生。同時他又對這種生活感到厭惡,他無法忍受生活的荒誕,于是就用“打野鴨”來自我安慰。實際上,奇洛夫不僅欺人,同時自欺,因為他從未真正將“打野鴨”付諸行動。對于奇洛夫來說,生活不依靠謊言是無法支撐下去的,于是,他就像《三姊妹》中的三姊妹整天說著“去莫斯科”一樣,常常把“打野鴨”掛在嘴邊。奇洛夫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物形象,他一方面玩世不恭,四處說謊,一方面又厭惡虛偽和謊言。加林娜走后,奇洛夫把大家聚集在咖啡廳。借著酒勁,他逐一揭開所有人的偽裝。奇洛夫得罪了他的朋友們,于是第二天大家惡作劇地給他送來花圈。收到花圈后奇洛夫回顧自己的人生,他感到生無可戀,決定自殺。最終,被朋友們救下來的奇洛夫冷靜下來,下定決心去打野鴨。
《打野鴨》的主題是什么?作者對奇洛夫的態度究竟如何?從這部劇誕生以來,這些問題就一直困擾著它的讀者。作品的主題要通過主人公的命運遭遇來呈現,梳理奇洛夫的情節線索,我們不免會陷入這樣的思考:奇洛夫的悲劇究竟是誰造成的?誰應該為奇洛夫的命運負責?是他人、社會還是命運?劇本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但是我們不難發現,奇洛夫的悲劇是他本身造成的,他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在清醒狀態下做出的選擇。《打野鴨》的矛盾沖突并不同于其他的傳統作品,它講述的不是人與人的沖突,也不是人與社會或者命運的沖突,而是人自身或者人與生活之間的矛盾。
在以人與生活的沖突為主題的作品中,我們找不到傳統戲劇中表現正反兩方沖突的故事情節,也沒有正反面人物,有的只是可悲可嘆可憐之人。作者并沒有給奇洛夫設置敵對方,他的生活看上去順風順水,稱心如意。他有大家所羨慕的一切,看到他自殺,他的朋友古扎可夫特別不理解:“到底出什么事了?怎么回事?你有什么不滿意?有什么不足的?你年輕,健康,有工作,有住宅,女人們愛你,高高興興地活著吧,你還需要什么?”[6](P283)是的,他還需要什么,這是他的朋友們永遠都弄不明白的問題,也是萬比洛夫要留給讀者的問題。
今天我們讀這部作品,依然會對奇洛夫感到熟悉。他玩世不恭,世故圓滑,可是又冷靜理智,對自己的行為感到不恥。他想改變現狀,卻又沒有能力從生活的漩渦中徹底擺脫出來,于是只能天天在口頭上喊著,去打獵,去打野鴨。“打野鴨”作為擺脫日常庸俗生活的象征,是奇洛夫在想象中對自己墮落生活的拯救。萬比洛夫在《打野鴨》中借助于奇洛夫的遭遇,表達了他對那些不滿于生活現狀,卻又沒有勇氣和能力做出改變的人們的嘲笑、同情和憐憫,而這也正是這部作品的主題。
表現人自身的矛盾以及人與生活之間的矛盾,類似的主題在契訶夫的多幕劇中很常見。可以說,《打野鴨》在主題意蘊上與契訶夫的多幕劇做出了跨越時間的呼應。也正因為如此,《打野鴨》讓萬比洛夫的作品超越了作者自身以及同時代作家中風行的“道德劇”的高度,具有了超越時空的藝術魅力,成為戲劇史上的經典。
二、萬比洛夫對契訶夫戲劇的發展
萬比洛夫的戲劇技巧極其嫻熟,其作品在繼承契訶夫戲劇藝術風格的基礎上,并不回避對戲劇性沖突和戲劇性場面的呈現。作品中精彩的戲劇場面不僅能把人物性格特征以及復雜微妙的人物關系清晰有致地呈現出來,而且大大增強了作品的觀賞性和劇場魅力。
《六月的離別》中的柯列索夫和校長列普尼柯夫構成了情節主線中最為重要的人物關系,作者安排這兩個人相遇在黑了燈的學生宿舍,柯列索夫并沒有認出列普尼柯夫,兩人互相抓住對方,扭打在一處。這種見面方式是后來二者之間矛盾關系的微觀寫照,同時也引發出戲劇懸念,充滿戲劇性。
《打野鴨》第二幕第二場,受盡委屈的加林娜在失去孩子之后,不想繼續生活在奇洛夫的謊言之中,她在咖啡館跟奇洛夫說出通信人的實情。奇洛夫卻利用父親剛剛去世的消息巧言如簧地讓加林娜心生內疚,改變了初衷。把加林娜支回家后,奇洛夫隨即與趕來的伊林娜卿卿我我,這一幕恰好被趕回來給他送雨衣的加林娜看到,傷心的加林娜放下東西悄悄離開了。在這個看似平靜甚至有些喜劇色彩的場面中,作者并沒有在加林娜再次上場后寫一場“大吵大鬧”的戲,而是將場面繼續下去,表現奇洛夫對伊林娜的欺騙。伊林娜看到了加林娜,奇洛夫冷靜地告訴伊林娜那個人是他的妻子,不過他們之間早就沒有感情了。奇洛夫輕松地騙過了伊林娜,讓她不再介意自己已婚的事實。這樣的場面安排不但符合人物性格——加林娜的隱忍善良、奇洛夫的無恥荒唐以及伊林娜的單純輕信,再一次清晰顯現在觀眾面前;而且更能從中看出萬比洛夫對戲劇場面的控制力:無言而去的加林娜內心的失望和痛苦,作者雖然對此不著一字,但觀眾卻完全能夠感受得到。這場戲不僅沒有因為編劇的控制而顯得拘謹松懈,反而絲絲入扣,張力十足。
萬比洛夫超常的劇作表現力也體現在《長子》當中,冒充長子的布西金與他的“妹妹”尼娜彼此心生愛意,布西金自知與尼娜不是親兄妹,然而尼娜卻并不知情,于是就只能克制自己的感情。在第二幕第一場,兩人聊起漂亮的鄰居女人馬卡爾斯卡婭,布西金告訴尼娜他喜歡馬卡爾斯卡婭,尼娜立即充滿醋意地說,她是個“老太婆”。馬卡爾斯卡婭的頭發是金色的,布西金說喜歡金發女郎,尼娜告訴布西金,馬卡爾斯卡婭的頭發是染出來的。布西金說他喜歡朝氣勃勃的馬卡爾斯卡婭,尼娜卻忍不住說自己簡直討厭她。布西金說他可憐這個孤孤單單的女鄰居,尼娜的回答是,我恨。聰明的布西金看出了尼娜的妒忌,故意激怒她,說要去追求馬卡爾斯卡婭。尼娜一反矜持的性格,威脅布西金說:“你敢走近她”[7](P143)。當布西金點破她的妒忌,說她在吃醋時,尼娜自己也被嚇了一跳,她辯解道:“當然,我就是吃醋,難道妹妹就不能吃醋?”[8](P143)布西金聽到尼娜的話,一時忘記了偽裝的身份,繼而又醒悟過來……一個小小的戲劇性場面,既詼諧有趣,又把兩人的微妙心理富有層次地揭示了出來。
如此生動有趣、引人關注的戲劇性場面在萬比洛夫的作品中并不少見,萬比洛夫在創作中既能深入挖掘人物內心,揭示豐富復雜的心理世界,又能夠營造出具有戲劇張力的場面和氛圍,這是他在繼承契訶夫戲劇傳統的基礎上所做出的發展,這種創作風格,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抒情性和象征性特點的同時,不失戲劇性和對觀眾的吸引力,而這對于劇作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畢竟能與觀眾進行溝通進而引發共鳴是每一個創作者的初衷和愿望,而戲劇性則是讓劇作家達成此目的的重要途徑。在此意義上,我們認為萬比洛夫的作品對于今天的話劇創作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1]何輝斌.戲劇性戲劇與抒情性戲劇[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2][4][5][6][7][8] [蘇]萬比洛夫.萬比洛夫戲劇集[M].趙鼎真、白嗣宏、童道明譯.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
[3]契訶夫精選集[M].李輝凡編選.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