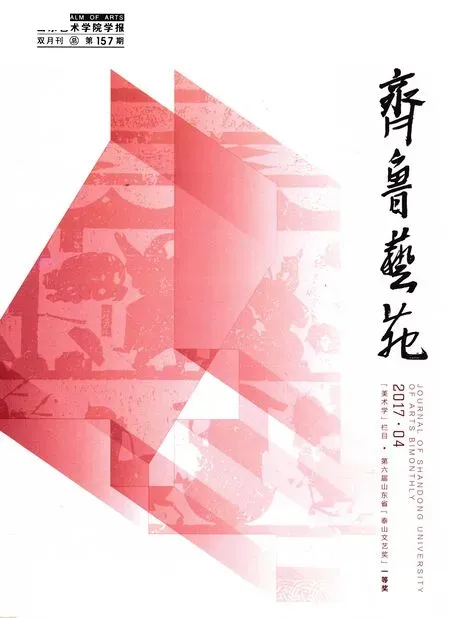芒福德對現代設計的反思
李青青
(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上海 200444)
芒福德對現代設計的反思
李青青
(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上海 200444)
劉易斯·芒福德作為世界級的文化巨匠,其研究領域十分廣泛,包括科技、城市、文化、藝術等方面。他常常因為建筑、城市規劃等方面的突出貢獻為中國讀者所熟知。實際上,他對現代設計也有著獨到而精辟的見解。他通過對城市、建筑、技術、文明的描述表達了他對現代社會、現代設計的獨特看法。他認為現代社會造就的生活環境存在著兩個極端:一是城市、建筑設計在縱橫向上的巨型化發展趨勢;另一個則是產品設計以及人類生存空間的精小化趨勢。芒福德對現代設計的反思與批判為我們理解現代設計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芒福德;現代設計;反思
劉易斯·芒福德*劉易斯·芒福德(1895-1990),美國著名城市規模理論家、歷史學家。作為世界級的文化巨匠,其研究領域十分廣泛,包括科技、城市、文化、藝術等方面。他常常因為建筑、城市規劃等方面的突出貢獻為中國讀者所熟知。實際上,他對現代設計也有著獨到而精辟的見解。他通過對城市、建筑、技術、文明的描述表達了他對現代社會、現代設計的獨特看法。他認為現代社會造就的生活環境存在著兩個極端:一是城市、建筑設計在縱橫向上的巨型化發展趨勢;另一個則是產品設計以及人類生存空間的精小化趨勢。芒福德對現代設計的反思與批判為我們理解現代設計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一、形:“巨大癥”
1.微觀:建筑的縱向發展
現代設計早期是通過建筑設計體現并蔓延到其他領域。芒福德對現代設計的關注也是從建筑開始的。在其作家生涯的前期,他著有許多建筑相關的論文與著作。他認為“建筑不像繪畫或詩歌,它的成型過程和結果都要服務于人類生活的目的。所以建筑首要責任是社會責任,幫助社會提高日常生活的品質。”[1](P183)可見,芒福德將建筑視為一種文化意義上的家園。然而,隨著現代設計在全球的蔓延,一棟棟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向世人展示著現代設計的權威。用芒福德的話來說,“他目睹了一幢幢摩天大樓拔地而起,組成雄偉軍陣,自海島尖頂開始雄赳赳一路行進直至新城的中心地帶。”[2](P187)芒福德把摩天大樓、工廠廠房、大規模生產以及城市向郊區的蔓延統稱為現代社會的“巨大癥”。這種追求體量、數量、規模的巨大化,讓生活于其中的人飽受折磨。芒福德對其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他認為這是一種物質誘惑,是一種對建筑、對城市的誤解。正如他在《棍棒與石頭》中試圖論述的理論一樣:“若妥善、正確理解,建筑就是文明本身,二者密不可分。文明又是什么呢?文明就是人類通過社會的人化過程……”[3](P186)而現代建筑卻將這種人文因素剝離,試圖建造一種“供人居住的機器”。
芒福德對現代設計造就的“巨大癥”最深刻的反思體現在他對摩天大樓的批判中。芒福德曾經生活的紐約城經過現代商業設計的洗禮,已經成為高樓林立的現代大都市,很多紐約人都滿懷欣喜的歡迎這種“建筑界的新事物”,高樓大廈在很多人眼里成為了城市發展的坐標,成為了美國進步的標志,“象征著國家和城市無法阻擋的上升前進勢頭”[4](P188)。而在芒福德眼里,“摩天大樓則是許多謬誤的主源”[5](P188)。城市太大、太擁擠、喧嘩吵鬧、快節奏都令生活于其中的人頭暈目眩。在他看來,“高層樓簡直算不上一種建筑,而是‘一種大批圈人、提高地價、大把摟錢的做法’”[6](P482)。在摩天大樓還是一種新生事物向全球蔓延的時候,芒福德就警覺到事態的嚴重,他認為千篇一律的高樓大廈將帶來一系列的城市問題,剝離人們對建筑家園的情感寄托,會影響甚至危害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在芒福德的年代,這些言論可能被認為是危言聳聽、杞人憂天,如今當我們再去回望這段歷史,我們會發現許多大城市甚至中國當今許多大都市的發展都已經或者正經歷著他當初的預言。
當然,芒福德對這些巨型化的大樓、廠房不是全盤的否定。他也承認建筑高層化是技術進步、城市發展不可避免的。他也推崇一些好形式的高樓,比如沙利文設計的一些摩天大樓,運用了現代技術、采用了新型材料,高大結實,為城市的大型車站、工廠等提供了所需的空間。芒福德還花筆墨褒揚過許多隱姓埋名的建筑師作品,他認為這些建筑作品能夠在現代化的思潮下,運用新材料并結合本土特色,具有時代和地域魅力。可見,他對現代建筑并不是持全盤否定的態度。
2.宏觀:城市的橫向蔓延
而從宏觀層面來講,芒福德對“巨大癥”的批判也是對工業城市無節制膨脹、蔓延的批判。芒福德一度認為城市應該是人類“愛的器官”、溫情的家園。然而由于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城市無限的膨脹,城市內部交通擁堵、人口爆棚,城市內部貧富懸殊。工人階級的生活處境越來越差,工業的發展一方面帶來了極大的物質滿足,另一方面有又迫使人們陷入了極大的痛苦之中:環境的惡化、資源的匱乏、交通擁堵、住房緊缺……
這種不斷蔓延的都市狀況,不斷追求巨大的物質增加和消費,在芒福德看來屬于“超大都市”階段*芒福德在其導師格迪斯影響下,將城市分為六個階段:原始都市、城邦、大都市、超大都市、暴虐都市、廢墟都市,前三階段屬于上升階段,后三階段屬于衰退直至死亡階段。,已淪為 “衰落中的城市”。而伴隨著世界大戰的威脅,芒福德看到這種衰落的速度和趨勢越來越快、越來越明顯,并已在世界各地逐漸蔓延開來,正如他所說“過度增長的城市,不再是孤立的現象或單純政治集中的象征,而開始成為主導的模式”[7](P264)。并且這種大都市的不斷蔓延還會帶來城市擴張的惡性循環,就像馬克思所認為的一樣:“城市愈大,搬到里面來就愈有利,因為這里有鐵路,有運河,有公路;可以挑選的熟練工人愈來愈多;由于建筑業中和機器制造業中的競爭,在這種一切都方便的地方開辦新的企業……花費比較少的錢就行了;這里有顧客云集的市場和交易所,這里跟原料市場和成品銷售市場有直接的聯系。這就決定了大工廠城市驚人迅速地成長。”[8](P301)所以說工業城市的無節制蔓延會不斷的陷入巨大癥的漩渦中,直到走向最終死亡。
芒福德對城市巨大化發展的批判不僅僅針對城市居民、工人階級的生存狀況惡化。由于芒福德生態學的立場,他對城市巨大癥的批判還指向城市蔓延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他認為 “城市與其周圍環境的這種密切聯系,不幸卻被現代人類瓦解著:他們計劃以種種受消費者歡迎的人工形式代替復雜的自然地形和生態聯系;這對他們自身是危險的。”[9](P12)近代工業城市環境污染嚴重,生態惡化,資源枯竭,芒福德曾經說過,“大都市蔓延區即生態災難區”。可見,芒福德已敏銳地發現,城市“繁榮”發展是以對“人類家園”破壞為代價。他認為這種發展模式從本質上是反人類的,它給人類生存環境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以至于在市中心想呼吸新鮮空氣、看蔚藍天空都成為一種奢望。“在這個世界里,玻璃、橡膠,玻璃紙完全地把他和禁欲的生活隔離開。大都市人最精彩的生活,就是離不開紙的生活”[10]。大都市人的生活已經完全被物質世界禁錮了。“世界上有些地區原有的宜人的生活方式在‘向四面八方蔓延的城市’(laville tentaculaire)的沖擊下受到損害。”[11]
芒福德認為,城市原本作為人類生存的場所、心靈的家園,作為人生的大舞臺,如今卻因為無休止的城市擴張,人們豐富多彩的生活因高昂的地價、高昂的交通延誤費、工人缺乏保障、資源存貯匱乏,環境污染而變得越來越沒有生氣。
二、質:“小而精”
芒福德洞察到:在現代社會中,與建筑設計、城市規模巨型化相對的還有另一個極端,即產品的精小化。根據芒福德《技術與文明》一書對 “小而精”的描述,我們可以發現:狹義上的“小而精”主要指產品外形的精細化、迷你化;而廣義上的“小而精”則是指基于現代科學技術、生物學知識、人體知識等,實現技術與設計的統一,最終達到產品質量的精致化。然而,芒福德對“小而精”持一種什么態度?從其相關描述中,我們或許能感受到,他對這種產品贊許背后略有幾分擔憂。
1.外在表現:“小而精”
芒福德所謂的“小而精”,與今天我們所說的“迷你化”相類似。而“迷你化”主要是指產品外觀的小巧化、質量的輕薄化, “小而精”在此基礎上還暗含了一種品質的精致化。
這種“小而精”的趨勢,在古生代和新生代技術時期*芒福德在《技術與文明》一書中將技術史分為三個時期:始生代技術時期(1000-1750);古生代技術時期(1750-1900);新生代技術時期(1900至今)的對比中尤為明顯。芒福德發現,古生代時期對體量的重視——大就是優,多就是好——到新生代技術時期就轉變為“很少含量卻極其重要”。這個時期的產品開始關注微小的力量,從追求數量到追求質量,開始意識到形狀的重要性。要知道“古生代技術不認為有可能通過改善形狀而增加效率,只相信增加功率或增大尺寸”。[12](P225)
當然,在新生代技術時期,這種“小而精”的趨勢通過另一種形式的對比而更顯突出。20世紀的世界發展飛速,在芒福德看來:一幢幢高樓大廈拔地而起,一座座城市不斷向外蔓延擴張,社會生產規模不斷增大的另一面;還有另一類產品表現出量小而少、質精而輕的品質。這類產品,一般都是運用了新型材料,外觀小巧,質量輕薄而精美,是一種新生代生活的代表,也是新生代新技術和新材料的體現,與那些千篇一律的劣質批量產品相比起來(盡管“小而精”的東西也是批量化工業產品,但其新穎的樣式和新生代的隱喻造就了其獨特性),更加受人歡迎。
然而,還有另一種形式的“小”比較令人堪憂,因為它缺少了“精”的品質。首先是城市空間越來越大,高樓大廈越來越多,而人類的居住空間卻越來越擁擠、狹窄。其次表現在,人類控制、征服自然環境的能力越來越強,而人類所獲取的宜居環境卻越來越少。再者,人類利用能源、開發資源的手段越來越多,而人類能夠利用的能源卻越來越匱乏。以及,機器生產的效率越來越高,工人的閑暇時間卻越來越少……20世紀出現種種“大與小”、“快與慢”、“多與少”的悖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越演越烈,芒福德通過對城市的走訪、對社會生活的觀察,目睹了工業化進程、城市化發展的二重性。他思辨地看待20世紀的現代化進程,通過現代設計(畢竟設計是關乎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吃、穿、住、行)給人類生活帶來的巨變。這種“小而精”的趨勢在他眼里有其產生的深刻動因。
2.內在實質:技術與設計的統一
正如芒福德所說:“體積小重量輕是新生代技術時期的品質。”[13](P207)這種新的品質究其動因,是由于社會的發展、科技的進步,產品設計的多樣化、個性化的技術壁壘慢慢減少。這就使得產品設計的小型化成為了可能。在芒福德的觀點里,產品設計的迷你化趨勢是科技與設計結合的產物。由于技術的突破,產品設計的多種形式成為可能;而由于新材料的應用,產品不僅體量變小、質量變輕,而且其材料本身就是一種現代的宣示。例如,由于電力的廣泛應用帶來了制鋁業的風生水起。而鋁又是一種極為輕巧的材料,具有易塑性,因此“輕巧的鋁也是一種挑戰,它要求更細致、更準確的設計。”[14](P201)以鋁為材料的設計產品越來越多,以其輕便的重量,高科技的外形,現代生活方式的隱喻迅速占領現代家庭。產品的設計開始重視微小的力量,不再像古生代技術時代以規模代替效率——更多意味著更好,更大意味著更強,如今變成了“很少含量卻極其重要”。
芒福德不僅關注產品設計“小而精”的趨勢,并且將設計的這種趨勢放在更為廣泛的社會背景中去考察,結合科學、技術以及消費等問題來考察設計問題。產品 “小而精”的趨勢是設計與新材料、新動力、新科學等融合的結果。在《技術與文明》這本書中,芒福德還專門論述到生物學對設計的影響。他說“從生物界還傳來了古生代技術頭腦完全陌生的概念:形狀的重要性。”[15](P224)例如對飛機的改進設計時,由于對飛機尾部產生的空氣阻力的研究,其形狀的設計才完全具有了技術上的意義,而不只是簡單的外殼造型。同樣的原理也運用在火車、汽車等機械設備的設計之中,在不增加功率的情況下提升速率——注重效率和質量,這也是設計“精”的體現。可見,在新生代時期,“小而精”是由于科技的進步才成為了可能。當然,要真正完成“小而精”的呈現,還不僅僅是科技、技術的進步能造就的,這就需要設計的融入。芒福德很早就意識到這一點,他指出,設計有利于將抽象的技術轉變為具象的物品,而抽象的技術、新的材料又讓設計的多樣化成為可能。可見,技術與設計這種雙向的關系,很早就為芒福德所關注。他在《技術與文明》一書中論述過機器體系對審美的影響,這也隱含了工業化社會、批量生產等對設計的影響。
從某種層面上看,芒福德在當時就已經相當重視設計與現代科學、技術之間的緊密關系。并且將其納入消費社會的大背景中進行考察,探討消費的合理性,在芒福德看來,這種 “小而精”的產品不僅是為了消費者追求個性化的表現,更是一種身份認同感的找尋,試圖通過這一類產品來進行身份定位。當然這種多樣化的設計,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消費,為造就一個“消費社會” 推波助瀾。因此他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認為這是科技與設計完美結合的表現,也是人們個性化需求的滿足,但是另一方面又助長了炫耀性消費的勢頭,造成了資源浪費。
三、情:對功能主義的修正
芒福德在其相關著作中談論過他對功能主義的態度,這也是他關注現代設計最直接的體現。芒福德小時候居住的房屋里布滿了維多利亞式的復古裝飾,房屋狹小擁擠。他從小就對這種建筑及建筑空間充滿了厭惡,因此當芒福德看到現代建筑簡潔、干凈利落的立面和空間,有一種如沐春風的感覺。他認為現代設計以其簡單明了、樸素大方等特征,將會成為社會有序發展的基礎;并且大膽宣稱“形式追隨功能”,形式簡潔、功能優先的設計才是未來建筑設計的走向。
但事實也證明芒福德并不是功能主義的盲目崇拜者,他擁有辯證的世界觀。他雖被勒·柯布西耶等人的設計理念所吸引,卻也不贊同其中的很多觀點。他反對勒·柯布西耶提倡的“房屋是供人居住的機器”,認為建筑是一種融合了當地人的風俗習慣、風土人情、區域文化的家園。他深受格迪斯有機論思想和霍華德花園城市理論的影響,“堅決反對將功能效果與機械效果混為一談”[16](P195)。他承認機械是工業社會無可取代的表現形式,但并不是現代文明的全部。芒福德站在人類文化的高度對功能主義進行了深刻的解讀。試圖厘清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一種誤解——功能與機械的混淆。他通過對形形色色的建筑不斷地走訪考察,認為合理的功能主義思想是包含人類的全部需求、思想、理想,即“除了物質的、生物的需求,也要包括精神心理的、超驗主義的、形而上的東西”。[17](P195)
芒福德在討論機械的設計問題時也提到了形式與功能的關系,從論述中可以看出他比較贊同沙利文的“形式追隨功能”,卻又超越了這種單純的追隨;推崇賴特的“形式與功能是一回事”的觀點,卻又不完全茍同。他認為,在設計一個產品時,可能由于成本的考慮,往往會在基本功能達到的時候就停止了美學上的完善。“也許在這個時候每個機械方面的因素都被充分考慮了,但由于沒有認識到人性方面的需求,還是造成了一種不完善的感覺。”[18](P309)他認為那些老式的電話、汽車、飛機,到處都是拼湊的痕跡,是一種設計不成熟的體現。成熟的設計應該是一種功能與形式兼顧,“形式由功能決定,形式突出功能,形式使功能具體化、明確化,使功能看起來更加真實”[19](P309)。他還提醒設計師和生產商,設計一個完美的產品,為了解決成本,不應該犧牲產品的美學意義,而是將功能與美學融合在產品生產的整個周期過程中。值得指出的是,在芒福德的觀點里,美學是與情感掛鉤的。這在他對有機建筑的維護中可見一斑,他認為有機建筑之所以被稱為有機,是因為“他體現了功能與情感這兩種人類需求的合理妥協”[20](P196),是一種人性化的功能體現。
當然,最能體現芒福德這種溫情功能主義的還是他關于建筑、城市的論述。他認為建筑對生活的體現就是其生命力所在。他說,“每一棟建筑、樓房屋宇都保存著當地社區諸多民眾生活的記錄和精神財富。”[21](P184)“每個時代的人都在他們建造的建筑物里留下了自己的傳記。”[22](P802)
總之,芒福德關于功能主義的解讀實際是對功能主義的修正,他將功能主義與形式、美學、情感等問題結合論述,給冷漠的功能主義注入了人性的、情感的溫度。這對我們今天的設計依然有有著借鑒和指導意義。
四、小結
芒福德對現代主義設計語境下的現代社會的反思是從外形的觀察開始,進而關注品質問題,最后深入到對情感、審美等問題的思考:由表及里,由末到本。他將現代建筑、城市擴張置于一個廣闊的社會背景中,并聚焦于現代工廠、辦公樓甚至是生產規模的“巨大癥”和產品設計的 “小而精”,在對現代設計尤其是這兩種極端現象的反思與批判過程中,芒福德也始終關注功能主義的發展,并將狹隘的功能主義結合美學和情感,提出了他認為的合理功能主義,這對功能主義理論的補充與完善有一定的意義。他關于現代設計的反思,對當代設計的發展也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1][2][3][4][5][6][16][17][20][21][美]唐納德·L·米勒.劉易斯·芒福德傳[M].宋俊嶺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7][10][11][美]劉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M].宋俊嶺等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3.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9][美]劉易斯·芒福德.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M].倪文彥,宋俊嶺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9.
[12][13][14][15][18][19][美]劉易斯·芒福德.技術與文明[M].陳允明等譯.北京:建筑與工業出版社,2009.
[22]Lewis Mumford,“The Modern City,”in Talbot Hamlin,ed. ,Forms and Functions of Twentieth-Century Architecture,vol.4,Building Typ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2).
(責任編輯:劉德卿)
10.3969/j.issn.1002-2236.2017.04.017
2017-01-15
李青青,女,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設計理論研究。
J50
:A
:1002-2236(2017)04-008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