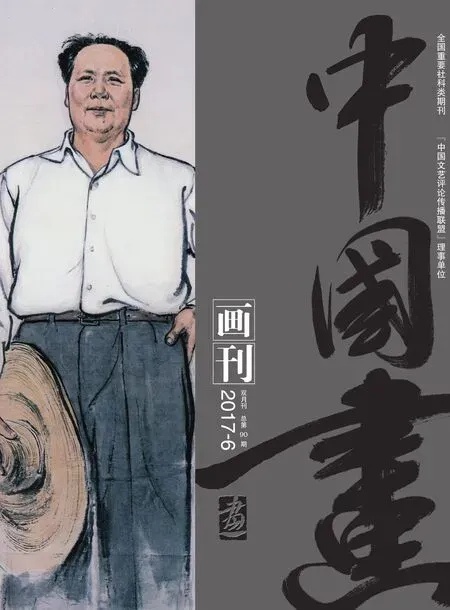卷首語
今年似乎成了我們業界先賢大師的“血拼”之年——從南至北風生水起間有點目不暇接,讓趨之若鶩的吃瓜群眾翹首引頸而疲于圍觀,頗有一番盛世崇藝、文化復興之態勢……
實則也未必——這些山海般的圍觀中,又有幾人能讀懂大師?絕大多數只不過又一次佐證了國人的陋習通病——“特好奇”“湊熱鬧”“好盲從”以及“附庸風雅”。前些日在北京故宮展示《千里江山圖》手卷,我從微信上得知盛況空前得不可思議——為了那“驚鴻一瞥”居然要排上六七個小時的隊……我在微信上不免調侃:恰恰我們的前輩大師,幾乎都沒有機會親眼目睹,不照樣高屋建瓴地成為了一代宗師?況且如今的印刷技術先進,比原作還要清晰可讀,在家平心靜氣地細細品味,遠比湊這個熱鬧獲益多多。
如今的業界直面先輩大師的傳世巨著還會產生多少反省?幾分的知恥和些許的懺悔——我們早已忘記了怎樣“照鏡子”“整衣冠”,換言之,在一面面明亮的鏡子面前我們早已麻木不仁或視而不見,已然蒙塵在恬不知恥的沾沾自喜間……難怪常常會有人哀嘆:我們的時代出不了大師……那么當下業界生態的持續惡化無疑是罪魁禍首——哪怕是有幾株好苗子也難免被糟蹋了,就是能讓先賢們再“轉世”,想必也是難逃厄運的……
在一個笑貧不笑娼的年代——萬眾可以無恥地叫馬云“爸爸”;癲狂追著王思聰喊“老公”——于今的“錢”不但照樣能讓“鬼”聽使喚,還會讓萬眾的道德良知淪喪殆盡,讓起碼的做人節操碎成一地!
我們業界已和銅臭味十足的商界如出一轍——前些年被我針貶過的丑陋和不堪,眼下已有愈演愈烈之態和變本加厲之勢——“皇帝新衣”“指鹿為馬”“掩耳盜鈴”乃至“欺世盜名”等等,居然已成為了今天業界的一種新常態……而隨著銅臭不斷地銹蝕,我們業界蛻變得愈加沒有良知和原則;愈加沒有主張和個性;愈加浮躁和偽善——上上下下表面都你好我好大家好,層層吹噓,到處捧場,一團和氣,目的只有一個:大家都是出來混口飯吃的……
我一直存疑:中國真的需要這么多書畫家嗎?而今業界頗似佛教界——許許多多生性慵懶和偷奸耍滑者,紛紛挖空心思地擠進來混飯吃,業已將原本相對矜持清凈的界別,折騰得魚龍混雜而烏煙瘴氣,不恥的行徑勾當比比皆是,令人不堪入目……如今在業界,似乎不上躥下跳;不招搖過市;不賣弄風騷;不侍媚權貴就會進退維谷——善良已得不到善侍,把原本就為數不多的厚道守望者逼得走投無路——“劣幣驅逐良幣”的惡作劇不斷地上演,這無疑是一個時代的不幸和悲哀……
因此,我一直認為:一旦藝術被蒙上了濃烈的功利色彩,被裹挾成為功利主義的載體和附庸,不但失去了其原本的價值和意義,還會散發出遠比銅臭更令人作嘔的酸腐味,正所謂的:雖存若殆也!
在當下人人為了點蠅頭小利,都不愿也不敢講真話的偽善大背景下,秉性使然,我還是寧愿選擇做那個天真的“小男孩”——至少我知道自己還沒有行尸走肉……
2017年歲末感懷以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