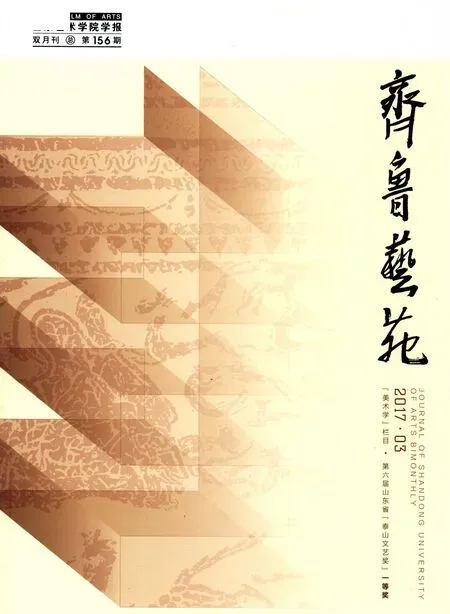樣板戲與文革美術的政治同構與主題共生
穆海亮
(河南大學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
樣板戲與文革美術的政治同構與主題共生
穆海亮
(河南大學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在相同的創作理念統攝之下,樣板戲與文革美術的題材選擇與主旨傳達如出一轍,形成了政治功利的同構與主題意蘊的共生。政治功利是二者共同的“合法性”基礎,這決定了題材與主題的政治化單一及其對現實的遮蔽,也必然伴隨著個人崇拜的審美幻象與文藝創作的斗爭思維。不過,由于樣板戲與文革美術對表現對象的選擇略有差異,表現時代的視角也存在不同,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二者藝術面貌的差別以及在文革之后的不同歸宿。
樣板戲;文革美術;政治同構;主題共生
從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是自然而然的,它是此前“十七年”甚至自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0余年來,中國大陸政治、思想、文化各層面醞釀、演進、集聚而成的必然結果。在文藝領域,從“十七年”到文革,完全沒有從文革到新時期那樣的明顯斷裂,而只是一步步將毛澤東文藝觀念推至頂峰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盡管文革時期的不同藝術門類存在表面上的千差萬別,但其精神實質、美學原則、創作理念、表現形式則是高度一致的。正是從這個視角切入,我們能夠更加清晰地看到樣板戲與文革美術之間那千絲萬縷、甚至“血肉相連”的關系。在相同的創作理念統攝之下,樣板戲與文革美術不僅在創作原則的“三突出”、形象譜系的“高大全”、審美風格的“紅光亮”方面高度一致,而且其題材選擇的政治預設、主旨呈現的斗爭思維也如出一轍,因而形成了政治功利的同構與主題意蘊的共生。
一、樣板戲與文革美術共同的“合法性”基礎
眾所周知,樣板戲之所以被定為“樣板”,絕不僅僅是江青等人直接干涉文藝創作的文化事件,而是自始至終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圖,是服務于文革時期的政治斗爭需要的,這是其在當時得以存在并“獨占鰲頭”的唯一“合法性”基礎。《人民日報》首次明確將現代京劇《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奇襲白虎團》《海港》、現代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交響音樂《沙家浜》向社會公布為第一批八個樣板戲時,就強調了其在政治斗爭中的重要意義:“在戲劇舞臺上,大破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戲劇樣板,大立無產階級的革命戲劇樣板,是一場尖銳的階級斗爭,是一場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粉碎資本主義復辟的斗爭。”[1]當“樣板戲”這一稱謂的正式提法首次在《紅旗》雜志的社論中出現時,其鮮明濃烈的政治色彩就更加展露無遺:“它們不僅是京劇的優秀樣板,而且是無產階級文藝的優秀樣板,也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各個陣地上的‘斗、批、改’的優秀樣板。”[2]即使樣板戲自身確有舞臺藝術(尤其是技術)層面的重要突破,但毫無疑問,其在藝術上的任何成就都是以鮮明的政治功利性為前提的。
與樣板戲一樣,文革時期的美術作品不管最終的藝術效果是成是敗,在當時都是服務于政治斗爭需要的,帶有明顯的極左政治特征。不管是“風雷激蕩”的紅衛兵美術,還是規模浩大的工農兵美術,不管是對“紅司令部”和“紅太陽”的歌頌,還是對所謂“文藝黑線”的批判,無一不是極左政治的產物及其重要表征。即使是代表著文革美術創作水平的專業美術家筆下的時代畫卷,其實也都是以明確的政治理念為先導,以毛澤東文藝觀念為唯一“指南”的藝術制作。所以,當時將樣板戲鋼琴伴唱《紅燈記》與樣板畫《毛主席去安源》(油畫,劉春華)同時推出,是絲毫也不奇怪的。《光明日報》率先稱“油畫《毛主席去安源》是‘洋為中用’的又一樣板,是美術史上的新篇章”[3]。《文匯報》則直接稱贊“這幅油畫,和鋼琴伴唱《紅燈記》一樣,是值得廣大文藝工作者學習再學習的革命文藝又一樣板”[4]。其背后都是政治意圖在起決定作用,尤其是江青本人的政治意圖。在雕塑領域,文革爆發前就已完成的《收租院》在此時被官方確立為樣板,與京劇改革、芭蕾舞劇改革、交響音樂改革等方面出現的成果相提并論,被認為“都是實踐毛主席文藝路線的光輝樣板,都是文藝革命化、大眾化、民族化的一個大飛躍”[5]。而文革雕塑的代表之作《農奴憤》幾乎就是《收租院》的翻版,其創作者為了克服“無沖突論”“寫真實論”等“資產階級”藝術觀念的影響,還特意集中學習了樣板戲《杜鵑山》在尖銳的矛盾沖突中塑造英雄典型的經驗。[6]
藝術作品理應具有相對獨立的審美價值,其可以承擔“載道”的文化功能,也可以在精神層面與政治展開平等對話;但是,一旦藝術作品從創作初衷到最終目的都甘作政治附庸,尤其是成為極左政治附屬物之時,藝術的價值就遭到異化,命運也不由自己掌控了,既有可能因迫切地迎合了政治的需要而風光無限,也有可能因政治的風云突變而遭到歷史的嘲弄。樣板戲和文革時期的多數畫作都在文革結束后體驗到冰火兩重天的落差,更有甚者,就在文革當中,就已有無數作品經歷過這樣的尷尬。在江青的指示下,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毛遠新命令遼寧省美術創作組創作歌頌遼沈戰役的系列畫作,沒成想,即將大功告成之時,“九·一三事件”突然發生,這些畫作自然就永遠難見天日甚至胎死腹中了。文革期間有過類似遭遇的畫家、戲劇家及文藝作品實在數不勝數,其中的榮辱沉浮,又豈是簡單的“成也政治,敗也政治”所能一言以蔽的?
二、題材與主題的政治化單一及其對現實的遮蔽
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政治服務,政治立場決定藝術品格,這是文革文藝活動的基本出發點。這就必然導致藝術創作的題材單一,主題先行。表面看來,樣板戲貌似取材廣泛,涉及不同的歷史時期,刻畫了不同階層的人物形象。《紅燈記》表現工人階級的革命斗爭,《杜鵑山》《白毛女》《紅色娘子軍》反映貧苦農民的階級反抗,《沙家浜》《平原作戰》表現抗擊侵略者的英雄壯舉,《智取威虎山》刻畫解放軍追剿土匪的頑強與機智,《奇襲白虎團》正面描寫了抗美援朝,《海港》《龍江頌》則是歌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工農奮戰。但實際上,這些作品都秉持著相同的理念,遵循著近似的套路,“光明”與“黑暗”截然對立,歌頌與批判涇渭分明,“大破”與“大立”交相呼應,其實質無非是歌頌共產黨領導革命和建設的重要業績,歌頌毛澤東思想在從前線到后方、從革命到建設各個領域的全面勝利,以及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工農兵勇往直前、戰斗到底的壯志豪情。作為“光明”的對立面,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等一切“黑暗”勢力都是作為備受撻伐的對象出現的,其唯一的歸宿只能是走向滅亡。這樣的題材看似紛繁多樣,實則是統一模式的自我復制;這樣的所謂“創作”就嚴格落實了由江青授意、于會泳提升到理論高度的“主題先行”。
文革美術的題材及主題呈現出與此極為相近的單一面貌。不僅數量巨大的紅衛兵美術是以運動的方式直接迎合文革的政治斗爭,對所謂“黑畫”“黑司令部”的批判和丑化極盡能事,對領袖及“紅司令部”的贊頌不遺余力;而且絕大多數的工農兵及知青題材作品都是服務于鞭撻舊社會、歌頌新時代的宏大主題。《大慶工人無冬天》(中國畫,趙志田)、《虎口奪銅》(油畫,吳云華)集中展現了工人階級不畏艱辛促生產的精神風貌,《老書記》(農民畫,劉志德)、《戶縣新貌》(農民畫,董正誼)刻畫了社會主義農村新風尚,《生命不息,沖鋒不止》(水粉畫,何孔德、嚴堅)、《提高警惕 保衛祖國》(油畫,關琦銘)、《為我們偉大祖國站崗》(油畫,沈嘉蔚)都是表現革命軍人保衛新中國的戰斗豪情,《春風楊柳》(油畫,周樹橋)、《學耕》(油畫,何紹教)則為規模空前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唱起了贊歌。就連原本離政治及斗爭最遠的山水畫作,其實也被統攝在了發揚革命傳統、贊頌社會主義建設新風貌的時代主題中來了,《遵義曙光》(中國畫,林豐俗、陳洞庭、梁世雄)表達了對革命圣地的神往,《錦繡江南魚米之鄉》(中國畫,錢松嵒)是對新中國農業豐收的贊美,《喜看群山多一峰》(中國畫,薩其晴、柴本善、楊南榮、賀定龍)、《萬水千山只等閑》(版畫,酆中鐵)其實只是借山水景色表達對新中國建設之功的贊頌。
題材與主題的政治化單一必然導致作品的虛假化,其表現生活與表現人的真實性被徹底泯滅了。盡管“源于生活”是當時被捧得很高的創作口號,但其實創作的源泉并非來自于真正的生活,作品中所呈現出來的只是為當時政治所需,被彌漫于文革乃至整個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烏托邦理念所過濾過的“生活”。作品刻畫的人物也絕非真實的個體,而只是抽空人的本質以傳達既定政治觀念的標簽和符號。就像我們不可能在樣板戲《海港》《龍江頌》中看到當時工農實際遭遇的生活苦難和精神困境一樣,我們也不可能在表現農村題材的《公社魚塘》(農民畫,董正誼)、《送糧路上》(農民畫,周文德)、《戶戶有存款》(農民畫,劉惠生)等畫作中看到當時真正的農民生活。當畫家在《我愛第二故鄉》(版畫,張兆鑫)、《送子務農》(中國畫,全太安)、《再做山里人》(年畫,徐福根)中極力表現知青下鄉的和諧、神圣與崇高時,這場運動背后可能存在的不公、迫害、荒謬、甚至給無數家庭帶來的撕心裂肺之痛則遭到了無情的漠視和遮蔽。
三、個人崇拜的極端化及其審美幻象
極左政治制約下的文藝活動自然而然地裹挾著以個人崇拜為主要表征的現代迷信和以階級斗爭為核心的斗爭哲學。樣板戲中的英雄人物無一例外都是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先進典型;那些由“中間”走向“先進”的人物,毛澤東思想及其人格的偉大感召力是他們發展進步的唯一精神力量;劇中人物陷入困境或精神迷茫之時,為他們鼓舞精神、指明方向、撥云見日的總是毛澤東的偉岸形象、崇高境界及其思想指引。《智取威虎山》中楊子榮能夠智勇雙全里應外合,一舉殲滅座山雕,是由于毛澤東思想賦予他敢于斗爭的勇氣和善于斗爭的智慧;《杜鵑山》中柯湘之所以比雷剛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就是因為她更早、更直接地接受了“毛委員”的思想指導;《奇襲白虎團》中的嚴偉才、《海港》中的方海珍、《龍江頌》中的江水英一遇到挫折,就會想起毛澤東的諄諄教導,于是他(她)們馬上兩眼放光,熱情滿懷,鼓起前進的勇氣,并找到前進的路徑。與此相應,毛澤東語錄經常在樣板戲中吟誦回響,旭日東升、朝霞滿天、《東方紅》背景樂等就成為樣板戲反復出現的重要舞臺意象。
文革美術中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同樣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毫無疑問,當時絕大多數美術作品都是在毛澤東文藝觀念統攝下“創作”出來的,同時又反過來支持了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和頌揚;也不用說,那些少數較能體現畫家獨特感悟的美術作品在完成之后,也必須以“創作談”之類的文字做出向毛澤東思想主動靠攏的姿態,才能獲取存在的合法性。單看文革期間問世的種類繁多、數量幾達天文數字的毛澤東肖像畫、雕塑、像章,就堪稱人類藝術史上空前絕后的景觀。根據有關研究,毛澤東像章制造數量達80億枚之多,甚至被稱為“世界九大奇觀”[7](P36-37)。文革前期最著名的宣傳畫《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澤東思想》(王暉)幾乎影響了整整一代人,而年畫《萬物生長靠太陽》(謝志高、胡振宇)那種以太陽來比毛澤東的做法成為文革美術的通用語匯。
然而,當毛澤東及其思想被神化為一切力量的源泉時,樣板戲與文革美術其實都出現了一個連江青們也沒有意識到的巨大悖論。江青們煞費苦心地在樣板戲舞臺上塑造“高大全”的“無產階級英雄典型”,但實際上這些“英雄”無一不籠罩在毛澤東思想的光環之下,他們自身的精神品格和意志品質被視為是毛澤東思想在其身上的靈光閃現,這樣不管他們表面上看起來多么“高大全”,其實際上的“英雄”成色都并非自足完成的,他們之所以呈現出“英雄”的面貌,唯一的理由就是要印證毛澤東思想的戰無不勝。而一個幾乎與樣板戲完全一樣的悖論也出現在文革美術中:當美術工作者極力參與甚至引領對毛澤東的造神運動,將其塑造為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象征能指時,美術作品中的毛澤東與其說是一個藝術形象,毋寧說已成為被意識形態完全抽空了實體性存在的虛空符號和審美幻象。
四、文藝“創作”的斗爭思維
在樣板戲中,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有一個集中的展示模式,那就是將毛澤東提出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視為創作的金科玉律。從作品的情節模式看,樣板戲處處彰顯著斗爭思維,甚至要求每一個細節、每一段唱腔都要體現“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斗爭”。如果說,《紅燈記》《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沙家浜》這樣的革命戰爭題材將敵我矛盾作為主線、將階級斗爭作為主題還有其合理性及基本的戲劇性的話,那么,在《海港》《龍江頌》這樣的建設題材中,也要根據毛澤東思想的指示,人為地加上一條揭批潛藏的階級敵人(錢守維、黃國忠)的線索,就顯得十分虛假了,這是對藝術作品完整性的極大損害。
從創作原則看,江青等人宣稱“搞戲就是搞階級斗爭”,作品的創作和修改過程本身都要體現階級斗爭的意識。經常被人提起的例子就是從《蘆蕩火種》到《沙家浜》的修改。《蘆蕩火種》是以阿慶嫂作為核心,其情節主線是地下斗爭,“有其內在的邏輯性和自在的戲劇性”[8](P217);修改后的《沙家浜》生硬地將郭建光提升為一號人物,突出的是正面武裝斗爭。但由于郭建光身上并無多少戲劇性可言,所以只好打補丁式地加上唱段和武打,并在結尾處將原本富有戲劇性和傳奇色彩的喬裝改扮智取胡傳魁,改為由郭建光帶人正面打進去。這樣的做法不僅未能改變郭建光形象干巴、說教、概念化的缺陷,而且還使原作的生動性和完整性遭到嚴重破壞。這樣非藝術(甚至反藝術)的修改是江青遵循毛澤東的意見強制要求的,藝術問題背后其實是政治問題。根據王彬彬的研究,由于1949年之前的地下斗爭主要由劉少奇領導,黨的正面武裝斗爭主要由毛澤東負責,所以《沙家浜》的修改“貫穿著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也就是江青所說的,突出阿慶嫂還是突出郭建光“是關系到突出哪條路線的大問題”。與此類似,《紅燈記》同樣經歷過從表現地下工作到突出武裝斗爭的修改過程,而且把故事背景從劉少奇曾擔任省委書記的滿洲改到了華北,也是出于同樣的政治原因:“怎樣對待和處理城市地下工作和農村根據地武裝斗爭的關系,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一個分水嶺。”[9]
就文藝“創作”的斗爭思維來看,文革美術與樣板戲如出一轍。一方面,絕大多數美術作品的表現主旨充溢著無處不在的階級斗爭意味。不僅《農奴憤》《紅衛兵贊》這樣直接反映斗爭史的雕塑作品是如此,直接批判打倒修正主義、走資派的宣傳畫作是如此,就連原本表現婦女兒童日常生活場景的美術作品也要貫徹“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最高意旨。《螺號響了》(油畫,邵增虎)是文革期間帶有典型廣東地域色彩的“漁港”題材的代表作之一,畫作表現的是夜幕下的海邊漁舍,一個嬰兒趴在母親背上酣然入睡。突然螺號聲響,遠處的男男女女背起長槍飛奔向前,這位年輕的媽媽來不及放下背上的孩子,抓起鋼叉沖出門去,她步履堅定,面色凝重,干練果敢,大義凜然。這樣一個原本可以表現得浪漫、溫馨的生活場景也被賦予濃郁的戰斗氣息。《處處崗哨》(中國畫,戴明德)表現春意蔥蘢的時節,一個七八歲的小姑娘在上學途中發現敵情,第一時間趕來匯報。她目光犀利,手指前方,嚴肅沉著,機警老練。《如果敵人從那邊來》(中國畫,單應桂)也是表現類似題材,正在挖坑埋雷的兒童面色凝重,聆聽著民兵的講解,警惕地注視著民兵手指的方向。這些作品中孩子們的童真童趣已蕩然無存,只是作為“階級兄弟”加入到全民戒備的行伍中來,這是真正的所謂“處處崗哨”了。
另一方面,美術作品背后的政治博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階級斗爭的表征。《毛主席去安源》堪稱文革美術的奇跡和“中國油畫的神話”,其以超過9億張的印刷量“成為世界上油畫印數最多的一張”[10](P101)。而該畫之所以能被江青欽定為“樣板畫”,不單單是由于其在藝術技法上的某些創新,更重要的是其承擔了表現兩條路線斗爭的政治功能。1961年中國革命博物館展出了《劉少奇和安源礦工》(油畫,侯一民)并產生重大影響;文革爆發后,劉少奇從公認的工運領袖變成了“地地道道的工賊”,《劉少奇和安源礦工》也就成為“劉少奇及其黨羽利用美術陣地瘋狂地進行篡黨篡軍篡政的反革命復辟活動”的罪證,于是舉辦“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亮了安源工人運動”畫展、塑造毛澤東工人運動的卓越領袖形象就成了極為重要而迫切的政治任務,為這次畫展而作的《毛主席去安源》首當其沖地就成為顛覆“反革命黑畫”《劉少奇和安源礦工》的武器。在這樣的背景下,畫作本身的藝術水準是次要的,《毛主席去安源》的根本意義在于,它“不是一幅普通的油畫,而是一把刺向中國赫魯曉夫心臟的利劍,是一首毛主席革命路線戰勝中國赫魯曉夫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贊歌”[11]。這樣的創作邏輯,跟樣板戲《沙家浜》《紅燈記》的修改是完全一致的。也正是出于同樣的邏輯,《喚起工農千百萬》(油畫,方增先)盡管同樣以嚴謹的造型、緊湊的結構、獨到的風格塑造了毛澤東的偉岸形象,完全符合當時的宣傳口味,盡管該畫將國畫的虛實之法、靈動之趣十分融洽地融入了油畫創作,甚至比《毛主席去安源》更能體現“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原則;但由于在凸顯毛澤東的工運貢獻、揭批劉少奇的“工賊”面目方面不及《毛主席去安源》來得直接,它也就終究未能享受《毛主席去安源》的待遇,而淪為“流產的樣板”。
五、對象選擇的差異及藝術歸宿的不同
文革美術與樣板戲的思想主旨和政治功用高度一致的同時,它們對表現對象的選擇略有差異,表現時代的視角也存在不同,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二者藝術面貌的差別以及在文革之后的不同歸宿。
其一,文革(尤其是文革前期)美術所歌頌的“光明”、所批判的“黑暗”與樣板戲的表現重心有所偏離。樣板戲歌頌的主要對象是中共的革命史和建設業績,文革美術歌頌的重心是“紅司令”及其領袖,尤其是對文革自身的極力吹捧;樣板戲批判的主要對象是站在中共及“勞苦大眾”對立面的日帝、美帝、漢奸、地主惡霸、國民黨反動派等等所謂的“階級敵人”,而文革美術中“階級敵人”的主要范疇,已經更多地指向了中共內部高層的路線之爭,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所謂黨內“走資派”,以及“九·一三事件”之后的林彪,等等。這在文革初期主要由造反派及紅衛兵舉辦的多次展覽中體現得極為鮮明。單在1967年就舉辦過一系列類似的展覽,如2月的“砸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漫畫展覽”、5月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革命畫展”、6月的“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以及10月的“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萬歲”美展,等等。其中展出的版畫《跟著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沈堯伊)、《無產階級革命派牢握大權》、油畫《東方紅》、水粉畫《徹底摧毀資產階級司令部》、漫畫《抓革命促生產》以及各個畫種的《炮打司令部》等紅極一時的畫作,都是完全配合文革的政治運動,大型泥塑《紅衛兵贊》更是直接贊頌“文化大革命的闖將”在“捍衛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英勇斗爭中”立下的“豐功偉績”。這些“充滿向資產階級司令部開炮的火藥味”[12]的作品完全附著于文革,也必然隨著文革的終結而走進歷史的墳墓。而樣板戲雖然定型于文革,甚至成為文革文藝之“魁首”,但其與文革并非純粹的毛與皮的關系,它主要是為中共政權合法性做歷史的和現實的注腳,在中共長期執政過程中,它就仍然具備政治上的安全性,因而在文革結束之后仍有繼續搬演于舞臺的可能性。
其二,樣板戲畢竟數量有限,且誰也不敢對“樣板”妄加改動,因而其題材的單一與模式化是空前的,貌似光鮮熱鬧,實為萬馬齊喑。而文革美術雖然也大力推廣過《毛主席去安源》這樣的樣板,但終究沒有形成哪些作品、哪個畫種一統天下的局面,這就為畫種的多元性、作品的生活味和藝術家的獨創性留下了哪怕是極其可憐的縫隙和空間。油畫、中國畫、版畫、連環畫、宣傳畫等各畫種仍在不同程度上獲得發展,新創作品仍然不斷涌現。不僅出現了像《綠色長城》(中國畫,關山月)、《女委員》(油畫,湯小銘)等一批既契合文革模式、又以較高藝術水準堪稱“時代經典”的畫作,而且出現了《漁港新醫》(油畫,陳衍寧)、《新課堂》(中國畫,歐洋)等一批體現出較濃郁的生活氣息和清新之風的佳作,尤其在中國山水畫領域,《山水》(陳子莊)、《秋山幽居圖》(黃秋園)、《黃河兩岸度春秋》(石魯)等在居于統治地位的文革模式之外發出了異質的聲音,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難能可貴地進行了帶有個人特色的藝術探索。這也是我們應該承認的。
[1]革命文藝的優秀樣板[N]. 人民日報,1967-5-31.
[2]歡呼京劇革命的偉大勝利[J]. 紅旗,1967,(6).
[3]又一朵大香花[N]. 光明日報,1968-7-6.
[4]我們時代的最新最美的圖畫——贊油畫《毛主席去安源》[N]. 文匯報,1968-7-16.
[5]在毛澤東文藝思想指導下不斷加工精益求精[N]. 人民日報,1966-12-14.
[6]堅持美術革命,要和十七年的文藝黑線對著干——《農奴憤》創作組部分同志創作體會[J]. 美術,1976,(1).
[7]周繼厚. 毛澤東像章之謎——世界九大奇觀[M]. 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3.
[8]董健,胡星亮主編. 中國當代戲劇史稿(1949-2000)[M]. 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
[9]王彬彬.“樣板戲”《沙家浜》的風風雨雨[J]. 文史博覽,2006,(19).
[10]王明賢,嚴善錞. 新中國美術圖史(1966-1976)[M]. 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
[11]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而創作——贊革命油畫《毛主席去安源》[N]. 光明日報,1968-7-12.
[12]中直文藝系統美術口評論組. 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頌歌——評“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萬歲”美展[J]. 新美術,1967,(1).
(責任編輯:劉德卿)
10.3969/j.issn.1002-2236.2017.03.013
2017-01-16
穆海亮,男,河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戲劇。
項目來源: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課題“期刊史料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編號11&ZD110)階段性成果。
J120.9
A
1002-2236(2017)03-006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