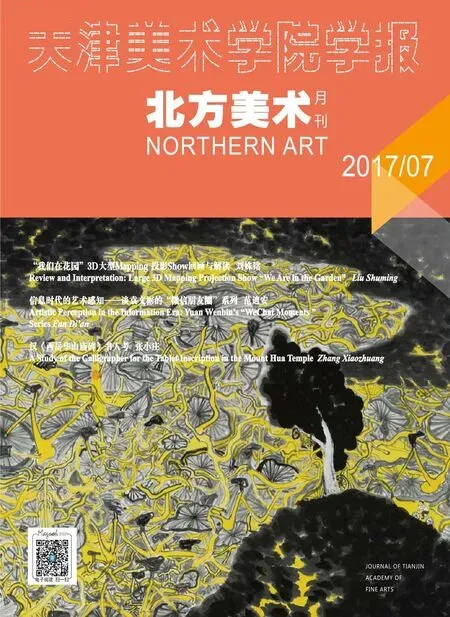“歷史的圖像與圖像的歷史”
——新時期的“農民工”油畫及其歷史意義
戚志雯/Qi Zhiwen
一、歷史時代與個人經驗的交織
“世事的發展變化匯成歷史的圖像,便是一部人類社會史;繪畫的創作演進,匯成圖像的歷史,便是一部人類美術史”①,在無數藝術家的努力下,中國農民逐漸從歷史的圖像中走出,向圖像的歷史中邁進,并形成一種新的、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永遠定格在觀者的眼中、心里。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所以“農民”這一群體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社會貢獻上來說都是舉足輕重的。藝術是對現實的反映,中國繪畫界對農民的關注自古便有,從最初山水畫中的人物點綴,到表現農耕時代的世風民情,再到戰爭時期的苦難農民、“文革”時期“歌頌”的農民典型,最后發展到近代擺脫陳舊模式面向生活、面向現實的新農民,“這些形象不僅指向了人們所要面對的歷史和現實,而且也指向了藝術家所處的歷史時代”②。
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民逐漸改變了20世紀那種“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發展模式,城鄉之間人口流動的壁壘被逐漸打破,并由此產生了蔚為壯觀的“民工潮”。“從社會學意義上講,‘農民工’這是一個源于農村卻居住在城市,介乎城市與農村之間,又不斷流動的新的社會階層。”③農民工群體生活在城市角落中,同時承受著艱苦的體力勞動和不公正的社會待遇,他們身處于城市卻心屬農村,他們惦念農村中的家人,沒有對城市社區的歸屬感。“面對城市的經濟和文化顯得無所適從,面對曾經參與建設的繁華街道他們只能是麻木地觀看,目光委瑣、呆癡而猶疑,這種不和諧狀況不僅導致他們內心的矛盾沖突,更讓這一特殊群體的‘邊緣化’程度加深了。”④
據《中國就業狀況和政策白皮書》統計,1990年全國農民工僅有1500萬人,2003年激增至9800萬人,而到2006年底已猛增至2億多人,超過了傳統上由城鎮居民構成的產業工人。在當時的歷史時代背景下,“農民工”作為新型的產業化隊伍,成為城市建設、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不可否認它極具時代表情。
面對國內外風起云涌的各種藝術思潮,面對商業化和大眾傳媒文化帶來的沖擊和負面影響,藝術家們有著自己的考量,之所以最終“執迷”于現實主義,選擇“農民工”題材,應該說是幾經思考之后的結果。雖然一方面似乎是“勞動經驗”影響了藝術家的創作實踐,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說這是歷史時代的選擇,因為“勞動經驗”不僅僅屬于藝術家個人,它也是一種根植于中國現代性的歷史經驗。一些藝術家的個人實踐語境與歷史語境之間發生的錯位和融合,讓我們更加明晰地看到他們是如何運用全部的敏感去轉化自身經驗的。
二、勞動經驗到藝術創作的轉化
中國當代藝術家中的很多人或者出生在農村,或者有過在農村、工廠勞動過的經歷。比如說:1946年出生在黑龍江的孫為民,在“文革”期間曾到河北地區的偏遠農村下鄉生活過;1955年出生的王宏劍在河南開封一個中學畢業后,曾下鄉插隊三年;1958年出生于烏魯木齊的徐唯辛曾作為知青下鄉插隊至三坪農場,有著在基層工作的經歷;忻東旺1963年出生在河北農村,十幾歲開始自學繪畫并兼做走村串戶的民間畫匠,后來又做過煤礦礦工、印刷廠設計員,是從農村進入都市的一個成功的先例。這些過往讓他們對勞動者的生活和心態有著比較深的體會和了解。相似的“勞動經驗”和對農民工的情感使得這些藝術家走在一起,用自己獨特的藝術語言來展現這群背井離鄉的“邊緣人”的生活境遇及內心世界。
在以上眾多的藝術家里,以忻東旺的“農民工”題材作品創作時間最早,數量也最多。他的成名作是1995年參加第三屆全國美展,并獲得銀獎的《誠城》。他對《誠城》這個題目的解釋就是“誠心誠意地做一個城里人”,而進城的目的就是要改變自己的農民身份。雖然畫家迫切地想要改變原來的身份,但他在創作中卻最終選擇了“農民工”題材,除了他自身的“勞動經驗”促使外,更多的是一種親切感,誠如他在創作油畫《裝修》時發出的感想:“為我的畫室裝修的民工們在冰冷潮濕的水泥地上只墊了幾塊磚頭搭起了大通鋪,我有些凄然。當他們用沾滿泥灰的大手解開打著各色花樣補丁的行李卷兒時,隨著汗臭味兒散發出的悠悠的溫馨使我一陣心酸。這是多么親切的味道,多么富有人性的味道,這味道飽含著生命中最質樸的元素。”⑤
“繪畫是視覺語言,作者通過可視、可感的形式和觀眾對話,并傳達感情,而作者本人的觀念、他的文化和哲學的思考,往往隱藏在形象后面,而不是赤裸裸地表露于外。”⑥忻東旺的作品深受盧西恩·弗洛伊德作品的影響,以筆下“咄咄逼人”(畫家本人語)的形象而自成一格。他畫中的農民工們身著廉價的西裝或漿洗掉色的工服,雙手布滿泥漬,未老先衰的容顏上,嘴唇開裂,表情尷尬而又無奈,眼神茫然而又困惑,他們沒有大范圍的肢體運動與張揚的姿態,只有承重的站立與凝視,這樣的形象更加凸顯了農民工兄弟被邊緣化、處于弱勢的一面,似乎是生活的重負將他們的身材壓成如此模樣。我們面對作品看到的就是這樣一群既不“美麗”也不“偉岸”的平凡人物,他們雖然生活得并不如意,但他們卻始終以一顆真誠的心去對待一切。這并非畫家的刻意寫生,而是他內心感受的真實表達,他以農民工中的一分子去正視他們的存在。“當我們即將被泛濫于媒體中的打情罵俏或者故作深沉的時髦男女淹沒的時候,反倒會為忻東旺畫中人物的沉重和茫然感到一種欣慰。”⑦
不管是《客》《邊緣》中的民工,還是《外面的世界》中的姑娘,忻東旺都對他們懷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正如賈方舟所說:“忻東旺始終懷有一種深深的憂患,他對這些身份低下和生活落魄的小人物,表達著他發自內心的尊重,他為弱勢群體造像立傳,從而揭示出這一被邊緣化的族群本有的生命價值和人性尊嚴。這些作品能顯示出的‘人文’情懷和人性力量,足以使每個有良知的都市人去反省我們的社會,乃至我們自己。”⑧
徐唯辛1958年生于新疆烏魯木齊市,雖然年長于忻東旺,但他真正開始從事“農民工”題材的繪畫創作卻是在忻東旺之后。徐唯辛的早期作品大多反映邊疆少數民族風情和環保問題,例如他的《馕房》《圣地拉薩》《酸雨》等。2000年前后畫家輾轉來到北京,在這座大都市中,到處可見為生活掙扎辛勞的來自各地的民工,他們時常被列為擾亂社會秩序的對象,這是一群被現代社會所無視的被“邊緣化”的人,是一群“沉默的羔羊”。正如徐思田所說:“隨著年齡增長,藝術修養的積累,就越發不滿足于僅僅表現邊疆風情,這種題材的文化含量不夠,于是他便遵循與時俱進的法則,將現實主義關懷投向了在城市辛勤勞動的民工。”⑨
《工棚》算是徐唯辛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畫家似乎有意識地讓畫面上的所有農民工都望向觀眾,而觀者也似乎不得不接受著他們的注視。“因為在城市生活的人們是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去注意那些民工的,所以這種奇特的構圖安排——‘強迫’每個觀畫者直面這群在惡劣環境下為我們的幸福生活添磚加瓦的農民工們,獲得了震撼人心的效果,并喚起我們對農民工處境的關注和思考。”⑩藝術家不再是高高在上地俯視,也不是袖手旁觀和帶有戲謔地調侃,而是以一種平等的眼光去正視農民工們,以寫實的技法來真實地描寫他們的生活、工作狀態,肯定他們的尊嚴,拒絕丑化和憐憫,表現他們的力量和美。畫面上充滿了畫家對農民工作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的尊重,使得作品具備了動人的魅力。
一方面,農民工的特殊處境讓藝術家們感到同情,所以不能對他們的境遇視而不見;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藝術家本人的農民情結和“勞動經驗”,使得他們對這些與自身有著相似經歷的農民工有著強烈的真情實感。以上這些因素使得藝術家感到了極高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們將自己的情感注入筆端,為時代發聲,為自己的“農民工兄弟”們發聲,向社會呼吁為農民工們尋求更多的人性關懷。油畫藝術家忻東旺和徐唯辛正是其中兩個較為典型的例子。
三、“農民工”題材油畫的社會價值
“我們正處于一個社會變動的時期,也是藝術創作風格多變的時期,沒有任何一個時代像我們今天這樣,文化沖突之大,社會發展之迅速。如果我們的藝術表現忽略了對這個時代精神層面的深刻把握,那么我們對這個時代就是失語的,藝術作品自然也就缺乏表現力。”[11]而如何“深刻把握”似乎應該包含兩個方面:真實反映和社會批判。
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真實地刻畫勞動的農民和工人,是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中國藝術家們立足于現實生活而去創作平民化和大眾化的作品,關注現實的生活和社會問題以及這種現實社會下的精神,他們對處在社會底層勞動者的理解和關懷超過了以往任何歷史階段。撥開被灰塵與泥漿掩蓋的外表和世俗的偏見,藝術家們以繪畫的方式真實反映農民工多側面的生活、情感、心理和思想狀態,展示出他們誠實、質樸、勤勞、執著的本質和不可褻瀆的尊嚴,將這些生活在城市底層的人毫不猶豫地帶到人們面前,這不僅有利于大眾去了解這個群體,同時也可以更好地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態。這些描繪農民工的油畫作品不僅在藝術形象上具有突破性,而且體現了中國社會從農業向工業轉型、從農村經濟向城市經濟轉變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真實情況,傳達了時代主題,“它幾乎成為中國歷史變遷和社會轉型的一個歷史的、文化的、精神的見證,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社會圖景的縮影,成為我們了解、認識、反思這個社會和時代的最好的窗口和解讀文本”[12]。
20世紀西方著名的藝術社會學家阿諾德·豪澤爾(Arnold Hauser)說:“藝術總是企圖改變生活,它絕不簡單地接受或被動地屈服于生活。當藝術介入生活的時候,它就會產生社會影響,這種影響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可能是贊美的,也可能是批判的。……在某種條件下,藝術可以診斷和醫治社會的病害。”[13]在當今時代,伴隨著工業文明而產生的一系列緊迫性問題的確撕裂了人類感性與理性的和諧,從而導致精神危機的出現,但這同時也給物質文明高壓下幾近崩潰的人文精神提供了重生的機遇,毫無疑問這個機遇將通過藝術來把握和完成。藝術自古以來便具有“成教化,助人倫”的道德教化功能,這個時期的畫家們不再做主流意識形態的解說員,而是開始更加獨立和深入地觀察社會現實,并尋求破解之法。關于“農民”“農民工”題材的藝術作品并非獨此幾家,但在此之前卻并未引起多大反響,原因在于那些作品只是將這些底層勞動者當作被丑化和憐憫的對象,而并未深究其背后所隱藏的價值與意義,只有部分藝術家在責任與批判意識的驅使下,站在農民工的視角思考社會問題,揭示諸多社會深層矛盾和癥結。這些鮮活的作品體現了繪畫藝術的先鋒作用,表達了當代畫家的人文精神和社會責任感,是藝術家對貧困者的文化聲援,振聾發聵。
總結
總而言之,新時期的“農民工”油畫作為“中國新寫實主義”油畫的崛起之作,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深刻的社會、歷史價值。現實主義的畫家們把視角放在平凡的生活中,描繪背井離鄉在城里辛苦勞作的樸實農民工,畫他們最樸實的生活,從而讓人去思考現實。我們有理由相信,這種鮮明的現實主義創作必然會得到越來越多的藝術家的關注,并且在未來的發展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人文價值和現實意義,這有待藝術家們去不斷地探索和挖掘。
人文精神在藝術中重生,感性和理性在藝術中得到調和。“當藝術深度成為人性的深度(美成為人類的屬性),成為人性覺醒向度的時刻,它便可以抵御人性深度的淪喪,擺脫日常感覺因停留在生活表面和外圍而帶來的平庸委瑣和淺薄無聊,人人都能夠成為生活的藝術家,得以詩意的方式,棲居在自由的存在之家……”[14],這是我們當今社會所力求達到的理想之境。
注釋:
①楊祥民:《歷史的圖像與圖像的歷史——改革開放30年中國油畫創作中的農民形象》,《藝術百家》,2008年第5期,第13頁。
②劉夢梅:《論二十世紀中國油畫藝術中的農民形象》,《商丘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第16頁。
③顧丞峰:《從主人公到看客——1942年以來美術作品中農民形象分析》,《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2006年第1期,第70—74頁。
④王勝選:《“89后”美術作品中農民工形象分析》,《陰山學刊》,2007年第2期,第58—60頁。
⑤水天中:《感受生命——忻東旺的繪畫藝術》,《美術觀察》,2005年第12期,第36—42頁。
⑥韓業騰、楊天民:《試論中國油畫的新現實主義》,《淮南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第77—78頁。
⑦薛曄:《畫家的社會責任——記油畫家徐唯辛》,《藝術·生活》,2005年第2期,第15—16頁。
⑧李鳴樓:《從忻東旺、朝戈的作品看當代油畫中的“人文精神”》,《美術大觀》,2009年第1期,第175頁。
⑨徐思田:《淺談以農民工為主體的繪畫創作》,《美術觀察》,2014年第9期,第133頁。
⑩程永君:《淺析油畫中農民工形象的社會歷史意義》,《美術大觀》,2012年第12期,第55頁。
[11]何金俐:《席勒美育理想的當代啟示——美育書簡今讀》,《勝利油田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第3期,第94頁。
[12]同⑩。
[13]阿諾德·豪澤爾著,居延安譯編:《藝術社會學》,學林出版社,1987年,第6—10頁。
[14]同[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