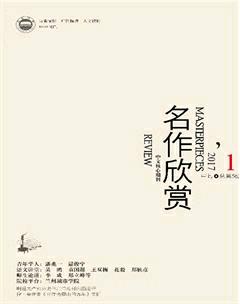《雨中的奔跑》:都市異鄉(xiāng)人的危機(jī)與救贖
摘 要:《雨中的奔跑》是李迎兵先生的一部帶有自傳性質(zhì)的描述在京漂泊者困頓與不屈生活的長篇小說。身份確認(rèn)危機(jī)、物質(zhì)困境、精神危機(jī)成為壓在他們身上的三座大山,他們會(huì)選擇追憶故土,更會(huì)選擇雨中堅(jiān)強(qiáng)的奔跑,而這,則成為萬千都市異鄉(xiāng)人真實(shí)的精神象征。
關(guān)鍵詞:都市異鄉(xiāng)人 城市危機(jī) 救贖之道
《雨中的奔跑》是山西呂梁籍在京作家李迎兵創(chuàng)作的帶有濃郁自傳性質(zhì)的長篇小說。正如書名所言,這是一部描寫個(gè)人坎坷經(jīng)歷的作品,寫盡了主人公“我”在追求夢(mèng)想與幸福的路上所遭遇的重重艱難與險(xiǎn)阻,卻還是沒有放棄自己對(duì)生的渴望與愛的信仰,不停地在雨中奔跑以此來對(duì)命運(yùn)進(jìn)行頑強(qiáng)的反抗。童年是人的生命源頭,在無力與現(xiàn)實(shí)作斗爭(zhēng)時(shí),“我”會(huì)退回到過去,把在故鄉(xiāng)的回憶作為自己的精神家園來獲得救贖。但是,“我”還能回到故鄉(xiāng)嗎?答案是否定的,“我”試圖回去,但是故鄉(xiāng)卻不再是“我”記憶里的故鄉(xiāng)了。即使重返故鄉(xiāng)“我”也依舊是個(gè)異鄉(xiāng)人,沒辦法找到自己的根與歸宿。“我”只能像蒲公英一樣繼續(xù)自己奔跑的使命,在前行的道路上汲取力量。
一、都市異鄉(xiāng)人的城市危機(jī)
關(guān)于“異鄉(xiāng)人”的定義,最早見于德國社會(huì)學(xué)家西美爾的《社會(huì)學(xué)——關(guān)于社會(huì)化形態(tài)的研究》一書。西美爾認(rèn)為“異鄉(xiāng)人”“不是今天來明天去的漫游者,而是今天到來并且明天留下的人,或者可以稱為潛在的漫游者,即盡管沒有再走,但尚未完全忘卻來去的自由”{1}。改革開放極大地推進(jìn)了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打破了之前城鄉(xiāng)固化的結(jié)構(gòu)模式,為人口的流動(dòng)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這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更多的都市“異鄉(xiāng)人”,他們?yōu)榱双@得更好的生存與發(fā)展的機(jī)會(huì),紛紛舍棄自己熟悉的故土,滿懷憧憬地走向象征夢(mèng)想開始的地方——大都市,試圖融入城市文明。然而,對(duì)于大城市而言,他們卻始終是個(gè)外來者,是這個(gè)城市的邊緣化存在,很難獲得身份認(rèn)同。《雨中的奔跑》以第二人稱的敘述方式這樣寫道:“你的出現(xiàn),讓這座城市多少有些難堪。城市像一輛正在行駛的郵車。你只不過是如同一只毫不起眼的包裹暫時(shí)棲居在這里。”這是一個(gè)外來者在這個(gè)城市的切身體會(huì),他與城市有染,城市卻與他無關(guān)。“我的到來,對(duì)于整個(gè)城市來說也許是微不足道的,但對(duì)于我自己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一步,命運(yùn)的車輛從此會(huì)走上新的軌道。”那么,來到城市是否就真的讓命運(yùn)對(duì)“我”另眼相看了?似乎并沒有。“我”面臨更嚴(yán)重的生存危機(jī),那遠(yuǎn)遠(yuǎn)不是農(nóng)業(yè)文明籠罩下的故土的生存境況所能比擬的。
首先,作為一個(gè)都市異鄉(xiāng)人,“我”在城市遭遇著身份確認(rèn)危機(jī)。20世紀(jì)90年代的政策規(guī)定外來務(wù)工者進(jìn)入城市必須要有三證:身份證、暫住證和務(wù)工證。這種制度造就的鴻溝猶如一條警戒線,將都市異鄉(xiāng)人下意識(shí)地視為威脅社會(huì)安定的“異類”,使他們無法在城市面前獲得應(yīng)有的尊重和身份認(rèn)同,時(shí)刻處于局促不安之中。就像文中的主人公在聽朋友說起警察將大街上好好走著的“三無”人員不由分說地拉上路邊的依維柯時(shí),會(huì)不由自主地哆嗦一下子,擔(dān)心下一次就會(huì)輪到自己。
身份確認(rèn)危機(jī)造成了都市異鄉(xiāng)人的被排斥感,然而真正威脅他們?cè)诔鞘猩娴氖滓獥l件還是物質(zhì)。人只有在物質(zhì)上比較充裕,精神才能更加自由,實(shí)現(xiàn)“詩意地棲居”。然而,“詩意地棲居”終究是一個(gè)理想化的彼岸世界,最起碼對(duì)于文中的主人公“我”是難以實(shí)現(xiàn)的。“我常常給書商田瓜當(dāng)槍手。所謂槍手,便是制造一大堆文字垃圾,然后掙出明天的飯錢。我不這樣干,就只能露宿街頭。”物質(zhì)的擠壓把人拋入一個(gè)近乎絕望的境地,女友宋歌的意外懷孕更是讓人感到無助惶恐,“我們就結(jié)婚吧?可是哪來的錢呢?結(jié)婚也是一種消費(fèi)啊!”最終他們選擇了去醫(yī)院打掉孩子。謀生尚且不能,謀愛更是困難。小人物在物質(zhì)的重壓下變得如螻蟻般卑微渺小,為了生存甚至不得不放棄人的基本權(quán)利——結(jié)婚生子。生存危機(jī)以極其慘烈的方式逼迫著都市異鄉(xiāng)人,在這個(gè)金錢至上的時(shí)代,強(qiáng)大的物質(zhì)霸主掌握著話語權(quán)和主動(dòng)權(quán),而那些深陷物質(zhì)困境的都市異鄉(xiāng)人只能被驅(qū)趕到邊緣化的地帶,一步步喪失自己作為人的尊嚴(yán),這無疑會(huì)加重他們的漂泊感與危機(jī)感。
與物質(zhì)困境相比,精神危機(jī)似乎更是一個(gè)難題。費(fèi)孝通在《鄉(xiāng)土中國》中指出:“鄉(xiāng)土社會(huì)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huì)……每個(gè)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著長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圍的人也是從小就看慣的。這是一個(gè)‘熟悉的社會(huì),沒有陌生人的社會(huì)。”{2}然而,“現(xiàn)代社會(huì)是個(gè)陌生人組成的社會(huì),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細(xì)”{3}。都市異鄉(xiāng)人在鋼筋水泥鑄就的森林里迷失了自己,成了無根的浮萍和失語的路人甲。“我在北京總是面對(duì)電話本上的一個(gè)個(gè)人名和號(hào)碼發(fā)呆……有時(shí),我會(huì)出于無聊之極,便占卜一般,隨便撥一個(gè)號(hào)碼。無論對(duì)方是誰,我撥通之后會(huì)突然改變主意,竟然不知所措,一下子就掛斷了。”身居鬧市之中,繁華喧囂卻絲毫沒有沖淡心頭的孤獨(dú)和寂寞。個(gè)體在都市之中遭遇著空前的精神危機(jī),他們不禁開始追問自己當(dāng)初選擇城市的目的,“我來北京尋找什么呢?是所謂的理想,還是虛幻的愛情?我一無所知。”“我”希望像當(dāng)年那個(gè)從湘西跑來京城的文學(xué)青年沈從文一樣實(shí)現(xiàn)自己的文學(xué)理想,然而“我”的尋夢(mèng)之旅卻充滿了坎坷磨難。宋歌含沙射影地諷刺“我”:“他成功了,而你呢?你會(huì)成功嗎?”就連“我”的詩人朋友周空也說:“文學(xué)快他媽的都成了婊子了,快成了當(dāng)官的擦腳布了,你丫的還這么不識(shí)時(shí)務(wù)?……你丫的混得也差不多快成孔乙己了,這是何苦呢?你丫的以為你是誰啊?”理想在現(xiàn)實(shí)面前顯得不堪一擊,而愛情也同樣讓人無奈絕望。宋歌和“我”的感情在真真假假虛虛實(shí)實(shí)中充滿了試探性的意味,我們就像在進(jìn)行拉鋸戰(zhàn)一樣進(jìn)行著感情的較量。宋歌渴望抓住身邊任何一個(gè)可以抓住的人做救命稻草以此改變自己的命運(yùn),但顯然“我”不是這樣的人,沒錢沒勢(shì)的“我”甚至連自己的命運(yùn)也無力把握。所以最后宋歌義無反顧地離開了“我”投向了金老板的懷抱。當(dāng)愛情也逝去的時(shí)候,“我”在這個(gè)城市更是顯得可悲可笑,所有看似美好的東西終于露出了它本來的面目,張牙舞爪地吞噬著一個(gè)追夢(mèng)青年的希冀。
二、都市異鄉(xiāng)人的救贖之道
作為一個(gè)在京漂泊的游子,城市無情地?cái)D壓著“我”的肉體和靈魂,“我”在與城市一次次的博弈中敗下陣來。這個(gè)時(shí)候,腦海中關(guān)于故鄉(xiāng)的回憶成為“我”拯救自己的良藥。于是,“我”的思緒不斷地退回到遙遠(yuǎn)的呂梁山,從故鄉(xiāng)的種種人事中找尋精神養(yǎng)料。莫言說:“作家的故鄉(xiāng)并不僅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過了童年乃至青年時(shí)期的地方。這地方有母親生你時(shí)流出的血,這地方埋葬著你的祖先,這地方是你的‘血地。”{4}這與《雨中的奔跑》中主人公對(duì)于故鄉(xiāng)的認(rèn)識(shí)不謀而合,“記憶的源頭只能是人的童年和老家”。看炮子爹殺豬時(shí)的害怕,上學(xué)時(shí)被人發(fā)現(xiàn)身上有虱子的局促,買到小人書時(shí)的激動(dòng),被猞猁欺負(fù)之后的委屈,為逞英雄攔汽車時(shí)的可笑,參加梅梅姑姑組織的革命運(yùn)動(dòng)時(shí)的震撼,對(duì)電影院放映的革命電影的熱忱……這些點(diǎn)點(diǎn)滴滴的碎片回憶都伴隨著“我”對(duì)童年的一次次回顧加工得以保存下來,成為主人公的獨(dú)特的個(gè)人體驗(yàn)。尤其是梅梅姑姑和奶奶對(duì)“我”的溫情照顧和陪伴,更是“我”時(shí)刻從冰冷的現(xiàn)實(shí)中閃回到故土的神思之中的重要原因。然而,作者筆下的故土世界卻不像沈從文的“湘西世界”那般恬靜美好,“我”還是會(huì)受到小伙伴們的捉弄和嘲笑,暗戀的梅梅姑姑也最終客死他鄉(xiāng),親近的奶奶后來也病逝了,內(nèi)心的怕與愛也絲毫沒有因?yàn)閹е貞浀难酃舛兴诒魏推鄄m。正因如此,才顯得李迎兵筆下的呂梁故土真實(shí)可感,充滿生機(jī)。那么,“我”還能回到原點(diǎn)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我知道自己已經(jīng)回不去了。我不可能回到原來死水一潭的生活圈子里了”。故鄉(xiāng)永遠(yuǎn)是記憶里的故鄉(xiāng),在現(xiàn)代文明的強(qiáng)勢(shì)入侵下,而今的故鄉(xiāng)也已經(jīng)面目全非。同時(shí),主人公的都市認(rèn)知經(jīng)歷使他再也無法忍受故鄉(xiāng)的貧窮與落后,即使回鄉(xiāng)也依舊是個(gè)“異鄉(xiāng)人”。所以,“我”不可能實(shí)現(xiàn)真正意義上的回鄉(xiāng)。正如梅娟所說:“在理性精神已經(jīng)透徹骨髓的人們身上,返鄉(xiāng)總是無往而無返的,它承受了離家之苦的回歸,再也無法按原路返回,只能承襲出發(fā)時(shí)的精神,這一歸途痛苦萬分而又毫無希望。于是,借助于鄉(xiāng)土懷舊這一審美的途徑,那些受了徹底的現(xiàn)代精神支配的人,透過這一情懷,去找尋所處空間的在家感、存在感和認(rèn)同感。”{5}從這個(gè)層面上來講,主人公只是把故鄉(xiāng)看作是精神家園,在一次次對(duì)故鄉(xiāng)的回望中實(shí)現(xiàn)“精神返鄉(xiāng)”。
“存在對(duì)人的關(guān)系是拋擲與被拋擲的關(guān)系。在這一關(guān)系中,拋者是存在,被拋者是人。人的生存本身就是作為被拋而成其本質(zhì)的。這就是說人的生存雖然直接是人自己去生存,但從根本上并不是由人自己所決定的,而是由存在的拋投所決定的。……是人的命運(yùn)所在。”{6}在龐大的時(shí)代洪流裹挾之下,個(gè)體似乎很難把控自己的命運(yùn)。城市對(duì)“我”進(jìn)行無情的碾壓,歸鄉(xiāng)也絕無可能,那么,“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著名美學(xué)家朱光潛指出:“如果苦難落在一個(gè)生性懦弱的人頭上,他逆來順受地接受了苦難,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劇。只有當(dāng)他表現(xiàn)出堅(jiān)毅和斗爭(zhēng)的時(shí)候,才有真正的悲劇,哪怕表現(xiàn)出的僅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靈感,使他能超越平時(shí)的自己。悲劇全在于對(duì)災(zāi)難的反抗。陷入命運(yùn)羅網(wǎng)中的悲劇人物奮力掙扎,拼命想沖破越來越緊的羅網(wǎng)的包圍而逃奔,即使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心中卻總有一種反抗。”{7}而主人公面對(duì)命運(yùn)的不公即使偶有抱怨也一直沒有放棄希望。正如書名《雨中的奔跑》,要在殘暴的命運(yùn)的攻擊下努力向前奔跑。“只有這不停的奔跑的腳步才是唯一的希望”。雖然命運(yùn)絲毫沒有因?yàn)椤拔摇钡呐Χ艞墝?duì)“我”的圍追堵截,但“生活總還是有些盼頭的。盡管,我每天一早醒來一點(diǎn)頭緒也沒有,但仍然要充滿希望地活著。我想一切都會(huì)好的。希望正是在我剛剛無法企及的地方。”“奶奶活著時(shí)曾對(duì)我說過,絆倒了,快爬起來。人只有好好地活著,一切就可以從頭再來。”在經(jīng)歷了大城市的幻滅感之后,“我”仍然能保持這樣的人生態(tài)度,從自我激勵(lì)中實(shí)現(xiàn)靈魂救贖,以此完成對(duì)命運(yùn)的不斷反抗。
三、結(jié)語
身份確認(rèn)危機(jī)、物質(zhì)困境、精神危機(jī)猶如三座大山一般壓在像主人公一樣的城市漂泊者身上,而這種普遍性的生存困境在巨變的中國大地上又無時(shí)無刻不在上演。面對(duì)急劇膨脹的物質(zhì)化社會(huì),面對(duì)不斷加速的城市化進(jìn)程,我們或歡欣鼓舞于那令人振奮的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或批評(píng)質(zhì)疑著這類泡沫式的、不計(jì)后果式的發(fā)展,大家都在詢問社會(huì)的去向如何,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如何,卻恰恰忘記去關(guān)心每一個(gè)擁有獨(dú)特價(jià)值的人將會(huì)如何?每一個(gè)猶如“城鄉(xiāng)結(jié)合體”的“都市異鄉(xiāng)人”如今如何?《雨中的奔跑》以一名親歷者的身份從“人”的視角對(duì)這一境況加以審視,記錄與見證著這一歷史時(shí)期隱匿在大都市中的痛苦、呻吟,以及他們的不屈與堅(jiān)強(qiáng)。同時(shí)也在引發(fā)人們的關(guān)注與思考:面對(duì)轉(zhuǎn)型期下的巨變社會(huì),個(gè)人自救終究勢(shì)單力薄,國家政策的有力引導(dǎo)和制度的充分保障才是解決都市異鄉(xiāng)人危機(jī)的有效之道。
① 蓋奧爾德·西美爾:《社會(huì)學(xué)——關(guān)于社會(huì)化形態(tài)的研究》,林榮遠(yuǎn)譯,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頁。
②③ 費(fèi)孝通:《鄉(xiāng)土中國》,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6頁,第7頁。
④ 莫言:《莫言散文集·會(huì)唱歌的墻》,人民日?qǐng)?bào)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頁。
⑤ 梅娟:《永恒的鄉(xiāng)愁——生態(tài)文學(xué)中的鄉(xiāng)土懷舊意識(shí)研究》,上海師范大學(xué)2012年碩士論文,第26頁。
⑥ 劉敬魯:《海德格爾人學(xué)思想研究》,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212頁。
⑦ 斯馬特:《悲劇》,見《英國學(xué)術(shù)論文集》第八卷,轉(zhuǎn)引自朱光潛:《悲劇心理學(xué)》,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頁。
參考文獻(xiàn):
[1] 李迎兵.雨中的奔跑[M].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9.(文中所引原文均出于此)
[2] 蓋奧爾德·西美爾.社會(huì)學(xué)——關(guān)于社會(huì)化形態(tài)的研究[M].林榮遠(yuǎn)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3] 費(fèi)孝通.鄉(xiāng)土中國[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
[4] 朱光潛.悲劇心理學(xué)[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3.
[5] 楊惠瓊.新時(shí)期的漂泊敘事與現(xiàn)代性體驗(yàn)——對(duì)空間、時(shí)間、性別的家園體驗(yàn)[D].福建師范大學(xué),2012.
[6] 吳妍妍.城市“異鄉(xiāng)人”的現(xiàn)代性認(rèn)同與傳統(tǒng)回歸[J].太原理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6(1).
[7] 蘇奎.漂泊于都市的不安靈魂[D].東北師范大學(xué),2006.
[8] 劉雨.現(xiàn)代作家的故鄉(xiāng)記憶與文學(xué)的精神還鄉(xiāng)[J].東北師大學(xué)報(bào),2006(5).
作 者:劉俊芳,太原師范學(xué)院文學(xué)院2015級(jí)在讀碩士,研究方向: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
編 輯:趙紅玉 E?鄄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