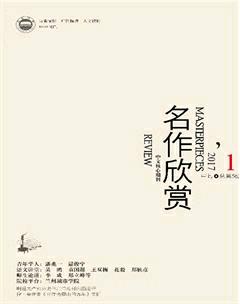一則重述的神話
劉海英
摘 要:《裸顏—— 一則重述的神話故事》是C.S.路易斯于1956年出版的一部小說,其副標題和“后記”都表明該小說與“丘比特與賽姬的神話”有密切關(guān)系。本文首先分析C.S.路易斯如何將《金驢記》中“賽姬和丘比特的神話”改寫為《裸顏》,然后依據(jù)作者的基督教觀念解讀該小說所表達的“信仰”和“愛”等宗教主題思想。
關(guān)鍵詞:C.S.路易斯 《裸顏》 神話 信仰 愛
一、引言
C.S.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1898—1963)是英國文學(xué)學(xué)者,文學(xué)批評家,小說家,他一生著作豐富,除了文學(xué)批評著作常為學(xué)者所稱道以外,基督教著作和奇幻文學(xué)作品也同樣吸引著大量的讀者。本文所要探討的《裸顏—— 一則重述的神話故事》(Till We Have Faces: A Myth Retold)是他于1956年出版的一部小說,其副標題和“后記”都表明該小說與“丘比特與賽姬的神話”有密切關(guān)系。本文分析C.S.路易斯如何將“賽姬和丘比特的神話”改寫為小說《裸顏》,探究此番改寫的原因,揭示小說的“神”和“愛”等宗教主題。
二、“一則重述的神話故事”
C.S.路易斯在《裸顏·后記》中寫道:“丘比特與賽姬”的故事最早出現(xiàn)在古羅馬作家阿普列尤斯(Lucius Apuleius Platonicus,約124-170)所著的拉丁文小說《金驢記》(又譯為《變形記》)中。{1}在神話故事中,賽姬是某國王的小女兒,因她貌美,被人當作女神膜拜,惹維納斯女神憤怒,女神便找兒子丘比特對她施加報復(fù)。但是丘比特對賽姬一見鐘情,經(jīng)常與她相聚,只是囑咐她萬萬不可看他的面孔。賽姬卻受到兩位姐姐的挑唆,違背丘比特的愿望,看到了丘比特的面容。丘比特大怒,殺死了賽姬的兩位姐姐,而且使賽姬四處流浪,賽姬經(jīng)歷了諸多苦難。最終,丘比特原諒了賽姬,并經(jīng)朱庇特允許,與她結(jié)婚。賽姬被封為神,且獲得了維納斯的諒解,“故事圓滿收場”,“愛”和“靈魂”(賽姬的名字即為“靈魂”之意)的“姻緣永遠不會破裂”{2}。C.S.路易斯指出:因為他視阿普列尤斯的作品為“材料資源”,而非“影響”或“典范”,他在創(chuàng)作《裸顏》時沒有拘泥于阿氏的寫法,他的小說與這則丘比特與賽姬的神話故事的最大差別,在于他把賽姬的宮殿寫成為凡人肉眼所看不見的事物,這一改動當然就使他的女主角具有了更錯綜復(fù)雜的行為動機和不同的性格特點,最后甚至改變了整個故事的性質(zhì)。{3}那么,C.S.路易斯的《裸顏》,究竟以怎樣的方式重新講述了《金驢記》中賽姬和丘比特的神話故事呢?《裸顏》的“故事性質(zhì)”(或曰“故事的主題”)是什么呢?
《裸顏》與《金驢記》這兩部作品都是以講故事的方式來闡釋人生哲理。《金驢記》的主人公魯巧與《裸顏》中的奧璐兒都親歷各種變故,最后成為宗教信徒,雖然他們二人的宗教信仰不同,但他們皈依宗教的人生歷程是相似的。《金驢記》{4}中的主人公魯巧在變成一頭毛驢之后,經(jīng)受無數(shù)苦難,先后服役于強盜、隸農(nóng)、街頭騙子、磨坊主、菜農(nóng)、兵痞以及貴族,同時經(jīng)歷各種奇聞逸事,包括神話傳說、愛情故事等,賽姬與丘比特的故事,就是他所聽到的一則神話故事,是“故事中的故事”。魯巧道聽途說這個故事,所以故事以全知視角的形式出現(xiàn)在魯巧的見聞之中,賽姬與她的兩個姐姐都是故事中的人物。但是,在《裸顏》中,賽姬的姐姐奧璐兒是作為第一人稱敘事者出現(xiàn)的,她從自己的視角出發(fā)講述妹妹賽姬由人變?yōu)樯竦慕?jīng)過,使小說的故事情節(jié)更為曲折,人物形象更加飽滿。《裸顏》轉(zhuǎn)換故事的敘述視角,使賽姬的故事成為奧璐兒的敘述對象,從兩方面起到了強化主題的作用:其一,它在賽姬和讀者之間增加奧璐兒這個人物媒介,使讀者通過奧璐兒的敘述來了解賽姬的經(jīng)歷,借賽姬姐姐的眼睛,來觀察賽姬其人其事,讀者便能如臨其境地感受到奧璐兒對賽姬的情感和態(tài)度的變化過程;其二,這種寫法也使讀者與賽姬之間產(chǎn)生距離,使讀者無法直接面對賽姬,增加了賽姬在讀者心中的神秘感,借此得以突顯《裸顏》的思想內(nèi)涵。
《裸顏》通過講故事來闡發(fā)信仰要義的方式,與《圣經(jīng)》中某些內(nèi)容具有內(nèi)在的相關(guān)性。斯騰伯格認為,整部《圣經(jīng)》的中心矛盾就是人與上帝之間既斗爭又親和的關(guān)系,從伊甸園內(nèi)亞當、夏娃背叛上帝開始,到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而為人類贖罪的人與神之間驚心動魄的全部斗爭,始終圍繞著人類到底信不信上帝,到底對上帝的存在、對他的威力和意圖了解多少這個焦點來展開。{5}《舊約》與《新約》中有很多這類的故事:《圣經(jīng)·創(chuàng)世記》(37-50)中約瑟曾被兄長們合謀出賣至埃及,被誣陷而入獄,最終成為埃及宰相,并在饑荒之年拯救全家人的性命,此時他才頓悟“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路加福音》(24:13-30)講述了一個發(fā)生在去以馬忤斯路上的故事,耶穌的門徒雖與他同行,卻不認識他,耶穌對他們說:“無知的人哪!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因此,《圣經(jīng)·阿摩思書》(8:11-12)對于不信神者,曾經(jīng)這樣說道:“日子一到,我必命饑荒降在地上。人饑餓非因無餅,干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到耶和華的話。他們必漂流,從這海到那海,從北邊到東邊,往來奔跑尋找耶和華的話,卻尋不著。”奧璐兒由一名不信“神”的人轉(zhuǎn)變?yōu)椤吧瘛钡男磐剑啃≌f正是以她對“神”的態(tài)度變化為線索,描述了她認識“神”的過程,路易斯筆下的奧璐兒,與《圣經(jīng)·創(chuàng)世記》(37-50)中的約瑟一樣,在經(jīng)歷了無數(shù)困苦之后才成為“神”的信仰者。不認識耶穌的人所在的世界猶如一片荒原,永遠沒有生機,T. S.艾略特曾經(jīng)借用耶穌復(fù)活的故事表明荒原有被拯救的希望,C.S.路易斯則借賽姬死而復(fù)活的神話,來告訴基督徒如何認識耶穌基督,如何堅定自己的信仰,他們都期待基督教精神在西方的復(fù)歸,以便使“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圣經(jīng)·約翰福音》11:26)。筆者認為,正如C.S.路易斯在《納尼亞傳奇》中“以獨特的方式闡述了他的基督教思想”{6}一樣,《裸顏》的“故事性質(zhì)”即其宗教主題,小說作者將古希臘羅馬神話故事重新進行講述,其核心思想是他的基督教觀念。
C.S.路易斯改寫一則古代神話來傳達他的基督教信仰,因為他相信,神話就是真理,真理孕育于神話之中,神話是上帝創(chuàng)造的生動可感的故事,目的在于讓人類切實把握真理的內(nèi)涵,為真理所感動,最終接納真理。“道成肉身”事跡具有神話特質(zhì),人們?nèi)粢浞终J識其中所蘊含的啟示意義,必須在理性的認知方式之外,馳騁想象力,通過具體的故事情節(jié),入窺救贖的境界。{7}C.S.路易斯的寫作目的就是要為讀者提供一個具體可感的故事情節(jié),以便讀者從中體會到基督教的真實性。弗雷澤在《金枝》中列舉了世界各民族的巫術(shù)和宗教儀式,他指出,許多地區(qū)在近似的社會發(fā)展時期都曾存在過集祭司與帝王于一身的人物,他們具有半神半人的性質(zhì),信奉者認為他們能夠控制降雨、賜子、豐收等自然力,他們的生死和健康也直接影響到疆域中的臣民和一切牲畜、植物的命運。圍繞這些神圣帝王產(chǎn)生了一系列禁忌和儀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死而復(fù)生”。當他們身體健壯,植物繁榮,是夏季和雨季;當他們受傷、性能力喪失或死亡時,大地荒蕪、萬物凋敝,是冬季和旱季來臨;當神復(fù)活時,荒蕪的原野會萬物復(fù)蘇,重新開始一片繁盛景象,進入新一輪的循環(huán)。{8}C.S.路易斯正是這樣一名神話篤信者,他深信通過他的神話小說,這個“降臨在人類想象力上的神圣的真實故事”{9},讀者能獲得比日常生活中見到的事物更為深刻的真理,他用自己的方式重述丘比特與賽姬的故事,目的是為了闡釋他的宗教思想。
三、神話與信仰
C.S.路易斯改寫“丘比特與賽姬的神話”以傳播宗教觀念的做法,可以從他皈依基督教及護教的經(jīng)歷中找到思想淵源。C.S.路易斯在自傳中寫道:他幼年時對基督教沒有太深刻的認識,只是很自然地跟隨父母去教堂參加禮拜活動{10},他后來在貝爾森學(xué)校每周日參加兩次教堂活動,成為一名虔誠的教徒{11},但是在威爾文預(yù)科學(xué)校學(xué)習期間,受到神秘主義思想的影響,動搖了他的基督教信仰{12},開始大量閱讀古希臘羅馬神話、北歐神話、凱爾特神話等書籍。他于1929年在牛津大學(xué)重新接受有神論{13},在1931年皈依基督教,他將這段經(jīng)歷歸結(jié)為上帝的恩典:上帝在他崇拜“假神”的過程中培養(yǎng)了他對“真神”的崇拜能力,并使他將這種能力用于護教事業(yè)。他認為自己從北歐、肥腴月彎、愛琴海岸、尼羅河畔的神死而再生的神話故事中,聽見了基督耶穌“道成肉身”的中心信息,各族神話均是基督教的先聲,當基督從死里復(fù)活時,許多民族共有的神話則成了事實。因此,他立志要通過文學(xué)作品為讀者揭示這一神跡的歷史意義,從此開始了他的護教生涯。他將坎坷的經(jīng)歷、堅定的信仰、不懈的熱情、淵博的學(xué)識、深刻的洞見、嚴密的邏輯、清楚的語言、豐富的想象力等多種天賦集于一身,借助不同體裁的作品(神話、童話、書信、科幻小說、奇幻文學(xué)、通俗神學(xué)著作等)來傳達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信息,為基督教進行辯護和解說。
C.S.路易斯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服役,在“二戰(zhàn)”爆發(fā)時應(yīng)英國廣播公司邀請,于1942—1944年間,向英國皇家空軍發(fā)表演講,解釋基督教信仰,其演講稿后來結(jié)集成書,便是《返璞歸真》。他在該書《前言》中寫道:此書的目的不是要闡述“我自己”的宗教,而是要闡述“純粹的”基督教,那種不管我是否喜歡,在我出生之前就已這樣,現(xiàn)在仍然這樣的基督教。{14}他力求在《返璞歸真》中,幫助人們以一種新的眼光看待基督教,將它視為一種激進的信仰,如果人們敞開心靈,充滿想象力地改變自己的生命,邪惡就會減少,良善就會得勝,因為對他而言,信仰就像冉冉升起的太陽,他不是靠這信仰看到太陽,而是借著信仰能夠看見,并且第一次開始理解他所處的世界,信仰未見之事是比看見事物更好的接近神圣真理的方式。{15}
C.S.路易斯最主要的神學(xué)觀念即他對耶穌基督“道成肉身”“死而復(fù)活”事件的認識。關(guān)于耶穌基督的真實性,C.S.路易斯在《返璞歸真》一書中這樣寫道:“我們必須承認不只存在一種現(xiàn)實,必須承認在人這種特定的情況下存在某個東西,它高于并超出人類普通的行為,但又是絕對真實的。這是一個真實的律,不為我們?nèi)魏稳怂鶆?chuàng)造,卻左右著我們的行為。”{16}他認為,這個“律”不是由人們發(fā)明的,但是我們知道自己必須服從它。在很多時候,人們不能真正認識耶穌,就像“嬰兒起初吮吸母乳而不認識母親是自然的,我們看見幫助我們的人,而沒有看見他背后的基督,同樣也是自然的”{17}。基于此,C.S.路易斯認為,在基督教的核心理念中,耶穌的死讓人們與上帝和好,讓人們能夠從頭開始。《新約》講的不是一個兩千年前去世的好人的故事,它講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和你一樣是人,又和上帝在創(chuàng)世之時一樣是神的人。他確確實實來到世間,介入人的自我,使人變成一個全新的“小基督”,“一個在自身小范圍內(nèi)擁有和上帝同樣的生命、分享他的力量、喜樂、知識和永恒的存在”{18}。他認為“道成肉身”不只是隱喻,它從存在的視角表述為“上帝成為人”,從人類知識的視角表述為“神話成為現(xiàn)實”{19}。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神學(xué)思想對于C.S.路易斯來說是“詩”,這類詩只是信仰的結(jié)果,不是信仰的原因,或者說,他相信神學(xué),因而神學(xué)對他來說是詩,但并非因為神學(xué)是詩而相信它。{20}
C.S.路易斯相信耶穌基督確實為救贖人類而來到世間,他除了在宗教演講中宣傳他的基督教理念,也善于在文學(xué)作品中表達宗教主題。《裸顏》是作者以想象的方式,來向基督徒宣講“真理”的護教作品。《裸顏》通過講述奧璐兒的故事,想要人們不斷地反省自己的過錯和缺點,以便認識“神”。人在不知道自己傲慢的時候,最為傲慢,奧璐兒不是任何善惡力量的代表,而是每一個平凡人的代表,她對神的控訴是許多人在遭遇困苦時所做出的慣常反應(yīng)。當老國王在奧璐兒的夢中對她說:“這里沒有狐能救你,我們已經(jīng)下到連狐貍也挖不到的地方”{21}之時,C.S.路易斯意在表明,“上帝相對于其他人而言對某一部分人更多地彰顯了自身——不是因為更愛他們,而是因為對上帝而言,向那些觀念和特性都處于錯誤狀態(tài)的人更難彰顯自己。”{22}通過這則改寫的神話,C.S.路易斯希望讀者明白,是奧璐兒自己,而不是“神”向她隱匿了真相,在她眼里,世界上除了黑暗,別無其他事物,她拒絕信仰“神”,同時就會失去接受神的賜福的機會,只有當她揭去面紗真誠地對待“神”時,才能真正認識“真理”。
奧璐兒的故事雖然來自遠古時期,卻與我們當下的時代息息相關(guān)。她的故事每時每刻都在發(fā)生,奧璐兒本身更像是個現(xiàn)代人,她的墮落就象征著整個人類的墮落狀態(tài)。基督教作為C.S.路易斯思想的“三大柱石”{23}之一,使他得以運用大眾的語言,以極其浪漫、富有想象力的方式,講述和捍衛(wèi)“純粹的”基督教信仰,為讀者展示了一條通往“真理”的途徑。路易斯通過自己創(chuàng)造的文本世界不斷思考著關(guān)于絕對真理的問題,背后支撐這種思考的是他對基督教上帝的信仰,這個信仰就是路易斯小說的宗教主題。
四、親情之愛與神圣之愛
奧古斯丁在《論信望愛手冊》中指出:“愛是一切誡命的宗旨,上帝就是愛。”{24}究竟怎樣的愛才是真正的愛?神圣之愛與人類之愛區(qū)別何在?無私的愛與自私的愛有何不同?C.S.路易斯作為一位20世紀護教學(xué)家,在《四種愛》的“前言”中對人類的“給予之愛”(Gift-love)和“需求之愛”(Need-love)進行了區(qū)分。{25}他認為,一方面,人類的給予之愛比需求之愛更接近“神的愛”(Divine Love),“神的愛”的本質(zhì)也是給予,不是需求{26};另一方面,人類的需求之愛不應(yīng)該被完全否定為自私自利的表現(xiàn),一個孩子轉(zhuǎn)向母親尋求幫助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從來都不求助的人往往不是無私的人,而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冷漠和傲慢的人。{27}進而,C.S.路易斯指出,當人給予愛時,如果期待自己具有上帝的權(quán)威,就可能將愛轉(zhuǎn)化為恨;而人在渴求愛需要愛的時候,因為能意識到自己的軟弱,會比付出愛的時候更具有慈悲的心。他以“回家”為例來說明人如何在看似與上帝距離最遠時,卻具備上帝的部分特征:當一個人必須攀爬山路才能到達山下的家時,他在中途的一塊巖石上,發(fā)現(xiàn)自己離家很近,但他還需要走很長的路才能到家,而在余下的路途中,他會發(fā)現(xiàn)他離家很遠。但如果他一直坐在巖石上■望,他永遠沒有機會到家,只有在他看似與家距離很遠時,才有可能回到家。{28}人的給予之愛看似與上帝的給予之愛距離很近,卻絕不能使人成為神,人類的給予之愛不但與神圣之愛在本質(zhì)上存在著差別,而且它還有變成恨的危險。
在此基礎(chǔ)上,C.S.路易斯在《四種愛》第三章進一步說明“親情之愛”(affection)的特征。他認為,親情之愛這種“溫暖的情懷”不僅僅發(fā)生在親人之間,還可能“跨越年齡、性別、階級、教育背景等界限”{29}。大家都需要它,它是“最謙卑的愛”{30},不必大聲向別人說出來,也可以與其他愛交融,它制造人們的品位,教會人們?nèi)プ⒁狻⑷ト棠汀⑷ノ⑿χ鎸托蕾p那些碰巧在那里的人。但親情之愛不但不是幸福的充分條件,而且可能使人處于“不幸的危險”{31}之中,因為人們覺得自己有權(quán)利擁有它,得不到這種愛會使人憤怒;而且,當一個人在這方面為家人付出的愛越多,他們越以為自己無私,他們與神圣之愛的本質(zhì)就越相違背,因此,如果沒有一種更高級的愛介入其中,幫助付出愛者變得馴服,他就會淪為魔鬼。人生若以親情之愛作為絕對的主宰,以自我為中心的種子就會發(fā)芽生長,使人不再具有超越自我中心而向更高境界提升的可能性。“親情之愛”作為人類之愛的一種形式,不可避免地帶有變成邪惡行為的傾向性。
《裸顏》中奧璐兒與賽姬在祭神之前那個晚上的談話,能充分說明奧璐兒對妹妹的愛是一種“親情之愛”,這種愛雖然屬于“給予之愛”,卻使她不但沒有接近神圣之愛,反而使她更加遠離了人的自然本性。在這場對話中,奧璐兒表露出,她的最大愿望是不要失去賽姬,她不希望她們之間的親情之愛關(guān)系發(fā)生任何變化。賽姬一直在談她對死亡、對陰山、對婚姻的看法,追問這世界的根基是什么,追問死亡的意義,訴說她對陰山的憧憬之情:
它(陰山)是那么美麗,使我油然產(chǎn)生一種憧憬,無止境的憧憬。那里必有某 處地 方可以滿足我的憧憬。他的每一樣事物都在呼喚我:賽姬,來!……記得我們常常怎樣瞻仰它,渴望它?還有那些我編的故事——那座黃金和琥珀砌成的古堡,那么聳入云天……我們以為永遠無法到那里去……我一生中最甜蜜的事莫過于憧憬——憧 憬到陰山去,去找出一切美的源頭—— {32}
這時候,奧璐兒卻感道:
“我覺得我已經(jīng)失去她了。明天的獻祭只不過是為一件已經(jīng)開始的事作結(jié),她已 經(jīng)離 開我,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了……正當賽姬說著的時候,我覺得盡管我很愛她,卻抹不去心頭的一股怨恨。雖然,極其明顯地,她所說的這一切在此刻帶給她無比的勇氣和慰藉。我卻不要她有這勇氣和慰藉,這些就像梗在我們中間的厚障蔽。如果眾神是為這怨恨的罪棄絕我,我的確犯了這罪。”{33}
所以,盡管賽姬囑咐奧璐兒“千萬別讓悲哀堵住你的耳朵,使你的心腸變硬”{34},奧璐兒最后還是對賽姬說:“我只知道你從未愛過我,你盡管去神那邊吧,你已變得和他們一樣殘忍。”{35}并且,她認為:“(神)殺她(賽姬)還不夠,必須假借她父親的手;把她從我身邊奪走還不夠,必須奪走三次,讓我心碎三次。第一次是用卜簽定她的罪,然后是昨晚那番離奇、冰冷的談話;現(xiàn)在呢?用這副粉飾、俗麗的恐怖模樣,來毒害我對她的最后印象。”{36}這就是說,奧璐兒對賽姬的愛因此使她成為“魔鬼”,愛變成了惡的來源,以至于她認為萬般無奈之時,就可以干脆“殺掉她”{37},可見,這種親情之愛已經(jīng)遠遠背離了上帝之愛的本質(zhì)。正如賽姬所言:
“你的確讓我領(lǐng)教了一種我從未見識過的愛。那就像窺入一座幽暗的無底坑一樣。這種愛是否比恨好,我實在不知道。噢,奧璐兒——你明知我對你的愛,明知它根深蒂固,不會因任何其他新起的愛而稍有減退,便利用它作工具、武器、策略和折磨人的刑具——我開始覺得自己從未了解過你。不管以后發(fā)生什么,你我之間的情誼算是就此斷絕了。”{38}
C.S.路易斯認為,賽姬的死,“不是神圣的愛取代了自然之愛(仿佛我們需要把銀子扔掉,騰出地方放金子似的),而是自然之愛應(yīng)召充當神圣之愛的形式,同時仍然保持了原來的自然之愛”{39}。而奧璐兒因為對賽姬的愛沒有達到神圣之愛的高度,她錯誤地唆使賽姬去看丘比特的面孔,這就像伊甸園中的蛇,誘惑夏娃去吃禁果,使她犯了原罪,給自己和后人的命運,帶來無窮的災(zāi)難。奧璐兒不懂如何愛上帝和如何愛人,她認為“我們要自己做主。我屬于自己,而賽姬屬于我,任何其他人都沒有權(quán)利占有她”{40},因而使自己和自己所愛的親人都遭受到困難,賽姬的親人實際上成了賽姬“最危險的敵人”{41}。奧璐兒與《圣經(jīng)》中約伯的共同之處在于,他們都不明白自己為何經(jīng)受那么多苦難,并曾經(jīng)一度埋怨上帝為什么不給她以啟示。奧璐兒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刻才明白:她只有在真正面對自己時,才能從上帝那里得到啟示。{42}
C.S.路易斯是個折中派,既認為苦難是上帝對惡人的懲罰,也認為苦難對好人有積極意義,人因受苦難而得完全,上帝利用苦難這種簡單的惡來達到自己救贖人類的目的,成就復(fù)雜的善;人對苦難的接受,對罪的懺悔,都有助于成就復(fù)雜的善。神圣之愛與仁慈不同,后者希望對方快樂,前者希望對方完美。上帝寧可讓人受苦而變得完美,也不讓人無條件地快樂,苦難使人完美,糾正純粹本能的愛的唯一辦法,是拿走這種本能的愛的對象,使人類之愛接受手術(shù)治療。苦難是唯一糾正人之愛的錯誤的方式,所以奧璐兒愛賽姬,上帝卻將賽姬帶走,使奧璐兒的親情之愛失去對象,使她經(jīng)受苦難,使她在痛苦中得以認識神。苦難不僅是一個人類無法解決的問題,還是一個人所無法了解的奧秘,人的理性不足以使他完全認識苦難,基督徒只能憑著對上帝的信心,接受上帝的全部贈予。
《裸顏》通過奧璐兒的苦難經(jīng)歷,告訴讀者:“在快樂中上帝對我們低語;在良心中上帝對我們說話;但是,在苦難中上帝對我們吶喊——苦難是上帝用來喚起耳聾者的世界的喇叭筒。”{43}小說的主人公奧璐兒在歷經(jīng)磨難之后,才會明白親情之愛與神圣之愛的區(qū)別,從而達到重新認識自己的信仰的目的。“愛”是一個重要且含義深刻的哲學(xué)和宗教命題,C.S.路易斯在小說中以重述神話故事的方式來闡釋他的相關(guān)觀念,具有震撼讀者心靈的作用。
五、結(jié)語
在以上的論述中,筆者主要根據(jù)路易斯的兩部基督教理論著作——《返璞歸真》和《四種愛》——嘗試解讀他通過改寫“賽姬和丘比特的神話”所呈現(xiàn)出來的關(guān)于“信仰”和“愛”的基督教觀念。需要說明的是,無論C.S.路易斯的宗教立場如何,他始終是一位成功的作家,他在《裸顏·后記》中并未明確說明這則重述的神話故事的主題是基督教信仰,而且他在全書中多次提及他對寫作的態(tài)度:全書開篇借奧璐兒的筆寫道:“我老了,并不十分恐懼神對我發(fā)怒……既然沒有恐懼,在本書中我將直言不諱,寫下那些幸福的人不敢寫的事情。”{44}第一部分結(jié)尾聲稱自己要趕快返回家中,寫完她的書,“必須在諸神設(shè)法叫我保持沉默之前迅速寫完”{45};第二部分第一章提道:“我要從頭開始重寫這本書……正是寫作這個行為改變了我所有的態(tài)度”{46};以及全書末尾的一小段話:“我,亞瓏,阿芙洛狄特的祭司,保存了這本書,把它收藏在寺廟中”{47},等等。這些語句都可以理解為C.S.路易斯在創(chuàng)作《裸顏》時,他首先是要寫一本小說,而不是在履行傳播基督教的義務(wù)。而且因為他相信“作者未必比讀者對于故事的含義有更為深刻的理解”{48}。本文解讀《裸顏》宗教主題的目的,在于引起更多讀者對路易斯著作的關(guān)注,包括關(guān)注他的文學(xué)作品、宗教作品和學(xué)術(shù)專著。
參考文獻
{1}{3}{21}{34}{35}{37}{38}{40}{41}{42}{44}{45}{46}{47} C.S.Lewis, Till We Have Faces: A Myth Retold, San Diego, New York, London: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85, p311, p313, p275,p75, p76, p137, pp291-292, p304, p294, p3, pp247-248, p253, p308.
{2} [美]伊迪絲·漢密爾頓:《神話——希臘、羅馬及北歐的神話故事和英雄傳說》,劉一南譯,華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頁。
{4} [古羅馬]盧齊伊烏斯·阿普列尤斯:《金驢記》,谷啟珍、青羊譯,北方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144頁。
{5} 劉意青:《圣經(jīng)與文學(xué)闡釋——理論與實踐》,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4 年版,第105頁。
{6} 張■:《〈納尼亞傳奇〉中的〈圣經(jīng)〉原型再現(xiàn)與C.S.路易斯的基督教兒童觀》,《西華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4年第7期。
{7}{32}{33}{36} [英]C.S.路易斯:《裸顏》(第2版),曾珍珍譯,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版,《譯者序》第3頁,第70—72頁,第71頁,第76頁,第161—162頁。
{8} [英]詹姆斯·喬治·弗雷澤:《金枝》,徐育新、汪培基、張澤石譯,大眾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473頁。
{9} C.S.Lewis: Miracles: A Preliminary Study, New York: Macmillan, 1965, p139.
{10}{11}{12}{13} C. S. Lewis: Surprised by Joy,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16, p6, p36, p68-70, p266.
{14}{16}{17}{18} [英]C.S.路易斯:《返璞歸真》,汪詠梅譯,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頁,第35頁,第186頁,第187頁。
{15} David G. Clark, C. S. Lewis: A Guide to his Theology,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pp120-121.
{19}{20} [英]C.S.路易斯:《神學(xué)是詩?》,載:《榮耀之重——暨其他演講》,鄧軍海譯,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6年版,第147頁,第137頁。
{22} C.S.Lewis, Mere Christianity, London:Collins,1977, p140.
{23} 汪詠梅:《理性、浪漫主義和基督教——C.S.路易斯神學(xué)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2-63頁。
{24} [古羅馬]奧古斯丁:《論信望愛手冊——致勞倫修》,載《論信望愛》,許一新譯,讀書·生活·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9年版,第115頁。
{25}{26}{27}{28}{29}{30}{31}{39} C. S. Lewis: The Four Loves, San Diego;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0, p11, p11, p13, p16, p54, p56, p60-62, p183-184.
{43} C. S. Lewis. The Problem of Pai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2,p93.
{48} C. S. Lewis: Letters of C. S. Lewis, W. H. Lewis ed., New York & Lond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6, p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