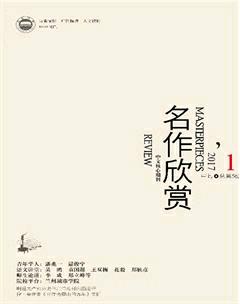縫隙中的掙扎
施海淑
摘 要:諶容的《人到中年》展現了四十二歲的眼科骨干女醫生陸文婷在年齡的縫隙、性別身份的縫隙中無奈掙扎的工作與婚姻家庭生活,討論了中年知識分子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所遭遇的尷尬、窘境。雖然涉及女性的工作與婚姻家庭,但《人到中年》從文本的表達手法到對陸文婷在種種縫隙中掙扎的描述,都顯示這部小說關注的更多的是“中年知識分子”的問題,而不是“女性”的問題。
關鍵詞:《人到中年》 陸文婷 縫隙
《人到中年》是諶容在新時期最受矚目、備受贊譽的小說。對于這部小說,最一般的評價就如它的題目所提示的,落腳點首先都放在“中年”上。確實十分明顯,這部中篇小說最大的篇幅所涉及的除了主人公中年眼科大夫陸文婷,就是陸文婷的丈夫、專攻金屬力學研究的傅家杰,以及先是她的醫學院同學再是醫院同事的好朋友姜亞芬和同樣是大夫的姜亞芬的丈夫劉學堯。當然,幾乎所有的評論都不可忽視的是,小說最重要的主人公是陸文婷。實際上,小說的展開,就是從陸文婷心肌梗塞暈倒躺在醫院病床上的朦朧不明、飄忽不定、明暗不分的感覺開始的。而恰恰就是那些不明、不定、不分的灰色地帶,清晰地映刻了“陸文婷”無奈的掙扎。
正如郜元寶在1995年就已經正確指出的:“盡管思想批判的光芒時隱時現,盡管被揭露的生活真實常常像陸文婷的眼科手術那樣,如履如臨,小心翼翼,割開了又縫合,縫合了又割開,盡管一切都似乎融化在東方女性輕輕的嘆息、溫柔的責怪和堅韌的承受之中,盡管整篇敘述始終顯得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我們還是感到了一個挺立的批判主體的存在,甚至好像可以看到作者滿臉的憤激和憂色。”{1}
《人到中年》立體地展示了陸文婷(們)在種種縫隙中的窘境:作為醫術精湛的眼科醫生,陸文婷用她的手術刀切開了眼疾患者的眼睛,又用針線縫上,給他們帶去光明;作為心肌梗塞病人,放下手術刀的陸文婷在用另一把“手術刀”切開了女性知識分子的生活后,在那些或寬或窄的縫隙中,卻束手無策,無所適從。
一、在文本的縫隙中
確實,《人到中年》是從描述躺在病床上的陸文婷大夫的意識開始的,具有十分鮮明的“意識流”小說的特征。但是,《人到中年》又有著與一般的,也就是那種從始至終使用“意識流”結構布局的小說不同。而結構布局的不同所造成的“縫隙”又滲透、泄露出更多文本深層的意涵。
按照較早使用并且創作了成功的“意識流”作品的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的觀點以及萊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等一些評論家的觀點,作為一種“現代派”文學創作的典型手法,“整個所謂‘意識流運動就是從經過夸張的男性文學向某種女性文學的復歸。只要小說內容從室外轉向室內,從野外轉向深閨,從逃婚轉向相愛,從行動轉向思量,從理智轉向情感,女性‘第一人稱(persona)都成為不可或缺的代言人,甚至在男性作家的小說里也是如此。而且,與小說最初興起的那些年代一樣,女性小說家占據著首要地位”{2}。蘇珊·S.蘭瑟(Susan Sniader Lanser)在那本著名的《虛構的權威——女性作家與敘述聲音》(Fictions of Authority : 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中除了提出她有關“意識流”的另外一個方面的意義的補充之外,也從敘事學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弗吉尼亞·伍爾芙等人對“意識流”的觀點,并十分明確地提出:“‘女性聲音——在她的論述中指‘敘述者語言形式上的性別——‘實際上是意識形態斗爭的場所,這種意識形態張力是在文本的實際行為中顯現出來的。”{3}在并不完全使用“意識流”手法的《人到中年》里,蘇珊·S.蘭瑟所謂的“張力”顯得愈加顯著。
《人到中年》一共有二十二章,除了第二十一章是對即將出國的姜亞芬在飛機場寫給陸文婷的信的“引用”之外,其余的二十一章除了個別段落的穿插之外,從敘事的手法角度而言大致可以分為兩類:“意識流”敘事——第一、三、五、十一、十七章;“第三人稱”敘事——第二、四、六、七、八、九、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章。
一共有二十二章的《人到中年》講的主要是陸文婷在心肌梗塞暈倒之前的三天里的種種經歷:既有在單位里與各種病人以及病人家屬的交往,又有與同事、好朋友姜亞芬、劉學堯的飲酒夜談,更有與丈夫傅家杰、兒子圓圓和女兒佳佳的家庭生活的碰撞。“意識流”敘事的部分是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的陸文婷對種種親身經歷的回憶、感受、評價;而“第三人稱”敘事部分則是對那些種種經歷的敘述,也包含對傅家杰、姜亞芬、劉學堯、孫逸民、趙天輝、秦波、焦成思等人的感受、評價、判斷等。
綜上所述可見,《人到中年》雖然是以陸文婷的“意識流”結構文本的布局,但卻又有明顯多于“意識流”部分的“第三人稱”敘事部分:如果說,“意識流”是具有女性性別意識——明顯或暗示——的表達手法,那么,“第三人稱”的敘事,則是公認的最根深蒂固、不言而喻的具有“男性中心主義”色彩的手法。就此層面而言,實在很難說《人到中年》是一個具有明確的、堅定的女性(主義)意識的文本。但是,兩種寫作手法的交織使用又是如此確然,與其去尋求彌合兩者間的鴻溝,從而不可避免地遮蔽它本來就被隱藏起來的矛盾,不如將兩者間的縫隙撐大,從而發現揭示矛盾甚至解決矛盾的可能方法。
確實,正如《人到中年》這個題目已經暗示的,在兩種寫作手法交織又沖突的表達中,陸文婷(們)的種種生活被撕開了或大或小的縫隙。
二、在年齡的縫隙中
“中年”確實是一個尷尬的年齡段,無病無災的年月,也許還能好點,那些20世紀五六十年代大學畢業然后走上工作崗位又經歷過劫難的、在1979年的“中年”又是怎樣的呢?
陸文婷,1961年24歲醫學院畢業,成為孫逸民主任眼中“很有希望”的眼科大夫;1979年,她42歲,已經成長為醫術過硬的骨干,但不僅不是“主任大夫”,甚至還不是“主治大夫”,她還和十八年前一樣是“住院大夫”。因此,陸文婷一個月的工資還是56.5元——不僅與高檔物品無緣,甚至雞、魚、花生和瓜子這樣普通的生活必需品都只能視而不見;一家四口住在十二平方米的房子中,家里唯一的一張三抽屜書桌給兒子用來寫作業,她和傅家杰除了趴在床邊的箱子上就再沒有地方可以看書、寫論文了;她在門診和病房之間輪崗,除了需要專心致志給病人治療,還要應付挑剔、跋扈、自私的高干夫人秦波。
與副部長焦成思的夫人秦波的接觸,最能看出陸文婷的尷尬處境:第一次在醫院院長趙天輝的辦公室見面,秦波就毫不客氣地打量陸文婷,一句話沒說,就毫不掩飾地表現出疑慮、不安和失望,接著“客客氣氣”地攔住了準備給焦成思做檢查的陸文婷,然后開始盤問陸文婷參加工作的時間、身體狀況、對手術的把握等問題,盡管趙天輝在旁邊極力推薦,都沒能消除她的偏見。
焦成思住進醫院以后,秦波與陸文婷第二次見面。秦波向陸文婷提出要給焦成思裝外國生產的人工晶體,當陸文婷說那樣的手術還在試驗階段時,秦波馬上就又改變主意了——她怎么會同意在焦副部長身上做實驗呢?當陸文婷表示焦部長的手術只是一般的手術沒有必要按照秦波的要求“采取措施”時,秦波不高興了:“我的同志喲!不要輕敵嘛,咹?輕敵思想往往造成失敗,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有過的……”{4}怪不得孫逸民叫她“馬列主義老太太”:對人總是輕辱的態度、滿心全是自私的打算卻又習慣地常常以“我的同志喲”表示“親切”,以“我們黨”“組織”“人民”“領導”“革命”等來掩飾個人的目的。陸文婷既沒有將給部長、主任等動手術看作是什么無上的光榮,也沒有將秦波的侮慢放在心里。每一次無聊的談話中,陸文婷可惜的是對時間的浪費和對工作的耽擱,但是她明白焦成思也是病人,對待病人她的態度是一樣的——“文革”時的“叛徒”焦成思是她認真手術的病人,現在的“副部長”焦成思也是她認真手術的病人,他和從農村大老遠來的張大爺以及膽小嬌氣的小姑娘王小嫚沒有什么不同。
陸文婷的丈夫傅家杰雖然沒有那么多需要應付的難纏的人,但在很多方面和她也是一樣狀況:眉清目秀,但是頭發卻禿頂了,額頭上也長了皺紋;度過了漫長的“科學、技術、知識統統打倒”的歲月,被造反派封閉的實驗室又打開了,被取消的研究項目又被列為重點了,他又成了大忙人,但他的家,卻依舊沒有空間放下一張書桌。堅強、體貼的妻子為了讓他有個安靜的環境安心研究,不得不提出了“分居”的建議——讓他搬到研究院去住,把耽擱的“十年”補上,把“八小時變成十六小時”。
這樣一對中年知識分子夫妻,他們為了“做出新的貢獻”需要刻苦鉆研,不斷提高業務水平,還需要照顧上小學的兒子和在托兒所的女兒,帶著孩子忍受很差的生活環境,載負沉重的生活重擔。盡管他們總是那么樂觀、隱忍、堅持,但是他的禿頂、皺紋,她突然的心肌梗塞卻將他們背后的艱辛、困難、苦澀等都呈現了出來。只有在各種壓力將人壓垮、倒下的時候,人們才稍稍有所意識,但那又能怎樣呢?
當醫院院長趙天輝在陸文婷的病床邊看到傅家杰的禿頂和皺紋時,他的判斷是:“看來,他不大會保養身體,當然也就不會知道怎樣愛護自己的妻子。”⑤醫院院長趙天輝怎么會知道傅家杰在北海給陸文婷念詩的浪漫、在家為她用塑料布隔出小“書房”的體貼、他去了單位但因不放心家里又回來的關心呢?他又怎么會知道這個傅家杰,既精通兩門外國語又擅長各種家務呢?院長趙天輝讓科室主任孫逸民調查中年大夫的工作情況、收入情況、生活情況、住房情況,并“做個材料”給他,可是,那有什么用呢?他留給孫逸民的是四六不著的承諾:“我拿了它去找市委,找衛生部去,見廟就燒香,見神就磕頭。求爺爺,告奶奶,也要把這張狀子遞上去。中央三令五申,要珍惜人才,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改善科技人員待遇,總不能到了下邊就變成一句空話吧!前天還傳達市委開會的精神,要重視中年干部。我還是相信,有辦法的,會解決的。”⑥
趙天輝的“承諾”就像秦波對一個早上連做了三臺手術又趕回家給孩子做飯,最后終于心肌梗塞倒下的陸文婷的“安慰”一樣:“你想吃什么,缺什么,有什么困難,盡管告訴我,我們幫你解決,不要客氣,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你還年輕,要樂觀些。對待疾病嘛,既來之,則安之……”⑦她又批評趙天輝:“趙院長,我是官僚主義,不了解情況,你怎么也不了解情況喲……趙院長,我可要給你們提個意見呀,像陸大夫這樣的人才,怎么平時不關心,讓她病成這樣呢?中年干部,現在是我們的骨干力量,我的同志喲,要珍惜人才呀!”⑧秦波自己又是怎樣的“關心”“珍惜”骨干力量的中年干部呢?
陸文婷、傅家杰還有和他們同齡的姜亞芬、劉學堯就是在這樣的“中年”縫隙中苦苦堅持、掙扎的。
三、在性別身份的縫隙中
中年知識分子的處境是尷尬的,除了在工作上的遭遇,還有來自家庭婚姻生活的重負:最常見的狀況是上有父母需要贍養孝敬,下有孩子需要撫養教育,生活中的一樁樁一件件大大小小事情,都需要付出精力與時間。陸文婷和傅家杰最需要照顧的是他們的兒子圓圓和女兒佳佳。
在那些不能正常工作的時候,傅家杰承擔了所有的家務,除了不會納鞋底,其余縫紉蒸煮等家務他都學會了,成了技藝嫻熟的全能“家庭婦男”,這倒能減輕了陸文婷的負擔——幸?抑或不幸?但他恢復工作之后,原來的家務活自然就落在了陸文婷身上:工作日里的中午,陸文婷放下手術刀脫下白大褂緊接著就要拿起切菜刀系上藍圍裙,生火做飯的所有步驟要在五十分鐘里完成,才能保證下午圓圓準時到校,她和傅家杰準時到崗。這還是最好的狀況,碰上突發事件,按部就班的生活節奏就會被打亂,就有可能影響到每個家庭成員的學習、工作。然而,意外總是不可避免,甚至總比想象的要多,要麻煩。
盡管托兒所早早就來電話告知陸文婷佳佳發燒了,但放下電話接診病人之后,她很快就把佳佳忘在了腦后,等到下班了她才想起來。當她趕到托兒所時,連阿姨都忍不住抱怨起來。陸文婷在托兒所的隔離室看到佳佳:“一個人冷冷清清地躺在小床上,她的小臉蛋燒得彤紅,小嘴唇兒張著,小鼻子吃力地閃動著,眼睛卻閉得緊緊的。”⑨有哪個母親看到自己的孩子病成這樣而不心疼呢?等她把佳佳帶到醫院打了針,取了藥再回到家時,已經快一點了,而圓圓也在焦急地等著她做午飯呢。圓圓的催促讓她更加心煩意亂,吼了圓圓之后,看到圓圓眼里打轉的眼淚兒又讓她覺得內疚起來。早上煤塊存的火一時是上不來了,又沒有剩飯剩菜,她只能讓圓圓到外面買燒餅充饑了……佳佳呢,她要上班了,她是多么不愿意再去麻煩院子里的陳大媽幫忙,但是她又怎么忍心再把生病的佳佳抱去托兒所呢?
陸文婷從來不懷疑自己的工作能力,她鉆研業務、認真細致,不僅有高度的責任心,而且有極大的勇氣。在她還很年輕的時候,在等級森嚴的醫院,她就敢提出對門診大夫的診斷不一樣的意見;在那個動亂的時期,造反派沖進醫院,她一絲不亂,鎮定地將干擾擋在手術室外,因為這件事而給派上“包庇叛徒”的罪名,她都沒往心里去;現在,在對待秦波那樣難纏的家屬時,她也不卑不亢。但是,對于婚姻,對于自己在家庭中妻子和母親的身份她卻常常有疑問,有顧慮:“或許,一生的錯誤就在于結婚。不是人常說嗎,結婚是戀愛的墳墓。那時候,自己是多么天真,總以為對別人說來,也許是如此。對自己來說,那是絕不可能的。如果當時就慎重考慮一下,我們究竟有沒有結婚的權利,我們的肩膀能不能承擔起組成一個家庭的重擔,也許就不會背起這沉重的十字架,在生活的道路上走得這么艱難!”⑩當初談戀愛的時候,陸文婷也曾發自內心的感慨過:“愛情竟是這樣的迷人,這樣的令人心醉!她簡直有些后悔,為什么不早去尋求?”{11}后來的家庭生活中,傅家杰疼愛她、體貼她、理解她、尊重她、支持她,想方設法為她在狹小嘈雜的環境中辟出一個學習的空間,也從不抱怨她對工作的全力以赴。兩個孩子也都那么聽話,沒有給她增添什么額外的麻煩。但是,陸文婷卻依舊免不了因為分身乏術而對自己承擔妻職、母職的能力產生懷疑。在那些她為了加班研究的傅家杰能專心工作而裝睡的深夜,在那些她焦頭爛額地奔波于醫院和家庭之間的短暫的中午,在那個姜亞芬夫婦來告別、傅家杰半開玩笑地“發牢騷”的夜晚,在那個佳佳生病圓圓挨餓的中午,她自責、自怨、自艾的情緒更加濃重。沉重的現實負擔和心理負擔終于把陸文婷壓垮了,在做了三臺手術之后匆匆趕回家的路上,她因心肌梗塞倒下了……
躺在醫院病床上的眼科大夫陸文婷,在模糊的意識中回憶和掛念的,除了那一雙雙在她手術刀下被治愈的眼睛,還有傅家杰的眼睛和他念的詩,還有圓圓一直想買一雙白球鞋的心愿,還有佳佳一直想扎著小辮去托兒所的心愿……然而,即使在那樣的生死關頭,她也依舊顧慮重重:緊接著圓圓想要的白球鞋而來的,是寫著三元一角、四元五角、六元三角……的標價牌;緊接著佳佳想扎的小辮而來的,是“她沒有時間,星期一早上醫院的病人也最多,哪怕一分鐘的時間,對她來說都是寶貴的”{12}。什么時候,陸文婷才能全心全意地做那些她早想對丈夫、兒子、女兒做的事情呢?
比起工作中的“游刃有余”,家庭生活對陸文婷來說,真是舉步維艱。如果說對工作中遇到的困難,作為大夫的她總有面對的信心與能力,那么對家庭生活中遇到的困難,作為妻子和母親的她可顯得太無奈,太無力了。
就是在“大夫”和“妻子”“母親”的縫隙中,陸文婷既無法選擇,又無法應對,當然,并不是她不愿意勇敢面對,不愿意盡力解決。佳佳生病不想去托兒所時,她都不愿意打電話給傅家杰,是怕占用傅家杰的工作時間;傅家杰合上書本不再使用臺燈怕影響她的休息時,她說服傅家杰住到研究院把耽擱的研究恢復起來——她是多么需要傅家杰的共同承擔啊,卻又不得不做出那樣的決定。對于一個人來說,那些實在是太過沉重的負擔了。
不少評論者認為,《人到中年》是一個“女性文本”。確實,《人到中年》所體現的掙扎是那么的明顯,不僅是陸文婷的掙扎,更有諶容的掙扎。諶容遙接“五四”時期廬隱、冰心、丁玲等對“新女性”問題的關注,又對當代女性的困境有著深切的體驗和深入的觀察,試圖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但是如果說,“女性文本”意味的是“以女性為中心”,那么《人到中年》實在很難稱得上是一個“女性文本”。就表達手法而言,它并沒有自始至終使用性別色彩濃烈的“意識流”,反而更多的章節采用的是“第三人稱”敘事的手法;就內容而言,它用于“知識分子”的筆墨也遠遠多于用于“妻子”“母親”的筆墨。它確實涉及了“女性”身份的問題,但是,即使是20世紀80年代最激進的中國女性主義研究者都沒有像歐美的女性主義者那樣提出完全拋棄妻子、母親的身份,更何況是聲稱自己很“傳統”的諶容,是不可能與后來的女性主義寫作者有一樣的思考與表述。也許,這就是戴錦華在探尋“新時期文化資源與女性書寫”時,認為“諶容的《人到中年》則率先以知識分子待遇的社會問題書寫,成為‘尊重知識‘科技興國等主流話語的先聲”的原因吧。實際上,《人到中年》也確實如戴錦華在評價整個20世紀80年代女作家的作品時所說的那樣:“女性角色的性別自我不僅朦朧曖昧,必須覆之以‘人性‘靈魂等超越性的光環……”{13}
{1} 郜元寶:《〈人到中年〉簡評》,《當代作家評論》1995年第3期,第101頁。
{2} [美]蘇珊·S.蘭瑟:《虛構的權威——女性作家與敘述聲音》,黃必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X頁。
{3} [美]蘇珊·S.蘭瑟:《虛構的權威——女性作家與敘述聲音》,黃必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頁。
{4}{5}{6}{7}{8}{9}{10}{11}{12} 諶容:《人到中年》,《諶容小說選》,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236頁,第205頁,第204頁,第273—274頁,第274頁,第215頁,第221頁,第189頁,第267頁。
{13} 戴錦華:《新時期文化資源與女性書寫》,見葉舒憲主編《性別詩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