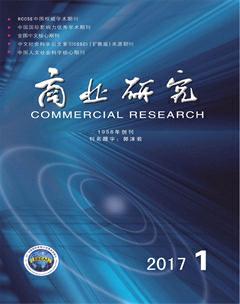北歐區域貿易研究相關學科路徑述評
劉程
內容提要:19世紀政治經濟學家搜集、整理史料的工作填補了傳統貿易史研究的空白,但其在理論分析上的缺陷又招致經濟學家批判。古典經濟學派繼而提出“自然稟賦理論”來解釋交易行為的分工基礎,新古典經濟學派則將貿易模式的持續變革引向“要素積累與成本理論”。晚興的制度經濟學派發現貿易參與者制度建設方面的特殊效用后,試圖通過“產權論”、“聲譽機制”等理論重新闡釋貿易行為。隨著新史學興起,史學家對經濟學的建構范式也提出質疑,并提出比較文明及整體史觀的研究路徑。但是,在當前區域貿易研究中實現各學科路徑的有效整合并非易事。或許只有堅持歷史邏輯為前提,將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全面把握研究視角才能更深入理解貿易互動影響下的區域文明。
關鍵詞:北歐;區域貿易;政治經濟學;經濟學;新史學
中圖分類號: F0-08;K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148X(2017)01-0100-08
當代貿易經濟學家馬克·卡森(Mark Casson)以關鍵事件為節點將歐洲國際貿易史概分為三大時段:中世紀至1800年(工業革命)為第一時段;1800至1945年為第二時段;1945年至今為第三時段①。其中,后倆時段(特別是第三時段)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而對時間上最漫長、最具基礎性影響的第一時段卻關照不足。事實上,第一時段在學術價值上的重要性并不亞于后兩個時段。第一時段處于歐洲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渡期,此時貿易模式的沿革、成熟已成為歐洲資本主義的重要部分。正是政治經濟學家(傳統史學家此時正關注政治制度史)對“資本主義主題”的早期探究率先開啟了歐洲區域貿易研究的大門,此后新史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紛紛介入。各學科的多元分析路徑不僅反映出該領域的深入程度,同時還展現出方法論上的幾次關鍵轉向。當前,北歐一體化的復雜因素引起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和考古學界的持續關注,但各學科長久以來的獨立研究反而破壞了北歐的整體性概念。學科內部的深化、碎化造成的學術壁壘令學科知識共享、交流成為空談,難以形成體系化認知。另外,當前史學(同樣包括其他學科)研究中提倡的“跨學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在于突破單一學科的陳規舊俗或正統范式的束縛。這要求史學工作者能夠精通多個學科。但現實情況卻常是所有史學家都不得不在本學科內完成研究工作,只將其他學科的某些理論和方法納入自己的研究當中,從多個學科中汲取創見和觀點。在此情境下,“跨學科性”名不副實,只能稱其為“多學科性”[1]。因此,打破這種名不副實,實現跨學科性與學科性的最佳結合就成為當前史學研究的任務之一。本文旨在對北歐貿易研究中主要學科相關理路的梳理與評述,嘗探擺脫此困境之路。在追溯這一多元分析路徑之前,有必要先對部分概念作以界定。
首先,本文的“北歐”與現代政治地理概念上的“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有所區別,此處泛指北海-波羅的海沿岸的所有國家和地區。自西向東包括比斯開灣沿岸、不列顛、法國北部、低地國家、德意志北部、斯堪的納維亞各國、波蘭、條頓騎士團轄地(現在的波蘭北部、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立陶宛以及俄國西北各省。該區域內的主要商業城市有: 倫敦、布魯日、安特衛普、阿姆斯特丹、卑爾根、科隆、呂貝克、漢堡、不萊梅、但澤、維斯比、里加、諾夫哥羅德等。當代史學家習慣稱該區域為歐洲的“北方地區”(Northern Land)或“北部歐洲”(Northern Europe),本文為便于論述仍稱為“北歐”。
其次,中世紀的北歐是否可視為一個“區域”? “區域”(region)作為一個一般性概念,是根據不同需要(如管理、規劃、研究、描述等)在地表劃出的可用性地理單元。經濟學通常把“區域”理解為一個經濟上相對完整的經濟單元。中世紀以來,北部歐洲以北海-波羅的海為軸線逐步實現了各王國、地區和城市在貿易、政治及文化上的交流。12世紀以后這種交流速度加快,往來頻繁,貿易規模和范圍不斷擴大,初步構建起海上貿易網絡,進而形成常態化的貿易區。14、15世紀,北歐貿易網絡繼續完善,區域一體化特征明顯,各王國、地區、城市和商人間的聯系更為緊密,不僅形成了共同的市場體系,同時還兼具了相近的宗教、文化、習俗和觀念,正是這種一體性構成了北歐的“區域”概念。因此英國學者大衛·尼古拉斯就將此時的北部歐洲稱為“日耳曼化”的經濟區域[2]。
一、政治經濟學的早期實踐
19世紀中葉以來,當傳統史學關注政治制度而忽略貿易之時,歐洲的政治經濟學家已開始其早期探究。國際貿易的主要參與者在中世紀末期先后發展成為歐洲諸強國,從而進入政治經濟學家的視野。直至當代,在傳統規范分析之外產生的以實證分析為主要路徑的內生貿易政策理論仍被稱為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3]。但該學科的研究重點并非針對區域貿易的歷史作細節性探究,更多是分析經濟行為,歸納理論以服務現實政治。
國內的政治經濟學說始于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著作,但西方政治經濟學說史的開山著作要遠早于此(以法國重商主義者A蒙克萊田在1615年出版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為始)。其中最系統的著作當屬法國學者布朗基于1837年所著的《歐洲從古代到現代的政治經濟學史》[4]。他在該書前言中指出:古代之有政治經濟學如近代之有政治經濟學一樣,雖然古代經濟思想在表述上缺乏系統性,但都是從事實與實踐中產生的[5]。他鼓勵從歐洲無限的經濟史料中發掘思想,提煉理論以服務當下。特別要關注近千年來的跨國貿易行為,它對一國政治文明的演進意義重大。19世紀中葉以后古典政治經濟學走向成熟,研究重點開始轉向生產領域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強調國家與市場的關系:經濟力量影響著國家的政治、軍事力量部署,后者則為前者提供支持。但國家或市場作為單獨一方都不占主要地位,最重要的還是它們之間的聯系、互動以及周而復始的變化,它們成為歐洲文明互補的兩個重要方面[6]。這種由經濟依存建立起來的權力關系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征。因此對歐洲貿易的整體研究就隱含于國家與市場關系的政治經濟學中,至今仍是國際貿易研究的主題之一[7]。
進入19世紀晚期,德意志歷史學派的著作和觀點成為西方政治經濟學主流。他們提倡歷史分析方法,將研究對象以政治-經濟史的內容展現出來。其中大量著作皆涉及古典以來的北歐貿易。如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對歐洲貿易的主要參與者(商人、商業城市和現代國家)分國別作過論述[8]。威廉·羅雪爾在《國民經濟學的歷史方法概要》和《國民經濟學體系》中提出:政治學要研究國家發展的規律,經濟學則需探求經濟發展的規律……必須采用歷史和比較的方法才能發現支配經濟生活的基本規律。而只有通過比較各國歷史的異同才能發現這些規律。他指出必須使用歷史方法來重新研究政治經濟學,認為政治經濟學不應當限于研究現代的經濟制度,還必須搜集和研究大量的“歷史材料”,特別是古代的歷史資料,而且要研究作為個體和整體的,過去與現在的國民生活。另外,一國參與國際貿易的行為是國民經濟活動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對于近代大國的崛起之路,都可以從它們參與國際貿易的歷程中探尋到蹤跡[9]。 G 施穆勒部分地繼承了羅雪爾的觀點,同樣認為歷史分析為政治經濟學的必經之路[10]。同時代的德意志學者迪特里希·施艾弗爾在其著作《歷史學的原初活動范圍》中也作出呼吁:“史學的領地”應當是政治,而非其他,但貿易的影響決不可忽視[8]。雖然法國政治經濟學家讓·巴蒂斯特·薩伊堅持認為,“與國內貿易相比,所有國家的國際貿易的數量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卻無法否認海運貿易對促進國家財富增長的重要性。他最終妥協似地寫道:在共同利益基礎上的國際貿易“可以發展國與國之間的友誼,擴大國與國之間的往來,產生永恒的繁榮”[11]。
總之,羅雪爾、施穆勒等學者大力倡導并躬身實踐于搜集史料的活動實現了政治經濟學與歷史學的結合,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更多是在填補當時傳統史學家的學術空白。但早期政治經濟學家忽視理論分析和概括的現象又導致其著作幾乎完全衍為經濟史料的堆砌,為此廣受經濟學家批評,后者則致力于彌補他們在理論分析上的不足。
二、經濟學相關理論路徑的實踐與轉向
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意志的歷史學派在經濟學領域同樣占據重要地位,僅1900-1927年間,德國就出版了不下340本經濟史著作。當時的經濟學家普遍認為,追溯較早時期的經濟史是一件“有意義、有用而且是有必要的工作”,因為世界經濟“演變的速度和模式深深植根于它的過去”,因此要敢于掌握過去的線索,大膽提出假設[12]。基于歷史總結獲得的理論認知同樣可以再去分析歷史,在更廣泛的歷史視域中進行反證。因此德意志經濟史學家摩澤爾(Justus Mser)率先提出要以“今日之情勢推及古代之研究”[13]。正是從此時起,現代經濟學的理論路徑被引入貿易史研究當中。
重商主義之后,近代國際貿易經濟學(以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為起點)最早在貿易史研究中引入體系化的理論闡釋路徑。國際貿易學家常引入兩個貿易模型作為基礎研究工具:古典模型(李嘉圖貿易模型)和新古典模型(由馬歇爾、哈勃勒、勒納、里昂惕夫、斯托爾珀和薩繆爾森等人所貢獻)。現代經濟史學家以這兩種模型分析近代主權國家間的貿易關系,并得出結論——貿易可使各國的稀缺資源得到最佳利用,它們自己生產部分物品,同時從他國獲得其他商品和服務,提高社會消費水平,從而增加國家的整體福利[14]。這一簡單的經濟學邏輯常被經濟家引入中世紀經濟史的分析當中。如斯密和李嘉圖的觀點所示,貿易與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專業化相結合,可使所有參與者受益。這種專業化趨勢在中世紀時就已存在于歐洲各王國之間,也存在于歐洲與外部世界之間[15]。在歐洲內部,最先形成的是利用自然稟賦進行的地區性分工以及部分生產部門的專業化,只是相應水平較低,生產部門也偏少。在中世紀盛期的北歐,區域性貿易可概分為三大專業化產區——以佛蘭德、英格蘭和下萊茵蘭為中心的制造品產區,易北河以東的谷物產區,波羅的海東岸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初級產品供應區[16]。MM波斯坦進一步完善了地理分工和專業化理論,獲得羅伯特·洛佩茲等經濟史學家的支持。他們對歐洲內部的地理分工做了更細致的區分,提出了依靠特殊資源形成的地方性專業產區以及生產部門進一步專業化的觀點。前者如英格蘭、法國北部和伊比利亞的羊毛產區、比斯開灣鹽產區、加斯科涅葡萄酒產區以及以斯堪尼亞和卑爾根附近的青魚、鱈魚產區等。后者如佛蘭德、萊茵蘭等紡織業和器具加工等部門的進一步精細化、規模化等。這些專業化產區、生產部門間的供需互動構成了北歐區域貿易的主要內容,同時也為所屬經濟體(城市或王國)帶來機遇和財富。16世紀以后,尼德蘭和英格蘭利用本國強大的制造業(包括成熟的運輸體系)將東、西歐不同產區置于由其主導的“早期剪刀差”模式之下,逐步掌控了北海-波羅的海貿易的主動權。
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模型影響經濟史學家的思維長達一個世紀,但新古典經濟學過于偏重經濟分析的理論路徑在20世紀60、70年代再受批評——它自囿于經濟領域,刻意忽略人口、心理、法律、政治以及文化等人文制度與經濟的互動影響。當代國際貿易學者批評這種傳統的、程式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為國際生產結構的理論,而非貿易的理論[17]。因此對貿易史的理論闡釋和路徑分析必須探尋新的方向。其中,制度經濟學派的興起,掀起了分析范式上的“革命”,同時也在方法論上實現了突破②。但從分析路徑的沿革歷程看,制度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古典經濟學依舊存在著承繼關系:如政治經濟學的任務是研究人類經濟生活中的各種制度,探討它們的起源和演變,因此國家與其居民間的關系就成為政治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共同主題。另外,制度經濟學派是在沿用新古典主義學派傳統分析工具的基礎上創新的制度分析方法:他們將制度因素內生化,專門考察制度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和作用,然后引入經濟史研究,對歐洲文明演進構建全新的解釋框架。
對于歐洲各經濟體與市場關系的探究,制度經濟學派取得了較大成果。制度經濟學者明確指出:中世紀晚期,近代早期的城市或國家擴張,必然會有一套相應的制度支持,能提供經濟擴張所需的軍事的(特別是海軍)和商業基礎設施的制度[18]。國家應該保護產權制度,建構完善的法律體系,提供公共產品以降低交易成本和解決市場失靈問題。作為回報,公民應支付稅收以便為這些公共產品提供資金[19]。實際上,這是對政治經濟學中反復強調的國民經濟體系理論的進一步發展。
制度學派的早期代表道格拉斯·諾思提出要從產權、國家主權和意識形態三大理論來審視和分析西方市場經濟演變的歷史。他提出制度變遷的理論框架: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增長的關鍵,確保“奮發進取的個人獲得其勞動成果”的法律制度是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在西歐,正是有效率的經濟組織的發展以及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制度的完善導致了西方世界的崛起[20]。SR愛潑斯坦進一步發展了諾思的理論,他指出:國家主權制度是近代經濟革命的決定性制度變量,這是英、荷、法等大國瓜分世界貿易的優勢之一[21]。內森·羅森堡更是將整個歐洲貿易網絡包括在內的市場、商業和金融體系視為“支持更大規模貿易的經濟制度”。隨著經濟的發展,經濟領域的擴張,各種新的制度要求又被提出來。這些制度中,有些是完全由經濟領域自行確立的,有些則產生于與政治領域的相互斗爭或相互影響。這些新制度的建立對西方經濟發展的貢獻甚至起著根本性影響[22]。其他學者如海爾布羅納和阿夫納·格雷夫等同樣堅持以制度理論對史實進行再解釋。前者概括出三種制度類型(即傳統運行的經濟,命令運行的經濟,市場運行的經濟)對西歐由莊園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進行討論[23];后者則提出“多邊聲譽機制”的理論模型來分析漢薩同盟等經濟體的內部制度建設和外部霸權政策[24]。阿夫納·格雷夫還關注制度的效率問題。他指出,如果制度富有效率且交易成本較低,依照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就會出現低利率,高水平的市場一體化以及密集型市場(dense markets)。在擴大市場交易規模的各要素之間則存在著相互鞏固的作用。其中,聲譽機制對持續性的交換行為十分重要——它是任何市場經濟中都不可或缺的關鍵性制度要素。聲譽機制促使公民表現良好(遵守承諾并信守契約),因為人們害怕由于違背承諾而被未來的交易排斥在外,其約束效力則取決于(從參與者所在的關系網得出的)與其未來交易的數量,以及利率(它將交易的未來值轉化為現值)。
盡管方法有別,但制度史學派歷代學者的研究基點卻幾乎一致:拋開經濟結構不論,經濟體內部的制度建設對于其經濟(特別是貿易)拓展的支持意義深遠。如諾思所言:“現代國家的經濟增長,不僅僅是新古典理論所說的要素積累的結果,同時也是制度不斷完善的結果”[25]。無論漢薩同盟、尼德蘭還是英格蘭,它們在適應北歐貿易發展,掌控北歐國際市場的過程中,都依賴于相較成熟的制度體系作為保障。同樣,制度建設的滯后也會拖累經濟體的進一步發展,漢薩同盟如此,尼德蘭亦然。另外,在區域貿易范圍內,當利率較低且未來交易的現值較高,以及當經濟體(包括其國民)預期未來會產生大量交易時,他們將傾向于表現良好,并通過行為加強自身信用。因此,市場交易的總體水平,特別是利率水平,將在很大程度上說明貿易網絡的效率以及作為其基礎的信用的發展程度。由此同樣可以得出,在從不活躍市場和高交易成本到高市場參與程度以及低交易成本的長期移動過程中或將存在多重均衡模式[26]。這些內外因素就構成了區域貿易網絡的穩定特征。格雷夫的“多邊聲譽機制”與當下國際貿易研究中廣泛流行的“社會網絡理論”緊密相關,這一源自社會學的分析路徑日益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在此暫不作討論。
制度經濟學家通過對衡量制度效率的以上指標(如長期利率、勞動力和資本市場)進行考察之后得出結論:自中世紀晚期始,西歐社會就已初具相對富有效率的制度,這導致較低的交易成本,家庭對要素和產品市場的大規模參與,以及高水平的市場一體化。極低的利率水平意味著財產權在西歐地區得到了很好的保護,且普遍存在著相對較高的信用水平,后者對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歐洲出現的現代經濟增長并非偶然,正是相對富有效率的制度的結果。這些制度最晚從15世紀開始就已成為該地區的典型特征。戴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和詹姆斯·羅賓遜等學者對北海沿岸各國近代的經濟騰飛作過考察,他們正是從大西洋貿易、制度變化和經濟增長的關聯作出具體分析和闡釋。他們認為北海沿岸經濟騰飛得以發生的基礎就在于英格蘭和尼德蘭等國商業的快速擴張,繼而引發了大西洋國家巨大的制度變遷,這些變遷由強大的新型商人團體所推動,他們大力支持限制君主機會主義行為的制度[27]。
部分歷史學家對此卻持異議,他們認為制度經濟學派的研究理路正陷入一種建構主義窠臼。制度經濟學家對制度抱有崇拜態度,他們認為制度決定了歷史與文明,決定了一切。但事實相反,恰是歷史決定著人們對過往的認知與理解。人類文明中建構起的諸多政治、經濟和社會理論無一不是基于對過去歷史的總結。因此,諸上研究路徑只可以為深入探究北歐貿易提供輔助參考,但決不能以論代史。不過如果要更清晰地做到論從史出,又要求我們必須借鑒各學科的成果,吸收多元方法論,經濟分析與歷史研究的辯證關系便是如此。
三、新史學的相關理論路徑
20世紀3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提倡借鑒人文社會科學中其他相關學科的理論、概念和方法對人類各地區和各時代的制度、習俗和思想進行探究,并從歷時性轉向共時性。宏觀歷史理論影響下的經濟史研究就屬于這一傾向,即借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概念去分析研究問題,或從某種理論框架出發去解釋經濟的發展歷程。但堅持宏觀經濟理路以研究貿易史的任務,至今仍為經濟學科內的經濟史家所承擔。在純粹的歷史學科中,可能僅有經濟-社會史的研究理路最接近于該領域。
在西歐文明演進的軌跡當中,經濟與非經濟因素的互動貫穿其中,特別是經濟與社會因素(包括政治、法律、宗教與文化)的互動在12世紀后突出地表現出來。因而圍繞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來討論中世紀的政治經濟體,使用經濟-社會史的研究方法將會更透徹,更具理論性,也更具說服力。例如,在歷史分期上,打破中世紀和近代僵化、標準化的區分,是現當代諸多歷史學家的夙愿。卡爾·馬克思、約翰·克拉潘、阿方斯·多布施、亨利·皮朗、費爾南·布羅代爾、莫里斯·道布、哈羅德·伯爾曼、佩里·安德森、艾倫·麥克法蘭和克里斯多夫·戴爾等學者皆在著作中從不同領域、不同視角對該時段下的西歐社會轉型作過闡述或強調。馬克·卡森提出的國際貿易第一時段(11-18世紀末)正是歐洲由傳統向現代過渡的轉型期,同時也符合布羅代爾強調的長時段研究單位。布羅代爾關注社會集體和環境的影響,把秩序和結構置于個人活動之上[28]。在他看來,長時段是以世紀為單位的結構變化,而結構是人類制度的建構組合,它變化緩慢,甚至呈穩定狀態。某些長期存在的結構成為世代相傳的穩定因素[29],限制著人類歷史變化的幅度,支配著歷史的進程。結構既是歷史運動的支撐物,又是歷史發展的障礙物,人類活動受到這些社會的、生產的、生理的、地理的和心態結構的局限。布羅代爾的“結構”概念提醒歷史學家去注意歷史中那些重復或周期性反復的,或在一個漫長時期中穩定存在的,限制著人類活動的各種架構,并把它們看做是一個整體的研究對象去加以理解和把握。所有的變革都是基于這些“結構”在長時段當中的變動。這影響了后世學者從北歐的地理、氣候、物產和群體心態研究貿易模式的變化。事實證明,正是地理構造的基礎性作用孕育了歐洲海上貿易[16],而氣候和物產則奠定了早期貿易實現地區性分工的基礎[30],同質化的群體心態和習俗則有利于構建共同的社會網絡[31],這些成為滋長、維系北歐區域貿易的必要條件。但另一方面,在以世紀為單位的中時段中,社會分工和地理分工在不斷擴大,專業化生產的細密化和規模化,社會群體心態(宗教信仰、消費觀念)也處于不動變化當中,最終由社會個體身份的普遍變動改觀了中世紀歐洲的社會結構,與同在變動的經濟結構相結合,促成北歐貿易模式沿革,最終奠定了全球貿易的基本模式。
經濟-社會史理路中應用最廣泛、最成熟的是歷史比較方法,因為所有試圖進行解釋的歷史研究都會或明或暗的涉及到某種程度的比較[32]。如利奧波德·馮·蘭克所言,歷史學家的任務就在于尋找各個歷史時代之間的區別以及前后歷史時代間的內在關聯[33]。馬克·布洛赫被稱為比較史學之父,他最早撰文區分了兩種歷史比較研究的方式:第一種方法是19世紀末盛行的宏觀歷史比較法。在這種研究模式中,歷史比較的單位是在時間和空間環境中都互相遠離的社會。第二種方法則采用謹慎、有限的探討方式,比較的單位仍是社會,但它們都彼此相鄰,互相影響且處于同一歷史時期[34]。二戰以后,西方史學比較研究開始轉向選取比較社會的某一特定領域,對核心概念和研究范圍加以準確界定,更多關注不同社會現象的差異性,將所有通過歷史類比來說明不同時空中的歷史形式都視作比較史學[35]。巴林頓·摩爾總結出比較研究的三個優點:首先,它可以提出非常有用的問題或新問題;其次,它可以從反面大致地檢驗已被接受的歷史解釋;最后,它或許可以推導出新的歷史結論。
鑒于北歐區域貿易研究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巨大跨度,比較史學研究展現出極大的參考價值。首先,北歐地理空間上的廣度適于橫向(水平)比較的視角[36]。漢薩同盟地跨易北河東、西歐洲的格局正符合布洛赫推崇的“歷史比較法”的展開——平行地研究這些空間上相鄰又同屬一個時代的社會[32]。中世紀晚期的北歐由于不同的地理環境提供了不同的自然稟賦,因此出現了地域性大分工,至近代時甚至出現了“早期剪刀差”的經濟格局。北海-波羅的海東、西兩端的發展歷程及其影響就成為區域貿易研究的主要內容。另外,北歐貿易區內各經濟體——特別是英格蘭與尼德蘭等國因其參與國際貿易的方式和程度差異同樣適宜比較。也只有通過比較才能清楚地認識到它們的本質特征,才有可能把必然和偶然加以區別,把個別和典型加以區別[37]。其次,長時段的歷史發展提供了縱向(垂直)比較研究的對象。通過對12至17世紀北歐發展不同階段的對比研究可以更清晰地觀察國際市場體系支配下的區域貿易,探尋貿易發展的內在規律。可以說,研究區域(貿易)史的最有效途徑就是堅持這種“趨同性”與“趨異性”的比較研究模式[38]。
比較研究的視野如今從區域上升到全球,從經濟史擴展至各領域。如美國“加州學派”就較早嘗試重新詮釋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擺脫西方中心論,強調比較與聯系的視角。王國斌、安德烈·岡德·弗蘭克和彭慕蘭等人將研究視角由西方擴至全世界,推動了區域貿易研究中全球史理論路徑的引入與實踐。作為區域單位的北歐現已成為這一浪潮的一部分。全球史學開創的新領域——國家間或區域間的互動交流模式(或稱全球模式),正在創建起一種全新的理論和路徑。過去大多數專業史學家只運用實證方法——考證和批判史料來完成特定時間與空間的研究,但如今全球史學家更多關注于跨國或全球范圍的問題和現象。全球史在描述人類各地區的社會制度與文化交流時同樣頻繁地運用到比較方法:因為民族國家(或其他研究單位)只有置于一個更為廣闊的地區體系或世界體系之下才能得到充分理解。巴勒克拉夫很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最好把“地區研究”或“區域研究”看做是通往規模更大的世界歷史觀念道路上的一個階段,看作是一種用一些便于管理的、相互關聯的研究單位來組織歷史知識的實際手段。這些地區研究或區域研究補充了國別史的研究成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國別史的錯誤。但是,它們并沒有取代在精神上和概念上都屬于全球性的歷史學。這種歷史學的眼光越過了地區史的界限,并且對一切地區和一切時代都進行了考察[37]。安德烈·岡德·弗蘭克則指出:“不能首先把歐洲視為一個獨立的實體,然后再設法從它的內部找到變化的根源,相反,世界體系內部之歐洲部分的變化和整個體系以及體系其他部分是密切相關的”[39]。因此,全球史學者自我標榜道:跨越學科的分工限制,打通歷史演化的各個層面以得出一個網絡式的、立體化的歷史演化之“體”,是全球史著力提倡和實踐的目標[40]。這對于當前的北歐貿易研究有著廣泛的啟示意義。畢竟自維京時代起,北部歐洲在實現內部通聯、整合的同時就已直接或間接地與整個世界接軌。維京人向冰島、格陵蘭島的海上探險,經“瓦良格商路”與基輔羅斯、中亞、拜占庭、地中海乃至東方的交往,表明它從未孤立于歐洲一隅。而整個9至15世紀里,逐漸實現區域一體化的北部歐洲也正是因為與亞洲、非洲和美洲新大陸的交往,才刺激其內部貿易霸權的轉移,促進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但相較于當前地中海研究的普遍熱情,以北海-波羅的海為軸線的北歐區域史則更需學界關注、深拓。
四、 余論
關于北歐貿易研究的史學史印證了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早期預言:歷史學和社會科學都不是“自我封閉的體系”,許多使人最感興趣和最有創造性的成就將會集中出現于“各個為自己劃定的那些界線的邊緣和交叉處”[37]。如今多學科研究路徑所展現出來的優勢已不言而喻。但多學科的引入同時也造成具體研究中的無所適從:各領域分散獨立的研究工作對整體概念下的北歐區域研究造成了認知上的困境,體系化的理論指導與實踐長期缺失。有鑒于此,如下幾方面建議或許有助于解決或避免此類困境。
首先,堅持歷史學科的基礎研究地位。任何社會科學理論的解釋都無法機械地凌駕于傳統史學的研究方法之上。如熊彼特所言:“經濟學的內容實際上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獨特過程,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的歷史經驗,他就不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的經濟現象”[41]。翔實的歷史數據和歷史經驗是經濟史研究深入展開不可撼動的根基,只有從批判與考證的路徑出發,對特定時空經濟行為的探索和解釋才具備科學性,才有助于經濟理論的提煉、歸納和完善,有效地服務當下。
其次,在貿易史研究中必須將歷史學的定性分析與經濟學的定量分析相結合,摒棄單一的理論解釋路徑,在整體把握和細節深入方面雙管齊下[42]。但區域貿易研究必需的宏大視野又要求我們注重突出論述體系的整體性:如果沒有一個“宏觀歷史”結構,就不可能將“微觀歷史”現象“納入范圍龐大的論述中去”[37]。宏觀把握又要求在相關研究中保持連續、動態的研究思維。社會科學當前最明顯的缺點就是缺乏時間元,缺乏細節深度,這種深度不可能產生于對社會靜止的研究。只有研究社會在連續不斷變化中呈現的各種力量的動態格局,才有可能達到一定的深度。對漫長歷史周期內區域貿易模式變動的認識同樣如此:當今全球貿易的基本模式源于古典以來人類參與貿易的方式、內容和地理空間上的動態變化,這種貿易模式的沿革歷程構建了國際貿易的“三個時段”。
最后,合理把握研究視角。如今我們無法再將研究中心囿于貿易自身,而應將其拓延至更為廣泛的經濟社會當中,更多關注貿易模式與經濟體的互動關系。自近代以來,貿易史研究已被提升到一個全新的高度。貿易具有流動性和交流特質,因此貿易推動的互動關系不僅表現在貿易與參與者之間,同時也反映在各參與者之間,正是在貿易群體的不斷交往、相互影響過程中,北歐才獲得統一性。可以說,貿易的互動特性推動著其他領域(政治、習俗、文化和社會)的網絡化滋長;反之社交網絡的拓展、深化也有利于貿易的維系和繁榮。北歐已發展成獨立的“文明單位”,其歷史深遠、內容豐富、關系復雜,理應獲得學界應有的重視。
注釋:
①原文出自[英]馬克·卡森為《國際貿易興起》(The Ris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叢書第一卷“國際貿易誕生”(The Emergenc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1200-1800)所作的序言。詳見Phillipe Dollinger, The German Hans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hoemmes Press, 1999, Introduction, pp.vii-xi.
②制度經濟學派實際上分為兩支:第一支是誕生于20世紀50年代的以加爾布雷斯為代表的現代經濟制度學派;另一支是稍晚出現的以科斯、諾思和威廉姆森為代表的制度分析學派。二者都源自凡勃侖和康芒斯的心理與法律等領域的舊制度理論,但后者因強調制度社會研究的多元視角而被廣為接受。新制度經濟學派以社會整體為研究客體,反對研究中的經濟概念化,提倡施以整體制度的分析方法作綜合考察。這種制度的分析方法或結構分析法,在歷史研究中即被演化為新經濟制度史學派的歷史分析方法。新經濟制度學派的分析路徑,源于其四大成熟理論體系:產權理論、交易費用理論、契約經濟理論和委托代理理論。這也是歷史分析中最常見的理論框架。
參考文獻:
[1][英]羅伯特·斯旺森. 中世紀研究的新路徑與新領域[J].世界歷史,2014(3).
[2]David Nicholas. The Northern Lands, Germanic Europe, c.1270-c.1500[M].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271.
[3]崔凡,寧丹虹.國際貿易中的網絡和中介——國際貿易研究的最新發展[J].經濟學動態,2010(8):113-118.
[4]Adolphe-Jérme Blanqui. Histoire de Leconomie politique en Europe depuis Les anciens jusque nos jours[M].Paris: Rarebooksclub.com, 2012.
[5]巫寶三.論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對象、方法和意義[M]//巫寶三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71.
[6][美]弗雷德里克·努斯鮑姆. 現代歐洲經濟制度史[M].羅禮平,秦傳安,譯.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2:5.
[7]Phillipe Dollinger. The German Hans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1999, Introduction, p.vii.
[8][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M].陳萬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236.
[9]何平.西方歷史編纂學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231.
[10][美]斯坦利·布魯斯.經濟思想史[M].焦國華,等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150.
[11][法]讓·巴蒂斯特·薩伊.政治經濟學概論[M].趙康英,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4:49-53.
[12][英]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M].吳曉鷹,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4.
[13][奧]阿方斯·多普施.歐洲文明的經濟與社會基礎(上冊)[M].肖超,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18.
[14]J. Grieco and J. Ikenberry. State Power and World Markets[M].New York: W.W. Norton, 2003.
[15][美]內森·羅森堡, L.E.小伯澤爾. 西方現代社會的經濟變遷[M].曾剛,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88.
[16]Ellen Sempl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anse Towns in relation to Their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1899,31(3):241,236-255.
[17]Carsten Hermann-Pillath. The True Story of wine and cloth, or: Building Blocks of an evolutionary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J].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6,16:387-417.
[18]Avner Greif.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Social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Success: Reflections From Genoa and Venice During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J].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995,151(4):734.
[19]E.G. Furubotn and R. Richer,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 The Contribution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M].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Michigan Press, 2000:414.
[20][美]道格拉斯·諾思.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遷[M].陳郁,羅華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1][美]S.R.愛潑斯坦. 自由與增長:1300-1750年歐洲國家與市場的興起[M].宋丙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22][美]內森·羅森堡, L.E.小伯澤爾. 西方現代社會的經濟變遷[M].曾剛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88.
[23][美]羅伯特·海爾布羅納,威廉·米爾博格.經濟社會的起源(第十二版)[M].李陳華,徐敏蘭,譯.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4][美]阿夫納·格雷夫.大裂變——中世紀貿易制度比較和西方的興起[M].鄭江淮,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25]Lance Davis and Douglass North.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M].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26][荷]揚·盧滕·范贊登.通往工業革命的漫長道路——全球視野下的歐洲經濟,1000-1800年[M].隋福民,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26-27.
[27]D. Acemoglu, S. Johnson and J. Robinson.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J].Working Paper[Z].NBER,Vol.9378, 2003.
[28]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374.
[29]何兆武,陳啟能. 當代西方史學理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521.
[30]Norman Pounds.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31]Margrit Schulte Beerbühl. Networks of the Hanseatic League[J].Translated by Chistopher Reid, in: http://ieg-ego.eu/en/threads/european-networks/economic-networks/margrit-schulte-beerbuehl-networks-of-the-hanseatic-league, 2012-1-13.Published by the Leibniz Institute of European History(IEG).
[32]G. Fedrickson. Comparative History[J].Michael Kammen.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C].New York: Ithaca, 1980:457,44-81.
[33][德]利奧波德·馮·蘭克. 歷史上的各個時代[M].楊培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28.
[34]Marc Bloch. Toward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J].In: Marc Bloch. Land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 Selected Papers[C].Translated by J. E. Anders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agan Paul, 1967:44-81.
[35]C. Vann Woodward. The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American History[M].Reprinted editio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190-191,112,270.
[36]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Europe[M].London: Penguin University Books, 1973.
[37][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M].楊豫,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223,190-191,112,270.
[38]張杰. 在整體視野中深化區域史研究[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04-06.
[39][荷]安德烈·岡德·弗蘭克,巴里·K.吉爾斯.5000年世界體系:跨學科研究法初探[J].世界體系: 500年還是5000年? [C].郝名瑋,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3-6.
[40]江湄.重新將“中國史”置于“世界史”之中——全球史與中國史研究的新方向[J].全球史評論,2014(7).
[41][美]熊彼特.經濟分析史[M].朱泱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22-23.
[42]王超華.西方學界關于英國工資史的研究[J].史學月刊,2010:1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