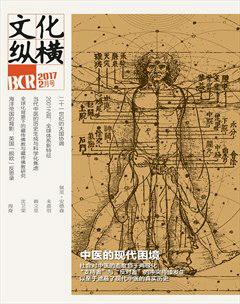從打造理想家居看中國新中產階級的形成
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給中國的社會結構帶來了巨大變化,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變化是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正在逐漸形成。這一新的社會結構變化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討論的重點包括如何劃分和界定中產階級、如何描述中產階級的政治面貌和性格[1]等在內的一系列題目。中產階級不僅有著相似的職業和收入,并且開始選擇他們特有的生活方式,因而家庭生活方式則成為了解形成中的中產階級的一個重要途徑。由于這一階層是中國第一代中產階級,他們心目中理想家居的形成過程顯得更為復雜。
基于對北京一個中產階級小區的調查,本文試圖勾勒出中國的中產階級的形成過程:通過綜合過去人生經歷中的消費經驗,利用手中各種資源來打造他們理想中的家居生活;并試圖探討中產階級是如何在此過程中確立屬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形成共同的身份認同。這樣做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住房的市場化改革不但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新中產的形成,房屋所有權的獲得更成為客觀上定義中產階級的一個重要指標;此外,在小區日常生活當中不斷形成的共同取向以及某些心照不宣的共同理解對于中產階級主觀認同的形成產生非常重要的作用,這種階級生活方式會強化階級認同,促進階級共性的產生。
一、住房市場化改革及中國新中產的形成
中國的住房市場化改革經歷了大致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1978年?1991年,這一階段改革的主要內容是以成本價將公房出售以及出租,這第一次動搖了住房福利觀念。[2]第二階段是1992年?1997年,這一階段的改革內容主要有兩個:經濟適用房及住房公積金。這一階段是中國房地產市場商品化和市場化的初期,但由于公有制企業以及行政事業單位依然主導了房屋分配(如從房地產開發商集團購買房屋,再以低價作為福利分配給其員工),這一階段也被認為是住房市場“雙軌制”時期。[3]1998年以后為房地產市場化改革的第三階段,也是房地產全面市場化的時期。截至1998年底,全國以及全面停止實物分房,中國的城鎮住房制度經歷了根本性變革,個人購房成為房地產需求的主體。[4]這一階段當中,很多公房被低價出售給租戶,因而個人的住房所有權在這一階段有了顯著增加。[5]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中國的住房建設表現出市場化的取向,但由于企事業單位和行政單位等配套改革滯后、制度慣性等原因,企事業、行政單位以及其他形式分配的住房依然占據居民住房供給相當大的比重。[6]
由于城鎮住房供給的雙軌制依然存在,企事業以及行政單位當中的雇員能夠以相當低廉的成本成為昂貴住房的擁有者,而這些以福利形式分配的房屋則成為了這些雇員的私有財產。正是因為這些福利的存在,國家控制體系下的雇員可以通過房屋分配迅速累積其擁有的經濟資源。有不少學者認為他們是來自體制內的中產階級。[7]體制外的中產階級(私人企業主、經理人員以及專業人士)雖然無法以低廉的價錢獲得房屋的所有權,需要直接在商品房市場上購買,但是基于他們的創業能力以及專業技能,他們可以在市場上獲得相當豐厚的經濟回報,因此在商品房市場上購買房屋對于他們來講也并不是十分困難。無論是通過政府、企事業單位、城鎮集體等非商品房供給,還是通過房地產企業開發的商品房市場供給,體制內外的中產階級都在住房市場化的改革過程中成為了房屋的擁有者。從這個意義上說,獲得房屋產權和中國新中產的形成是相輔相成的。相比較沒有房屋產權的城鎮居民,擁有產權的城鎮居民無疑有著更大的優勢來建構一個安全而舒適的家居生活,因此他們成為了市場化改革的“贏家”。因此是否擁有房屋產權也已經成為定義當今中國新中產的一個重要指標。[8]
二、中產的理想家居生活:以KC為例
如果說成為業主是過上中產階級生活的第一步,那么緊接著要進行的就是要在這個擁有產權的房屋中打造中產的理想家居生活。下面讓我們深入一個名為KC的中產小區來看一看中產的理想家居生活是怎樣的。
KC位于北京城區外的東部發展帶,距離中央商務區約10公里,市中心15公里,總占地10.3公頃。作為整個大KC別墅區的其中一個組成部分,KC的定位是聯排疊拼別墅(stacked townhouse)。這是聯排別墅(town house)的一種延伸,由復式住宅上下疊加在一起組合而成,各自有獨立的入口。每個單位上下三層,上疊單位擁有閣樓和屋頂露臺,下疊單位擁有私家花園和地下室。KC提供多種戶型選擇,單位面積約在180?250平米左右。根據2005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北京市2005年的人均住宅面積為32.68平方米,相比較而言,KC的業主擁有更多的居住空間。小區價位處于中位水平,2005年開盤時均價為人民幣7000元/平方米,[9]北京市2005年商品住宅期房均價為7076元/平方米。
KC是一個低密度的地產項目,整個小區僅提供384個住宅單位,容積率低至1,樓間距為20米左右。區內有2.7公頃的園林區及一個占地7000平方米的人工湖,綠化率帶到50%。除此之外,KC的配套設施包括有會所、幼兒園、兒童游樂場、室內泳池、運動中心、高爾夫練習場、網球場、燒烤區等等。每個住宅單位配有一個私家車位,同時,小區還提供公共車位供業主臨時使用。物業提供24小時保安巡邏服務以保障業主的安全。
KC最主要的目標人群是北京的中產階層。根據KC開發商在項目開盤時所做的一項初步調查顯示,大部分KC的業主的職業及教育背景基本符合我們對于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定義:他們之中有外企、私企,以及國企的高級職員,也有些在國家機關及各事業單位,如電視臺、大學、醫院、政府部門等任高級職務。大部分業主擁有大學或以上學歷。
三、中產階級對于理想家居的想象
問起KC居民對于理想中的家的要求,大多數情況下會聽到諸如“面積要大一點的”、“小區環境好”、“密度別太大”、“有四到五間房比較好”等等形容詞。有意思的是,幾乎所有的受訪者在談及對理想家居的想象時,都沒有提及產權問題。這當然不是因為他們認為房屋產權不重要,恰恰相反,他們大多數認為擁有房屋產權已經是建構理想家居的一個先決條件,因此不需要再單獨特意強調了。根據開發商在KC開盤時所作的一個簡單調查,絕大多數KC居民在購買KC以前,已經通過單位分配或者商品房市場上購買房屋成為了業主。因此僅僅擁有產權對于他們來說,已經不足以滿足他們對于理想家居的想象了。
一般人很容易將中產階級對于家居生活的要求歸結于他們借助市場經濟改革所提升的經濟水平。錢固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打造理想家居并非有錢就足夠。中國的新中產發現,在開始享受住房市場化改革所賦予他們的各種自由選擇與自主權的同時,他們也需要利用各種資源,小心權衡各種利弊,從而做出對自己最為有利的選擇。因此認為新中產憑借足夠的經濟基礎,就可以提出對于家居生活的各種要求,這樣的解釋無疑太過流于表面。根據我們的研究,在打造理想家居的過程中,新中產的經濟水平即購買能力、他們所處的人生發展階段以及他們過往的居住經驗都起著重要作用。
(一)更私密的居住空間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中國的新中產來源比較復雜,有些新中產出身于中國的老中產階級家庭(如國家干部、企事業單位干部、軍隊干部等),有些是在市場改革過程中把握住機會創業成功,有些則是憑借自身努力在教育或者職業發展中取得優勢而移民至一線城市。他們的成長背景不同,對于理想家居生活的想象在開始階段是有很大的分歧的。出身干部家庭的C君心目中的理想家園起點明顯很高。他的父母住在干休所里面,環境很好,有水榭,樹林等等。他的姨媽在北京郊區買了個很好的別墅,這些經歷都影響著他對于理想家居的要求,給了他一個有形的目標去追求。
但不是所有人都像C君這樣幸運。相當一部分新中產并沒有太過雄厚的家庭背景做支撐,可以依靠的只能是自己的努力。他們并不像C君一樣對于理想家居生活有著非常明確的目標,對于他們來說,對于理想家居生活的要求是慢慢形成的。來自湖北農村,現在成為某IT 公司創始人的F君就是他們其中的一位。
我的小時候是在農村嘛,畢竟環境不好……我最開始來的時候,工作單位是國企……工資也不高,400多塊錢一個月……我98年換工作,到另外一個公司,就從宿舍搬出來了,2000年去的新浪,干了四年,現在再出來自己單干。出來以后就是出來租的房子,那個時候我已經跟我太太結婚了。一開始租房子的條件相當不好,租的是平房,相當的艱苦。一間房,很潮濕,也沒有廁所……我印象最深的是97年,那個時候出去做銷售,站在朝陽門的橋上,看著外交部的大樓,感慨,北京是好啊,可是沒有一平米是我的,也不知道未來的路在那里,覺得未來的路很渺茫,印象特別深,到現在我還記得,那天是冬天,陰天。所以那個時候我沒有想象過我未來的家應該是什么樣子的。
可以看出,像F君一樣從低收入家庭出身的中產階級,在他們畢業最初的幾年或者事業剛剛起步的階段,職業應該如何發展都沒有一個清晰的路徑,他們主要精力都放在如何在北京這個一線城市生存下去,因而不會對于家居生活做出太高的要求。當問起F君最開始對于家的要求時,他說當時的要求是很低的,有地方住就好,對于是否能滿足家庭成員對于私密性以及空間的要求并不在他的考慮范圍以內:
我在99年買第一套房子的時候,我當時只有兩萬塊錢就能買那個房子。然后就想,如果以后有錢了再買一套,沒錢的話就住這兒也不錯。
相比起F君,出身干部家庭的C君在最初階段對于理想家居生活的想法要更成熟,尤其對于家庭成員之間如何能夠最大限度的擁有私密的空間,他們是有相當明確的想法的。這從他和太太挑選住房時的要求就可以看出來:
我首先要選一個人口密度小的,不要有電梯啊特別多的共用公共場所,因為會跟鄰居接觸比較多。最好是townhouse(筆者注:聯排別墅),自己能獨立一點……我知道我應該有幾間臥室,為什么我選這個戶型,因為我需要有老人跟我一起住,我需要有保姆,我們兩個工作都特別忙,保姆必須要住在我家,不能用小時工。我們兩個需要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所以必須有一層是單獨屬于我們倆的。
很明顯,C君和F君對于理想家居生活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但如果我們對比一下成為了KC業主的F君對于家居生活的想象,不難發現他的要求和幾年前相比有了非常顯著的變化。和他開始時想象的正相反,F君并沒有心滿意足地在他那6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面一直住下去。當他的身份從租客變成了業主,甚至在短短幾年之內擁有了兩套房子以后,F君對于家的要求,尤其是關于家居空間對于家庭成員私密活動的保護上,有著明顯的提升:他想要四到五間房,男女主人一間,孩子住一到兩間,老人住一間,最好再有個書房。之所以特別看重書房,是因為他想要有個自己的空間,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用顧慮小孩子或者太太的要求。
對比C君和F君對于心目中的家的要求所產生的一系列變化,我們可以看出,F君出身于經濟水平很低的農村家庭,這樣的家庭出身限制了他一開始對于理想家居生活的想象。但是隨著事業上取得成功,累積了足夠的經濟資源并成為業主,同時不斷積累購買裝修房屋以及在不同小區的居住經驗,他對于理想家居生活的要求在短短幾年之內迅速向C君這樣出身于干部家庭的中產階級靠攏。今天的F君們對于家的要求不再迷茫,他們敢于提出對于家居生活的夢想,并且有自信這些夢想將于不久的將來實現。出身于不同階級的新中產們開始對于理想家居生活產生了越來越一致的要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標志著中產階級內部開始形成共同的生活取向,促進了中產階級主觀認同的產生。
(二)更舒適的社區環境
隨著中產階級滿足自身對于理想家居生活要求的能力越來越高,他們對于理想家居的要求也由住宅本身拓展到整個社區環境。這里的社區環境既包括小區配套設施、綠化等等硬件環境,也包括小區物業管理、鄰居素質等人文環境。
大部分KC業主選擇KC的一大原因是因為這里的小區環境非常舒適。很多以前住在比較近市中心地帶的KC業主都選擇了逃離密度高的小區,搬來了KC。如曾經居住在望京小區的N君,就是因為密度太高太嘈雜而選擇搬來近郊的KC居住:
望京是這樣,我家住的很大的那一片都是一個開發商。所以他根本不會考慮景觀的問題,雖然是不同的小區,但是都是一個開發商。他就是把所有能夠蓋樓的地方都蓋上樓了。剛住進去的時候還算是有點綠化,后來整個小區都住滿了,他沒有地下車庫,所有的車都停在路面上。那只好不斷地把草皮一塊一塊的砍掉,然后改成車位。然后我老公每天回家最痛苦的一個事情就是找車位。特別影響心情。
除了對硬件環境關注以外,KC的業主們更加關心的是小區的軟性環境,特別是鄰居的素質。他們當中的一些是被KC的廣告語“CBD的后花園”吸引來的。這個廣告語暗示著在這個小區居民的主要工作地點應該是北京的CBD,也就是說他們應該大部分是事業比較成功的人士。另外一些業主甚至是聽說很多在中央電視臺工作的人選擇住在這里才決定在這里買房。其實在KC這樣一個低密度小區,跟鄰居之間的交往并不會很頻繁。為什么中產階級業主們對于鄰居的構成這樣關注呢?
答案在于他們之前累積的居住經驗。如前文所述,KC的業主們大多數都不是第一次買房,他們之前的居住經驗當中,很多因為以往的鄰居的某些行為產生了一些不愉快的經歷,而這些經歷已經嚴重到影響他們對于家居生活的期望。他們當中的大多數認為這些不愉快的鄰里關系最主要的因素在于他們屬于不同階層的人。C君和C太太就對當時鄰居的做法感到非常難以接受:
我們買的第一個房子,精裝修的,小區園子里面綠化也很好,很漂亮。買了以后呢,剛開始住的時候覺得很不錯。但是慢慢慢慢,鄰居我覺得很糟糕。那個地方在木樨園,附近就是大紅門服裝市場,買房子的很多是江浙福建那邊的,絕對是很有錢。早上坐電梯的時候,有的男業主穿著貂皮的大衣,帶著翡翠的戒指,帶的金鏈子比狗鏈子還粗。他們很有錢。但是,在電梯里面小便,自己閑著沒事拿打火機去燒電梯的按鈕,在電梯里面旁若無人的抽煙,在電梯里面光著膀子,在任何場合大聲說話。他們也有他們的孩子,我們也有我們的孩子,孩子們在一起,他們的孩子會罵臟話,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里面,我也不屑于和他們一起。我們也沒辦法改變他們。
C太太也認為和這些明顯不屬于同一階層的鄰居無法溝通:
他們認為很好的事情是我們認為最不好的事情。他們認為在電梯里面抽煙是很正常的。以前我們還會提醒說不要在電梯里面抽煙,他們覺得我們是外星人。我們在那邊是少數。
像C太太這樣的經歷在KC業主當中并不算罕見,而這樣的經歷也影響到他們對于理想家居的選擇。從上述C君夫婦的敘述中可以看出,對于KC業主來說,他們和這些令人不滿意的鄰居之間的區分并不在于經濟水平,而更加類似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及的文化資本與秉性(habitus)。和經濟資本不同,文化資本的累積和秉性的形成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并不是短時間可以改變得了的。因此,KC的中產階級業主們開始主動地采取行動——離開令他們感覺不舒服的鄰居,去主動尋找令他們滿意的人文環境。一方面,他們拒絕考慮把家安在密度太高的小區,這樣可以最大限度減少和鄰居們的接觸以避免不愉快的經歷再次發生;另一方面,他們也會盡力從開發商或者物業管理公司那里了解未來鄰居的大致情況。比如C君等業主就試圖提前了解購買KC的業主的背景情況。他在購買KC之前曾經再三和售樓處的人了解里面的鄰居是個怎樣的狀態,鄰居所從事的職業是他主要考察的目標。KC令他滿意的地方在于大部分業主都是在國貿附近上班的經理人員或者專業人士,還有很多在中央電視臺工作,從事這類職業的人和他的背景差不多,因此他認為大家的素質應該也差不多,應該可以避免之前發生的那些不愉快的情況出現。
當然,這些私下收集到的信息并不能保證KC業主可以全面了解這里鄰居的素質,也不能擔保住在KC小區里面的全部都是符合他們要求的中產階級,但不能否認的是,中產階級業主對于社區的人文環境愈發重視,對于鄰居素質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因此,類似KC這樣的低密度小區就非常符合中產階級的要求,因為它將鄰居之間交往的空間盡量縮小,同時給了業主更多的控制權來控制自己和鄰居的交往。也正是由于KC業主以往的居住經驗以及對于鄰居素質比較高的要求,他們對于自己在小區內的表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表現出更高的自制力以及更高的容忍度,期望通過這樣的行為共同打造出吻合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居住環境。KC的居民們搬進來不久就發現住在這里的人年齡差不多,從事的工作差不多,教育、職業甚至家庭生活的經歷都差不多,這使得大家能探討到一起,對一些事情的看法相當一致。這讓他們對于居住在這里充滿期待,也更樂于和鄰居們交往。這些共識和認同為之后KC業主為了維護自身作為業主的權益所進行的一系列行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四、中產階級小區與中產階級形成過程
本文檢視了中國的新中產階級從初次成為業主,到逐漸擁有幾個物業這種身份上的轉變對于他們心目中理想家居生活的影響。可以看到中國的新中產已經不滿足于被歸類于“先富裕起來”的人,他們迫切地希望通過尋找理想家園來與社會上的其他富裕階層進行區分,而這一區分的過程,則正是中產階級生活共性以及主觀認同建立的過程。盡管中產階級的來源十分復雜,但我們依然可以看到,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加以及住房經驗的累積,中產階級業主對于理想家園的設想變得越來越一致,家庭出身的影響逐漸減弱。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希望選擇跟自己差不多的人一起居住生活。在無形當中,他們慢慢建立起一種規范,希望小區里的人都可以以大家都認為是合理的、有素質的方式生活。像KC一樣的中國城市社區越來越多,說明社區的階層化越來越明顯。中產階級小區正逐漸形成。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中產階級的生活正在慢慢形成共性的取向和要求。
當然,是否這就是當代中國新中產的生活方式,目前還言之尚早。KC所呈現的也并非就是中產階級理想家園的唯一選擇。中產階級對于理想家園的要求還在不斷變化,他們也在不斷嘗試各種可能性。比如他們當中的不少人就提及有了孩子或者孩子大一點以后,可能還是會從郊區搬回到市中心,這更加方便孩子上學。但從KC所呈現出的中產階級生活的原型,我們還是可以看出中國的新中產正在學習如何像中產一樣的生活,他們試圖通過打造理想家園來表現得更加像中產階級,這正是中產階級主觀認同建構的重要途徑。
(作者單位: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
注釋:
[1] 作為一個新興的社會階層,中國新中產的定義以及其在社會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自然是人們首先關心的問題。中國的新中產階級構成比較多元化,根據社會學最常用的職業劃分,新中產的主要組成部分包括經理人員以及私營企業主(Liu, S., “Homemaking and middle class formation in urban China”, Hsiao, Michael Hsin Huang (ed.), Chinese Middle Classes: Taiwan, Hong Kong, Macao, and China, Routledge,2013; Li, J. and Niu, X.H., “The new middle class(es) in Peking: a case study”, China Perspectives, Vol.45(2003);張宛麗:《對現階段中國中產階層的初步研究》,載《江蘇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他們在市場經濟改革過程中在職業結構以及收入上處于相似的位置;此外,一部分國家和社會管理者也因為可以享受各種福利政策,盡管賬面工資不高,但可用于消費的收入并不低,因而成為了新中產的一部分。而關于中產階級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學者間則有不同意見,有些認為中產階級是既得利益者,因此在政治上應該更多地扮演各種利益的平衡者以及沖突的緩沖體;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中產階級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更有可能成為促進轉變的改革力量,甚至有可能會推動政治改革的進程(呂大樂、劉碩:《中產小區:階級構成與道德秩序的建立》,載《社會學研究》2010年第6期)。上述關于新中產的兩個焦點議題固然可以幫助我們初步勾勒出新中產的面貌,但也給我們對于新中產的研究帶來了諸多限制:這類討論往往將結構性的階級位置等同于階級利益,而階級行動就等同于階級政治以及與政治相關的活動,這樣的分析對于我們了解新中產到底是如何形成以及轉變并沒有太大的幫助。
[2] Li, S.M. and Zheng, Y., “The road to homeownership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Beijing 1980-2001”, Urban Affairs Review, Vol.42(2007); Wu, F., “The ‘game of landed-property production and capital circulation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with reference to Shanghai”,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Vol.31(1999).
[3] Li, S.M. and Zheng, Y., “The road to homeownership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Beijing 1980-2001”, Urban Affairs Review, Vol.42(2007).
[4] 李思明、陳峰、邵一鳴:《持續與變遷:當代中國的政經、社會和空間發展》,香港教育圖書2008年版。
[5] Li, S.M. and Zheng, Y., “The road to homeownership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Beijing 1980-2001”, Urban Affairs Review, Vol.42(2007).
[6] 李思明、陳峰、邵一鳴:《持續與變遷:當代中國的政經、社會和空間發展》,香港教育圖書2008年版。
[7] 張宛麗:《對現階段中國中產階層的初步研究》,載《江蘇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Li, J. and Niu, X.H., “The new middle class(es) in Peking: a case study”, China Perspectives, Vol.45(2003).
[8] Bian, Y.J. and Liu, Y.L., “Social stratification, home ownership, and quality of living: Evidence from Chinas Fifth Census”,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Chinas 2000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Beijing, 2005; Li, J. and Niu, X.H., “The new middle class(es) in Peking: a case study”, China Perspectives, Vol.45(2003); Tomba, L., “Creating an urban middle class: Social engineering in Beijing”, The China Journal, Vol.51(2004). 張宛麗:《對現階段中國中產階層的初步研究》,載《江蘇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
[9] 《中國房地產報告NO.3——房地產藍皮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