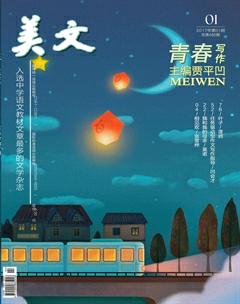秋千上的女子
張曉風
楔 子
我在備課——這樣說有點嚇人,彷佛有多模范似的,其實也不是,只是把秦少游的詞在上課前多看兩眼而已。我一向覺得少游詞最適合年輕人讀:淡淡的哀傷,悵悵的低喟,不需要什么理由就愁起來的愁或者未經規劃便已深深墮入的情劫……
“秋千外,綠水橋平。”
啊,秋千,學生到底懂不懂什么叫秋千?他們一定自以為懂,但我知道他們不懂,要怎樣才能讓學生明白古代秋千的感覺。
這時候,電話響了,索稿的——緊接著,另一通電話又響了,是有關淡江大學“女性書寫”研討會的,再接著是東吳校慶籌備組規定要即交散文一篇,似乎該寫點“話當年”的情節,催稿人是我的學生張曼娟,使我這犯規的老師惶惶無詞……
然后,糟了,由于三案并發,我竟把這幾件事想混了,秋千,女性主義,東吳讀書,少年歲月,粘黏為一,斯扯不開……
漢族,是個奇怪的族類,他們不但不太擅長于唱歌或跳舞,就連玩,好像也不太會。許多游戲,都是西邊或北邊傳來的——也真虧我們有這些鄰居,我們因這些鄰居而有了更豐富多樣的水果、嘈雜凄切的樂器、吞劍吐火的幻術……以及哎,秋千。
在臺灣,每個小學,都設有秋千架吧?大家小時候都玩過它吧?但詩詞里“秋千”卻是另外一種,它們的原籍是“山戎”,據說是齊桓公征伐山戎的時候順便帶回來的。想到齊桓公,不免精神為之一振,原來這小玩意兒來中國的時候正當先秦諸子的黃金年代。而且,說巧不巧的,正是孔老夫子的年代。孔子沒提過秋千,孟子也沒有。但孟子說過一句話:“咱們儒家的人,才不去提他什么齊桓公晉文公之流的家伙。”
既然瞧不起齊桓公,大概也就瞧不起他征伐勝利后帶回中土的怪物秋千了!
但這山戎身居何處呢?山戎在春秋時代住在河北省的東北方,現在叫作遷安縣的一個地方。這地方如今當然早已是長城里面的版圖了,它位在山海關和喜峰口之間,和中共高干常去避暑的北戴河同緯度。
而山戎又是誰呢?據說便是后來的匈奴,更后來叫胡,似乎也可以說,就是以蒙古為主的北方異族。漢人不怎么有興趣研究胡人家世,敘事起來不免草草了事。
有機會我真想去遷安縣走走,看看那秋千的發祥地是否有極高大奪目的漂亮秋千,而那里的人是否身手矯健,可以把秋千蕩得特別高,特別恣縱矯健——但恐怕也未必,胡人向來絕不“安于一地”,他們想來早已離開遷安縣,遷安兩字顧名思義,是鼓勵移民的意思,此地大概早已塞滿無往不在的漢人移民。
哎,我不禁懷念古秋千的的風情起來了。
《荊楚歲時記》上說:“秋千,本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趫,后中國女子學之,楚俗謂之施鉤,涅槃經謂之罟索。”
《開元天寶遺事》則謂:“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豎秋千,令宮嬪輩戲笑以為宴樂,帝呼為半仙之戲,都市士民因而呼之。”
《事物紀原》也引《古今藝術圖》謂:“北方戎狄愛習輕趫之態,每至寒食為之,后中國女子學之,乃以條繩懸樹之架,謂之秋千。”
這樣看來,秋千,是季節性的游戲,在一年最美麗的季節——暮春寒食節(也就是我們的春假日)——舉行。
試想在北方苦寒之地,忽有一天,春風乍至花鳥爭喧,年輕的心一時如空氣中的浮絲游絮飄飄揚揚,不知所止。
于是,他們想出了這種游戲,這種把自己懸吊在半空中來進行擺蕩的游戲,這種游戲純粹呼應著春天來時那種擺蕩的心情。當然也許也和叢林生活的回憶有關。打秋千多少有點像泰山玩藤吧?
然而,不知為什么,事情傳到中國,打秋千竟成為女子的專利。并沒有哪一條法令禁止中國男子玩秋千,但在詩詞中看來,打秋千的竟全是女孩。
也許因為初傳來時只有宮中流行,宮中男子人人自重,所以只讓宮女去玩,玩久了,這種動作竟變成是女性世界里的女性動作了。
宋明之際,禮教的勢力無遠弗屆,漢人的女子,裹著小小的腳,蹭蹬在深深的閨閣里,似乎只有春天的秋千游戲,可以把她們蕩到半空中,讓她們的目光越過自家修筑的銅墻鐵壁,而望向遠方。
那年代男兒志在四方,他們遠戍邊荒,或者,至少也像司馬相如,走出多山多嶺的蜀郡,在通往長安的大橋橋柱上題下:
“不乘高車駟馬,不復過此橋。”
然而女子,女子只有深深的閨閣,深深深深的閨閣,沒有長安等著她們去功名,沒有拜將臺等著她們去封誥,甚至沒有讓嚴子陵歸隱的“登云釣月”的釣磯等著她們去度閑散的歲月(“登云釣月”是蘇東坡題在一塊大石頭上的字,位置在浙江富陽,近杭州,相傳那里便是嚴子陵釣灘)。
我的學生,他們真的會懂秋千嗎?他們必須先明白身為女子便等于“坐女監”,所不同的是有些監獄窄小湫隘,有些監獄華美典雅。而秋千卻給了她們合法的越獄權,她們于是看到遠方,也許不是太遠的遠方,但畢竟是獄門以外的世界。
秦少游那句“秋千外,綠水橋平”,是從一個女子眼中看春天的世界。秋千讓她把自己提高了一點點,秋千蕩出去,她于是看見了春水。春水明艷,如軟琉璃,而且因為春冰乍融,水位也提高了,那女子看見什么?她看見了水的顏色和水的位置,原來水位已經平到橋面去了!
墻內當然也有春天,但墻外的春天卻更奔騰恣縱啊!那春水,是一路要流到天涯去的水啊!
只是一瞥,另在秋千蕩高去的那一剎,世界便迎面而來。也許視線只不過以二公里為半徑,向四面八方擴充了一點點,然而那一點是多么令人難忘啊!人類的視野不就是那樣一點點地拓寬的嗎?女子在那如電光石火的剎那窺見了世界和春天。而那時候,隨風鼓脹的,又豈只是她繡花的裙擺呢?
眾詩人中似乎韓偓是最刻意描述美好的“秋千經驗”的,他的秋千一詩是這樣寫的:
池塘夜歇清明雨
繞院無塵近花塢
五絲繩系出墻遲
力盡才瞵見鄰圃
下來嬌喘未能調
斜倚朱闌久無語
無語兼動所思愁
轉眼看天一長吐
其中形容女子打完秋千“斜倚朱闌久無語”“無語兼動所思愁”頗耐人尋味。“遠方”,也許是治不愈的痼疾,“遠方”總是牽動“更遠的遠方”。詩中的女子用極大的力氣把秋千蕩得極高,卻僅僅只見到鄰家的園圃——然而,她開始無語哀傷,因為她竟因而牽動了“鄉愁”——為她所不曾見過的“他鄉”所興起的鄉愁。
韋莊的詩也愛提秋千,下面兩句景象極華美:
紫陌亂嘶紅叱撥(紅叱撥是馬名)
綠楊低映畫秋千 (《長安清明》)
好似隔簾花影動
女郎撩亂送秋千(《寒食城外醉吟》)
第一例里短短十四字便有四個跟色彩有關的字,血色名馬驕嘶而過,綠楊叢中有精工繪畫的秋千……
第二例卻以男子的感受為主,詩詞中的男子似乎常遭秋千“騷擾”,秋千給了女子“一點點壞之必要”(這句型,當然是從唯弦詩里偷來的),蕩秋千的女子常會把男子嚇一跳,她是如此臨風招展,卻又完全“不違禮俗”。她的紅裙在空中畫著美麗的弧,那紅色真是既奸又險,她的笑容晏晏,介乎天真和誘惑之間,她在低空處飛來飛去,令男子不知所措。
張先的詞:
那堪更被明月
隔墻送過秋千影
說的是一個被鄰家女子深夜打秋千所折磨的男子。那女孩的身影被明月送過來,又收回去,再送過來,再收回去……
似乎女子每多一分自由,男子就多一分苦惱。寫這種情感最有趣的應該是東坡的詞:
墻里秋千墻外道
墻外行人墻里佳人笑
笑漸不聞聲漸悄
多情卻被無情惱
由于自己多情便嗔怪女子無情,其實也沒什么道理。蕩秋千的女子和眾女伴嬉笑而去,才不管墻外有沒有癡情人在癡立。
使她們愉悅的是春天,是身體在高下之間擺蕩的快意,而不是男人。
韓偓的另一首詩提到的“秋千感情”又更復雜一些:
想得那人垂手立
嬌羞不肯上秋千
似乎那女子已經看出來,在某處,也許在隔壁,也許在大路上,有一雙眼睛,正定定的等著她,她于是僵在那里,甚至不肯上秋千。并不是喜歡那人,也不算討厭那人,只是不愿讓那人得逞,彷佛多趁他的心似的。
眾詩詞中最曲折的心意,也許是吳文英的那句:
黃蜂頻撲秋千索
有當時,纖手香凝
由于看到秋千的絲繩上,有黃蜂飛撲,他便解釋為打秋千的女子當時手上的香已在一握之間凝聚不散,害黃蜂以為那繩索是一種可供采蜜的花。
啊,那女子到哪里去了呢?在手指的香味還未消失之前,她竟已不知去向。
——啊!跟秋千有關的女子是如此揮灑自如,彷佛云中仙鶴不受網弋,又似月里桂影,不容攀折。
然而,對我這樣一個成長于二十世紀中期的女子,讀書和求知才是我的秋千吧?握著柔韌的絲繩,借著這短短的半徑,把自己大膽的拋擲出去。于是,便看到墻外美麗的清景;也許是遠岫含煙,也許是新秧翻綠,也許雕鞍上有人正起程,也許江水帶來歸帆……世界是如此富艷難蹤,而我是那個在一瞥間得以窺伺大千的人。
“窺”字其實是個好字,孔門弟子不也以為他們只能在墻縫里偷看一眼夫子的深厚嗎?是啊,是啊,人生在世,但讓我得窺一角奧義,我已知足,我已知恩。
我把從《三才圖會》上影印下來的秋千圖戲剪貼好,準備做成投影片給學生看,但心里卻一直不放心,他們真的會懂嗎?真的會懂嗎?曾經,在遠古的年代,在初暖的薫風中,有一雙足悄悄踏上板架,有一雙手,怯怯握住絲繩,有一顆心,突地向半空中蕩起,蕩起,隨著花香,隨著鳥鳴,隨著迷途的蜂蝶,一起去探詢春天的信息。
(選自《星星都已經到齊了》
九州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