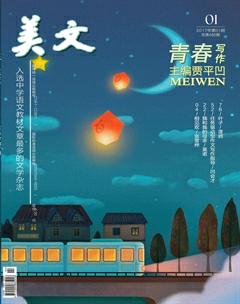萬般柔情都深重
孫婷
女兒家是水做的,因此她總有萬般柔情。
在張曉風出版的散文集《星星都已經到齊了》一書中,我深深地為四個字所著迷:鳥靜花喧。只這四字,于我眼前仿佛立即展開一幅國畫花鳥圖,中國傳統文化中溫婉典雅、含而不露的審美意境就這么徐徐地延伸開來,緩緩地,無聲無息地一直抵達到我的靈魂深處,千言萬語都不必再說。
萬般柔情都深重。
讀張曉風的散文,我時常會想起臺灣另外兩位著名的女性作家:瓊瑤和龍應臺。瓊瑤的文學成就主要集中在通俗文學領域,她筆下那些悲情的男女主人公影響了內地整整一代人的審美觀和愛情觀。瓊瑤的中國古典文學功底深厚,單從她的筆名“瓊瑤”出自《詩經》“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就可窺見一斑。而經她的小說改編的影視劇,無論從演員的容貌篩選,還是從劇本中男女主人公的姓名,甚至在臺詞創作上,都烙印著鮮明的古典詩詞風貌。瓊瑤筆下的女兒家或古典含蓄,或溫婉柔美,或敢愛敢恨,或縱情肆意,但她們又都是那樣情意綿綿,無怨無悔。這種女子是飄遠的,她們只能存在于古典的世界里,是詩人和詞人想象出來的女兒們的千嬌百媚。這種美雖不真實,不存在于現實世界中(即使在中國古代社會,女人也并不都是詩人們筆下的這般情態),但它足以構建出一個朦朧悠遠、可望不可及的審美世界,令人身不能至,心向往之。
龍應臺則是與瓊瑤有著截然相反的文學氣質的女性作家。前不久重讀龍應臺的“人生三書”系列,雖然是寫給兒子以及有關親情的隨筆文章,但其文筆的犀利和理智在三本書中鋒芒畢露,時時閃跳著智慧與思考的理性之光。許是母親的影響使然,龍應臺的兒子安德烈在與她的書信往來里,母子間的對話充滿了對世界各種問題的理性思索與探討,儼然是一對現代社會所提倡的新型母子關系模式。與瓊瑤相比,龍應臺身上的中國古典文化氣質似乎不那么濃烈,似乎更“西式”,更“現代”,但她骨子里那揮不去的鄉情,訴不盡的親情,藏于內的柔情卻依舊是中式的,古典的。
那么,張曉風呢?
若把瓊瑤書中的古典氣質比作濃得化不開的花團錦簇,萬紫千紅都開遍的話,龍應臺文字里的古典氣質就剩下一個烙印印在書里的角角落落,無論你留心或是不留心,那烙印就深深地刻在作者的靈魂深處,于不經意間才會被人發現。張曉風是介于瓊瑤與龍應臺之間的。張曉風的文字仿若國畫里的花鳥畫,亦動亦靜,似動還靜,細細品其文字,有一種欲語還休的綿延未盡之感。讀她《秋千上的女子》一文,開頭便是“我在備課”,于是文中引了很多為了備課而參閱的有關“秋千”的古詩詞,此外,張曉風還旁征博引,埋首到古典文獻中,翻找出秋千的發源地和它的流傳故事。如此看來,這篇文章該是一篇多么有理有據、詳述得當的散文作品啊!似乎是的,似乎又不是。掩卷而思,秋千倒是被我這個讀書的人忘記了,而“秋千上的女子”卻不知怎的,活現于我眼前來了。
我只覺得眼前活跳出一個青春正當時的少女,于春意盈盈、時光潛行中,一派天真爛漫之態。園中春色漸濃,花鳥爭喧,少女無憂無慮,成長的沉重尚未浸洗過她,社會的禁錮還不曾綁縛于她,這秋千上的花容月貌美得如此短暫,卻如此驚心動魄,縱使只有笑聲傳出園外,也足以讓人“多情卻被無情惱”了。
文學的審美意境,也恰在于此。
好的文學作品,便是能讓人忘記一切頭頭是道的說理,剩下的,只是那意猶未盡的對美的想象。
張曉風的感情是熱烈的,浪漫的,但她下筆時是理性的,有節制的。在回憶父親的《塵緣》一文中,張曉風娓娓訴說著父親生前的點點滴滴,平靜如水,淡淡的,如同閑話家常一般,卻使我在其文章結尾處,讀到“而我的父親呢?父親也被歸回到什么地方去了嗎?那曾經劍眉星目的英颯男子,如今安在?我所挽留不住的,只能任由永恒取回。而我,我是那因為一度擁有貝殼而聆聽了整個海潮音的小孩”時潸然落淚。瞧,她就這么無聲無息的,讓我流下了眼淚。
席慕容為《星星都已經到齊了》一書作序,題目是《相見不恨晚》,很是貼切。其實,我認識張曉風的文字是很晚的事了。以前總愛讀那些偏理性的文章,欣賞作家們在文中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豪情萬丈,讀得多了久了之后卻是什么觀點都沒記住,什么論述都拋在了腦后,接觸到張曉風的散文,倒是被她這種在節制中不乏熱情,藏浪漫于理性背后的文風所喜歡和鐘愛。即使豪情萬丈起來,她亦是柔柔的,緩緩的,如寫戈壁之行的《戈壁行腳》,將所有的自由無拘,所有的豪邁縱情最后都化作一段文字,輕輕地寫在心上:
我睡去,在不知名的大漠上,在不知名的朋友為我們搭成的蒙古包里。在一日急馳,累得倒地即可睡去的時刻。我睡去,無異于一只羊,一匹馬,一頭駱駝,一株草。
我睡去,沒有角色,沒有頭銜,沒有愛憎,只是某種簡單的沙漠生物,一時尚未命名,我沉沉睡去。
睡去,除了沉沉睡去,如沙漠里任何生物一樣沉沉睡去,還有什么能描述出人在造物主面前的卑微和渺小呢?
這便是張曉風的柔情,纏纏繞繞,似水繾綣,卻有著萬般深重的剛勁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