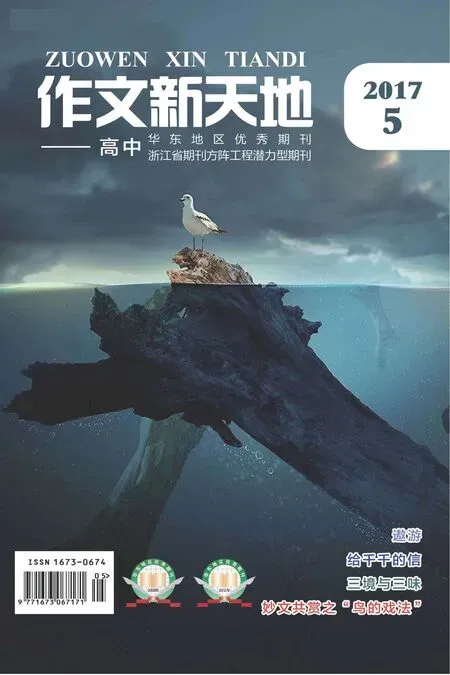例談聯想在議論文論據分析中的運用
◎王勇 江蘇省儀征中學
寫作雜談
例談聯想在議論文論據分析中的運用
◎王勇 江蘇省儀征中學
聯想作為一種思維活動,在生活和寫作中經常運用到,它是指人們根據事物之間的某種聯系,由一事物想到另一有關事物的心理過程。也就是說,人們在看待事物、思考問題時,都離不開聯想。可以說有了聯想,就能夠視通萬里,思接千載。
論據分析中的聯想是指,在敘例以后,以已知論據為基礎,推測分析與之相關的種種可能發生或已經發生的情況,將論據進行合理的引申,從而讓論據分析更加充分,觀點證明更有說服力。聯想在議論文論據分析中的運用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 由此及彼
1 .最簡單的由此及彼的聯想,就是由一個事例聯想起另一個類似的事例。需要注意的是,聯想起的事件一定要略寫。
示例:有時候磨難,恰恰能夠歷練人生,綻放光彩。司馬遷遭受腐刑,卻能在這樣的恥辱中寫成《史記》,汗青溢光,那是因為他有堅定如山的信念,剛毅如鐵的意志,于誹謗譏嘲中堅持自己的志向,才突圍成為“史圣”。這讓我想到了不屈服于命運的貝多芬,他在雙耳失聰的情況下,還譜寫出不朽的交響曲。
2 .由此及彼,還可以指事例在不同方面、角度、領域所帶來的啟迪,如自然的例子對人類的啟迪,科學的例子對人生的啟迪,個人的例子對眾人的啟迪,等等。
示例:英國數學家多番維爾傾注了三十多年的精力,把圓周率值推算到小數點后八百多位。可是后人發現,他在第三百多位時就出現了錯誤,也就是說,他后面二十來年的努力都是白費。科學是容不得半點馬虎的,多番維爾如果能在推算過程中經常客觀地審查自己的步驟和數據,就可能不會留下這個遺憾了。科學如此,人生又何嘗不是?常常聽人后悔自己什么做得不好,什么不該做,事后再多的悔恨也于事無補,我們應該從中吸取教訓,對“出”的意義有一個更好的認識。
3 .由此及彼,還可以是引用他人的論述或評價來補充或佐證自己的分析。有時選擇了事實論據之后,可聯想到相關的理論論據,引入文章,使議論更見深度。
示例:一部《水滸傳》,洋洋灑灑近百萬言,作者卻并不因為是寫長篇就濫用筆墨。有時用筆極為簡省,譬如“武松打虎”那一段,作者寫景陽岡上的山神廟,著“破落”二字,便點染出大蟲出沒、人跡罕到景象。待武松走上岡子時,又這樣寫道:“回頭看這日色時,漸漸地墜下去了。”真是令人毛骨悚然。難怪金圣嘆讀到這里,不由得寫了這么一句:“我當此時,便沒虎來也要大哭。”最出色的要數“林教頭風雪山神廟”,寫那紛紛揚揚的漫天大雪,只一句:“那雪正下得緊。”一個“緊”字,境界全出,魯迅先生贊揚它富有“神韻”,當之無愧。
二由個及類
作為證明論點用的論據,往往都是個例,在論據分析時,我們需要由個及類,讓偶然變成必然,從個性發掘共性。我們可以從一個孤立的事件聯想到具有共同特點的一類事件,也可以從一個個體的人聯想到擁有相同特質的一類人。
以人物為例,來談談如何由個及類。我們所舉的論據常常是一些正面人物,而這些人往往是某個群體的代表,由個及類,需要我們準確地找到這個群體,扣住論點來揭示群體實質,然后再舉出若干這個群體中的其他例子,這些例子就不再需要詳述,簡單帶過即可。
示例:大愛是寧愿將自己滿腔尚未實現的抱負沉淀成對百姓濃烈的愛。那位被唐憲宗當作一塊磚隨便扔往柳州的柳宗元,面對僻遠、冷落、荒涼的邊境,選擇用大愛來承擔自己的憂愁。于是,他興辦學堂、禁止巫術、墾荒屯田、種樹植株、推廣草藥。幾年的時間里,他成功讓柳州獲得了發展,獲得了百姓的擁戴。中國古往今來這樣的例子很多,如韓愈之于潮州、蘇軾之于杭州,正是這些士人,展現了知識分子的良知,撐起了中華民族的脊梁。
三由實及虛
議論文中舉到的事實論據,一般用記敘性的語言(加少數描寫性的語言),記敘具體的事件。論據分析時則采用議論性的語言,進行抽象的表述,將事件的本質或意義揭示出來,從而證明論點提出的看法和主張的影響、價值、效果等。同樣的意思,先是寫實,后是寫虛。
示例:米勒畢生以農民的身份抵擋巴黎精致的畫室藝術,對于上流社會,他始終有一種寧靜的藐視,當人們向他嘖嘖描述王子命名儀式的場面時,他感嘆道:“可憐的小王子!”他只是那樣固執地畫他筆下的農民,在銅黃色所鋪設的寧靜安詳底下,我突然讀懂了他的靈魂,那是一種精神的亢奮和難言的內心的悸動。對于米勒來說,任何財富都阻擋不了他對完美的追尋,他只是勇敢地追尋靈魂的高潔,決不肯在自己的土地上讓出哪怕是木鞋大小的地方。
四 由反及正
對于論據,如果我們能同時從正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就可以增強論證的說服力。實際運用中,先反后正的處理更符合人們的認知。那么這種由反及正的論據分析,該如何表述呢?“反”其實是假設之反,也就是用假設分析法,假設出現與論據表述相反的情況,表明其危害或后果;“正”就是意義評價,對論據進行分析評價,指出論據中所能體現論點的地方。
示例:字面上的簡不等于精練,藝術表現上的繁筆,也有別于通常所說的啰唆。魯迅是很講究精練的,但他有時卻有意采用繁筆,甚而至于借重“啰唆”。《社戲》里寫“我”早年看戲,感到索然寡味,卻又焦躁不安地等待那名角小叫天出場,“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亂打,看兩三個人互打,從九點多到十點,從十點到十一點,從十一點到十一點半,從十一點半到十二點,——然而叫天竟還沒有來。”在通常情況下,如果有誰像這樣來說話、作文,那真是啰唆到了極點。然而在這特定的環境、條件、氣氛之下,魯迅用它來表現一種復雜微妙、難以言傳的心理狀態,卻收到了強烈的藝術效果。
五 由人及己
論據分析時,我們常常需要談談其現實意義,即論據對“我們”有著怎樣的影響,又引發“我們”怎樣的思考。這里的“我們”可以代表很多身份,可以是中學生,可以是當代青年,也可以是當代人。應該是什么身份,是根據文章的需要來確定的。
示例: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先生,在談及自己“文化大革命”時期雖下鄉勞動仍不忘閱讀的經歷時,眼眸中閃動著淚光。在那樣艱苦的時期,一個青年,用頑強守護著心靈的凈土。無盡的折磨,疲倦的勞動,都沒能占領這最后一片精神的凈土。在那樣的年代,尚且手不釋卷,現如今的我們,又怎能以“沒時間”“沒錢”這樣不堪一擊的借口,來丟掉心中最后的一片領地呢?與這些人相比,難道我們不該為易中天先生的執著擊節叫好嗎?
這里的“我們”是指廣泛的當代人,如果換成中學生,則可以表述為:
易中天先生下鄉勞動仍不忘閱讀,而身處寬敞明亮的教室,以閱讀為責任的我們,卻常常以“作業太多”“時間太少”“考試不考”等理由,而忽略閱讀,任由自己的心靈在題山卷海中變得麻木,和易中天先生相比,我們難道不汗顏嗎?
論據分析在議論文寫作中分量極重,卻常常得不到重視。其實,從議論文的寫作目的來說,論據分析的重要性其實是大過論據的,因為分析才是對觀點的演繹、對意義的闡釋,才能夠說服讀者。根據筆者的搜索,常見的論據分析方法有:意義評價法、因果分析法、假設推理法、比較分析法等。筆者這里所說的“聯想法”可以說是對上述方法的有益補充。靈活運用這些分析方法,就能使論據分析搖曳多姿、富有特色。
本欄目責任編輯:李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