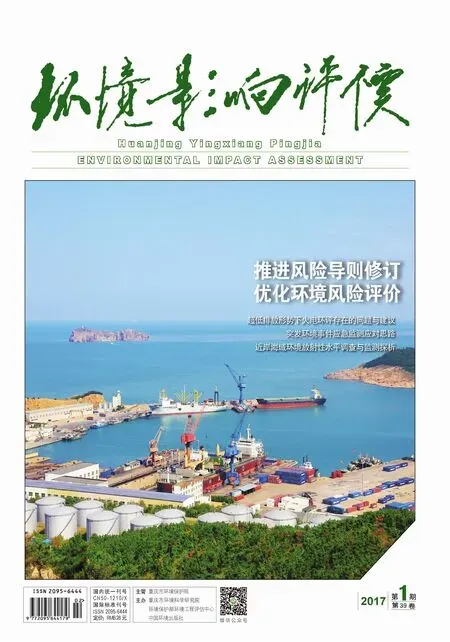環境影響評價現狀監測數據的審核與判斷
曹家新
(福建省沙縣環境監測站,福建沙縣 365500)
環境影響評價現狀監測數據的審核與判斷
曹家新
(福建省沙縣環境監測站,福建沙縣 365500)
為避免錯誤的監測數據給環評結論造成不利影響,結合環境影響報告書評審過程中發現的問題,通過實例對建設項目環評現狀監測數據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對數據的審核與判斷進行探討,對錯誤的監測結果進行有效識別,并提出在實踐中完善項目環評現狀監測的幾點建議。
環境影響評價;現狀監測;數據審核
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現狀監測,作為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的主要技術依據,顯得十分重要。污染源調查不僅是為污染綜合防治提供依據,也是環境影響評價的基礎工作[1]。環境影響評價現狀監測數據的準確度將直接關系到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結論的正確與否。環境影響評價現狀監測除了要按導則的要求進行采樣布點,監測的頻次、調查分析的項目是否合理外,現狀監測是否委托有資質單位進行,引用的數據、資料是否準確有效也同樣重要。判斷環境現狀監測數據是否真實可靠,無疑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將直接對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結論的準確性和可信度產生決定性影響。
1 噪聲監測中存在的問題
噪聲對人們生產生活產生的影響不容忽視。消除噪聲污染,對其加強監管,首先要了解噪聲的源強。因此,做好噪聲監測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噪聲監測必須按相應的監測技術規范進行,如關注聲級計的選擇、監測時間、監測點位的布設是否合理。例如,交通噪聲的測點在兩路口之間,路邊人行道上,離車行道路沿20 cm處,離路口應大于50 cm,測各測點20 min的等效聲級Leq[2];而鐵路邊界噪聲的測量則是距鐵路外側軌道中心線30 m處,若測量機動車行駛的輻射噪聲,測點取離軌道中心7.5 m處,高度距軌道1.5 m處[3],采樣時間間隔不大于1 s,連續取1 h的等效聲級。
1.1 交通噪聲監測結果不符合聲傳播規律
根據聲傳播規律,點聲源聲傳播距離增加1倍,衰減值為6 dB;線聲源聲傳播距離增加1倍,衰減值為3 dB。如果監測結果與傳播規律有明顯偏差,就要分析原因。例如,某路段20 m與40 m的噪聲監測結果衰減值為7.5 dB,就超出了線聲源聲傳播規律,監測結果不可信。因為即使公路車流量較小,按點聲源進行傳播,聲傳播距離增加1倍,衰減值最大為6 dB,現在線聲源聲傳播距離增加1倍,衰減值卻超出6 dB,監測結果肯定不可信。
1.2 車流量監測數據不符合監測規范邏輯
按《聲環境質量標準》(GB 3096—2008)規定的監測規范,交通噪聲一般是測量20 min,而交通車流量一般要求出具每小時的量,即小時車流量結果應為“20 min的車流量×3”。因此,監測報告中的車流量數值若不是3的倍數,其數據判定為可疑。如某監測報告在測交通噪聲的同時,測得小型車車流量為107輛/h,車流量不是3的倍數,就不合邏輯。
>>路邊高層建筑的交通噪聲隨高度的變化,與道路的數量及周邊物體有很大關系。

1.3 路段敏感點垂向噪聲監測數據理想化
樓層高度受交通噪音的影響有一定的規律:一般情況下,城市的高層建筑往往樓層越高噪聲越大,如對一幢20層的建筑來說,1—5層噪聲最小,10層中等水平,20層最大。這是由于樓層愈高,俯瞰的范圍就愈大,很遠處的交通噪聲也能傳播過來,相疊加的有效噪聲源就多;而樓層愈低,許多原本可能直達的交通噪聲源被有效遮擋,噪聲就愈小,因此低樓層的噪聲可能最小。但如果路邊建筑面對的只有一條道路,情景就有所變化,可能低層最小,中間層最大,再高層又逐漸減小。這是由于地面或其他物體反射的結果,造成高層建筑中部噪聲最大,再高時則由于聲音隨傳播路程增大而衰減變小。總之,路邊高層建筑的交通噪聲隨高度的變化與道路的數量及周邊物體有很大關系。大量的研究表明:中低頻噪聲對低層建筑的影響要比高層嚴重,其根源在于頻率越低受影響程度就越大。
某環評監測結果顯示:某大廈垂直噪聲1層>3層>5層>7層>9層,其數據就過于理想,可信度不高,因為并不一定是樓層高其受影響的噪聲就小。
1.4 結構噪聲監測低頻噪聲不符合邏輯
結構傳播固定設備噪聲測量的是低頻噪聲(<500 Hz),倍頻帶聲壓級測量的倍頻帶中心頻率為31.5 Hz、63 Hz、125 Hz、250 Hz、500 Hz。測量35 dB以下的噪聲(倍頻帶聲級)應使用1型聲級計。
低頻噪聲與高頻噪聲的差異就是高頻噪聲的衰減與距離成正比,距離越遠衰減越明顯,而低頻噪聲卻衰減緩慢,因其聲波較長,能輕易穿越障礙,長距離穿透而直入人耳。低頻噪聲的一般規律是室內噪聲倍頻值31.5 Hz>63 Hz>125 Hz>250 Hz>500 Hz。如果某監測報告對民宅客廳監測結果為250 Hz為55 dB,125 Hz為52.9 dB,監測結果250 Hz>125 Hz,其數據就存在問題。
1.5 統計聲級監測數據之間存在矛盾
統計聲級是指在整個測量時間內或次數中出現時間或次數在N%以上的A聲級,單位為dB(A),最常用的是L10、L50和L90。L10表示在測量時間內有10%的時間超過的噪聲級,相當于噪聲平均峰值(噪聲峰值);L50表示在測量時間內有50%的時間A聲級超過的值,相當于噪聲平均中值(平均噪聲);L90表示在測量時間內有90%的時間A聲級超過的值,相當于噪聲平均底值(背景噪聲)。L10=70 dB表示噪聲級高于70 dB的時間占10%。
一般的情況下,L10大于Leq值,主要從L10、L50、L90之間的關系可以看出來。如果某報告中L10=63,Leq=68,L10?Leq,顯然數據不可信。
1.6 工業企業廠界噪聲監測布點不科學
在環評報告中經常發現,一些監測單位對工業企業廠界噪聲監測布點很不科學,該布點的地方沒有布點,而沒有影響的地方卻加密布點。測點設置應主要針對噪聲敏感建筑物受影響較大、距離較近的位置。無敏感目標的一般可以不測,有必要時才設點。受影響的噪聲敏感點必須設點監測聲環境,尤其是噪聲敏感點方向的廠界(特別是受高噪聲設備影響),應著重設置噪聲監測點。
此外,汽車制造等機械制造類項目許多工段為間斷生產,且噪聲級變化較大,需要測量代表性時段的等效聲級。有鍋爐、空壓機、風機和冷機等間歇運行高噪聲設備的工業項目,要注意高噪設備的運行特點,測量代表性時段的等效聲級。一般要求測量應在無雨雪、無雷電天氣,風速為5 m/s以下時進行,但風電項目還需要測量敏感點聲環境和距離衰減,此時應注意工作風速(測風塔和風機)和地面風速不同。監測單臺風機廠界噪聲時,噪聲測點應該設置在風機機位占地的邊界(廠界)處,并根據風機槳葉轉子迎風特性,將噪聲測點布置在風機機位占地邊界噪聲較高的一側[4]。而在風電項目竣工環保驗收時,風機噪聲測量的氣象條件為“無雨、無雪、風速12 m/s以下時進行”,同時期在測量風機噪聲時,應在噪聲測量儀上安裝專用裝置,以消除風力對噪聲測量儀器的影響[5]。
2 水質監測中存在的問題
評價一個地區的水環境現狀,往往要對該區域內的水質進行監測。在環評報告中,水質監測主要有污染源監測、地表水監測、地下水監測和飲用水源監測等。不同的監測對象應選擇不同的監測方法,而且對于不同的分析方法,其檢出限也有所不同。除監測方法的選擇外,試樣的前處理、可疑數據的取舍等都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2.1 樣品未檢出的表示方式不科學
監測數據未檢出,只是說明在當前方法的檢出限內未檢出,在報告中不能寫“未檢出”,而應寫“<”或“檢出限+L”。例如,金屬鋅與鎳的分析方法都是火焰原子吸收光度法[分別是《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GB 7475—1987)和《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GB 11912—89)]。對樣品的未檢出,應表述為鋅<0.05 mg/L,鎳<0.05 mg/L。若鋅采用雙硫棕分光光度法進行分析,樣品的未檢出則應表述為鋅<0.005 mg/L。它既包括了未檢出的含義,也給出了分析人員所用方法的檢出限值[6]。
2.2 數據與分析方法的檢出限不符
在環境監測中,檢出限是某特定分析方法在給定的置信度內可以從樣品中檢測出待測物質的最小濃度或最小量。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檢出限,就是同一方法也會因取(進)樣量、試劑、用水、儀器等因素而存在差異。若試樣經測試未檢出,其結果應表示為“<方法的檢出限”,既包括了未檢出的含義,也給出了分析人員所用方法的檢出限值,在符合統計量的前提下容易折算為1/2檢出限值進行統計計算。例如,某監測報告采用《水質 總磷的測定 鉬酸銨分光光度法》(GB 11893—89)對地表水的總磷進行監測,監測結果表示為0.002 mg/L。這種情況就存在問題,因為該方法總磷的檢出限為0.01 mg/L,而分析結果卻大大小于該方法的檢出限,顯然不合邏輯。
2.3 測得的溶解氧超出飽和溶解氧值
溶解氧與水溫有著密切聯系,各種溫度下都有其飽和溶解氧值,在一定溫度下的監測結果通常不能高于其飽和溶解氧值。例如,某監測值顯示水溫22℃地表水的溶解氧為10.5 mg/L就有異常,因為22℃的飽和溶解氧值僅8.73 mg/L,監測值居然高出飽和值。同樣,20℃的飽和溶解氧值僅為9.08 mg/L,若測得地表水的溶解氧為9.50 mg/L,也應視為異常。對于溶解氧存在的過飽和現象,要進一步核實,查找原因,如水中可能存在氧化或還原性氣體,也可能造成溶解氧監測的過飽和現象[7]。
2.4 未測水溫卻得出溶解氧指數
眾所周知,DO的標準指數計算式為:
式中,DO為監測值;DOs為評價標準值;DOf為當時水文條件下的飽和溶解氧值;T為水溫,℃。
如果某報告書中對監測斷面水環境質量現狀的監測數據中并未包含水溫,也就無法查出其飽和溶解氧值DOf,但環評報告中卻給出溶解氧的單因子指數,顯然結論不可信。
2.5 糞大腸菌群值不符合稀釋梯度的倍數
采用“多管發酵法”進行監測的結果不符合“糞大腸菌群檢數表”中稀釋梯度的相關倍數,監測結果就值得懷疑。
如某報告對河流的監測結果中,糞大腸菌為“<2個/L”。河水未經消毒處理,根本不可能這么理想。河流水質一般糞大腸菌都是大于24萬個/L;此外,糞大腸菌的監測方法一般采用多管發酵法,其監測數據是按“糞大腸菌群檢數表”乘以一定稀釋倍數得出,即使按稀釋梯度10、1、0.1,分析結果也要<20,不可能小于2。因此,上述監測結論明顯不正確。
2.6 CODMn與BOD5的監測數據不符合規律
在水和廢水測定中,某些指標存在一定的相關性。在CODCr、CODMn和BOD5中,CODCr的氧化劑重鉻酸鉀的氧化能力最強,可氧化大部分有機物,所有能被氧化的物質全部都作為COD被檢出,只有多環芳烴、芳香族有機物、吡啶等不被氧化。氧化能力次強的是高錳酸鹽指數的氧化劑高錳酸鉀,但因高錳酸鉀能氧化有機物比較有限,一般僅限于不飽和烴及其衍生物、苯的同系物、醛等,并且高錳酸鉀不是徹底氧化的;而BOD5測定的雖然也是水體中的還原性物質,但其過程是一個完全的仿生物自然氧化過程,涉及諸多因素[8],一般略小于高錳酸鉀指數。因此,一般來說,CODCr>CODMn>BOD5。如某報告對某河流水質斷面的監測結果顯示BOD5=2.63 mg/L、CODMn=2.30 mg/L,斷面BOD5監測結果大于高錳酸鹽指數,顯然不正確。
2.7 氨氮監測值與總氮監測值倒掛

如某報告顯示,河流斷面氨氮=0.427 mg/L、總氮=0.35 mg/L,斷面氨氮數據高于總氮,該結果明顯存在問題。
3 環境空氣與廢氣監測中存在的問題
環境空氣質量現狀評價是環境空氣影響評價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環境空氣質量現狀的調查與監測,了解評價區環境質量的背景值,為分析和計算擬建項目對環境空氣的影響提供基礎數據,為區域大氣污染物總量控制提供科學依據[9]。因此,其監測數據正確與否也同樣對評價結果構成影響。
3.1 環境監測分析方法選擇不對
監測分析方法的靈敏度要滿足環境質量標準的要求,否則得出的結果就可能沒有意義。如在《空氣和廢氣監測分析方法(第四版)》中敘述《空氣質量 甲醛的測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GB/T 15516—1995)適用于環境空氣和工業廢氣中甲醛的測定。在采樣體積為0.5~10.0 L時,測定范圍為0.5~800 mg/m3。環境空氣采樣要求采樣10 L,則監測結果最低為0.5 mg/m3,還遠高于《工業企業設計衛生標準》(TJ 36—79)中甲醛一次最高容許濃度0.05 mg/m3的評價標準[10]。因此,如果用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測定環境空氣中的甲醛,選擇的方法就不正確,要選擇靈敏度更高的分析方法。
因此,對于環境空氣質量監測中的某些項目,尤其是特征污染物,在委托監測時最好能告知評價標準,以便監測單位能夠根據評價標準來確定采樣體積,選擇合適的靈敏度,確保監測結果滿足環評的需要。
3.2 無組織排放濃度評價取值錯誤
要注意一些污染物排放標準對無組織排放濃度進行評價時,不是取平均值進行評價,而應取最高值。如果按習慣以平均濃度對結果進行評價,就可能得出錯誤結論。
例如,某水泥廠粉塵無組織排放測定結果分別為參照點0.18 mg/m3,其余測點為0.46、0.68、0.58、0.69 mg/m3。某環評報告分析認為,扣除參照點值0.18 mg/m3后的平均值為0.42 mg/m3,即(0.28+0.50+0.40+0.51)÷4≈0.42,對照《水泥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GB 4915—2013)表3中規定的水泥廠粉塵無組織排放標準限值為0.5 mg/m3,從而判斷該水泥廠無組織排放粉塵達標就錯了。因為有1個測點為0.69 mg/m3,扣除參考點值后為0.51 mg/m3,仍屬于超標。因此必須判定該水泥廠無組織排放粉塵超標。
3.3 鍋爐房裝機總容量未考慮備用鍋爐
《鍋爐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GB 13271—2014)表4中規定了燃煤、燃油鍋爐房裝機總容量與煙囪最低允許高度之間的關系,實際工作中容易忽視鍋爐房中備用鍋爐的容量[11],該標準還規定了“不同時段建設的鍋爐,若采用混合方式排放煙氣,且選擇的監控位置只能監測混合煙氣中的大氣污染物濃度,應執行各個時段限值中最嚴格的排放限值”。
如某企業新建鍋爐房有2臺2 t/h鍋爐,1用1備,合用1根30 m高的煙囪排放,就不能簡單地認為2 t/h鍋爐執行30 m高的煙囪,而應根據裝機總容量(4 t/h)執行35 m高的排放要求。
3.4 排氣筒高度執行標準未進行折算
在《大氣污染物綜合排放標準》(GB 16297—1996)中,規定了若排氣筒高度處于標準列出的兩個高度之間時,其執行的最高允許排放速率以內插法計算,當排氣筒高度大于或小于標準列出的最大值或最小值時,以外插法計算最高允許排放速率,若排氣筒高度低于15 m,其排放速率按外推計算結果再嚴50%[12]。但《惡臭污染物排放標準》(GB 14554—1993)則不一樣,其規定排氣筒高度不得低于15 m,在兩種高度之間的排氣筒,采用四舍五入的方法計算排氣筒高度[13],而不同于《大氣污染物綜合排放標準》中的內插法。
4 結語
環境監測是環境影響評價的技術基礎,環評中對監測數據的審核與判斷十分重要,一個錯誤的監測數據不僅可能“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導致錯誤的環評結論,還可能給投資者帶來巨大損失和浪費。因此,在環評中必須不斷總結經驗,使用科學、準確的監測數據為環評服務。
為完善項目環評現狀監測,建議做好如下工作:
(1)委托有資質、監測質量好、信譽好的監測單位開展相關工作。
(2)事先對監測方案進行審查,如點位的布設、監測的頻次是否滿足導則要求,監測的污染物因子有沒有缺漏。在監測因子選取、點位布設和監測頻次的確定上,應嚴格按照國家標準、環評導則以及有關技術規范的要求進行,保證監測數據能夠如實反映各監測要素的真實情況[14],才能使環評監測方案具有科學性、代表性。
(3)事后對監測單位提供的監測報告進行數據審核,如數據是否符合邏輯,其相關性如何,有效數字是否滿足要求。一旦發現異常數據,要及時溝通,必要時重新監測復核,以確保監測結果的真實可靠,為項目環境影響預測評價提供科學依據。
[1] 陸雍森. 環境評價[M]. 2版. 上海: 同濟大學出版社, 1999: 25.
[2] 國家技術監督局. GB/T 3222—1994 聲學 環境噪聲測量方法[S]. 北京: 中國標準出版社, 1994.
[3] 國家環境保護局. GB 12525—90 鐵路邊界噪聲限值及其測量方法[S]. 北京: 中國標準出版社, 1990.
[4] 沈燕, 蔣志剛, 張景明. 江蘇風力發電項目竣工環境保護驗收噪聲監測之我見[J]. 價值工程, 2013(26): 96- 97.
[5]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DL/T 1084—2008 風電場噪聲限值及測量方法[S]. 北京: 中國電力出版社, 2008.
[6] 曹家新. 環保驗收監測中標準應用及檢出限等問題的探討[J]. 福建分析測試, 2011, 20(1): 33- 39.
[7] 楊文光, 潘偉清. 地表水監測分析中溶解氧的過飽現象及其原因探討[J]. 廣東化工, 2011, 38(7): 224- 251.
[8] 黃慧坤. 辨析高錳酸鹽指數、化學需氧量、生化需氧量[J]. 云南環境科學, 2004, 23(S1): 181- 182.
[9] 李愛貞, 周兆駒, 林國棟. 環境影響評價實用技術指南[M]. 北京: 機械工業出版社, 1999: 75- 76.
[10] 曹家新. 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現狀監測應注意的若干問題[J]. 干旱環境監測, 2014, 28(3): 39- 44.
[11] 環境保護部. GB 13271—2014 鍋爐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S]. 北京: 中國環境出版社, 2014.
[12] 國家環境保護局. GB 16297—1996 大氣污染物綜合排放標準[S]. 北京: 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1996.
[13] 國家環境保護局. GB 14554—1993 惡臭污染物排放標準[S]. 北京: 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1993.
[14] 游大龍, 阮強, 胡濤. 環評中環境現狀監測存在問題與對策分析[J]. 環境影響評價, 2015, 37(6): 34- 36.
The Review and Judgment on the Monitoring Data of Current Status i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CAO Jia-xin
(Shaxia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 Shaxian 365500, China)
In order to avoid negative impact caused by false monitoring data i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this paper analyzed issues on monitoring data i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Based on the problems arising i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report during the reviewing process, it discussed the review and judgment on data through practical examples. In this case, false monitoring results were effectively identified. In combination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current status monitoring o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current status monitoring; data reviewing
2016-08-21
曹家新(1964—),男,福建沙縣人,高級工程師,注冊環境影響評價工程師,學士,主要從事環境監測與環境影響評價,E-mail:caojiaxin2002@163.com
10.14068/j.ceia.2017.01.012
X830
A
2095-6444(2017)01-004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