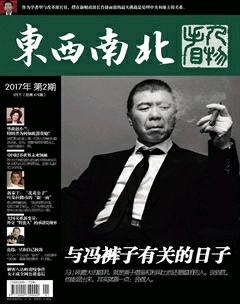快手:3億用戶的“隱形獨角獸”
吳丹
沒有對內容的刻意推薦,沒有給用戶貼標簽,快手長成了自己獨特的模樣。快手似一面鏡子,看著里面的大千世界,一時間眾說紛紜。
2016年6月9日以前,江湖還沒有快手的傳說。
X博士那篇《殘酷底層物語》在社交媒體引發大量關注后,有關“快手APP”的議論一時不絕于耳。最令人驚奇的是它的幾個數字:在各種APP排行榜都是前十,累計用戶量3億,月活躍用戶超8000萬(官方數據)。從這幾個數字來講,它確實是短視頻社交領域穩穩的行業第一。
然而關于他們的正式新聞報道,甚至不能用“很少”來形容,而是壓根就沒有。
如果在網上搜索“快手CEO 宿華”,只會得到一些零碎信息,“華仔,清華畢業,在谷歌和百度待過。曾有過一次小型公開演講,地點是母校”,僅此而已。搜索另一位合伙人程一笑,得到的信息會更少:一笑,極客,在人人網做過產品,玩過微博,被有些人寫文章稱為產品大牛。
但究竟,快手從何而來,宿華和程一笑是誰,這幾年是怎么創業的?沒有更多信息。對很多人來說,它是一只忽然“冒出來”的獨角獸。
“總是要面對媒體的。也想過站出來把快手的故事給大家講一講,要不然老是被猜測,我們也很困擾。”2016年7月15日,快手CEO宿華首度露面,這是一個關于“靜默無聲”的產品哲學故事。
誕生和成長
宿華不認為快手的特點和他個人的氣質有什么關聯,他已在北京五道口生活了近15年。在五道口的15年,宿華一直被某種狂奔突進的創業環境所包圍。他們也曾租住在“民間硅谷”華清嘉園。那是段“樓上在做無人機,樓下做團購”的日子。“做無人機的事就不多說了,他們要我保密。”宿華笑道。
快手是宿華的第三次創業。他職業生涯起點較高,清華博士讀了一半,因為需要養家就退學去了谷歌。兩年后開始了“各種折騰”。
第一次折騰,因“2008年金融危機、融不到錢”而告終,在百度蟄伏近兩年后又開始第二次創業,產品后來被阿里收購。
這么著,時間線走到了2013年夏天,他和程一笑相見的時間點。相識那天,兩人從晚飯后一直聊到凌晨兩點。“朋友介紹的,我們見了一面。很投緣,有種相見恨晚的感覺。”宿華簡單的描述之間,流露出一種人生知己相逢的感覺,“我們彼此價值觀相似,易于相互理解;技能經歷又很不同,亦很互補。”
這個時候的程一笑,又在干什么?
答案是,4個人,在京郊天通苑創業,做一個把短視頻和照片轉成GIF動圖的工具,名曰“GIF快手”。產品通過微博、QQ空間等導流,已攢了90萬用戶,兩年前曾獲過30萬美金的天使投資。其投資人、晨興資本合伙人張斐描述,投資原因有一條是“當時在微博上有不少人用”。事實驗證了他的說法,即使現在搜索微博,也還能找到2011年主持人何炅用快手拼了多張他與汪涵合照的GIF動圖,評論跟帖超過6000條。
程一笑在微博上有幾百個粉絲,不怎么愛說話,個人介紹一欄寫的是“做些好玩的東西”。而宿華的微博壓根就找不到。
如前所述,兩人見面后相談甚歡,決定合在一起干。“我當時有7個人,一笑他們4個人。兩個團隊合并后都搬到了宇宙中心五道口。”宿華回憶道,“但是公司名字我們沿用了快手,因為我們都覺得,這個東西更好玩兒。”
一番談話下來,他們怎么就決定轉型做短視頻社交了呢?
這其中有一個原因是,宿華之前的創業、程一笑之前的人人網工作,都是在社交領域,他們對轉型的更多判斷根據是,2013年,WiFi技術已成熟,智能手機越來越普遍;有聲音稱,富媒體的視頻表達是未來;長視頻并非人人能拍,短視頻上手快,能做成很好的社交產品。
唯一的遺憾是:市場上并沒有成功案例。資料顯示,其他短視頻社交平臺最早上線的也是2014年前后。客觀來講,直到今天短視頻社交領域也算不上有過大爆發,未有過上市公司,也并沒有現象級產品出現,商業模式都在摸索中。
或許正是創業前期的懵懂與未知,牽引他們走到了一起。
從此,五道口便又多了4個從天通苑來的創業者。一幫人悶著頭又干了3年。
如果讓宿華形容這些年的用戶增長曲線,他八成會先把手平放,然然慢慢上揚,以此顯示出一種勻速上漲的樣子。他說快手幾乎沒有暴增暴減的時候,一直平穩上漲。
唯一的一次用戶暴減,是發生在當年轉型決定做出后,新版本突然上線之時。“那次上線,我們就突然轉型了,短視頻轉GIF的功能藏起來,只支持直接上傳短視頻,用戶打開一看,產品主要功能換了,舊功能找不到了,馬上有人開始各種罵,‘這什么情況?——因為不適應,用戶一下走了90%。”宿華說轉型是快手至今做出的最重大決定,此后再沒有大幅度改變,這點和網友的外圍觀察是吻合的。“后來他們都回來了。這個改版從無聲到有聲,其實是在適應用戶需求的正常發展。”
3年間,快手的產品哲學是:不對用戶做任何刻意的事,對產品保持極度克制。
或許,3億用戶的秘密來自這里。
快手產品觀
社交產品往往免費,商業模式要從大的用戶流量中沉淀出來,才會有后來的廣告、游戲、電商等變現故事。同時用戶還要活躍,要天天來,只有“黏在”平臺上,才能掉進“廣告、游戲”等模式中。不像電商,講求交易量,再活躍沒有交易行為都是空。
按此邏輯,用戶數和黏性成了做社交的關鍵指標。微信用戶數超7億,陌陌過2億(據公開資料)。整個社交領域,用戶過億的應用數得過來。
怎樣的軟件,可以實現最大用戶量,讓上億中國人來用?在上億的國人中找共通性,好像要比在他們中找“小資”、“二次元”、“小清新”、“90后”、“中產”等要難——貼標簽往往很容易,但也限制了你。
問題還有,在分眾趨勢如此明顯的今天,還存在能俘獲上億用戶的軟件嗎?如果有,如此大量的用戶,他們的共同需求又會是什么?
“你看了快手后會發現,這個世界上的人們生活真是豐富多彩。你的朋友圈子真的太窄,多的是你想象不到的奇特和新鮮。”
在其它社交平臺上,很容易看到對快手的類似評價。
快手找到了3億用戶的共通性,實現路徑是:不給用戶貼標簽,不打擾用戶,讓平臺自然生長。“我們的用戶群分布情況,跟中國互聯網網民的地域分布非常像,百分之十幾用戶來自一線城市,百分之八十多來自二、三線城市——中國網民地域情況就是這樣分布的。”宿華說。這個結果并非巧合,而和初心有關。
在宿華和程一笑決定合伙干的時候,他們就定下了快手的一些基本原則:給普通人用,沒有明星導向,不捧紅人,做一只“隱形”的手。
這也是為什么,快手上至今沒有醒目的標簽、大V位置、平臺推薦等原因,就連火熱的直播,也只是被隱藏在它的視頻流里,快手官方并沒有單獨辟出一條分欄。
宿華多次用“老百姓”一詞形容他們的用戶。“我們覺得老百姓挺需要一個展示自己的平臺,不管他是在二、三線城市還是北上廣深,也不僅僅是去某個平臺看網紅,看明星,而是展示自己。”“我和一笑喜歡去默默觀測,這個世界到底是怎樣運轉的,老百姓到底怎樣會更開心。”“我和一笑就是普通的老百姓。最愛吃的,一直是五道口的一家干了多年的米粉,吃了十多年,現在還是每周都去吃。這樣的生活,挺好的。”
而客觀事實也正是,“老百姓”用戶支撐起了快手上所有的高流量內容:有人在記錄自己的跑酷生涯,也有人在表演 “鄉村非主流”的搞笑短劇;有人在彈各種鋼琴曲給粉絲聽,也有人講各種段子;有人曬自己三胞胎的日常生活,也有人給自己過90大壽的奶奶求祝福;有富二代環球旅行住上萬元一晚的奢華酒店,也有驢友一輛自行車全國騎行;有小情侶秀恩愛,也有失戀求安慰;有女人在曬美貌,也有男人炫多金。儼然一個小社會。
宿華稱,目前在快手上發過視頻的用戶已超1億,而依照快手官方“不做刻意的事”的態度,與其說是平臺在“推動”這些內容,不如說是快手用戶的創造與選擇造就了它,而內容反過來又定義了快手。
“以前我們都用相冊記錄生活,現在有移動互聯網,拍成短視頻傳到快手,沒事的時候翻翻,是生活的記錄、記憶的回放。”宿華笑著說,如果他不做快手,擱在幾十年前,很可能會去做一家相機或者膠卷公司。他目前在快手上也關注了幾百個人,“關注的一個中學生,原是個活潑的假小子,幾年一晃過去了,現在上了大學,長成大美女,長發飄飄。”
他每晚也都會刷刷快手,平均一兩個小時,和用戶們互動。沒人知道他是創始人。
快手的特點也反映了兩位創始人的特點:低調,克制。
至今,宿華和一笑從不會主動跟親戚朋友推薦快手,也不會主動告訴親戚朋友們,那些被傳到他們微信群、QQ群里的短視頻,就是他做的快手里的;他們更希望看到,自己的親朋好友玩快手是因為喜歡,而不是因為認識自己;公司前臺背景墻至今依然是一片空白,沒有任何logo標識;不喜采訪和曝光,公司也沒有搞宣傳的人。
“我們都是比較宅的人,喜歡有推理、演繹的邏輯思考。”宿華這么定義自己和程一笑。
爭議與未來
如果3億用戶的基數不變,快手可能還會有另外一幅樣子嗎?快手的內容結構,是偶然還是必然?
旁人對快手的疑惑,更多的爭議焦點在于,快手到底如何定義“平臺規則”這件事?它支持什么,鼓勵什么?一件顯而易見的事是,社交平臺的屬性、價值觀會定義它的內容與結構。微博將內容限制在140字以內,由此誕生大量“段子手”;微信開發訂閱號,只有“干貨”才會被轉發,誕生了大量有內容基因的“自媒體”;豆瓣鼓勵用戶給書籍和電影評分,前期用戶都是文藝青年。
隱形的快手,對“平臺規則”是怎么理解的?宿華說:一、合法合規;二、要有包容性,只要內容是自然產生的,要去包容它的多元化;三、內容真實有趣,但不鼓勵嘩眾取寵的行為。“可以偶爾開個小玩笑,但長期故意這樣,肯定不符合平臺定位——這就不是在記錄生活了。”
沒有對內容的刻意推薦,沒有給用戶貼標簽,快手長成了自己獨特的模樣。快手似一面鏡子,看著里面的大千世界,一時間眾說紛紜。
而快手也正在經歷一個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的快速發展期。
和此相關的,還有它正在進行中的商業化。“視頻瀑布流里的原生廣告會是很重要的方向。電商、游戲等都在考慮,類似公司已經有很多經驗了。”宿華說。
和并不新鮮的商業模式比起來,他們前不久的一項舉措可能更讓人振奮:進軍全球市場。
“如果說中國的老百姓有短視頻的記錄需求,國外的老百姓一樣有。”對此,宿華也談到幾個難點,語言、習慣、資源。
目前快手已經在東南亞市場有所建樹,核心技術團隊在新加坡,產品在印尼和印度都在研發中。宿華稱,快手會是一家一直在進化的公司。
以上種種,似乎隱含一層意思,快手也許比大眾想象的要目標遠大。
當下的問題是,快手能否變現成功,會實現多大規模?在變現的路上,它會否遇到問題?它的發展路徑,還可能呈現怎樣的形式?
國外曾火爆一時的短視頻應用Vine于三年前上線,上線前就被Twitter收購。微視(由騰訊推出)、小咖秀、秒拍、美拍等也面臨爆紅之后的增長態勢考驗。在變現上,短視頻平臺這一領域未有成功案例。
除商業外,用戶和創始人也有各自關心的東西。
快手上已有大量網紅,沒人會懷疑,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會去思考下一步的變現方式。
低調已被打破,越來越多的人會開始關注快手的未來。五道口成府路口,橙色的快手logo的廣告牌被高高懸掛,讓路人驚訝:這個廣告牌替換掉了原來的那個誰?
宿華的答案是,現在每天有幾千萬人要訪問快手,需要大規模招人提升技術后臺。得讓人到了公司樓下后就會知道,雖然網上搜不到這家公司,但“我們還是一家很認真的公司的,在做事”。
(趙靜薦自新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