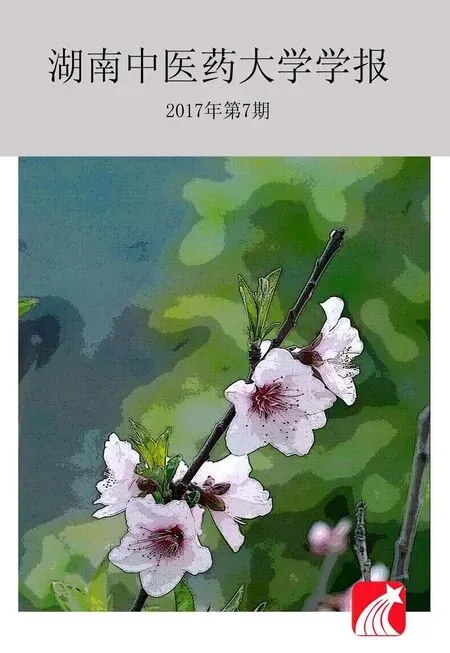國醫大師孫光榮論“隨證治之”
葉培漢,孫貴香*,何清湖,楊玉芳,胡志希,張冀東,孫光榮*
(1.湖南中醫藥大學,湖南 長沙 410208;2.國醫大師孫光榮湖南工作室,湖南 長沙 410208;3.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醫基礎理論研究所,北京 100700)
國醫大師孫光榮論“隨證治之”
葉培漢1,2,孫貴香1,2*,何清湖1,2,楊玉芳1,胡志希1,張冀東3,孫光榮2*
(1.湖南中醫藥大學,湖南 長沙 410208;2.國醫大師孫光榮湖南工作室,湖南 長沙 410208;3.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醫基礎理論研究所,北京 100700)
國醫大師孫光榮臨證58載,認為“隨證治之”是對中醫治法的高度概括,是針對“觀其脈證”獲知的“主證”“知犯何逆”把握的“主變”而抓的“主方”,對如何擇用有效方藥“隨證治之”進行深入探索,將自身多年臨床經驗總結成歌訣,并闡發其內涵,對于從事中醫臨床者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國醫大師;孫光榮;隨證治之;中醫治法
國醫大師孫光榮,出身于中醫世家,幼承庭訓,師承名醫,在臨證58載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擅長治療中醫內科、婦科疑難雜癥,尤其是腦病、腫瘤、血液病、情志病、脾胃病以及帶下病等療效卓著。孫老師始終秉持中醫藥“以人為本、效法自然、和諧平衡、濟世活人”的核心理念,治學行醫既講求正本清源,又善于開拓創新[1-3]。臨床上以中和思想為指導,時時強調“護正防邪,存正抑邪,扶正祛邪”;體現中和辨治特點,認為臨床思辨的重點不外“調氣血、平升降、衡出入”;遵循中和思想組方用藥,以“三聯藥組”之功能按君、臣、佐、使結構組方,“遵循經方之旨、不泥經方用藥”,形成孫氏系列經驗方[4-6]。
“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語出《傷寒論》第16條,條文原為“壞病”的治療法則,今已不限于此,因其高度概括了中醫臨床辨證論治的全過程,對中醫診治過程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其中,“隨證治之”指的是通過患者癥狀、體征的表現,證候的演變,動態分析把握病因病機,明之以法,處之以方,投之以藥。孫老師在臨證之中,認為“隨證治之”實際上就是概括了中醫治法的精髓,是針對“觀其脈證”獲知的“主證”“知犯何逆”把握的“主變”而抓的“主方”,講求個體化治療[2,7,8]。對于如何擇用有效方藥“隨證治之”,孫老師深入研究并總結:“經方本是萬方宗,方證相符立見功。時方多是古驗方,究明方旨古今通。師承驗方有奇效,東南西北不相同。自擬新方要有據,切勿雜糅亂糊弄。先定治則與治法,君臣佐使井然從。最忌濫伐無過者,扶正祛邪要適中。須知專病有專藥,從順其宜力更雄。”并對其內涵逐一進行了闡述。
1 經方本是萬方宗,方證相符立見功
目前中醫學界普遍認為,經方是東漢張仲景所著《傷寒雜病論》(宋代之后分為《傷寒論》《金匱要略》)所記載之方劑,是相對于宋、元以后出現的時方而言的。其中,《傷寒論》方113首,《金匱要略》方262首,除去重復的,共計178首方,151味藥。經方被后世醫家稱為“醫方之祖”“方書之祖”,張仲景也被尊為“醫圣”。
經方是本,是源[9],因其組方嚴謹、藥量精當、煎服講究、針對性強、效如桴鼓,具有“普、簡、廉、效”的特點,故后世醫家大都是以經方為準繩,或直接用經方,或從經方中演變、延伸。
如何學習和運用好經方一直是中醫學界所關注和探討的問題。孫老師提倡“萬方宗經,學用并行”,在學與用中及時發現問題,在問題中深化學習,在學習中思考借鑒,在借鑒中創新認識,學以致用以求臨床最好療效。歷代名醫運用經方有其獨到的見解,對于學習和運用經方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尤其是對名醫大師運用經方驗案的學習,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之效,不失為學習經方的一條捷徑。
經方的核心理論是方證對應,方與證是經方運用的關鍵[10]。孫老師認為,方證對應是經方制方的主要原則,講求“有是證必用是方”,臨床上運用起來既簡單又有效。如《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言:“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脅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脅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咳者,小柴胡湯主之。”并且強調“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只要出現其中一二主證就用該方治療,不必等到所有癥狀都出現。類似這樣嚴謹的方證對應關系在《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中隨處可見,如“發熱而嘔者,小柴胡湯主之”,“嘔而胸滿者,吳茱萸湯主之”,桂枝湯證“汗出,脈浮緩”,麻黃湯證“無汗,脈浮緊”。
2 時方多是古驗方,究明方旨古今通
經方是源,時方是流。如小柴胡湯與逍遙散,四逆散與柴胡疏肝散,傷寒三承氣湯與溫病諸承氣湯等,脈絡清晰、源流分明[11]。時方雖是流,但也是經過反復驗證的古方,既創造性地彰現了經方的特色,同時又擴大了經方的應用范圍,是對經方的補充完善,臨床處方時不可不重視。如醫家張元素謂九味羌活湯“冬可以治寒,夏可以治熱,春可以治溫,秋可以治濕”,“視其經絡前后左右之不同,從其多少大小輕重之不一,增損用之”。
時方多以陰陽五行、臟象、經絡、運氣等為核心理論,更強調對疾病病因病機的認識[12]。特點是方劑名表示效用者多(如咳血方、枳實消痞丸、玉屏風散、當歸補血湯、清絡飲、清暑益氣湯等),功效經絡臟腑化(如導赤散、瀉白散、易黃湯、實脾散、平胃散、龍膽瀉肝湯、溫膽湯等),結構較為松散,藥物加減多變,照顧面較廣[11]。
無論是經方還是時方,都應強調從臨床出發,為臨床服務。究方義,明方旨,既對經方有扎實的基礎,又對時方有足夠的研究,如此才能古今相通,“經”“時”結合。
3 師承驗方有奇效,東南西北不相同
由于東西南北氣候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差異、用藥習慣不同,出現了不少驗方,有些也稱秘方。《簡明中醫辭典》解釋:驗方是指有效驗之方藥。廣義上,經方、時方和專方大都是經臨床驗證有效者,也都可稱之為驗方[13]。如苗醫、瑤醫、壯醫、羌醫、藏醫、蒙醫等,均形成了地區獨特的醫藥特點;民間祖傳的奇效驗方,如醫治蛇傷的“季德勝蛇藥”、用于傷科的“曲煥章百寶丹”等;各個醫家在數十年臨床積累下來的遣方用藥習慣,形成了其獨特有效的驗方,經醫家本人或徒弟門人總結整理,后人繼承,有些還形成了門派。
驗方是許多醫家和人民與疾病斗爭留下來的寶貴經驗,雖然有些并非名家論著,但卻代代相傳,屢試屢驗。作為服務于人民健康事業的醫者,應該多拜讀醫著,多拜師學習,“博采眾方”,汲取其精華。
4 自擬新方要有據,切勿雜糅亂糊弄
由于臨床疾病復雜多變,習得的方藥可能并不符合患者的病情,《醫學源流論·出奇制病論》對此深有感觸:“病有經有緯,有常有變,有純有雜,有正有反,有整有亂。并有從古醫書所無之病,歷來無治法者,而其病又實可愈。”故而,并非不可自擬新方。
《醫學源流論·出奇制病論》指出:“既無陳法可守,是必熟尋《內經》《難經》等書,審其經絡、臟腑受病之處,及七情、六氣相感之因,與夫內外分合,氣血聚散之形,必有鑿鑿可徵者,而后立為治法。或先或后,或并或分,或上或下,或前或后,取藥極當,立方極正。”《醫學源流論·方劑古今論》云:“圣人之制方也,推藥理之本原,識藥性之專能,察氣味之從逆,審臟腑之好惡,合君臣之配偶,而又探索病源,推求經絡。”故而,自擬新方當學習前人,“取藥極當,立方極正”,深入病機,考慮周全,才能游刃有余。否則只會冒昧施治,藥物雜糅,盲目堆砌,貽害無窮矣。
孫老師躬身力行,“勤求古訓”,結合自己多年的臨證經驗,創立了以“中和”為核心的醫學流派,以中和思想組方用藥,以“三聯藥組”之功能按君、臣、佐、使結構組方,追求中藥相須、相使、相畏、相殺減毒增效功能最大化,“遵循經方之旨、不泥經方用藥”,形成孫氏系列方。如以小柴胡湯為核心化裁之“孫光榮扶正祛邪中和湯”,以射干麻黃湯為核心化裁之“孫光榮化痰降逆湯”,以甘麥大棗湯為核心化裁之“孫光榮安神定志湯”,以理中丸為核心化裁之“孫光榮益氣溫中湯”,以苓桂術甘湯為核心化裁之“孫光榮滌痰鎮眩湯”等[5],均結構嚴謹,有依有據,誠可給新一代的中醫臨床執業者以啟迪。
5 先定治則與治法,君臣佐使井然從
治則即治療疾病的法則,是指導治法的總則。治法是在治則的指導下確立的具體措施和方法。治則在先,高度抽象,注重整體;治法在后,內容具體,針對性強。孫老師認為,治療總則不外正治、反治、扶正祛邪、補偏救弊、因人因時因地制宜、調平陰陽、水火相濟等內容[14]。中醫治法主要包括藥物和非藥物(如針刺、艾灸、推拿、拔罐、手術正骨、飲食、氣功、五禽戲、八段錦、太極拳等)手段。此處僅言方藥。
方從法出,法隨證立。治則與治法是溝通疾病證候與方藥之間的橋梁,故而,要使投出的方藥直達病所,就必須先確定使用什么治療原則、采用何種治療方法。“隨證治之”的最終目的也即是確立針對性的治療方法,既考慮原來的治療方法,又重點考慮變化的病證,兩相兼顧,從而確立治則與治法。《醫學心悟·醫門八法》高度歸納總結前人經驗,明確提出治療八法,曰:“論治病之方,則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溫、補八法盡之。……病變雖多,而法歸于一。”
藥有個性之專長,方有合群之妙用。方劑具有多成份、多環節、多途徑、多層次的綜合協調作用,使其治療范圍較廣,可彌補單味藥物治療勢單力薄的缺點,并能調和藥物的毒性,避免或減少不良反應。
方劑的組成有一定的法度,應按照“君、臣、佐、使”的組方原則。《素問·至真要大論》云:“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方中的主藥喻之為君,輔助藥喻之為臣,中和調節藥喻之為佐,引經入絡藥喻之為使。《神農本草經》進一步補充:“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合和。”一般處方用藥多在四種以上,均按此四項配伍,即使少于四種藥或多至二三十種,亦不能離此法則。否則漫無紀律,方向不明,即前人所批判之謂為“有藥無方”。
6 最忌濫伐無過者,扶正祛邪要適中
大道至簡,“邪正”而已,邪與正的關系既對立又統一[15],正如《素問·通評虛實論》所說:“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素問·刺法論》),正能勝邪則病退;“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素問·評熱病論》),邪盛正衰則病進。
扶正和祛邪的關系既相反相抑,又相輔相成,是辨證的統一[16]。虛宜扶正,使正氣加強,以抵御和驅逐病邪,正足邪自去;實宜祛邪,使邪氣祛除,以減少對人體正氣的侵犯和損傷,邪去正自安。若虛實混雜,單純“扶正”,恐助其邪,使邪益盛;單純“祛邪”,慮其虛證,猶恐諸病蜂起,故“扶正”“祛邪”雙管齊下方為上策。或扶正以達到祛邪之目的,或祛邪以達到扶正之目的,或兩者并行兼施以達到雙向調節之良效,使機體最終達到“陰平陽秘”的和諧狀態。但切記要以“中和”為度,莫好大貪功,反致濫補、濫伐。《醫學源流論·用藥如用兵論》就曾針對濫用藥物的情況,警示后人說:“兵之設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興;藥之設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孫老師強調“中和”,其意在此。
7 須知專病有專藥,從順其宜力更雄
專病專方是對疾病全過程的特點與規律進行概括與抽象,抓住核心病機進行論治,是專門針對某種疾病有獨特功效的方藥[17],如《蘭臺軌范》所言:“一病必有主方,一病必有主藥。”專病專方是辨證論治的升華,因專病專方最開始也是辨證論治過程中提煉的,故形成“專病專方”后也就發展和豐富了辨證論治的內容,并沒有背離其精神[18]。實際上,專病專方與辨證論治就是辨病與辨證的關系[17]。
專方主要針對三種情況:疾病名、主證、理化檢查的陽性結果[13],具有可重復性、專門化、標準化、規范化的特點。如消瘰丸治淋巴結核、四神煎治鶴膝風、黃芪桂枝五物湯治血痹、小建中湯治胃痛、千金葦莖湯治肺癰、強肝湯治慢性肝炎、加味活絡效靈丹治宮外孕、青蒿素治瘧疾、雷公藤治類風濕病等[17,19]。然這種一方一病、對號入座的做法顯然有其局限性,故岳美中教授指出:“中醫治病,必須辨證論治與專病專方相結合。”[19]任應秋教授也曾說:“所謂專病,也并不是孤立靜止的,是變化和運動著的。所以在專病專藥的運用中,若不注意先后的階段性,不顧輕重緩急,一意強調固定專藥,也是不對的,較妥善之論治是與辨證相結合的。”[20]
“從順其宜”的治療思想是孫老師據《中藏經》最早總結而來的,如《中藏經·論諸病治療交錯致于死候第四十七》曰:“大凡治療,要合其宜。”《中藏經·水法有六論第十五》曰:“病者之樂慎勿違背,亦不可強抑之也。如此從順,則十生其十,百生其百,疾無不愈矣。”《中藏經·火法有六論第十六》亦曰:“溫熱湯火,亦在其宜,慎勿強之。如是則萬全萬當。”
具體說來,“從順其宜”就是治療手段要合其宜、用藥組方精當合宜、給藥途徑要合其宜,一切要因時、因地、因人而宜,才能達到療效力雄的目的。
深研孫老師有關“隨證治之”的歌訣,要能達到“力更雄”的境界,僅僅照搬經方是不夠的,僅僅依賴師門或自己的經驗方也是不夠的,中醫“隨證治之”的方法是先進的、科學的、豐富多彩、效驗如神的,關鍵是要有真功夫:一是要遵從并牢記經方,二是要儲備師門和多家驗方,三是要遵循“中和”思想而精準確定治則治法,四是要善于因人因時因地制宜。
[1]余瀛鰲,孫光榮,周一謀,等.中醫文獻研究的現狀與對策[J].湖南中醫藥導報,1995,1(5):6-8.
[2]孫光榮.中醫藥創新切勿循“以西律中”之路[J].中醫藥通報,2015,14(6):1-3.
[3]孫光榮.關于21世紀發展中醫藥若干問題的思考[J].湖南中醫藥導報,2000,6(3):9-12.
[4]高 揚.孫光榮:一位潛心求索中醫藥繼承創新和發展的老中醫[J].海峽科技與產業,2014(2):93-98.
[5]劉應科,孫光榮.以中和思想組方用藥——遵循經方之旨,不泥經方用藥[J].湖南中醫藥大學學報,2015,35(9):1-8.
[6]曹柏龍.孫光榮教授臨床經驗總結及補腎化瘀法治療糖尿病腎病Ⅳ期療效觀察[D].北京:北京中醫藥大學,2016.
[7]葉培漢,孫貴香,何清湖,等.國醫大師孫光榮論"觀其脈證"[J].湖南中醫藥大學學報,2017,37(2):119-123.
[8]葉培漢,孫貴香,何清湖,等.國醫大師孫光榮論"知犯何逆"[J].湖南中醫藥大學學報,2017,37(5):465-468.
[9]劉渡舟,劉燕華.古今接軌論[J].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1995(3):8-10.
[10]閆軍堂,劉曉倩,馬小娜,等.劉渡舟教授經方運用學術思想探析[J].中醫藥學報,2013,41(3):1-5.
[11]劉曉麗,溫興韜,黃 煌.經方與時方思維特點的比較[J].中醫雜志,2012,53(12):995-996.
[12]陳樟平,陳 瓊,劉軍城.陳瑞春論經方與時方的應用[J].江蘇中醫藥,2011,43(7):74-75.
[13]舒鴻飛,段龍光.略談經方時方專方與單(驗)方[J].光明中醫,2001(3):23-26.
[14]孫光榮.華佗《中藏經》導讀:揩拭塵封明珠解讀醫家寶典——試析《中藏經》其書與其學術經驗[J].中國中醫藥現代遠程教育,2012,10(1):3-16.
[15]葉雅風.淺析古代樸素辯證法對中醫學的影響[J].中國民族民間醫藥,2009(14):69.
[16]李俊蓮.“扶正祛邪”治則理論探討[J].中華中醫藥雜志,2005(5):275-276.
[17]王 琦.學習岳美中老師“專病專方與辨證論治相結合”學術思想[J].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12,32(7):875-876.
[18]房定亞.專病專方不可忽視[J].北京中醫學院學報,1984(1):35.
[19]陳可冀,江幼李,李春生,等.岳美中老大夫醫話二則[J].中醫雜志,1981(3):12-14.
[20]張壯戰.談談補陽還五湯與腦血管意外[J].新中醫,1984(8):7-8.
(本文編輯 賀慧娥)
Na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ster SUN Guangrong on"Treatment Methods Selection According to Syndromes"
YE Peihan1,2,SUN Guixiang1,2*,HE Qinghu1,2,YANG Yufang1,HU Zhixi1,ZHANG Jidong3,SUN Guangrong2*
(1.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Changsha,Hunan 410208,China;2.Na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ster SUN Guangrong Studio of Hunan,Changsha,Hunan 410208,China;3.Institute of Basic Theory for Chinese Medicine,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Beijing 100700,China)
Na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ster Sun Guangrong,with 58 years of clinical experience,points out that"treatment methods selection according to syndromes"is actually a high-level summa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rapy,which is the"main prescriptions"according to"main syndromes"informed from"pulse and syptomes observing"and"main changes of symptoms"grasped from"knowing what mistaken therapy was applied".In this paper,how to choose effective prescriptions to treat syndromes was further explored.The poems of clinical experience were summarized to describing its connotations,which have a great reference value for TCM clinical doctors.
na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ster;SUN Guangrong;treatment methods selection according to syndrome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rapy
R2-0
A
10.3969/j.issn.1674-070X.2017.07.002
本文引用:葉培漢,孫貴香,何清湖,楊玉芳,胡志希,張冀東,孫光榮.國醫大師孫光榮論“隨證治之”[J].湖南中醫藥大學學報,2017,37(7):700-703.
2017-03-25
國醫大師孫光榮湖南工作室建設項目;國家中醫藥管理局2014年中醫藥行業科研專項(201407004);湖南中醫藥大學中醫診斷學國家重點學科開放基金項目(2013ZYZD21);湖南省學位與研究生教改項目(JG2014B043);湖南省衛計委科研項目(B201546)。
葉培漢,男,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醫診斷學,國醫大師孫光榮學術思想研究。
* 孫光榮,男,國醫大師,教授,主任醫師,E-mail:13911126358@139.com;* 孫貴香,女,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E-mail:84663423@qq.com。
——中醫藥科研創新成果豐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