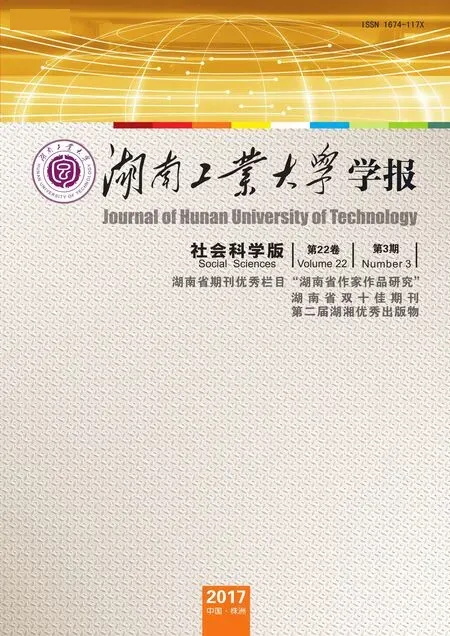張愛玲自譯作品中的變譯現象
——以《桂花蒸阿小悲秋》為例
趙 琰
(湖南生物機電職業技術學院,湖南 長沙 410128)
張愛玲自譯作品中的變譯現象
——以《桂花蒸阿小悲秋》為例
趙 琰
(湖南生物機電職業技術學院,湖南 長沙 410128)
自譯是一種特殊形態的翻譯,涉及到了翻譯者和創作者的身份重疊。自譯者擁有較大的自主權和創作空間,自譯作品是譯者創作生命的循環。基于接受美學理論中的讀者接受論,張愛玲在自譯短篇小說《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充分發揮其主體性,有意識地選擇翻譯策略,產生了大量的變譯現象,譯文雖不完全忠實原文,但順應了目的語讀者的交際需要。
自譯;讀者接受理論;張愛玲;《桂花蒸阿小悲秋》;變譯
一 自譯和自譯者
(一)自譯
自譯,即由作者翻譯自己的作品,是翻譯研究中比較復雜卻不常見的現象。絕大部分翻譯學術專著或論文集的索引中都沒有“自譯”(self-translation)這一術語。較詳細的介紹只出現于《翻譯研究詞典》,其中談到波波維奇將自譯界定為“由作者將原作變成另一種語言的翻譯”。[1]國內外對自譯者和自譯作品的研究十分有限,國外比較著名的自譯者有貝克特、納博科夫和泰戈爾等,國內比較著名的自譯者有蕭乾、張愛玲、卞之琳、白先勇等。
(二)自譯者和作為自譯者的張愛玲
自譯者,即是創作者,又是翻譯自己創造的作品的翻譯者。這種雙重的身份必然使自譯者不同于一般的譯者。在翻譯界,不同譯者對于同一文本,由于理解不同,會出現各種不同的譯本;而對翻譯作品的優劣評判是根據是否把握了原作的意蘊,忠實于原作等。而作為自譯者,同時也是最能把握作品的原作者,對自己作品的自譯便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這一標準的糾葛。自譯這種特殊的翻譯現象,也因此減少了因為重譯而離原著越來越遠的弊病,它能更準確地把握原作,甚至有時會幫助我們更好地解讀文本。但另一方面,自譯作品中一文兩作的情況很明顯,因為自譯者擁有更大的自主權和創作空間,比一般譯者更傾向于在譯文中進行變動,譯者的主體性在自譯過程中更加突出。隨著作者的創造心理,譯入語語境的變化和讀者的轉變,自譯者在翻譯自己作品過程中采取更多靈活的翻譯方法。
在中國自譯史上,張愛玲的自譯最為典型,自譯在張愛玲文學翻譯生涯中是最具特點的。她自譯的作品共有十四篇,包括散文、短篇小說和中長篇小說幾種類型。有人總結過,除了《金鎖記》,她的自譯作品大多不能稱得上是“忠實”。這是因為張愛玲利用自己的原作者身份,在自譯過程中充分發揮了譯者主體性,對原作進行了改寫式的翻譯。但她的這種改寫翻譯是有特定原因和特定目的,并不是隨心所欲的。因此,對其自譯的研究能助于改進某些翻譯策略,并且幫助我們理解文學作品跨文化傳譯過程中的一些問題。發表于1962年的ShameAmah,原文是張愛玲1944年在上海發表的短篇小說《桂花蒸阿小悲秋》,后來應著名作家聶華苓之請收入她所編的英文作品集中。《桂花蒸阿小悲秋》的女主人公阿小是張愛玲最偏愛的一個人物,[2]5這也是譯者選擇該作品自譯的一個直接動機。《桂花蒸阿小悲秋》描寫了一個上海女傭一天24小時的生活。這部小說的獨特之處是:作為一個勞動階級女性,阿小身上沒有苦大仇深的階級意識,她不是被動的、可憐的,而是主動地跟試圖控制她的洋主人拉鋸,顯示了一定的歷史能動性。
張愛玲在翻譯過程中做了很多刪減和改動。如原文約12 740個字的《桂花蒸阿小悲秋》,其中約3 588個漢字所表達的意思沒有被譯成英文。除刪減外,譯文中有很多改譯現象,少量增譯現象。這些刪減、改譯和增譯既避免了給讀者帶來交流障礙,又恰當地傳達了小說情感和內容。
二 讀者接受理論和自譯者
(一)讀者接受理論
王佐良在評論嚴復的翻譯時指出:“吸引預定的讀者是任何翻譯家不能忽視的大事。”[3]翻譯是對話性的,是為特定讀者服務的。讀者接受理論便充分表明了讀者的作用和重要性。接受美學(reception aesthetics) 又稱接受理論(reception theory),于20 世紀60 年代后期在德國誕生。接受美學理論認為,在文本的解讀過程中,讀者及其具體化在其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中心地位。接受美學的核心即讀者,而讀者的具體化也就是他的“期待視野”與文學本文的“期待視野”相互融合的過程。接受美學的一個重大貢獻,就是確立了讀者的中心地位。翻譯活動不應只是原作者和原作的獨白,而是譯者帶著“期待視野”在文本的“召喚結構”的作用下,與隱含的作者進行對話和交流后形成的“視野融合”。然而譯者在追求“期待視野”與文本融合的同時,還必須考慮譯文與譯文讀者的關系,考慮譯文讀者與譯文的“視野融合”問題。[4]給讀者閱讀是翻譯的最終目的。譯文的讀者有著各自的“期待視野”與“審美要求”,并且對同一部作品的理解也會隨著時間的流逝、體驗的加深、時代的變遷而發生轉變。因此,譯者面對讀者,更多地要考慮現時讀者群體的需求與接受水平,譯作才能喚起讀者群的大體相同的反應。
(二)張愛玲自譯中的讀者觀
張愛玲獨特的讀者觀表現為她很照顧目的語讀者,不惜調整原作內容或結構以便于他們理解與接受,這使她在翻譯過程中注意調和讀者主體和譯者主體,產出高品質的譯文,也使她的創作具有更持久的魅力。張愛玲的自譯作品與原作相比有不少出入,如果從“忠實”角度看,不能說達到了要求。但并沒有譯者不尊重原作或是對原作誤讀的問題。我們認為,當時張愛玲急需在新的環境中重新確立她的作家地位。張愛玲對原作的改動是為了文學作品的流傳,出于為己所用的目的。特殊的翻譯充分發揮了譯者主體性,甚至有些“背叛”原作,出發點便是讓讀者接受,最基礎和最關鍵的一步就是讀者的接受和理解。張愛玲的自譯作品在“信”上惹人爭議,但在“達”和“雅”上卻達到了很高的高度,翻譯與寫作相融合,譯作與原作同樣優美。
《桂花蒸阿小悲秋》的英文題目ShameAmah取自文中男主人公因為阿小宗記錯電話號碼而所說的一句半責備、半開玩笑的話。譯者一方面是為了使題目更加明確,另一方面也是顧到英文讀者的接受,而文中的題記完全忽略不譯也是為了不給目的語讀者造成困擾。另外人名在自譯過程中也發生了變化。女主人公阿小譯成Ah Nee ,男主人公哥兒達譯成Schatht, 百順改成Shin Fa,秀琴改成Ning Mei,都是考慮到英文讀者的感受。還有譯文出現的刪節和增譯等都是自譯者在考慮讀者接受的情況所做的變動。這些都充分體現了張愛玲作為自譯者在充分發揮了其譯者主動性,并且始終把讀者的接受作為其翻譯活動考慮的重要因素。
三 《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變譯現象
長期以來,人們把“忠實”視為翻譯的唯一標準,因此忽視了對變譯的研究。變譯現象自古有之,卻飽受偏見。“所謂變譯, 指譯者據特定條件下特定讀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減、編、述、縮、并、改等變通手段攝取原作有關內容的翻譯活動。”[5]
變譯中的譯者需要具備更高的素質來充分發揮其譯者主體性,在目標讀者的攝取心態和有效需求的影響下,讀者能夠大膽地對原文相關信息進行變譯。而在自譯過程中,自譯者充分發揮其譯者主體性對自己創作的作品進行有意識的變譯,通過合適的手段和方法的運用,更好地為目的語讀者服務。雖然自譯作品屬于一種重寫式翻譯,但是自譯者并不是任意為之。為了更好地服務于目的語讀者,而采取靈活的翻譯變通方式,在自譯作品中會出現較之其它翻譯形式更多的變譯現象。
從《桂花蒸阿小悲秋》中英文的對比研究發現,自譯作品ShameAmah基本保留了原文的語言特點、情節結構和敘事主線,但在細節部分卻有很多調整,即變譯之處,如大幅度的刪減、增譯、改譯和段落合并現象等。
(一)改
譯文中有很多改譯現象。一是張愛玲在譯文中對原作有刪減的地方進行補綴產生了改譯;二是為了便于目的語讀者接受。
1.對題目和題記的改譯。首先是題目和題記的翻譯調整。《桂花蒸阿小悲秋》的英文題目ShameAmah取自文中男主人公因為阿小宗記錯電話號碼而所說的一句半責備、半開玩笑的話,這樣使得題目和故事情節非常貼近,即揭示了主題又反襯出真正應該難為情的應該是洋主人,而不是阿小。中文題目《桂花蒸阿小悲秋》下附有作者好友炎嬰的題記:“秋是一個歌,但是 “桂花蒸”的夜,像在廚房里吹的蕭調,白天像小孩子唱的歌,又熱又熟又清又濕。”[6]104從題目和題記來看,作品極具中國傳統文學的色彩,因為作品中再也沒有出現過“桂花蒸”的字樣,作者便借炎嬰的題記來解釋這一含義。但是題記烘托的抒情氣氛并不能被英文讀者所體會,而且英文題目中也沒有“桂花蒸”的字樣,因此相應的題記也要作刪除,這么做是為了題目更加明確和讀者更好地接受。
2.對姓名的改譯。張愛玲向來重視人名及人名翻譯,文中這樣翻譯人名她必然有自己的考慮。在譯文中,“阿小”改為“Ah Nee”,“哥兒達”改為“Schacht”,“百順”為“Shin Fa”,“秀琴”為“Ning Mei”,文中有名字的四個人物全被改名。“阿小”是個成年女性,而一個成年女性都還沒有個正式的名字,這一名字暗示著她的渺小和普通,也暗含了中國底層女性卑微的地位。如果音譯名字就無法刻畫這些含義,意譯又會誤會成她只是個子小巧才被叫這名字。英語中有這樣的人名,如Mrs Kelly James Née White,即詹姆斯太太,婚前原姓懷特。其中的“Née”一詞是源于法語,用來提示原名,使用于已婚婦女名字之后,婚前名字之前。張愛玲將該詞稍做改動,用“Ah Nee”來傳遞原名隱含的信息,包含了女人無名無姓或有名無地位的含義。據水晶分析,張愛玲像福樓拜,替故事中角色起名字是煞費思量。哥兒達這個名字的靈感顯然來自《金瓶梅》,因為他實際上是個西洋“西門慶”。[2]19普通讀者一看或一聽“哥兒達”的名字就知道是外國人的名字,還給人“公子哥兒”“花花公子”的聯想,非常符合該人物性格特征。這個名字也無法音譯或意譯,張愛玲改譯為德國名字“Schacht”,以順應英美讀者心理。張愛玲還細心地在下文中作了這樣一處改動:“他(指哥兒達)要是不在上海,外國的外國人都要去打仗去的,早打死了!”[6]106譯為“If he’s not in Shanghai,the Germans in Germany have to go to war,he’d be dead long ago”.[7]93也印證了此分析。該譯文發表的1962年距二戰結束時間不遠,德國人形象還沒有翻身,一個德國人在中國做一些為歐美正統讀者認為傷風敗俗、不夠體面的事情,應該不會引起英語讀者的抗議和拒絕。此外,將“百順”改為“Shin Fa”,“秀琴”改為“Ning Mei”,是出于原姓名音譯出來不容易標注和發音,不利于讀者的記憶。
3.對文化意義詞匯和諺語的改譯。小說中極具中國文化色彩的詞匯和諺語具有豐厚的民族文化,直譯往往使讀者不知其意,張愛玲充分考慮目的語讀者閱讀,采取了意譯的翻譯策略,即避免了給讀者帶來交流障礙,又恰當地傳達了文化信息。例如:“這點子工夫還惦記著玩! 還不快觸祭了上學去! ”[6]104譯為:“Only a moment left and your mind still on playing! Feed, you little devil, and go to school.”[7]98中國有祭祀的風俗,人們在很多節日都會向神佛或祖先備供品行禮。 祭祀時人們會在供桌上擺上很多供神享用的貢品,任何人都不能碰也不能吃這些貢品,否則就是心不誠。如果有人有了偷吃了這些食物,那便是“觸祭”了。這里張愛玲考慮了目的語語境和讀者接受,使用“feed”和“devil”兩個詞使讀者了解到百順吃了不應該吃的東西受到了責罵,從而向西方讀者展現燦爛多彩的中國文化。又例如:“隨李小姐信不信,總之不使她太下不來臺……”[6]119譯 為:“Whether she believed it or not it would make it less embarrassing.”[7]108又如:“他馬上聲音硬化起來,丁是丁,卯是卯的。”[6]120譯為:“The moment he spoken of rendezvous his voice hardened, he became businesslike.”[7]110如果直譯“下不來臺”和“丁是丁,卯是卯”,目的語讀者會不知所云,張愛玲憑借深厚的英文功底精心選用了“embarrassing”和“businesslike”,準確地向讀者傳達了諺語涵義。
(二)減
譯文中有很多刪減。刪減后,譯作中小說的主線變得更簡單清晰,也弱化了洋人的“不上等”形象,目的就是為了讀者接受。如原文約12 740個漢字的《桂花蒸阿小悲秋》,其中約3 588個漢字(將近占到三分之一)所表達的意思沒有被譯成英文。所刪減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點:第一,刪去了很多對阿小的東家——洋人哥兒達的負面描寫;第二,刪去了對阿小正面形象的描寫;第三,有關樓上新婚夫婦的所有事;第四,刪去了有關異常氣味的描寫;此外,還刪去了一些對主題基本上不產生影響的細節。比如一封中文家書和一些零碎的細節描寫。在所有刪減中,前兩類的量最大。
1.對阿小的東家——洋人哥兒達的負面描寫的刪減。為了進入白人的主流社會,照顧英語讀者的種族自尊心,不惹目的語讀者反感,在20世紀60年代《桂花蒸阿小悲秋》被輸入英語世界時,只好刪去原作中對哥兒達那些明顯的負面描寫。研究者水晶對哥兒達的結論是“無論明喻暗喻,張愛玲無非想指陳一點:哥兒達無非是一個從事不名譽賤業的牛郎(男娼)”。[2]29例如:“主人臉上的肉像是沒燒熟,紅拉拉的帶著血絲子”“她(廣告上裸體美人)是哥兒達先生的理想,至今還未給他碰到過。碰到了,他也不過想占她一點便宜就算了。如果太麻煩,那也就犯不著;他一來是美人遲暮,越發需要經濟時間與金錢,而且也看開了,所有的女人都差不多。他向來主張結交良家婦女,或者給半賣淫的女人一點業余的羅曼斯,也不想她們劫富濟貧,只要兩不來去好了。他深知久賭必輸,久戀必苦的道理,他在賭臺上總是看看風色,趁勢撈了一點就帶了走,非常知足”。[6]105
2.對阿小正面形象的描寫刪減。在小說里,阿小不僅勤勞善良,還很有自己的見解,獨立思考,有正義感。她經濟獨立,自己掙錢養活自己和孩子。在譯作中,張愛玲刪除了那些對阿小內心感受和心理活動的描寫。例如:主人說:“阿媽,今天晚上預備兩個人的飯。 買一磅牛肉。 ”阿小說:“先煨湯,再把它炸一炸? ”主人點點頭。 阿小說:“還要點什么呢? ”[6]107譯為: “Amah,” he said, “dinner for two tonight.Buy a pound of beef.” “Yes, Master.”[7]96譯文中刪去了阿小發表自己見解和思想的部分回答,讓讀者看到的是一個對主人唯命是從,沒有自己思想和見解的女仆形象。這樣保守、思想麻木的中國女人形象正好符合西方讀者的閱讀心理。又例如:“她對哥兒達突然有一種母性的衛護,堅決而厲害。”[6]120張愛玲刪除了對阿小所具有的正義感的描寫。在小說里,阿小非常正義地想保護自己的主人,并且想挽回自己主人的面子,但是為了符合目的語讀者的閱讀心理,張愛玲選擇了刪減阿小的正義感。
3.對有關樓上新婚夫婦的所有事的刪減。為了更加突出主線,張愛玲翻譯時刪去少量人物和相關事件,《桂花蒸阿小悲秋》篇幅不長,全篇沒有故事,也沒有什么情節,涉及的人物有12個之多,人物穿插在阿小一天忙碌而平淡的工作和生活中,譯成英文的話難免使英語讀者糊涂。
4.對有關異常氣味的描寫的刪減。鑒于有些描寫很可能會造成誤解或誤讀,引起英語讀者的不悅,譯者刪減了部分此類描寫。如開篇不久有一段對擁擠電車的描寫:“她被擠得站立不牢,臉貼著一個高個子的深藍布長衫,那深藍布因為骯臟到極點,有一點奇異的柔軟,簡直沒有布的勁道;從那藍布的深處一蓬一蓬發出它內在的熱氣”。[6]104張愛玲在譯文中將這部分描寫都省掉了。
(三)增
譯作中還有少量增譯現象。為了便于讀者理解女主人公現在的情境,增加了一大段介紹阿小以前的合法丈夫如何遠赴澳洲淘金和如何失去聯系的內容,這不同于普通的增譯,也算是對刪去內容的一種補償。
(四)編
原文中有多處段落在譯文中被分成了許多小段落,使原作內容更加條理化、有序化,使之更完美,編排成更易于目的語讀者接受的結構。
自譯這種特殊形態的翻譯形式,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另一個視角,由此也會加深對翻譯的認識和理解。張愛玲在自譯其小說《桂花蒸阿小悲秋》的過程中,為了最充分最直接地滿足目的語讀者對象而在自譯過程中采取變通手法,使得譯文中出現了大量的變譯現象。對這些變譯現象進行分析,并將讀者接受理論和自譯者的主體性結合起來,能助于改進某些翻譯策略,并且幫助我們理解文學作品跨文化傳譯過程中的一些問題,尤其是對自譯這種翻譯形式有更加深刻的認識。
[1] SHUTTLEWORTH M, COWIE M.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 水 晶.替張愛玲補妝[M].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3] 王佐良.翻譯:思考與試筆[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9:480.
[4] 曹英華.接受美學與文學翻譯中的讀者關照[J].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3,35(5):100-104.
[5] 黃忠廉.變譯理論[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96.
[6] 張愛玲.傾城之戀[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
[7] CHANG E.ShameAmah!Eight Stories by Chinese Women[M].Taipei:Taipei Heritage Press,1962.
責任編輯:李 珂
Translation Variations in Eileen Chang’s Self-Translated Short:Novel Shame Amah as an Example
ZHAO Yan
(Hunan Biological and Electromechanical Polytechnic, Changsha 410128, China )
Self-translation is a special form of translation which has an identity overlap of translators and creators. Since the translator has a greater autonomy and creative space, self-translation works are the cycle of the translator’s creation. Based on the reception theory, the paper analyses how Eileen Chang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self-translating her short novelShameAmahand it is found that the translated text has lots of translation variations, which is not exactly loyal to the source text but conforms to the communicative needs of target readers.
self-translation; reception theory; Eileen Chang;ShameAmah; translation variations
10.3969/j.issn.1674-117X.2017.03.024
2017-03-06
趙 琰(1986-),女,湖南株洲人,湖南生物機電職業技術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翻譯理論與研究。
H315.9
A
1674-117X(2017)03-012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