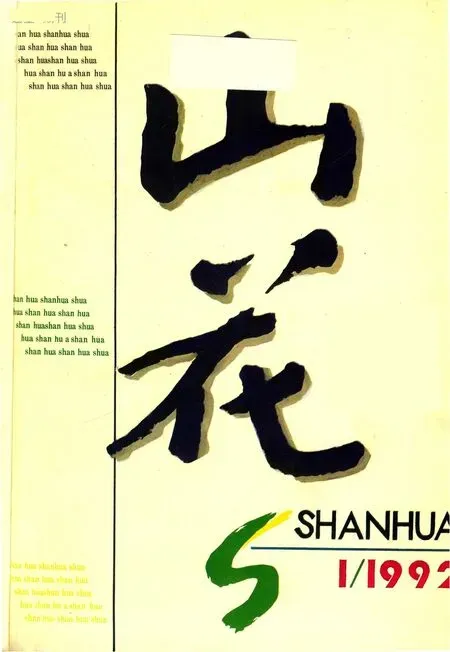英格麗德遇見安娜希特的一天
夜晚的降落在這里靜謐如尚未解凍的河流。黑森林腹地,金希齊河谷。手機地圖上閃爍的藍點提醒著,這里已相當靠近瑞士,所以你可以想象一切積雪與深谷。
有一個關于夜晚的古老故事,主角是一朵花。應該說,有三個女人都變成了花,長在田里。其中只有一個敢在夜里回家。要破除被變成花的魔咒,需有人在白天的田野中認出她,摘下她。要怎么才能認得她?回答是:“因為她敢在夜里行動,回到了自己的家,不像其他田里的花一樣沾滿了露水,所以你認得她。”
關于這個無數夜晚中尋常又不尋常的一個,我們的花兒叫作安娜希特和英格麗德。
17:00
安娜希特
“通心粉,水管粉,還是蝴蝶粉?”
“水管粉。”
“紅汁,白汁,還是青汁?”
“紅汁。”
“埃撲瑟?”
安娜希特一邊重復著“埃撲瑟”的發音,一邊把食指和拇指卷曲成一個很小很小的圈,想說明這叫“埃撲瑟”的東西到底是什么。顯然這是一樣對于這盤意面很重要的調味品,或者關乎人的口味喜好。而安娜希特想要我明確自己能否接受它。
我仍搖搖頭。
她起身,走進廚房里,端著一盆青翠的豌豆走了出來。
這下我點點頭。
餐館連我在內只有六個客人。自然,時候尚早,天才剛黑下來。其余五個客人也還在享用餐前酒。其中一桌坐在最角落,三男一女,爺爺奶奶的年紀。另外一個跟我一樣的獨行客人,坐在吧臺上慢慢喝酒,一個中年男人。店內沒有音樂。橘色的燈光讓有些陳舊的桌椅和墻紙顯出家常氣氛的暖意來,隔絕了窗外的冷雨與嚴寒。
安娜希特后來說,小鎮上的東方游客不少。但這個星期以來,只有我走進了她的餐館。“你明天會來么?”后來她問。之后的每天,我都來。部分是因為德國菜的分量讓我恐懼,意面多少能讓我的胃不那么緊張。部分是因為,這個夜晚發生的事,攪拌出了我對這個小鎮的某種深層情緒。于是我一次次地來確認其中的細節。
這是安娜希特的尋常一天。
天邊的陰云暗示了這一天的雨和雪。貓躍上窗臺,像往常一樣蹲坐著打量這條通往火車站的石子路上偶爾閃過的人影。河不遠,簡直可以說近在咫尺。只是凍了一整個冬天后,剛開始解凍的水流平緩得像是定格的電影。安娜希特步行穿過鐵橋。鐵橋邊上,正在維修福音派教堂的幾個年輕工人在早晨的冷雨里抽煙。教堂據說要五月份才能完成修繕。這是鎮上最大的一座教堂,比安娜希特常去的使徒教會教堂氣派得多。使徒教會的教堂不過是一座小房子,在小鎮市政廳發行的年度大事手冊上,雖然作為三個教派之一會列在最末,但通常只有兩行字。福音派教會和天主教教會占的篇幅則多得多。在河谷兩岸絢麗得像是童話世界的木結構房屋里,福音派教堂的棕色砂石外墻樸素得就像懸掛于正中的木頭十字架。雖然在小鎮居住了二十年,但關于小鎮的若干細節,安娜希特仍講不清楚,或許,也并不是那么在意和關心。比如,為何這座福音派教堂是拜占庭式?會想這種問題的人,大概不是安娜希特。
穿過橋,往前再走五分鐘,就能看到火車站背后的倉儲式超市。她的口袋里有一張寫滿字的采購清單。紙片的一角沾了一滴黃油油漬。今天早上給小女兒和丈夫做餡餅時濺上來的。小女兒正放寒假,晚上在相鄰一條街的德國菜館打工。那是個帶旅舍的餐館,總有晚來的客人,或者喝酒喝到很晚的客人。小費因此也大方一些。女兒跟安娜希特一樣苗條,還繼承了父親的一頭金發,如今是鎮上數一數二的漂亮姑娘。雖然吃餡餅的時候還是會把拇指放進嘴里吮一吮。
自家餐館的生意不好也不壞。房子是丈夫的祖產,因此省掉了房租,但也不能說沒有競爭。在小鎮,有七家客棧都兼營餐館。夏天,或者雨雪沒那么嚴重的時候,客棧里多少有些客人。住店,吃飯,生意就可以做下去。如果人們想嘗嘗地道的德國風味,鎮上也有兩家有點年頭的餐館可以選擇——磨坊餐館和弗里茨餐館專營德國菜。如果想喝兩杯,找狐朋酒友聊天,可以去小酒館,有茨威格小酒館和木屋小館兩家。糕點鋪則分布在黃金地段,錯落著避開彼此的生意——咖啡豆糕點鋪在市政廣場上,班貝克糕點鋪在河岸,魏德樂咖啡館在半山腰。裝修得富有情調,甚至可以說帶著藝術品位。無論是班貝克糕點鋪里展示的古老新娘頭飾和其他首飾,還是咖啡豆糕點鋪里的藏書與油畫,與咖啡相佐的糕點似乎更能讓主人有空余享受和展示品位。如果說還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那是出鎮的公路邊,土耳其人開的“小城肉夾饃”,據說生意還不錯。安娜希特就見過來鎮上洗浴博物館參觀的中學生,在土耳其人開的店門口排著隊買肉夾饃。
安娜希特與丈夫經營的這家小餐館,是鎮上唯一一家意大利菜。談不上有什么特色,至少從外表看來如此。對于一個小鎮來說,或許也不需要那么多特色。餐館從十幾年前開業到現在就沒有重新裝修過。墻上掛著的幾幅噴印出來的梵高畫作早已發黃。只有意面的味道是真不錯。大概,讓小店熠熠生輝的還有美麗的安娜希特。安娜希特并不是意大利人,甚至也沒去過意大利。“我在慕尼黑附近的一個小鎮長大,是亞美尼亞人。”安娜希特的皮膚白得透明,灰藍色的一雙眼睛。
總之,小餐館還是能運轉下去,讓他們養大了兩個女兒。但更多的錢也沒有了。一家人就住在餐館樓上。安娜希特曾想搬到山上去。那些靠著樹木和草叢的獨棟房子,炊煙升起時看起來就像一幅真正的油畫,而不是噴印畫。但自從開了餐館后,丈夫就辭去了洗浴用具廠的工作。生活讓兩人陀螺一樣運轉。陽光好的日子,工人們會從廠房里走到鐵軌或河岸邊曬太陽。安娜希特在餐館后廚里總是能看見他們。這讓她想起,第一次見到丈夫時,他穿的也是那樣一身藍色工裝。
芝士筒旋轉著,下雪一樣把紅色的意面醬掩蓋成乳白色。安娜希特轉動芝士筒的手勢不急不忙,無名指上一枚金色的戒指發出微光。二十五歲,后來她告訴我,嫁到小鎮的那一年,二十五歲。婚姻、生育、勞作、家庭,像每個女孩被告知被訓誡的那樣去渴望,去生活。安娜希特用二十年的時間,雕塑出現有的生活。這生活可濃縮為無名指上的一枚金戒指,每天清晨和夜晚把手浸泡進水池的一個動作,或者,沿著通往火車站的道路走去超市采購完了再走回家擰開門鎖上樓放下重物的身姿。
“為什么到小鎮來。”安娜希特看著我,不說話。明明是我問她的一個問題,當她沉默下來時,問題的來路和去路卻變得可疑。
她只是說,夏天來臨的時候,小鎮的男人們會把木材扎成幾十米長的木筏,沿著河谷向下漂流。這是為紀念本地最古老的產業與傳統而例行的儀式。幾百年間,黑森林的木材都是這樣成捆地扎成木筏,沿著河谷順流而下,到達某地后被搬上岸,木材被用于房屋或者船塢的建造。
一旦木筏堵塞在河道里,最先感受到的是魚群。順流而下的魚群會堵塞在木筏前逡巡跳躍,幾百米長的白色陣列激起河本身所沒有的浪花,簡直要將河水沸騰。
木筏漂流的時候,全鎮的人站在岸上看熱鬧。木筏入水的一刻,幾噸重的木頭激濺起巨大的水花。雖然制成需要兩個月以上,但木筏仍散發著新鮮刺鼻的芳香。然后,“轟”一聲,木頭歸于水。
只要有木筏漂流,安娜希特都會去河邊看。孩子小的時候,就抱著孩子去。古老的事物讓人低下頭來,讓人敬畏。當這古老之物是一條河時,一條非人力所能左右的河流時,它激起人的渴望,但又給予安慰。
河為了慶祝夏天的來臨,總是在兩岸的草地上奉上一簇簇鮮花。比起河里的動靜,懷里的孩子總是要伸手去抓那些或黃或白的花朵,仿佛它們才是慶典的主角。花自然不會講話,但它們會做表情。就像《小意達的花兒》里說的那樣,安娜希特告訴孩子,你一定注意到,當風在微微吹動的時候,花兒就點起頭來,把它們所有的綠葉子都搖動著。這些姿勢它們互相明白,跟講話一樣。
孩子聽得認真極了,原來媽媽能聽懂花語!而人群中,安娜希特看起來不過像其他抱孩子的女人一樣,對著孩子喃喃細語,幾乎悄無聲息。
更引入注目的圖景是,男人們穿著燈籠袖襯衫,馬甲上有精美的刺繡,皮革寬檐帽迎風微微顫動。用力撐長蒿,讓木筏滑出去。就是這樣,如果你的渴望是讓木筏往前漂,那你就得用力往后撐。
木筏漂動起來聲勢浩大,帶動著河水的激流,形成特殊的水流回旋。孩子們尖叫著跟著男人們唱起歌來,歌聲跟水花一樣脆亮。
安娜希特說,對,就這樣,順流而下。
18:00
英格麗德
只來了十三個人。
英格麗德將祖傳老屋的一樓改建為書店。2007年2月2日,晚上六點,正式開業。店里還沒有多少書,至少不像日后我見到的那樣,所有的墻壁都被書柜占據,書密密麻麻站到了天花板下,構成了書的洞穴與知識的秘境。選擇2月2日來作開業紀念日,英格麗德有自己的考慮。那是從凱爾特人開始,用來紀念女神布里吉德的節日。冬天即將過去,第一朵鮮花從愛爾蘭雪地里冒出來,春天即將到來。布里吉德女神是光明,啟發和治愈。以女性的力量給世界帶來療救。
鎮長哈斯先生是僅有的十三位客人之一。在黃油椒鹽脆餅和木柴緩慢燃燒迸發的香氣中,哈斯先生像其他十二位客人一樣,禮貌地說了幾句。歡迎一家書店在小鎮誕生。那個夜晚之前,英格麗德聽得更多的,是來自小鎮居民的閑言碎語。“一家書店?小鎮本身的歷史我們已經讀得夠多啦!”倒也不是諷刺,人們多半是抱著同情,在路邊停下來跟英格麗德交談。一次次的交談不過是帶來更多的失望,但英格麗德已經執意去做。她已經四十歲了,對于何為失敗,何為挫折,自覺已經有了一些認知與承受。正如每年雪都一次次地來,但人們清楚,冬天總會過去。而她不過認定,第一朵花終會破雪而出。
十三位客人中,有人帶來了單簧管。有人帶來了捐贈的書籍。有人帶來了鮮花。香檳斟滿。老木地板“吱吱”響著給這個夜作見證。英格麗德把西塞羅的名言“一個沒有書的房間就像沒有靈魂的身體”制成海報放在壁爐旁邊。音樂流動。語言從人們的身體上漂浮起來,撫摸著舊書的扉頁,喚醒其中被固定成文字的詞。那么一瞬間,英格麗德確定了,在這個舊書店里,自己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守護。而這一切的核心,就是書店的理念——詞語,書本與寫作。
自然,煥發出巨大的熱情。不論是英格麗德自己,還是圍繞書店慢慢形成的一個小圈子。第一年,這里一共舉行了十二場活動。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每年也都有十場以上活動。每個月總有這樣一個夜晚,書本與閱讀讓人們聚攏,成為最關心的事。世界在其外,又在其中。
這一度成為英格麗德傾心而往的世界。正如當她還是個小女孩時,就癡迷于手指撫摸書頁,文字從嘴里誦讀而出時的快樂與安慰。
她長了一頭火紅的頭發,皚皚雪地里就像一團移動的火苗。每周四次,她從附近的小鎮開車過來,開門營業。其中三天是上午10點到下午3點,還有一天則是晚上6點開始的讀書會。
開車過來的路上,窗外一直可以看到與公路并行的金希齊河。不那么冷的日子,搖下車窗,河流的聲響與氣息就涌進來。河與森林,就是河谷居民的一切。跟她共享這一路風景的,還有鴨子、牛、狗和各種昆蟲。他們不像英格麗德的車行進得這么快,甚至走著走著就停下來,跟河流為伴。
稱心如意。如果問起其他人對英格麗德生活的看法,大概會得到這么一個答案。丈夫哈羅德是本地活躍的知識分子。寫作,宣講,公益事務,戶外運動,是個大忙人。本地報紙上時不時就能見到他的蹤影,最多的一系列報道,是他跟幾個朋友,徒步到阿爾卑斯山。“壯舉!”知道的人都這么說。孩子呢,一男一女,西蒙和凱拉,都已成年,長得足夠漂亮,也繼承了父母的頭腦。還有什么。住在鄰鎮的農場里,大房子,大草坪。確實,生活得稱心如意。
如此之下,我那些以“為什么”開頭的問題多少顯得刻意,帶著一個陌生人窺視般的好奇,和些許質疑與挑釁。但英格麗德似乎不太介意。不想回答的時候,她只是捧著手中的茶杯,沉默不語。為什么是一家舊書店?因為有意思的東西都有點歷史。為什么做讀書會?因為文字需要宣讀,需要喚醒,需要人通過人來完成交流。為什么選擇在這個小鎮開?因為這里有祖產,可以不用付房租。
也不是所有事都稱心如意。不少熱心人總是把家里不要的舊書一股腦地送來書店,英格麗德花了很多耐心與口舌解釋說這是一個“古本店”,而非舊貨店。但小鎮居民還是熱衷于認為,把不要的書送給英格麗德,就是給書找到了歸宿。堆積如山的廢品一度讓英格麗德心生厭惡。幽默雜志、工具手冊、編織教材是最多的。沒有什么比在你喜歡的事上蒙上一層錯誤的假面更讓人煩心的了。分類和搬運讓她腰疼得厲害,再怎么,已經四十多歲了。最后的解決辦法是,每年參與市政廳舉辦的公益活動“書籍圓桌”,把其中尚有價值的書進行展示,任由人們取走。剩下的書儲存在市政廳的倉庫里。那些書慢慢就朽成無意義的紙張。
不需要的東西源源不斷地涌來,而期待之事也并不一定會發生。
英格麗德喜歡童話。她著迷于純真的想象與陰暗的世界間碰撞出的奇幻之地。
開業頭一年,她就組織了五場有關童話的活動。“世界童話之旅”、“氣球里的童話”、“童話里的女性”(邀請全國著名的童話專家席格麗·弗爾來書店)。還有一場精心策劃,從2007年底持續到2008年1月的紀念阿斯特里德·林德格倫誕辰百年的展覽。林德格倫是《長襪子皮皮》的作者。
林德格倫所有德語版本的書籍都展示了出來,其中有很多是初版版本。另外圍繞林德格倫作品與生活的各種著作、照片、報道、傳記、海報、電影等也都一一展示。德國南部不少童話迷都前往小鎮看展覽,最遠的人來自康斯坦湖、圖賓根。還有五所學校組織了孩子們前來參觀,上戶外“德語課”。
這次成功振奮了英格麗德,所以在開業第二年年初,她精心推出了一場關于童話的講座,邀請了專家席格麗·弗爾來講授“童話里的死亡——關于生命的思考”。預售票價8歐。倒不是為了盈利,而是要支付弗爾前來小鎮的路費和住宿等。英格麗德花了不少功夫在金希齊河谷沿岸的小鎮張貼海報,也聯系認識的童話迷們幫忙擴散消息。
但只來了二十個人。
弗爾坐在英格麗德精心布置的講臺上,被蠟燭和松枝環繞。弗爾講得很好。但那之后,英格麗德不再組織收費的講座。
但這些失望,跟更大的現實相比,終究只是小事。所謂更大的現實,是你可以長成一朵花,可以在冬天尚未結束時就第一個鉆出來,但你不能讓雪地上鮮花盛開。
開業五年后,書店的讀書會活動已減少至每年只舉行三次。而我推開店門,認識英格麗德的這一天,正是2015年的第一次讀書會。
參與者比我想象的更參差不齊。不只是年齡,也包括階層。其中一個男子看起來像個流浪漢,毛線帽子和襯衫都臟成了黑色,他進門后安靜地坐在最后一排。我在外圍坐著,看英格麗德已經開始忙碌起來。跟每一個人擁抱、寒暄、奉茶。
“如果不記得渴望的感覺,就想想露水。”英格麗德熟稔那個關于走夜路的花兒的古老故事。魔咒被破除,是因為花兒身上沒有露水。而之所以沒有,是因為花兒敢在夜晚走路回家。再回到田野里時,身上沒有夜氣凝結出的露水。露水被勇氣驅散。
而沒有被驅散的露水,無聲無息地掛在花身上,變成了身份的標記。英格麗德說,書店開業前,丈夫幫忙做了許多準備,比如他劈了許多木柴,堆積在壁爐旁。木柴壘得整整齊齊,一直頂到天花板,就像一個裝置藝術作品。木柴后面,她整理出了一個小小的辦公室。執意要開書店,只是想有一個真正的屬于自己的空間。不只是捧上書本就可以擁有的想象空間,也有社交的空間,人和人關系的空間。那些木柴似乎知道她的心意,整齊地站立在辦公室的門口,像在守衛。
丈夫自然會幫助她,比如把木柴壘起來。可是關于木柴被投進壁爐,“噼啪”作響地燃起來,直至變成灰燼的一切,英格麗德自己見證。她說,火燃起來的時候,火苗躥升讓溫暖猝不及防的時候,或許,就蒸干了露水。
19:00
英格麗德
這個夜晚沒有月亮。
與花苞在雪地里迸開讓人產生的渴望不同,月圓讓人產生的渴望情緒更隱秘深層,以致于被稱作“月之迷醉”。有這樣的逐月人,在夏季,那些最適合在戶外看月亮的時候,追逐著月亮到山頂上去。月亮潔白,巨大,輝照在黑森林的落葉松與冷杉的頂端。讓漆黑的樹冠被鍍成近銀色的白。風穿過樹葉與樹葉連綴而成的秘密圖景,折射到月亮表面的凹陷處發出回響。裸露出的皮膚承接著墜落的月光。一種溫柔的觸感。要絕對的專注與靜默才能感受到那黑暗中的灼熱。
英格麗德的“月圓之夜”讀書會,就吸引了一些愿意在月亮下晾曬自己的人。
與平日在書店里的讀書會不同,“月圓之夜”雖也設定主題,也讀書,但更像是返老還童的游戲,為尋找螢火蟲或號角而進行的露營冒險。一朵花想要尋找更多的花。
通常從七點開始,先是自助晚餐,然后點燃篝火圍坐在一起。與小鎮規整的石子街道和斑斕的中世紀半木結構房屋不同,山上的世界呈現出的是另一種古老。與土壤,與風,與雨水,與月亮和太陽共生而出的古老。除了必須的長凳、桌子外,英格麗德精心布置了很多細節來迎接月亮。比如老油燈,手搖的鈴鐺,還有抵御夜晚寒氣的毯子。
那是些什么樣的夜晚呢。英格麗德想出了如下主題——
愚蠢的問題(像孩子一樣發問吧,愚蠢的問題才是勇氣與智慧的開端);
會說話的石頭(童話故事里那些無聲的見證者);
幽默之夜(讓我們開懷大笑的故事才是好故事);
神秘之夜(我們又愛又恨的另一個世界);
恐怖之夜(看看誰先嚇破膽);
東方之夜(佛陀與菩提樹的智慧);
印度之夜(時間在那里停止);
非洲之夜(部族史詩與古老神話);
小鎮歷史之夜(談談我們最熟悉的地方的陌生之處);
音樂之夜(帶上你的樂器來一場演奏吧!);
太陽之夜(關于太陽的故事,詩歌,傳說);
月食之夜(今夜22:01分一起見證月食);
……
成群結隊,會讓人興致高昂。在“月圓之夜”活動的大部分時候,人們從山腳步行而至,沿著小路攀爬,越過樹叢,來到這曾是城堡所在地的林間空地。以一場聚會的名義,人們走出家門,讓頭頂被晚風吹拂,暴露自我于曠野之中,結成短暫的聯盟。
自助晚餐一般在木頭搭建的廊橋上舉行。廊橋有結實的屋頂,橫跨山澗,就像一座巨大的成人樹屋。一次,月亮還未破云而出時,淅淅瀝瀝下了些雨。朋友們躲在廊橋的屋檐下,有人攥緊了領口,有人無所謂地喝著啤酒,等待雨過去。時間的痕跡在這里不依賴鐘表的提示,只來自于自然賦予的信號。比如,風,或者雨。英格麗德跟丈夫并肩站著,對這一切感到滿意。
他們創造出了一個時空,用于盛放文字、想象、情感和盼望。而這種相聚與另一種更大的相聚融匯在一起。不止是這幾十個小鎮居民,還有與人類誕生以來理智與情感凝結而成的偉大作品相聚。朗讀、交談、復興、再生,英格麗德知道,對這種相聚的渴望,是她一次又一次奔走與努力的動力所在。是她,一個普通讀者,在今時今日,對古典價值的恪守與愛護。
但是,月食發生的那個夜晚,就暗示了之后的衰敗。往常,詹森也會帶狗來。那是條牧羊犬,年紀有些大了,總是耷拉著眼皮趴在詹森腳邊。如果有麻雀從樹林里驚飛掠過,它也只是猛地豎起耳朵、瞪大雙眼,卻不肯離開主人放肆地追逐一通。那晚,詹森也帶了狗來。照舊是簡單的自助晚餐,芝士、香腸切片、面包。礦泉水與啤酒,還有熱茶。朗讀進行了一陣,關于月亮的詩歌、故事與歌謠。狗突然吠個不停,沖著英格麗德身后的樹林。詹森試圖喝止這條老狗,但也起身望了望,飽滿的月亮照得林間空地一片雪白,一覽無遺,只有松針和苔蘚鋪就的軟綿綿的土壤。如果真能看見什么,那只會是雨后冒出來的蘑菇群。但老狗卻仍叫個不停,沖進了小樹林。
詹森也沖了進去,但顯然,他的腿腳并沒有老狗利落。很快,狗就消失了。再幾秒鐘過后,詹森也消失了。云何時蔓了過來,遮住了月亮,誰也不知道。有三兩個人提議,該進樹林去幫幫忙——老詹森沒有帶電筒。
簡單商議后,三個朋友結伴走向了森林。常規被打破,人們開始談論鎮上的其他怪事。比如斯塔西家后院里種的那株奇怪的植物,葉片帶刺,莖干也張牙舞爪像外星人的觸須。暫時還沒結出什么果實來,可是誰知道呢,也許那就是能通天的魔豆。更奇怪的是彼得的鼾聲,每次禮拜日總是從后排座位上響起,他睡得就像一個嬰兒,沉靜又安穩,鼾聲既不高亢也不低沉,有節奏地跟著牧師的講道在教堂里低徊。據說他常常說些鎮上人們從不知道的奇怪事。諸多瑣事,從朋友們的嘴里吞吐出來,讓林間空地上突然升起了人間煙火。
英格麗德問,要不要繼續朗讀呢?沒有得到積極的響應。玩樂的心,或者好奇,或者只是月食來臨前的疲憊?讓剩下的人都只懶懶地攤在長椅上,看篝火“噼啪”作響。紛紛放下了書本。
有誰率先唱起歌來。一首月光與搖籃的小調。又有誰跟唱了起來。歌聲作槳,在森林中推出一條路來。更多的人跟著唱起來。歌聲齊整而洪亮,在天地間留存下轉瞬即逝的澎湃氣息。一位老婦人突然垂下頭做起禱告來。英格麗德也受到了強烈的感染,與往常聚會里智性帶來的火花與愉悅不同,這種感召與愉悅,幾乎是純生理性的。卻那么強烈。
是什么呢。直到四個男人(其中自然有老詹森)與一條老狗從林子的另一頭出來,大家都在一首接一首地唱著歌。有多久沒這樣整齊大聲地高唱了呢?英格麗德后來回憶,大概從自己不再是唱詩班的成員之后,就沒有了吧。為何齊整的歌聲讓人忘憂,讓人忘我。她轉頭看看身邊的丈夫,他也在忘情地唱著。
十點零一分。月亮一點一點被陰影遮蓋了。大家都仰頭看著這奇跡。月亮碩大,潔白,近在咫尺。而地球也開始顯出自己的形狀來,蔓延、滑動,用黑遮蓋了白。風吹得樹林“沙沙沙”地響。英格麗德覺得平靜,“永恒”這個詞驀地從她心頭浮現。
那是最后一次“月圓之夜”的活動。第二年,雖然像往常一樣貼出了布告,宣布今年仍將舉辦三次“月圓之夜”,但報名者寥寥,最后活動只能取消。
大概是詹森的狗沖破了理想的氛圍,某種略顯緊繃的矜持,然后瑣碎與日常就涌進來,身體被喚醒,繼而長久地松弛。也無所謂打敗,只是在日常面前,什么都顯得微弱,而已。
在童話里,關于花的枯萎有很多講法。比如那株趕夜路回家的勇敢之花,因為沒有露水的痕跡,而被認出、摘下,花兒變回女人,魔咒破除。生命在物像內部轉換,并未中斷。而在另一些故事里,花兒漸漸枯萎,是因為它們頭天夜里去參加了盛大的舞會,跳得腿也疲憊,臉也疲憊。這樣盛大的舞會要一夜接一夜直跳到花完全死去。舞會是葬禮的前奏。但無論是一枝花的怒放,還是一整個花園的寂滅,生命的秘密與歡樂,都在花的內部,最里面最里面。是花最后的秘密。
之后,英格麗德將更多的精力轉向內在的自我,不只是依賴書本的慰藉。她整理了家族中“一戰”時上前線打仗的家人們往來的明信片,一共130多張,在小鎮上展出。她還策劃了一次“被燒毀的書”展覽,將“二戰”期間禁書的名單做了完整的呈現。也期許交流與溝通,但展示思想,單向道地展示,更輕松些。
月亮會告訴你很多事,英格麗德說,月亮會缺損,會充盈,會被陰影覆蓋,又會瞬間再度飽滿。就像那些真正的渴望,你從不可能得到它們。只是在人們的交談聲中,某些微妙的時刻,孤獨被稀釋。那也只是某些微妙的時刻。
在后來我知曉這一切之前,那個我站在書店里的夜晚,晚上七點,英格麗德像往常一樣,開始拿起一本書,講述當晚的主題。那是艾瑟·施溫卡格(Else Schwenk-Anger)的傳記。這是一位1930年代出生在金希齊河谷小鎮的童書作家,女性。除了拿畫筆,從事出版業,她終生也致力于幫助孤兒和被遺棄的兒童的生活。她創作,更在生活與抗爭,不甘于已有的現實。
這是個沒有月亮的晚上,細雪降到人身上前就融成了雨。但離2月2日,第一朵鮮花從雪地里鉆出來的日子,也不遠了。
英格麗德拿著書,開始講話:“一位偉大的女性說,我要生活。而這,就是我的生活!”
20:00
安娜希特
向日葵在河谷并不常見。在冬日,花店里售賣的主要是黃水仙。安娜希特的餐館里,每張餐桌上也裝飾著幾株水仙。與東方的水仙不同,這里的水仙并沒有香氣,徒有水仙透明脆弱的外在。但在戶外,偶爾你也能撞見野生的水仙,鮮嫩的花瓣在寒冷的空氣里抖動,展示著春天的美意。
向日葵長在餐館的墻上。這世上最著名的向日葵,由梵·高的畫筆涂抹而出,噴印成可復制流傳的裝飾畫,進入一個個渴望燃燒的房間,慰藉某些時刻將視線投于畫面的靈魂。安娜希特墻壁上的向日葵,也是如此。
這些向日葵被視作梵·高畫作里最具裝飾性的作品,熾焰燃燒般的黃,人的痛苦與煎熬掩映在植物的花瓣與莖葉之間。靜物畫總是這樣,讓時間與情感都被物的美態定格并化解,徒留彼此凝望時的靜謐。安娜希特如此熱愛向日葵,以至于當我提起它們的時候,她激動地舉起手指,似乎要穿透空氣與墻壁,指點出那些印刷出來的葉片背后的秘密。
悖謬也在于此,這幅流傳甚廣、在復制傳播過程中被消解了神秘的畫作,原本寄托著梵·高最強烈的感情之一。那是1889年,高更到達阿爾小鎮前,梵·高為裝飾摯友高更的房間,用最簡陋的顏料銘刻下的對朋友到來的雀躍與亢奮。鉻黃,赭石黃,維羅納綠,沒有更多的顏色了,但每一筆卻如琴聲訴說著幽微又激昂的情緒。只有在對同類訴說時,在我們以為孤獨會像俄羅斯方塊一樣被一點點消除時,才會如此訴說。
無論如何,向日葵都裝點著安娜希特的墻面,寄托著她的渴望。至于這渴望的所指,顯然不是夜深后越來越多的酒客身上。也不是酒客荷包里可以掏出的錢幣,以及錢幣積攢后能換來的更好的房子、更好的食物、更好的布匹。
因為安娜希特餐館的名字實在是奇怪——到十字架去。白色的字體涂抹在當街的落地玻璃上,暗示著這貌不驚人的小餐館最大的不同。
安娜希特說,亞美尼亞的傳統面包由小麥粉與水糅合而成,面團被碾成薄層,放上橢圓形墊子,貼在傳統錐形黏土烤箱壁上。說是面包,它卻扁平而細長。而且一個人做起來也很困難,通常是一群女人接力完成,又快又好。只烤三十秒,面包就好了,從烤箱壁上取下來,可以放好幾個月。但這面包最獨特的地方,是在婚禮上,會像新娘的潔白頭紗一樣,披掛在一對新人的肩膀上。小麥粉的清香傳遞出古老質樸的寄寓,像面包一樣長存吧,像面包一樣予人保暖和安慰,像面包一樣讓生命延續,代代不息。
安娜希特的肩上搭過這樣的面包。那時她還沒離開慕尼黑旁邊的小鎮,她出生和長大的地方。新郎是同學,是鄰居,是亞美尼亞后裔。她一度以為,自己會像外婆和母親一樣,在離家不過一百米的地方,延續女性的命運和喜樂。
面包再好,最多也只能保存六個月。大女兒出生后,不幸開始加速降臨。父親母親突然相繼去世,家里的毛料店開始經營不善,哥哥到餐館去幫廚,嫂子生下了第三個小孩。安娜希特說,從沒有人告訴她,孩子會帶來如此的痛苦。生產的痛苦只是先兆,與哭鬧的孩子對峙著無數個不眠夜真正撕裂了她。肉體的痛苦讓精神極度孱弱,懷中那一坨幼嫩的血肉,從破損的乳頭里永不休止地索取乳汁。
這些,沒有預示就愴然發生。安娜希特說話時喜歡打手勢,跟我坐得很近,說話時直視對方雙眼,語速緩慢。但說到這些,她的雙手靜止,語速提升,灰藍色的眼睛里漾出悲哀來。離家不過一百米的幸福生活,原來是這個樣子。
錢,當然是問題,但也不全是。更多的問題,藏在衣櫥的縫隙里,木地板的空格里,嬰兒床的扶手里。安娜希特的抹布一遍遍地拂過這些無法進入的角落,正如這座房子里沒有誰的情感能填補她內心日益擴張的縫隙。女兒也不能。
可以說,來小鎮是一場逃離。掙脫離家方圓一百米的咒語,去一個陌生的地方開始新的生活。女性對生活的抉擇,往往就是這樣一次又一次的出逃,折返,渴望,靜滅。摒棄原有的定義,鼓足勇氣推門出去,似乎,一生中總要遭遇這樣的時刻。行李不多,最重的是已經五歲的女兒。安娜希特沿路看見森林,河,木屋,牛,蜜蜂和花朵。
第二段婚姻比之前的平順,不知是真的平順,還是上一段失敗的婚姻讓人學會了隱忍。丈夫繼續在衛浴用具廠工作了幾年后,女兒誕生,兩人于是決定開一家小餐館,一家人可以在一起工作和生活,更多的時間可以彼此陪伴。
在小鎮上生存并不算艱難,對于一個外來者而言。安娜希特友善,禮貌,很快就被使徒教會吸納為核心成員。這對生意也有幫助。與更多的人交談,了解他們的喜好,做出更受歡迎的食物。
安娜希特說,食物美味的秘密在于情感。用心地揉制面團,耐心地切割,每一個步驟都帶著心和對食物的感恩的話,食物不會難吃。她常常帶自己做的面點到教會去作為事工的奉獻之一。這些面點跟自己餐館里會送給客人做小點的面點略有不同,沒有堅果和果仁,也不刷黃油,只是最簡單的白面點。
從家出發去教會,需要經過火車站大街和市政廣場,沿著山勢往高處走,路越來越陡。走到后面,幾乎是在攀爬。安娜希特從沒回過愛美尼亞,只是聽哥哥說過。有一年哥哥突發奇想,決定回去看看“真正的老家”。中巴車在山路上盤旋,車里多半都是跟哥哥一樣的歸鄉游子,男人們高聲唱著歌,對著窗外不甚優美的景色評頭論足。哥哥說,不好也不壞呢。
在陡坡上爬了一遍又一遍后,安娜希特覺得餐館名字應該叫作“到十字架去”。熱騰騰的食物,干凈的床單,女兒的呢喃,這些固然是安慰,但永不止息的河流,沿著陡坡往上攀爬時可能到達的地方,向日葵般熾烈燃燒對上帝的信念,讓她更深地平靜。
看著木筏漂流時,安娜希特總是想,木筏被放進河水里,是為了到達某個地方,被人撈起來后,木筏被拆解成木頭,木頭會完成各自的使命。這些都是我們的知識和想象,我們不是木頭,所以要這樣來解釋它們的命運。但對于木頭本身來說,在土壤里長成,被砍伐,沿著陌生的水流漂流,最驚心動魄的事情都已經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了。木頭從作為一棵樹開始的渴望,也許永遠不會有人知道是什么。
快九點了,餐館里喝酒的人們開始松弛和喧鬧起來。在我離開餐館去書店后,原先那桌客人已經消失了,只剩一個人在吧臺喝酒的男人還在。又來了更多的男人女人。
酒意一上來,桌與桌之間的藩籬就被打破了。原本也都是熟人,這下更放心大膽地喝起酒來。安娜希特把音樂調大聲了些。有人推開椅子,在地板上“篤篤”地踱步,像某種笨拙的舞蹈。又一個人推開椅子站起來。安娜希特的手指也在桌面上跳起舞來。戴著戒指的無名指與拇指合扣起來,食指和中指則交替著舞步。在吧臺上沉默了太久的男人,突然轉身舉起酒杯說——干杯啊干杯!
在一幅幅向日葵畫的布景的映襯下,這里平凡得就像梵·高在阿爾住過的黃色小屋。但正如梵·高的眼睛看見的不是平凡無奇,這一刻,每個人眼睛里看見的,都不是一家平凡無奇的小餐館。安娜希特尤其如此。
離“到十字架去”餐館一百米,“自由之書”舊書店里,另一群人正在進入另一個世界。與這個世界的歡樂并無二致。
21:00
露水
越往鎮子外面走,雪就越深。有些地方,雪地上完全沒有人的痕跡。雪第一次降落在人類世界的時候,那個絕對的第一次,聲音和顏色都是新的。土地和雪第一次彼此接觸。之后,動物和人類的眼睛第一次看到白色的漂浮物,緩緩降落。
圓月光耀著河谷。自古以來如此。
安娜希特和英格麗德,都聽見過露水在花瓣上凝結的聲音。聲音時而微弱,時而巨大,讓她們屏住呼吸,直至穿透身體,讓心臟的律動加速。渴求在身體里滾成越來越大的雪球呼嘯著要沖過所有阻礙,讓人不能低眉垂眼視而不見。
一次次地變作一朵花,一次次地被看作一朵花,站在田野里。直至某一天,聽見露水淹沒莖稈的聲音時,再也不能止息,花兒靜靜走進夜里。
作者簡介:
郭爽,1984年生于貴州,2005年畢業于廈門大學中文系,2015年獲德國羅伯特·博世基金會“無界行者”創作獎學金。現居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