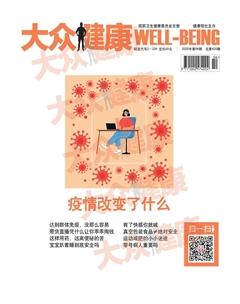靜脈曲張,何時手術(shù)最好
張茹 王鑫
夏天來了,我們會看到有些人的小腿上“青筋暴起”,就像蚯蚓一樣,非常難看,有人形象地稱之為“蚯蚓腿”。這種病癥叫做靜脈曲張。靜脈曲張不僅影響美觀,還會嚴重影響腿部健康。
雖然靜脈曲張的發(fā)病率在逐年升高,但就診率卻不高,很多人認為靜脈曲張不嚴重、不致命,可以不用治療。但是從開始的不痛不癢,到后來的靜脈炎、色素沉著甚至潰爛,當腿上的“小蚯蚓”變成了“大蟒蛇”,又有多少人追悔莫及!
靜脈曲張分6期
靜脈曲張是發(fā)病率非常高的一種血管病,在任何年齡段都可能會發(fā)病。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我國有10%~20%的成年男性、20%的成年女性存在靜脈曲張的表現(xiàn)。

靜脈曲張的早期表現(xiàn)都是潛在的,癥狀不太重,最多覺得腿有點不舒服、發(fā)脹,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這種病會越來越嚴重,并會伴隨著越來越多的并發(fā)癥:皮炎、水腫、色素沉著、靜脈出血、潰瘍、靜脈血栓等。血栓脫落后可能引起肺栓塞,嚴重的還會致命。所以,靜脈曲張要及早治療。
靜脈曲張一般分為以下幾個進展階段,有癥狀的讀者可以比對一下自己疾病的程度。
0期——無明確體征期:腿酸脹、無力、腿腫、易抽筋
1期——血管擴張期:毛細血管擴張、網(wǎng)狀靜脈曲張、蜘蛛網(wǎng)狀靜脈曲張
2期——靜脈曲張期:皮下淺靜脈持久性擴張、無并發(fā)癥
5期——水腫并發(fā)癥期:局部皮膚瘙癢
4期——皮膚改變期:濕疹、色素沉著
5期——可愈合的潰瘍
6期——無法愈合的潰瘍
為何靜脈曲張會找上門
靜脈曲張發(fā)病機制分為內(nèi)因和外因。
內(nèi)因,是由于自身生理條件造成的靜脈曲張易患體質(zhì)。由于先天性靜脈壁薄弱,靜脈瓣發(fā)育有問題,關(guān)閉不嚴造成血液倒流形成靜脈曲張。另外,隨著年齡的增長,靜脈也會隨之出現(xiàn)異常擴張。
外因,與生活方式有關(guān),比如久站久坐、肥胖等都可能造成靜脈曲張。所以,從事久站久坐工作的人和胖人要提高警惕了,長期站著或者坐著會造成下肢靜脈壓力增高。另外,肥胖雖不是直接原因,但過重的力量壓在腿上可能會造成腿部靜脈回流不暢,使靜脈擴張加重。
防治靜脈曲張小竅門
輕微的靜脈曲張,雖說無痛無害,但卻有礙美觀。夏天即將來臨,當穿起短褲或泳衣時,雙腿腫起了彎彎曲曲、藍藍紫紫的青筋,簡直大煞風景。日常生活中一些簡單的小活動,可以舒緩靜脈曲張,減緩病情發(fā)展。

1.鍛煉小腿肌肉。
小腿肌肉是一個輔助血泵,被譽為人體的“第二心臟”,每收縮一次,可以泵回30ml~40ml血液,幫助靜脈把血液輸回心臟,可緩解小腿靜脈壓力。當小腿長期缺乏運動時,這個功能便會大大減退,主動或被動屈曲踝關(guān)節(jié)的活動,如騎腳踏車、步行和游泳等都有助于強化小腿肌肉。
2.睡眠時,把雙腳輕輕墊起。
這樣可以促進雙腳血液流動,舒緩靜脈的壓力。
3.穿著彈力襪或彈力繃帶。
彈力襪的作用越來越被認可。尤其是教師、外科醫(yī)師、護士、發(fā)型師、專柜銷售人員、廚師、餐廳服務(wù)員等需長時間站立的職業(yè)者,使用彈力襪或者彈力繃帶可以有效減緩病情的發(fā)展,預(yù)防深靜脈血栓、老爛腿等并發(fā)癥。
4.控制體重。
在日常生活方面,應(yīng)控制體重,還應(yīng)避免服用避孕藥,避免穿著過緊的衣物及高跟鞋,避免蹺二郎腿及久坐或久站。有靜脈曲張的人,在靜站或靜坐約一個小時后,一定要起來活動身體5分鐘~10分鐘,再適當補充水分,不要讓自己處于一種脫水的狀態(tài),減少深靜脈血栓的發(fā)生。
5.戒煙。
抽煙會使血壓升高,動、靜脈受損,因此,靜脈曲張的病人應(yīng)該立即戒煙。
何時需要做手術(shù)
下肢靜脈曲張一般進展緩慢,病程可長達十余年。許多患者常因“不痛不癢”而拖著不治療,直到出現(xiàn)嚴重并發(fā)癥才考慮手術(shù)治療。其實,這是一個誤區(qū)。
沒有嚴重臨床癥狀、不痛不癢的時候其實正是最好的手術(shù)時機!因為此時手術(shù)效果良好,術(shù)后恢復(fù)也快;當出現(xiàn)皮膚濕疹、潰瘍、血栓性靜脈炎等并發(fā)癥時,不但患者所受痛苦增加,手術(shù)效果也會受影響。
當然,如果下肢靜脈曲張出現(xiàn)色素沉著或瘙癢或潰瘍等并發(fā)癥時,雖然已經(jīng)錯過了最佳手術(shù)時機,但仍需積極治療。亡羊補牢、為時不晚。切記,不可以諱疾忌醫(yī),把小病拖成了大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