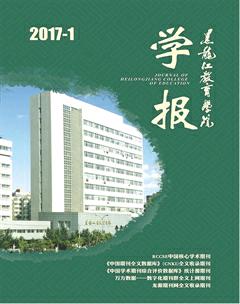清代女彈詞中“女扮男裝”故事模式的創作原因
陳嘉怡
摘要:清代女彈詞中的“女扮男裝”現象非常普遍,一般在作品中采用“女扮男裝”故事模式有兩點原因,一是展示才華,二是逃避婚姻。在“才女風尚”中獲得更多文學培養的彈詞女作家們無法逾越性別的限制,因此就借助故事中“女扮男裝”的女主角去考取功名,完成一次才名的社會公認,從而去彌補內心因性別限制帶來的不平衡感。另外,她們在設計“女扮男裝”的故事時,潛在心理上是為了逃避婚姻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其實質不過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一次心靈叛逆。但是,彈詞女作家們的這種易裝思路其實是幼稚而天真的,她們在反叛的過程中不自覺地在向“賢妻良母”的閨訓靠攏,因此不可將這種叛逆意識過分夸大為女性意識的覺醒。
關鍵詞:清代文學;女彈詞;女扮男裝
中圖分類號:I23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17836(2017)01010203
在中國古代文學傳統中,女性創作的文學常常被淹沒于以男性作家為創作主體的主流文化圈中,即使有如李清照、朱淑真一類的盛名才女也不過如彗星般閃過文壇。然而到了清代,社會上開始極力推崇“才女文化”,女性識字讀書甚至是進行文學創作已然成為當時名門閨秀、仕宦千金之中的一種風尚。男性文人、士大夫因為清初理學統治下禁止狎妓的律令而將吟風弄月、清談酬和的對象轉向家中的妻妾女兒,因此把依附于男性審美下的“才女文化”風尚進一步強化了。作為經濟最發達、物產最豐富、文化最繁盛的江浙地區則成為“才女文化”流行的中心。而作為日常大眾休閑娛樂的藝術活動,女彈詞以其特有的“空靈蘊藉、閑散舒緩”的陰柔藝術氣質受到了廣泛的欣賞和傳播。在這里需要解釋一下“女彈詞”這個概念。首先,“彈詞”這個詞本身可指具有商業性的說唱表演方式,也可指一種韻文體文學體裁,或稱之為“彈詞小說”。那么,“女”彈詞可以理解為從事彈詞說唱表演的女藝人,在當時被稱為“女說書”“女先生”“女先兒”等,在袁枚的《隨園詩話》卷五中就提到過“杭州宴會,俗尚盲女彈詞”;“女”彈詞也可以理解為從事彈詞文本創作的女作家,如邱心如、陳端生、陶貞懷、孫德英、程惠英等,在現存的清代彈詞中約有五十余部文人案頭之作,其中80%為女性作家所創作。因此,在本文中筆者所使用的“女彈詞”這一概念基本繼承胡曉真的定義“其中女作家創作的彈詞小說,多半是長篇巨制,文字也傾向于清雅典麗,明顯地以閱讀為主要考量”[1]。所以,本文的研究對象是指在清代由女性作家創作的彈詞小說。
本文基于以往的學術研究對清代女彈詞中出現的“女扮男裝”現象進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從女作家的個人經歷入手,結合時代背景并根據中國古代婦女的地位來探討這些女性彈詞小說中“女扮男裝”故事模式的創作原因。
“女扮男裝”現象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并不少見,其易裝形象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巾幗英雄形象,源自漢樂府《木蘭詩》中塑造的“安能辨我是雌雄”的花木蘭,在清代女彈詞中有不少女將軍的形象,如《玉釧緣》中的明蘭君、明蕙君,《再生緣》中的皇甫長華,《榴花夢》中的桂恒魁、桂恒超等;第二類為才女狀元形象,源自《十國春秋·前蜀》記載臨邛女子黃崇嘏,這大概是最早關于女子“女扮男裝”中狀元的故事,在清代女彈詞中有大量這類易裝形象,如《再生緣》中的孟麗君、《筆生花》中的姜德華、《玉釧緣》中的謝玉娟等;第三類為追求自由婚戀的女子形象,祝英臺就是這一類女扮男裝類型的文學典范,但是在清代女彈詞中卻少有為了追求自由婚戀而易裝的女嬌娥,她們易裝恰恰是為了逃避“整日逼生和逼死”的婚姻。根據上述易裝形象的類型分析,筆者總結出清代女彈詞作品中采用“女扮男裝”故事模式的兩點原因:其一是展示才華;其二是逃避婚姻。
女彈詞中的女主角,如《再生緣》中的孟麗君、《筆生花》中的姜德華、《玉釧緣》中的謝玉娟、《金魚緣》中的錢淑容、《天雨花》中的左儀貞、《榴花夢》中的桂恒魁皆是才智過人甚至是文武雙全的奇女子。她們輕而易舉就可以狀元及第,才學見識遠高于她們的父兄及未婚夫婿,她們可以參與國家政事,出征平亂,與男子們同殿為臣。這些完美女子的形象塑造不得不說是女性作家自我心愿的投射,是她們借女主角的“功成名就”滿足自我的內心欲求。古代關于女子的記載非常稀少,有關這些彈詞女作家的生平只能從作品的序言中得到一些只言片語,這些表述再加上韻文體彈詞小說的文本本身已經足以證明她們確實才華橫溢。筆者結合現有的資料試分析一下才女們那種類似于男子“懷才不遇”的苦悶心理。《金魚緣》的作者是孫德英,關于她的才名在鈕如媛的序中有這樣的描述:“垂髫時即不肆嬉游而好書好靜”,“每于針黹之暇,手不釋卷”,“異書雜傳,無不博覽記誦”,“幼雖未聆師訓,克己吟詠。”[2]佩香女史陳儔松在《榴花夢·序》中這樣評價其作者李桂玉:“性本幽嫻,心耽文墨,于翰章卷軸,尤為有緣。每于省問之暇,必搜羅全史,手不停年披,出語吐辭,英華蘊藉。”[3]坐月吹笙樓主人在《娛萱草彈詞·序》中提到《夢影緣》的作者鄭澹若:“昔鄭澹若夫人撰《夢影緣》,華縟相尚,造語獨工,彈詞之體,為之一變。”[4]王蘊章在《然脂馀韻》卷三中也提到鄭澹若:“澹若女史,為夢白中丞之女公子,著有《綠飲樓集》。”而《再生緣》的作者陳端生更是出身于名士家族,祖父陳兆侖學識淵博,他曾在《紫竹山房文集》中表達自己對女子有才學的看法:“世之論者每云,女子不可以才名,凡有才名者往往福薄。余獨謂不然。……嫻文事,而享富貴以沒世者,亦復不少,何謂不可以才名也。誠能于婦職余閑,流覽墳素,諷習篇章,因以多識典故,大啟性靈,則于治家相夫課子,皆非無助。……由此思之,則女教莫詩為近,才也而德即寓焉矣。”[5]這段話可以表明當時一部分漢族名士家族在教育女子方面的一種觀點,即在保證婦德女紅教育的前提下,為了讓女子在出嫁后更好地為“相夫課子”服務,女子學習詩書也是“必要的”。由此可見,女子“才名”的價值在女作家的內心中和社會普遍認知中存在著不小的差異。在清代生活的才女們受科舉制義的影響很深,她們的內心其實很渴望與男子們同場比試,這種心態不是為了“炫才”,而是希望自己的才學得到認可。在同時期的小說作品《儒林外史》中我們可以一窺究竟。魯編修教導自己的女兒魯小姐讀《四書》《五經》,寫八股文章,每常嘆道:“假若是個兒子,幾十個進士、狀元都中來了!”[6]彈詞女作家們有自信才華勝過周圍的男子,卻因為性別的限制不能進行科舉從而加官進爵,光耀門楣,這就造成了她們心理上“老天既產我英才,為什么,不做男兒作女孩?”的苦悶。在這樣“烘烘烈烈為奇女,要此才華待怎生”卻“恨不為男”的心理支配下,彈詞女作家們就只好通過女主角“女扮男裝”這種途徑來逆轉“抑郁今生不展眉”的命運。女扮男裝后的才女們與兄長、未婚夫婿同場比試,輕松就能高中狀元,讓男子們在科場上成為自己的手下敗將,加官進爵,為江山社稷建言獻策,位列三臺成為肱骨之臣。這些女子博取功名并不是為了高官厚祿、潑天富貴而是為了反駁“女子不如男”的普世觀點,完成她們對自我才學的價值確認。這些在現實中不可能實現的天真想法卻是彈詞女作家們對心中抑郁苦悶的一種宣泄和釋放。這些在“才女風尚”中獲得更多文學培養的彈詞女作家們其實都懷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壯志”,但是女性性別的限制是她們一生都無法逾越的,因此她們只能借助故事中“女扮男裝”的女主角去考取功名,使自身的才學在虛構的故事中得到認可,從而去彌補內心因性別限制帶來的不平衡感。
這些女彈詞中的女主角除了是“文章魁首”“抱經天緯地之才”以外,從身份上來講她們依舊是“生居綺閣,長出名門”的大家閨秀。婚姻是她們一生之中最重要的大事,改變并決定了古代女子們一生的命運。僅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決定了一個女子一生的“歸宿”,平民俗婦或許可以坦然接受這樣的命運安排,但是對于這些通讀詩書的古代“知識女性”而言,這種門當戶對、利益結合式的婚姻讓她們感到反感甚至可以說是恐懼。自古以來就有“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的說法,可見一場婚姻對于女性和男性的重要程度是極為不對等的,這個男人的成敗榮辱決定了這個女子后半生是平安富貴還是顛沛流離。實際上,古代女子在婚姻中完全依賴于丈夫,依靠丈夫生存,為侍奉姑舅、教導子孫操勞一生,毫無自主的權利。《金魚緣》中女扮男裝的錢淑容如此說:“……況且是,世間最苦無如女,諸事依人難自專。命好者,夫倡婦隨情好合,生男育女樂欣然。也無非,操勞白首因人累,再不能,一刻心閑與意閑。命薄者,鳳寡鸞孤悲只影,只落得,花蔭月夕珠淚漣。還有那,終風暴雨如仇敵,或遇著,逆子頑孫氣惱添,悟徹塵緣皆若此,兒因此,了無情愛系心牽……”[7]227這段話正是作者孫德英內心真實的想法,一位有林下之風的才女卻有“不愿適字之意”,“……每為論及婚嫁,……惟怏怏不樂。”尊長“勸責兼施,開導百端,卒莫能易,不得已,允遂其志”。有的女作家不愿意成婚,是害怕未知婚姻帶給自己的束縛與不幸,而更多的已婚女作家,像《再生緣》的作者陳端生一樣,難逃婚后凄苦不幸的境遇,“……句山太仆女孫也。適范氏。婿諸生,以科場事為人牽累謫戍。因屏謝膏沐,撰再生緣南詞,托名女子酈名堂,男裝應試及第,為宰相,與夫同朝而不合并,以寄別鳳離鸞之感。曰,婿不歸,此書無完全之日也……”[8]陳端生這樣聰慧靈秀的女子期望的也不過是一世安穩,琴瑟和諧的婚姻,但是丈夫因科場舞弊案被流放伊犁,就注定她寥落蕭索的一生。 因而,女彈詞中的女主角們為了逃避婚姻只能“改變性別”靠一襲青衫偽裝成男人。 但是“易裝”并不簡單,在《禮記·曲禮》中就有“不同巾櫛”的規定,它要求男女不能著同樣的服裝,因此女子的“易裝”行為就不是換一套男裝那么簡單了,而是顛倒陰陽、攪亂乾坤的大逆不道之事。“女扮男裝”既可以擁有男子在社會中的權益和地位,相應地也要承擔身為男子的家國責任。“衣服不只是社會和性別秩序的標志,它還創造并維護了社會秩序和性別秩序。”[9]“女正位乎內, 男正位乎外”[10]是封建時代對男女社會分工不同的定位,而漢族的女子更是因為裹足被牢牢地禁錮在閨閣之中。彈詞中的女主角們要逃避婚姻就必須“走出去”,要自主生存就必須考取功名,享受俸祿使其獲得經濟上的獨立。但是,無論是閱讀者還是“女扮男裝”故事的創作者都很清楚,故事中的情節只是滿足作家內心欲求的一場幻夢。在中國古代“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女子作為男子的附屬品必須遵守封建禮教對其提出的“德言容工”的要求,最終彈詞女作家們也不得不妥協于封建社會的現實,讓這些易裝女子恢復“女兒身”回歸家庭,相夫課子,做一個符合封建道德規范的“賢妻良母”。如果這些女子拒絕恢復“女裝”,像孟麗君一樣產生“何必嫁夫方要識,就做個一朝賢相也傳名”,可以“蟒玉威風過一生”這樣離經叛道的想法在當時的社會是得不到認同的。因此,梁德繩在續寫《再生緣》時安排孟麗君在成婚后做了個“循規蹈矩毫無錯,寬宏大量大賢人”。盡管這些“女扮男裝”故事中的女主角命運遭際不盡相同,但是她們“不管經濟多么獨立、政治地位多么高貴,都逃脫不了婚姻的‘柔情法網,最終都會成為性壓迫的犧牲品”[7]235。“女扮男裝”是彈詞女作家們為自己尋求的一條心靈反叛的出路,但是連她們自己也知道這條路不能一直走下去,最終她們的離經叛道都會被封建倫理拉回正途,與門當戶對的男子成婚是她們無奈的卻也是必然的結局。
清代女彈詞中女主角們鋌而走險的“女扮男裝”,既可以暫時性地逃避婚姻,又可以在科場上一展才學。而女作家們在設計“女扮男裝”的故事模式時,其潛在的創作心理或是為了避免遇到一個庸碌無為、毫無共同語言的俗夫,逃避婚姻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或是為了在被婚姻的枷鎖鎖定終生之前完成一次才名的社會公認,用科舉功名為自己的驚世才華正名。因此,這類故事模式其實質上不過就是彈詞女作家們“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一次心靈叛逆。但是,不得不承認彈詞女作家們的這種易裝思路其實是幼稚而天真的,她們想要逃避不確定的婚姻,卻逃不出“相夫課子”的傳統禮教對她們思想的侵蝕,她們在反叛的過程中亦不自覺地向“賢妻良母”的閨訓靠攏,扮男裝時也不忘為未來的夫婿掙兩個多情美妾。她們把中狀元的過程處理地簡單隨意,殊不知考取功名之中的不易,并不是只要有才華就可以狀元及第的,而且在清代文字獄盛行,漢族名士頗為滿族權貴所忌憚,“從古才人易淪謫,悔教夫婿覓封侯”是多少才女在面對殘酷的社會現實時無奈的嘆息。夫婿的功名富貴固然重要,但是登高跌重、樹大招風,面對榮耀顯達所帶來的不安與恐懼,才女們在面對一個庸碌無為的丈夫時亦可聊以自慰。
“女扮男裝”的故事模式是女作家們為自負才華卻無處表現而尋求釋放的一個突破口,是對婚姻所帶來的惶惑不安而做出的短暫性心靈游離。但是,在封建倫理的籠罩下她們是找不到真正的出路的,偶爾的叛逆只是因為心有不甘卻還沒有達到女性意識覺醒的反抗地步,因此我們對彈詞女作家們在創作“女扮男裝”故事模式時所展現出女性對自身命運不能自主而嘗試著去爭取的萌芽意識應給予充分的肯定,但是卻不能夠過分抬高這種“女扮男裝”故事模式所產生的一些啟發效應。
參考文獻:
[1]胡小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5.
[2]譚正璧,譚尋.彈詞敘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52.
[3]李桂玉.榴花夢(第一冊)[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8:2.
[4]橘道人.娛萱草彈詞[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0:1.
[5]陳寅恪.寒柳堂集[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68.
[6]吳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138.
[7]盛志梅.清代彈詞研究[M].山東:齊魯書社,2008:227—235.
[8]郭沫若.《再生緣》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陳端生[N].光明日報,196101.
[9]格爾特魯特·蕾娜特.穿男人服裝的女人[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40.
[10]廖名春,朱新華,楊之水注解.周易·尚書·詩經[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29.
Abstract:In female literature of Qing dynasty “a woman disguised as a man” is a very common phenomenon. Generally speaking, there are two reasons for this story mode: to display their talent and escape from marriage. In the “talented woman fashion” female writers obtain more education of literature but cannot break away from the gender restriction, so with the help of heroines in “a woman disguised as a man” story mode, they obtain scholarly honor or official rank, and get recognized by the society so as to make up for the sense of imbalance caused by gender restriction. Also, they design “a woman disguised as a man” story mode subconsciously to escape the uncertainty caused by marriage. In essence, it is a spiritual rebellion with the mentality of “trying to do what is known impossible”. However, female writers intention is actually childish and naive, as they unconsciously get closer to the “becoming a good wife and devoted mother” female precept, and therefore their rebellious consciousness can not be exaggerated as the awakening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Key words:literature of Qing dynasty; female literature; a woman disguised as a man
(責任編輯:劉東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