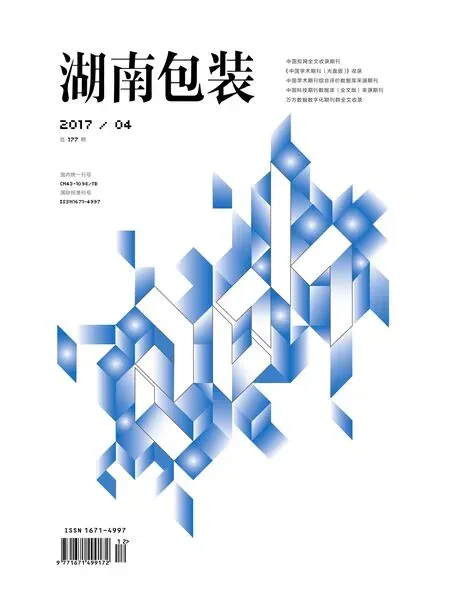湘西苗族鼓舞傳承困境與突破轉型
田茂軍
(吉首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湘西苗族鼓舞是苗族人民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創造的文化藝術,是鼓樂、表演、舞蹈等藝術形式的有機結合,深刻反映了苗族人民的生產生活習慣,傳遞出苗族人民獨特的審美、信仰及精神特質。2006年被國務院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隨著近些年苗族鼓舞的傳承發展及其影響的深入人心,苗族鼓舞已成為外界認識和理解苗族傳統文化的主要媒介,具有特殊的文化符號意義。與此同時,受現代文明的沖擊和城市化進程的影響,苗族鼓舞在傳承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著一些新問題。作為具有民族“符號”意義的苗族鼓舞,亟待在新時代新形勢下進行自我調適,實現這一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傳承與發展的突破與轉型。
1 苗族鼓舞傳承過程面臨的困境
民族傳統文化的發展,與所處時代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有著重要的關聯,這種關聯常常呈現出“不平衡”的狀態。隨著現代經濟的迅猛發展,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社會生產和生活方式發生了急劇變化,苗族鼓舞的傳承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各種原因相互之間也有著緊密的聯系。
1.1 現代綜合藝術的競爭擠壓
苗族鼓舞是苗族人民民族文化的載體,融音樂、舞蹈、表演于一體,體現了苗族人民的獨特的審美和文化內涵。隨著人們生活水平及審美觀的變化,苗族鼓舞除了在祭祀、節慶等場合下具有儀式和“符號”的功能,還衍生出娛樂健身等功能。
社會和科技的發展帶來的現代文化高速發展,改變了人們傳統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近年來,民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與外界交流不斷增多,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也隨之不斷地滲入。面對電影、電視節目、戲劇、電子競技游戲、現代歌舞、卡拉OK等各種現代綜合藝術形式的競爭擠壓,苗族鼓舞所具有的吸引力已逐漸衰弱,許多場合,僅僅作為節慶活動的喜慶熱鬧的輔助元素。商業化的行為、娛樂文化對于民眾的文化認同和文化自覺的內在要求是逐步消解的,人們在高速運轉的現代化生活中,也很難產生應有的對傳統文化本身的堅守。苗族鼓舞的傳承機制面臨著危機。
1.2 新興媒體的生活介入
互聯網信息時代,新興媒體對我們生活的影響極為廣泛。科技發展,導向的是生活習慣的改變、生活方式的改變,最重要的是思想觀念的變化。近年來,隨著科技的迅速普及與發展,新媒體在大眾生活中的介入,能最大限度地滿足大眾對于文化和娛樂的需求,新興媒體的覆蓋區域和覆蓋人群日益擴大,對資訊和娛樂消遣的需求,已逐漸充斥著人們的日常生活。這也是民族傳統文化在廣大民眾特別是青少年人群中遭受冷遇的重要原因。
現代媒介技術的發展,產生了主體傳承觀念和文化自覺的客觀要求與追求時代同步的主觀意識的矛盾。媒介技術為年輕人追求時尚、娛樂消遣提供了極大地方便。這種狀況下導向了民族傳統文化遭受冷遇。另外,新興媒體所形成的亞文化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如冷漠、不合群、社會責任感缺失、生活能力變差等,對于社會意識和民族精神的培養也是消極的。低頭族、手機控等等新詞語的出現,就反映了新媒體生活介入的反向效果。
1.3 依附于苗族鼓舞的信仰文化式微
現代文化的沖擊,大眾的民俗傳統觀念已經逐漸淡化。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苗族鼓舞漸漸失去其儀式性,更多的是作為旅游吸引物和“地方性知識”不斷地呈現在旅游現場、節慶活動現場。在這樣的語境中,文化的本真性不斷被忽視,附著于苗族鼓舞的信仰元素逐步被消解,苗族鼓舞的展示已成為一個具有功利目的的行為——吸引游客。娛樂休閑和經濟利益至上沖刷著苗族鼓舞所蘊含的民族文化的“原真性”。
從以往的神秘、嚴肅的儀式活動,到外放、表演的舞臺化活動,苗族鼓舞具有象征意義與符號表征的核心部分正在被消解和重新建構,呈現出舞臺化、景觀化的特征。“以往具有神秘性的各種宗教儀式,在為游客展演的過程中日趨簡化,其娛神、通神的屬性,亦即神圣性逐漸衰減,而世俗性、娛樂性和表演性卻在不斷增加。[1]”旅游的介入,市場化的沖擊,舞臺化的呈現,形式大于內容,信仰文化因素逐漸減弱,文化娛樂因素逐步強化。“在蜂擁而來的游客面前,少數民族文化只不過扮演著配角,竭盡全力陪襯著那個充滿功利色彩的主角。[2]”
2 苗族鼓舞的突破與轉型
面臨嚴峻的傳承危機,如果仍維持傳統的傳承機制,對于民族文化的傳承與延續已無實際意義,甚至會成為民族文化消亡的推手。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主體,可對承接對象進行創造性超越,使民族藝術發展鏈中的環節具有合規律的變異性(特別是應含有創新基因),于動態中不斷將本民族藝術整合為新的文化資源,以不斷增強其時代適應性與自身發展能力[3]。
2.1 苗族鼓舞的發展變化是文化變遷的自然規律
文化的傳承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在傳承中不斷發展的,是動態的。著名社會學家華勒斯坦認為,“變化所采取最常見的形式便是適應,即持續、細致地對據認為是傳承而來的普遍經驗與傳承的方式進行調整[4]。”現代文化介入所形成的生活及思維方式的轉變,必然會形成新的文化需求和變遷。經濟的自我發展促使文化也按照與之相適應的方式被創造和傳承, 其中也包括民俗文化[5]。文化主體依照生活水平和時代需要,會自然地對文化進行改造,以適應新的文化及生活需求。
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與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水平和審美水平緊密相連,息息相關。近年來,苗族鼓舞與文化旅游、日常健身娛樂文化聯系緊密,其文化特性和表演特征發生變化。苗族鼓舞較以前,在服飾道具、舞蹈動作、表演形態等多方面,都做出了調整。這是適應時代特色的自我調適,也是文化變遷的自然規律。
2.2 非遺保護語境下苗族鼓舞發展的多元化
非遺保護倡導在日常生活中的保護和傳承。在非遺保護的語境下,必須實現傳承方式的多樣性和發展的多元化。民族傳統文化適應時代、環境的變化與自身發展的需要進行調適,是為了更好地傳承。當然,調適要建立在保持其原有的文化內涵的精神要素的基礎之上。
傳統和現代不是對立的,社會的“人文化”強調了傳統文化的現實意義。“地方性知識”在這樣的語境下就具有特殊的文化價值,它體現的文化多樣性具有“傳統”與“民族”的標簽,也存有現代化轉向的訴求。苗族鼓舞的發展,其內在的儀式性逐漸式微,其文化屬性內在隱藏的經濟屬性,可以推動其生產性保護。隨著交流活動的增多,必然會出現吸納借鑒的意識和行為,以不斷適應新時代的文化需求。因此,苗族鼓舞傳承及發展的形式和內容上要實現多樣化,在保持其獨特性和民族性的核心價值基礎上,使文化與社會經濟結合,實現活態傳承。
2.3 苗族鼓舞的發展具有動態性
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是一種活態文化。苗族鼓舞的傳承和發展是隨著苗族人民的生產生活不斷發展的,其文化特性由最開始的祭祀儀式演變到后來的娛樂性,就是發展過程中產生的變化。一個民族社會群體的文化正是通過“傳→承→積累創新→傳”的過程,完成了民族社會文化的生產和再生產[6]。在歷史長河中,苗族人民也對苗鼓的打法不斷創新。既有氣勢恢宏的“憾山鼓”,又有風趣幽默的“猴兒鼓”;既有記錄勞動場景的“插秧鼓”,又有展示豐收喜悅的“五谷豐登鼓”。還有動作、服飾等等的演變,都體現了苗族鼓舞在社會文化生活環境中調適。
民俗最大的特征就是既有傳承又有變異,在不同的時空下,傳統民俗文化總會發生變化和調整,以適應新的環境。只有這樣,它才能夠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代代相傳[7]。苗族鼓舞的發展,與苗族的其他文化一樣,不斷地適應當下的社會需求和時代特征,一直處于傳統與現代、傳承與創新的狀態之中。
3 苗族鼓舞轉型發展的有效途徑
3.1 苗鼓進校園、進課堂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在對“保護”的闡述中提出,“傳承”是確保非物質文化遺產生命力的重要措施,“特別是通過正規和非正規教育”,強調了教育是傳承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途徑。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對于傳承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推動文化創新有著重要意義。開展各種形式的非物質文化教育是傳承和發揚民族傳統文化的有效途徑。
在非遺保護實踐中,需要進一步強化對青少年的非遺文化教育。苗族鼓舞進校園、進課堂,實現與學校教育為主的全方位教育體系的結合,是一項綜合性的系統工程。必須是正規教育(學校)與非正規教育(社區、家長等)相結合、書本知識與實踐體驗相結合,讓兒童從感性興趣入門,逐漸進入理性理解階段,從而真正認識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性,成為其傳承者[8]。可通過將苗族鼓舞文化編入地方的鄉土教材,并納入學校的教學計劃,加深青少年對于苗族鼓舞的了解,增強青少年對于苗族鼓舞的保護意識。各中小學還可以利用體育課、校園文化活動等形式,學習苗族鼓舞,積極投身到保護實踐中。
苗族鼓舞進校園,不僅是中小學,還要進高校,發揮高校的人才優勢,融入學校教育和學生生活,進一步擴大影響,營造氛圍,完善人才培養機制。近年來,吉首大學開設苗族鼓舞課程,納入專業教育課程體系中,舉辦展演活動,現實效果突出,具有借鑒意義。
3.2 苗鼓進社區、進廣場
苗族鼓舞的保護主體是以廣大民眾(包括傳承人)為主的社會各方力量。隨著苗族鼓舞的不斷傳承發展,其娛樂以及健身功能凸顯,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民眾參與的積極性很高,適合成為大眾學習和實踐的對象。“非遺”進社區、廣場,是倡導在日常生活中的傳承。這種傳承以社區及文化廣場為紐帶,開展學習和展演活動,讓更多人了解苗族鼓舞,身體力行地投入到傳承行為中去,進而喚起全社會的文化保護意識。
苗族鼓舞進社區、廣場,還要加強推進苗族鼓舞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公眾教育。可通過開展非遺文化宣講、非遺主題日活動等形式進一步提高教育效果。
3.3 打造苗鼓文化產品
長期以來,困擾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傳承活動無法直接產生經濟效益。毋庸諱言,經濟利益是“非遺”傳承與發展的內在需求。苗族鼓舞在現代日常生活中,已形成功用性轉變。苗族鼓舞除了在旅游場域中表演,還用于節日慶典和日常表演中。其娛樂性的轉向,具有“熱鬧”“特色”“喜慶”的內在屬性。這種狀態下,一定程度上可以實現民眾傳承苗族鼓舞的經濟訴求。
苗族鼓舞的傳承發展不能單一地指向表演技藝,還有其制作技藝。這同樣屬于苗族鼓舞內在蘊含的經濟價值,可以作為文化產品產生更多的經濟效益。湘西經濟開發區的吉首山里人民族鼓樂廠,是一家苗鼓加工企業,采用新材料,批量生產現代組合鼓,獲得了國家發明專利,遠銷海內外,產生了較好的經濟效益。
3.4 與鄉村旅游、文化旅游的融合
非物質文化遺產“從遺產到資源”早已成為文化傳承和經濟發展結合的社會實踐。苗族鼓舞文化內涵深厚,能凸顯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具有文化功能和旅游功能。苗族鼓舞是苗族地區的獨特文化,能夠滿足旅游者對于“異質”文化的需求,本身就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性知識”,能夠很好地融入到鄉村旅游和苗族文化風情旅游活動中。湘西吉首的德夯苗寨就有“天下鼓鄉”的美譽,“苗鼓”文化每天吸引著成百上千的人前去觀光。
苗族鼓舞與鄉村旅游和文化旅游融合,還需要進行內容和形式的創新,開發衍生產品,與更多的苗族傳統元素結合,與現代流行元素結合。在2016年的湘西旅游產品設計大賽中,有許多作品以苗鼓作為原型,與現代生活、現代藝術結合,形成良好的活態傳承產業鏈,產生了較大的經濟效益。在2015年的吉首鼓文化節中,著名土家族歌手阿朵將苗族鼓舞和苗族武術結合創作的《阿朵鼓》,表演形式新穎,產生了巨大的反響。這些成功的案例,都指向了苗族鼓舞相關的文化創意產品的打造。
3.5 與現代健身、體育的融合
苗族鼓舞的動作是音樂、體育和舞蹈的結合,表演者需要全身用力協作配合方可完成表演,具有娛樂和健身價值,可滿足大眾對于健身的需求,且易于推廣。苗族鼓舞的現代突破轉型,可借鑒廣場舞流行的方式,結合當前全民健身事業大發展的契機,主動地融入到全民健身活動中去。與現代健身和體育的融合,可將苗族鼓舞與現代健美操、舞蹈結合,豐富全民健身運動的內容,又能進一步擴大苗族鼓舞的影響和傳承面。
在此,需要進一步加強全民健身運動和傳統體育文化活動的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完善公共體育、文化服務體系,劃分專門場地,提供苗鼓,組建隊伍,推動民族文化的發展和進步。另外,還可進一步提高表演層次,以市場導向為目標,形成良好的傳統文化展演氛圍,發揮市場對于文化傳承的有效配置。
3.6 舉辦鼓王大賽,提高社會參與度
社會學家布爾迪厄認為,“大師的名字的確是一種偶像。這需要描述一整套社會機制使藝術家個人作為這個偶像即藝術品的生產者成為可能。也就是說,需要描述藝術場(分析家、藝術史論家)的構成,藝術場是對藝術的價值創造權力的信仰不斷得到生產和再生產的場所[9]。”新中國成立以來,苗族鼓舞的“藝術場”正在逐步構建:鼓王的評選。湘西苗族鼓舞共推選出5代鼓王,分別是龍英棠、石順民、龍菊蘭、龍獻菊、王黃娟。“鼓王”是苗族鼓舞傳承中突出的個體,他們民族傳統文化意識濃厚,有自己的知識體系,有對群體意識的自覺超越,能夠發揮主觀能動性作用,從而產生更廣泛的影響。
鼓王的評選,其內在是公平、公正的評定機制,是一種激勵機制,是政府與社會的認可行為。“鼓王”稱號,意味著對苗鼓技藝的最高的肯定。2013年至今,湖南·吉首國際鼓文化節已連續舉辦4屆,每年的重頭戲就是鼓王大賽。鼓王大賽,能夠提高傳承人的社會地位,提高社會的參與度,擴大影響,營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使苗族鼓舞展現出新的時代感和生命力,可推動苗族鼓舞的繁榮。
4 結語
苗族鼓舞承載著廣大苗族人民的生活生產習俗和獨特的民族精神信仰,是外界了解苗族文化的重要媒介。近年來,隨著社會現代化進程快速推進,苗族鼓舞在苗族社會中的功能價值逐步減弱,傳承發展遭遇傳承困境,這是社會、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響的結果。苗族鼓舞傳承的生命力,取決于置身其中的民眾的生活需求。苗族鼓舞的發展,需要正視其發展所展現的文化規律內核,形成新的傳承發展機制,保留其民族文化的個性和核心價值,允許多樣化發展,從而實現突破轉型。苗族鼓舞要走活態傳承的路子,進行生產性保護,實現活態傳承。
苗族鼓舞的突破轉型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進校園、進課堂,進社區、進廣場,強化苗族鼓舞的教育,營造全民學習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環境和氛圍。打造苗族文化產品,與鄉村旅游、文化旅游相結合,走產業化利用的道路,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共贏。還需要加強品牌意識,樹立消費認知,構建文化專屬品牌產品即文化衍生品[10]。可以與現代健身、體育相結合,舉辦鼓王大賽,適應并滿足社會的文化和生活需求,提高社會參與度,感受民族文化內涵,進而提升文化自覺感。
苗族鼓舞在傳承困境下的突破和轉型勢在必行,在新的傳承和發展機制之下,苗族鼓舞的傳承和發展大有可為。
[1] 明躍玲.鄉村旅游語境下民間技藝的變遷:基于湘西德夯苗寨的個案分析[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10(6):48-52.
[2] 阮金純,楊曉雁.云南少數民族文化傳承模式及其現代化進程中的困境[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5):62-66.
[3] 宋生貴.民族藝術傳承主體的當代變化——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發展民族藝術的美學研究[J].內蒙古社會科學,2005(1):78-84.
[4] (美)華勒斯坦等著,劉鋒譯.開放的社會學:重建社會科學報告書[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5] 陳華文.論浙江民俗的演變軌跡及其特點[J].民俗研究,2008(2):198-211.
[6] 潘年英.從文學自覺到文化自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7] 安德明.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反思[J].河南社會科學,2008(1):14-20.
[8] 鄭土有.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兒童意識”——從日本民俗活動中得到的啟示[J].江西社會科學,2008(9):24-29.
[9](法)皮埃爾·布爾迪厄.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與結構[M].中華編譯局,2011.
[10]陳培瑤,吳余青.文化創意產品設計研究的現狀分析[J].湖南包裝,2017,32(01):5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