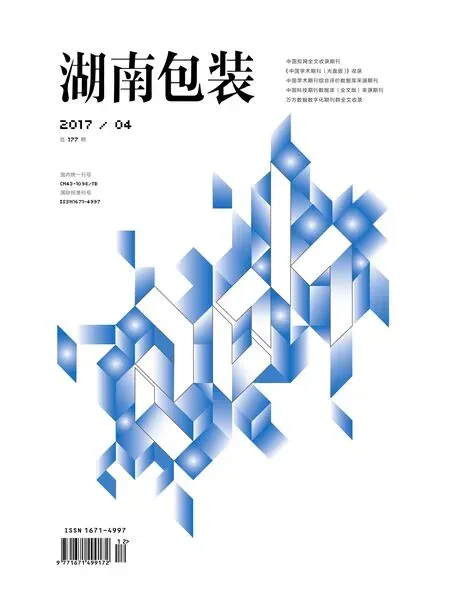旅游精準扶貧下湘南村域環境文化保護策略研究
王麗梅 張光俊 王麗娜
(湘南學院美術與設計學院,湖南 郴州 423000)
1 相關概念的辨析
1.1 精準扶貧
我國的扶貧開發工作已經實施了近30年,當前的扶貧問題都屬于剩下的“硬骨頭”。精準扶貧針對過去“漫灌”、粗放式扶貧現象,在扶貧對象、方式、措施和效果等方面都更為明確。中辦發(2015)25號文中將精準扶貧定義為“通過對貧困戶和貧困村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引導各類扶貧資源優化配置,實現扶貧到村到戶,逐步構建扶貧工作長效機制,為科學扶貧奠定堅實基礎”[1]。精準扶貧強調扶貧資源更多、更準確地向扶貧對象傾斜,即“誰貧困就扶誰”,實現“精確滴灌”,將扶貧落實到戶到人。
1.2 旅游扶貧
旅游扶貧的概念在我國20世紀90年代初已被提及,但沒有確切的定義。通過分析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大致有以下幾種觀點:旅游扶貧屬于典型的產業扶貧方式,不僅能輸血,也能造血;旅游扶貧的開展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一般是在具備一定的旅游發展條件和基礎的貧困地區(或欠發達地區)實施;旅游扶貧的出發點和歸宿是貧困人口,即重點在扶貧,這是旅游扶貧區別于一般意義上旅游發展的根本之處[2]29-30。由此看出,旅游扶貧重在扶貧而不是發展旅游,在實現旅游貧困地經濟發展的同時使貧困人口脫貧。
1.3 扶貧旅游
國內很多學者一般將扶貧旅游等同于旅游扶貧,但也有不同的觀點。李佳(2010)指出“扶貧旅游以貧困人口的持續獲益和發展為目標,以可持續旅游為基石,以機制構建為核心,是一種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新理念和使用工具”[3]。扶貧旅游重點是旅游,其偏重于旅游研究,是旅游發展的一種模式,是可持續旅游與消除貧困的一種方式,與旅游扶貧是有差異的[4]。扶貧旅游的內涵較窄,貧困地區舉辦某一旅游活動、設計旅游線路、創新旅游產品都屬于扶貧旅游的內容。這與國際上的PPT模式:有利于貧困人口發展的旅游(Pro-poor Tourism)含義上較為接近,即利用各種旅游類型或形式,讓貧困人口獲益,更加強調旅游可持續發展,而不是扶貧本身。
1.4 旅游精準扶貧
旅游精準扶貧最早出現在2014年國務院出臺的《關于促進旅游產業改革的若干意見》中的第七條“加強鄉村旅游精準扶貧”。旅游精準扶貧是精準扶貧理念在旅游扶貧領域的具體應用[2]37-39。旅游精準扶貧對象瞄準更準確,聚焦于真正能進行旅游扶貧開發的地區,幫扶那些“可扶之人”。不是所有的貧困地區都適合旅游開發,也不是所有貧困人口都能參與旅游扶貧。旅游精準扶貧針對不同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因地制宜地確定合適的旅游扶貧開發項目,采取切實可行的旅游幫扶措施,并能促進旅游的可持續發展。
2 湘南村域環境傳統文化探討
湘南地區一般指位于湖南省南部的郴州、永州、衡陽三市,毗鄰廣東、廣西、江西三省區,是典型的梯級過渡地帶。湘南區位優越,緊鄰珠三角城市群,是湖南通粵達海的“南大門”。湘南地區歷史文化悠久,人文景觀資源豐富,具有代表性的有紅色文化、地方戲曲文化、福地文化、神農文化和傳統民居建筑文化。湘南地區的風土人情、傳統工藝、故事傳說、非物質遺產等,都具有優秀的民俗文化特點,是開發扶貧旅游可以依托的重要文化資源。
傳統文化的保護、傳承和利用是相互依存的鏈條。鄉村尤其是貧困村莊,由于信息的閉塞性,受外來文化的沖擊性較少,其歷史的獨特性和文化生態的適應性保存得較為完整,并以獨特的方式呈現出來,擁有不可取代的價值和意義。
3 湘南鄉村旅游開發中的文化失憶
在開發旅游扶貧項目時,應采取多元手段,將當地農村特有的歷史人文、生活習慣,甚至宗教文化完整保存并加以提煉,融入到規劃設計之中。這樣的設計能讓游客感受到實實在在的鄉土文化氣息,提高旅游項目的檔次,增強旅游地的文化內涵,同時,鄉村旅游經濟的發展又促進了人文景觀的傳承,兩者相互促進,互為基礎。
當前,湘南地區在精準扶貧的背景下鄉村旅游如火如荼地開展。有些貧困村莊盡管交通條件欠佳,但占據了較好的生態環境資源,在扶貧的旗幟下也在尋求鄉村旅游的出路。如郴州市蘇仙區兩江口村,距離市區一個小時的盤山公路可以抵達村莊。村莊背靠青山,兩條小溪在此交匯,典型瑤族特色的建筑群墻體經歷時間的洗禮,顯現出斑駁的滄桑感。但在開發鄉村旅游過程中,利用政府撥的有限的資金將原有墻體粉刷成非正統的土黃色,古老的瓦片也被統一風格的塑料瓦片取代。通過與該村村民交流了解到,很多村民認為政府義務給他們房屋穿衣戴帽,面貌為之一新甚至覺得非常歡欣。像這種不經過深層次探究村莊歷史文化而將文化元素簡單符號化的現象不在少數,還贏得了村民的支持。
湘南地區開展旅游扶貧的過程中,另外一種民俗文化商業化的傾向也在持續著。湘南地區有不少瑤族村莊,由于其他民族的侵襲,迫使他們遷往高山密林處生活,靠山吃山,“吃完一山過一山”。瑤族民俗文化原本是未經過任何修飾、雕飾的原生態文化(如每年舉辦一次的瑤族盤王節的祀典活動),而在旅游扶貧開發過程中,為滿足旅游消費者的審美訴求,當地文化在被詮釋的過程中強行被賦予了新的文化想像(傳統特色活動接連上演,成為大眾娛樂活動),導致“非真實”的文化失憶。
“非真實”的文化失憶,是民族地區旅游業發展過程中通過一系列的措施,在一種平臺上展示的與“原真性”文化相異的,但以民族地傳統文化為母體的一種旅游者眼里的“真實”,在民族地居民眼中的“非真實”的一種文化存在狀態[5]。文化失憶在旅游精準扶貧中經常被作為借助的途徑,原本純樸的民俗、可欣賞的民俗加入了技術手段,變為消費民俗、商業化民俗從而失去生命力。徐贛麗曾分析桂北壯瑤3個村寨在旅游開發過程中出現的民族文化商業化問題,“當地民族的民俗開發成商品,使以前以自我享用、傳承和創造的文化轉變成可在市場交換的、可供游客消費的符號”[6]。過去“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的民俗文化產品成為商品化、同質化的手藝,原本粗放的制作工藝和表演形式也被美化、去粗野化。若長期不當發展,民族文化和傳統文化只會被弱小化和邊緣化而失去其“原真性”,鄉村文化旅游必然會陷入低俗商業化的傾向,從而失去市場競爭力。
4 旅游精準扶貧下湘南村域環境文化保護策略
旅游精準扶貧下湘南村域環境文化保護要以精準扶貧戰略為指導,挖掘扶貧項目的鄉村文化資源,整合傳統旅游要素,通過精準規劃旅游生態系統、引領多元主體參與,實行市場準入制度等方式探討保護策略。
4.1 精準規劃旅游生態系統
旅游生態系統的構建可以從吃、住、行、游、購5個方面進行。
(1)吃:湘南地區特色農家小吃品種豐富,如:臨武的鴨肉、資興的東江魚、安仁的抖辣椒、汝城的糍粑、嘉禾的油茶、米豆腐、血灌腸等都具有地方特色。蔬果有永興的冰糖橙、宜章的臍橙、耒陽的古巴桃、櫻桃、甜柿等。鄉村旅游開發時除了開展田園品嘗、采摘活動,還可以開展舂米、抖糍粑、車水、曬谷等農事活動,不僅展示了當地的農家特色,也是對農耕文化的精神回望。
(2)住:城市居民一直生活在方格子的高層建筑中,對鄉土氣息的庭院房屋會有一種心理的向往。湘南古民居青磚黛瓦,裝飾白色線條的馬頭墻糅合了南北方的精華,又具有獨特的文化內涵,旅游景區民宿的設計應傳承湘南民居特色,而不是城市化的“小洋樓”設計。此外,富有湘南特色的小木屋、竹屋、樹屋也都可以作為住宿的題材。
(3)行:湘南地區現存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騾馬古道(又稱湘粵古道),古道南起廣東樂昌市坪石鎮水牛灣,北至湖南郴州市裕后街,也稱“九十里大道”,古為中原通往嶺南的交通要道,沿用至今近2000年。騾馬古道經過的村落,如郴州兩灣洞村,在開發旅游扶貧時應將這一地域特色進行良好的呈現,比如再現富有傳統特色的人力車、騾馬車、挑夫等鄉村形象,抓住游客探奇新鮮的旅游心理。
(4)游:鄉村旅游生態系統的規劃要以文化游覽為導引,設置合理的游覽路線和景觀節點才能引人入勝。體現湘南農耕文化的旅游項目有:“神農嘗百草”、“春分藥王節”。湘南諸多扶貧村也是紅色文化的發源地,如鄧中夏、蕭克、黃克誠、羅榮桓將軍故里。民俗文化有昆曲、花鼓戲、皮影戲、香火龍、伴嫁歌、“瑤族盤王節”等。例如,湘南的塔山瑤族村從村民的住宅到生活用的器皿都體現了瑤族風情,建設了民族風情館,形成了古鎮一條街。此外,福地文化、宗教文化都可以融入并連成一系列關系緊密的文化節點。
(5)購:旅游產品的定位要突出鄉村旅游資源價值和市場需求,形成依托鄉村資源特色和適應游客體驗性需求的產品體系[7]。湘南地區首先可以依托當地紅色文化創新紅色旅游紀念品;其次依托“藥王文化”、瑤族等少數民族文化開發中草藥等天然保健品;還可以借助安仁縣陶瓷藝術家周國幀故里展示陶藝文化,讓游客參與到陶藝制作的過程并形成消費。
4.2 引領多元主體參與
旅游精準扶貧下湘南村域環境文化保護要吸引多元主體參與其中。首先,政府和對口扶貧單位不僅僅是提供資金支持,在協助開發鄉村旅游時,能夠在規劃方案上提供幫助。郴州政府對坳上古村的保護模式值得借鑒。坳上古村原有大量明清古建筑,但十幾年前條件好的村民自行將古建筑拆除建上新房,近幾年在旅游扶貧的政策影響下,政府對傳統民居文化更加重視,制定政策禁止村民私下改建房屋,并規劃了一塊新區做新農村建設,使得剩余50多棟古建筑得以完整保存,現已開展了初級鄉村旅游。
其次,村集體和村民也要提高文化素質,認識到文化保護的重要性。經調研得知,坳上古村仍有部分村民認識不到位,認為那些破舊的房屋既不能舒適地居住又不能拆除,滿懷抱怨的情緒,村集體有義務去給這類住戶做好思想工作。
最后,要引領參與精準扶貧的企事業單位和非政府組織做好文化宣傳和保護工作。一可以通過舉辦不同級別不同類型的休閑旅游文化節,借助網絡、電視臺、報紙、微博、微信等多元媒體加大宣傳力度;二可以創建湘南地區鄉村旅游農業專業網站,打造一批休閑旅游的精品路線,并借助專業網站向國內外展示更多鄉村旅游產品[8]。
4.3 實行市場準入制度
湘南地區旅游精準扶貧已經進入常態化,但是旅游地本土文化資源優勢未能得到充分體現。不能將旅游精準扶貧理解為簡單的旅游開發,必須實行市場準入制度,否則旅游地被開發成旅游“飛地”,缺少本土文化特色,旅游扶貧也將是曇花一現。旅游部門應對擬開發鄉村旅游的村莊設置一些前置條件,加強監督和管理。
實行市場準入制度保障傳統文化的傳承,可以從以下兩方面進行:一是評估村莊的客觀條件,應將村莊具有濃郁的傳統文化氛圍作為首要條件,再評價其生態環境、交通條件、村容村貌、周邊是否毗鄰風景區等必要條件;二是對從業人員的素質要求,不能將扶貧村的困難戶都列為從業人員進行旅游接待,他們應具備基本的文化素質,并進行過職業技能培訓,可以為游客解說當地的風俗習慣、文化傳統,讓游客對本土文化有所認知并加以傳播。
5 小結
湘南地區在旅游精準扶貧的方針下發展鄉村旅游,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對本土文化的忽視也將成為制約旅游長期發展的瓶頸。精準定位扶貧村是否具備發展鄉村旅游的基本條件,精準規劃旅游生態系統,引領多元主體參與,將文化和旅游結合開發成文旅融合型村莊,并以可持續發展理念為指導,才能更好地保護本土傳統文化,形成活態可持續發展的傳統文化生產性保護產業鏈,這才是旅游精準扶貧的內涵所在。
[1] 陳湘漪.精準扶貧背景下不同類型鄉村旅游經營者發展的影響因素研究[D].廣西大學,2016:11.
[2] 鄧小海.旅游精準扶貧研究[D].云南大學,2015:29-30,37-39.
[3] 李佳.旅游扶貧理論與實踐[M].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0:42-43.
[4] 張祖群.Pro-poor Tourism公益性研究:文獻基礎、機制與展望[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12,(3):11-18.
[5] 王瑀.民族地區旅游扶貧開發與文化失憶的真實性解讀[J].成都紡織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3,30(03):22-23+26.
[6] 徐贛麗.民俗旅游與民族文化變遷——桂北壯瑤三村考察[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64.
[7] 桂拉旦,唐唯.文旅融合型鄉村旅游精準扶貧模式研究——以廣東林寨古村落為例[J].西北人口,2016,37(02):64-68.
[8] 胡瑞波,尹幫峰,冉航飛,等.歷史文化名村樓上村特色旅游資源保護開發與利用[J].湖南包裝,2017,32(3):7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