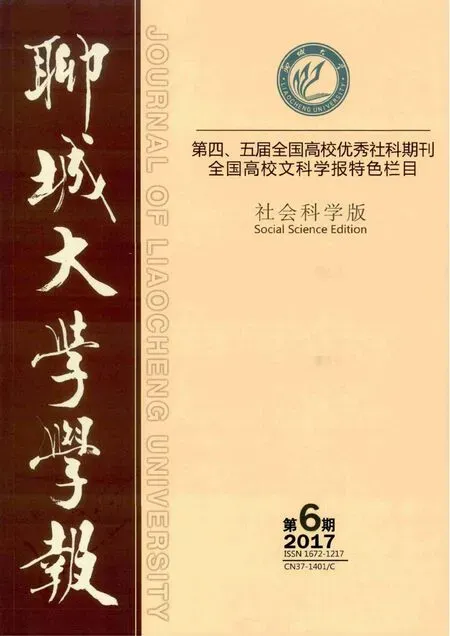論新媒介環境下文學作品改編的特質
王傳領
(聊城大學 傳媒技術學院,山東 聊城 252059)
論新媒介環境下文學作品改編的特質
王傳領
(聊城大學 傳媒技術學院,山東 聊城 252059)
新媒介環境下文學作品改編的“路徑依賴”主要側重于兩種策略——“通俗化”和“奇觀化”,二者都是在不同的路徑上向著一個方向努力,那就是提升影視作品的觀賞性。由于現代影視藝術將畫面、聲音和特技等多種元素融為一體,其本身就有著文學作品難以比擬的傳播優勢。因此,在新媒介傳播的大環境之下,以“通俗化”和“奇觀化”對文學作品進行改編的策略仍然是最符合觀眾審美且最能提升影視作品傳播效果的最優選擇。“通俗化”和“奇觀化”是文學作品改編的必然選擇,但同時文學作品在影視化潮流中也要為此付出一定的代價,如犧牲審美經驗的多樣性等。因此,文學作品的改編要盡量避免極端化的創作陷阱。
新媒介;大眾文化;文學作品;改編路徑;審美經驗
作為當代影視產業發展的重要基礎之一,大量的文學作品開始被影視從業者發掘出來,改編成為用以制作影視作品的文本。于是,過去較為單純的文學作品開始具有了文學和影視的雙重屬性——它們在作為文學文本供受眾欣賞的同時,還被按照影視創作的原則加以改編成為影視作品文本,供受眾進行二次欣賞。甚至,越來越多的文學作品在創作之初就已經考慮了其日后被改編成劇本的可能,因而自覺地被賦予了更多可以進行影視表現的因素。被改編成劇本的情況不僅涉及傳統意義上的文學作品,由互聯網發展而產生的網絡文學也被卷入了這場大眾文化的狂歡之中。尤其是在新媒介時代,后者占據了當代文學改編的更大范疇,也產生了更多重要“IP”①所謂“IP”,原指“知識產權”,其在當代漢語語境中指的是具有重要商業價值的大眾文化符號,既包括文學作品和影視產,也包括人名和文化意象。只要具有文藝創作價值和商業價值,任何文化符號都具備成為“IP”的潛力。。之所以將文學作品的改編稱之為大眾文化行為,主要是由于這種行為發端于民間,其行為目的也是將文學與影視二者進行對接,從而達到文化傳播與商業盈利的雙重效果。因此,以大眾文化的視角來審視文學作品的改編,毫無疑問是符合當代文學發展趨勢,亦是遵循文學發展實際的考察方法。
由于大眾文化的發展更多地依托于當代文化工業的發展,因此對于大眾文化的批判一直都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傳統。在很多學者看來,雖然文化工業生產出了更多的文化產品,但是其作為文學與藝術的“原真性”早已喪失,不僅淪為了謀取利潤的商業工具,甚至還會對文藝創作造成難以挽回的墮落和膚淺化。“從利益方面看,人們樂意把文化工業解釋為工藝學的。千百萬人參與了文化工業強制性的再生產過程,而這種再生產過程又總是在無數的地方為滿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標準的產品。”②[德]休克斯?霍克海默、特奧多?阿多諾:《啟蒙辯證法》,洪佩郁、藺月峰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135頁。盡管如此,文化工業在為大眾提供更多的接觸文學與藝術的機會上仍然功不可沒。尤其是在以互聯網技術為基礎的新媒介時代,現代社會的生活時間呈現出碎片化的趨勢,長篇的文學閱讀越來越難以被大眾所接受,與之相反的微博、微信等碎片化閱讀卻日漸興盛。因此,當更多的文學作品被改編成影視作品時,大眾才有可能對這些文學作品進行重新審視。這種審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由于這一類影視作品是由文學作品改編而來,其中必然包含原作中的文學因素,無論是人物形象塑造還是敘事策略,大眾都能在欣賞這些影視作品時或多或少地體會出原作的精髓。二是當大眾欣賞這些影視作品之后,如果感到意猶未盡,那么其就有可能向上追溯其原著,以實現心理的完全滿足,從而擴大原有的文學消費群體。因此,文學作品的改編不僅為影視產業的發展帶來了生機,也為自身更好地傳播增添了砝碼。
一、通俗化與奇觀化:文學作品改編的“路徑依賴”
“路徑依賴”理論來源于生物學,近年來被頻繁引入政治學和經濟學的研究之中。這一理論認為,“一種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會在一定時期內持續存在并影響其后的制度選擇,就好像進入一種特定的‘路徑’,制度變遷只能按照這種路徑走下去。”①楊龍:《路徑依賴理論的政治學意義》,《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03第1期。縱觀當代影視作品不難發現,文學作品的改編已然形成了一定的操作法則。這套法則誕生于大眾文化的傳播之中,并且在文化工業的生產與消費中不斷進行改造,以適應不斷變化的文化消費市場。它不僅規范著文學作品改編的過程,還將文學作品的創作也納入其改編過程之中。經過幾十年的不斷驗證和積累,這套法則似乎已經成為文學作品改編的不二法門,也為改編之后的影視作品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貢獻。正是由于這種改變策略的成功,因而才形成了文學作品改編的“路徑依賴”。事實上,就目前業已改編成功的文學作品來說,其總體改編的“路徑依賴”并不復雜,主要體現在“通俗化”和“奇觀化”兩種策略之上,而這兩種策略恰恰也正符合了大眾文化的傳播特性。
首先,“通俗化”原則是文學作品改編的首要策略。
作為大眾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影視作品在本質上是屬于市民文化的一部分,它的創作首先也是要滿足世俗社會的需要。因此從這一角度來說,只有贏得大眾的青睞,影視作品才能最終達到擴大傳播范圍與收獲經濟利益的雙重目的。誠然,作為影視作品創作基礎的文學作品,其本身已經屬于大眾文化的范疇——尤其是近年來如火如荼的網絡小說等。但是作為純文字的作品,其通俗化程度較之影視作品仍然較低,其影響范圍亦是難以望其項背,對這些作品的欣賞仍然需要一定的閱讀門檻。所以,文學作品還要再一次被“通俗化”,從而成為大眾都可接受的影視作品。這樣不僅能最大程度地滿足參差不齊的大眾審美趣味,還能增強文學作品的滲透力,所以這幾乎也是所有文學作品被改編成為影視作品時最為重要的策略。無論是古典名著,還是網絡小說,都要在這一策略的運作之下才能最終成為大眾喜聞樂見的影視作品。文學作品的“通俗化”改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作品內容上的通俗,主要指改變之后的作品要便于觀眾理解,盡量少地出現生僻概念和突兀的情節等;二是作品體量的恰當,這主要指的是要能在合適的篇幅內將文學作品的精華納于其中,盡量防止觀眾出現審美疲勞。2015年,長篇電視劇《瑯琊榜》熱播,不僅創下了極高的收視率,還掀起了大眾對于這部電視劇的廣泛討論。無論是在故事情節、人物塑造,還是在服飾、美工等各個方面,《瑯琊榜》都幾乎做到了盡善盡美,其成為一部現象級影視作品也就在情理之中。反觀其原著小說,雖然是用白話文寫就,但是其中不乏生僻之字,需要讀者具有一定的閱讀經驗才能較好地欣賞其中的精彩之處。況且,本部作品共有六十八章、九十二萬字,其規模已經超出了普通人所能承受的閱讀極限。因此,正是由于原著在改編成為電視劇時進行了二次“通俗化”,這部作品才能進入更多人的視野。毫不夸張地說,影視作品的成功改編給予了小說二次生命,也讓原著能夠獲得以往難以想象的經濟回報。正如多米尼克?斯特里納蒂所言,“大眾文化是通俗文化,它是由大批生產的工業技術生產出來的,是為了獲利而向大批消費公眾銷售的。”①[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納蒂:《通俗文化理論導論》,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19頁。盡管文學作品的通俗化影視改編讓其背負了“商業文化”之名,但是其讓更多的觀眾欣賞到了文學作品的精彩,也為提升原著的影響力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其次,文學作品的改編還要遵循“奇觀化”的策略。
對于“奇觀”理論的最重要的表述來自于法國理論家居伊?德波。他在代表作《景觀社會》中認為,奇觀是“在現代生產條件無所不在的社會中,生活本身展現為景(spectacles)的龐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轉化為一個表象。”②[法]居伊?德波:《景觀社會》,王昭風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4頁。而在影視藝術的理論范疇中,“奇觀”又特指“在影像文本中所攜有的具有強烈視覺沖擊力與吸引力的影像和畫面。”③路璐:《“奇觀”制造:美國熱播電視劇的新影像話語策略》,《現代傳播》2008年第1期。雖然這兩種對于“奇觀”的解釋不盡相同,但其實都是表述了一種建立在大眾文化思潮和現代媒介技術之上的社會景象。一方面,大眾文化思潮為“奇觀”的發生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包括文學、體育、藝術等在內的各個領域都在不斷涌現所謂的“奇觀”景象;另一方面,現代媒介技術的發展為這些“奇觀”景象的呈現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能。因此,大眾文化思潮和現代媒介技術的雙向發力使得“奇觀”文化成為現代藝術最顯著的標志之一。這種“奇觀”文化在滿足受眾本身的獵奇心理和對于精神快感的追逐的同時,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藝術作品的傳播。從這一角度來說,文學作品的改編在遵循“通俗化”策略的同時,還要在“奇觀化”策略上下足功夫,只有這樣才能產生更多的戲劇沖突,從而達到傳播效果的最大化和最優化。同樣是以電視劇《瑯琊榜》為例,這部戲最大的“奇觀”看點在于梅長蘇如何以一人之力掃清朝堂污濁,從而洗清赤焰軍冤屈并輔佐靖王成功奪嫡。電視劇將原著九十二萬字的龐大篇幅濃縮在了五十四集劇情之中,在通過演員的表演來展示梅長蘇如何運用計謀將太子、寧國侯、譽王乃至皇帝拉落馬下的同時,輔之以精彩的智斗、武打和戰爭場面,從而將超越真實生活的“奇觀”完美地展現在觀眾面前。這些“奇觀”的呈現不僅滿足了觀眾對于破解謎題的好奇心,還將正義、勇敢、堅忍和聰慧等人們心向往之的理念植入其中,方才制作出了如此精良的藝術作品。
由此觀之,作為文學作品改編的“路徑依賴”的兩種策略,“通俗化”和“奇觀化”都是在不同的路徑上向著一個方向努力,那就是提升影視作品的觀賞性。盡管現代影視藝術將畫面、聲音和特技等多種元素融為一體,其本身就有著文學作品難以比擬的傳播優勢,但在與游戲、體育等高度發達的產業的競爭中,其仍然缺乏絕對的自信與足夠的內力。因此,在新媒介傳播的大環境之下,以“通俗化”和“奇觀化”對文學作品進行改編的策略仍然是最符合觀眾審美且最能提升影視作品傳播效果的最優選擇。
二、極端化:文學作品改編的陷阱
在新媒介時代,“用力過猛”是文藝創作中經常出現的癥候。尤其是在競爭日趨白熱化的市場中以銷量、票房和點擊量等商業化原則進行衡量對比時,文學作品改編的“技術變形”問題是最難避免的陷阱。因此,作為典型的大眾文化產品,以“通俗化”和“奇觀化”策略進行改編之后的文化產品盡管在商業價值和傳播效率上都取得了成功,但需要警惕的是,這其中也同樣潛藏著極端化的風險。這種風險一般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對于“通俗化”和“奇觀化”的改編策略的極端化運用;二是改編過程中對于原著尊重程度的極端化。事實上,無論這種風險的哪個層面,都會偏離我國主流文化的發展要求,從而對當前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造成一定的傷害。畢竟,我國文學作品的改編“就應該具有與其社會主義屬性相應的主旋律,同時也應該具有與其開放屬性相適應的多樣化面貌,以及面向最廣大公眾群體的大眾化形式”。①王一川:《主旋律影片的儒學化轉向》,《當代電影》2008年第1期。這既是由我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所決定的,也是當前大眾文化發展的必然選擇。
首先,盡管文學作品的改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通俗化”和“奇觀化”的改編策略,但是這種改編策略的運用也需要在一定的范圍之內才能發揮其最好的作用。對于“通俗化”和“奇觀化”的改編策略的盲目運用,不僅不能達到原本期待的效果,反而會將原著及其改編作品推向極端。一方面,“通俗化”策略的極端運用必然會導致改編的作品背離原著的創作理念,甚至會出現過分庸俗乃至低俗的藝術效果。以經典小說《西游記》為例。盡管被稱作史上最強“IP”,但是《西游記》的眾多改編版本質量卻參差不齊。除了較為成功的《大圣歸來》《大話西游》等電影之外,仍有眾多作品沉迷于對唐僧等角色的貪嗔癡而無法自拔。盡管創作者一廂情愿地認為新媒介時代的受眾樂于欣賞庸俗化的藝術作品,但票房和觀眾評價仍然給予了這些作品直接的回擊。另一方面,“奇觀化”策略的過分運用必將會使得改編作品呈現不恰當的魔幻色彩。英國女作家J.K.羅琳的著名小說《哈利波特》堪稱魔幻小說的代表,由其作品改編的電影也成為了魔幻電影中最為經典的系列。但是,在眾多被改編的文學作品中,魔幻系列畢竟只是其中之一,大量的現實主義作品并不具備魔幻因素。然而,“奇觀化”的改編策略卻使得這些原本嚴肅的文學作品被加入了魔幻因素,未免貽笑大方。以《鐵道游擊隊》為例。由劉知俠創作的文學作品本是我國現代抗日小說的經典,但是在被改編成為電視劇之后,劇中人物騎著自行車不僅可以直接起飛,還能躲開飛來的子彈。這些屢見不鮮的情節使得電視劇在失去了原著小說的熱血和悲壯的同時,也將自己歸入了“神劇”之列。這些魔幻因素不僅不能增加電視劇的看點,甚至成為了作品最大的敗筆。因此,“通俗化”和“奇觀化”的改編策略的運用固然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這些策略的極端化運用卻會將改編之后的作品推向難以挽回的深淵。
其次,文學作品改編的極端化還涉及到對于原著的運用程度問題。無論是完全遵照原著來改編還是過分地偏離原著,都是這種極端化的體現方式。一方面,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是兩種不同的藝術類型,它們之間存在著表現手法、矛盾處理方式等多種差別。如果文學作品的改編過分遵照原著,那么不僅文學作品中的部分精華可能無法運用影視藝術的手段表現出來,其改編后的藝術作品也會呈現出類型上的模糊化。這既是對原著的傷害,同時也是對影視作品的不負責任。正如卡爾科?馬塞爾所言,“改編本身就是一次文學創作活動”。②[法]卡爾科?馬賽爾:《電影與文學改編》,劉芳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第122頁。這就意味著文學作品的改編同樣需要藝術的創造,這種創造雖然是基于已有的文學作品而進行的,但它在價值上卻與文學作品的原始創作不相伯仲。因此,文學作品的改編“最重要的是忠實原著的精神價值和藝術價值,保留其中的精華成分,這是一個關系到改編之成敗與否的問題”。③田本相、宋寶珍:《談電視劇的名著改編》,《中國電視》1998年第6期。另一方面,文學作品的改編還存在著過分偏離原著的情形。在很多文學作品的改變過程中,改編者只是將原有的文學作品作為自己想象的來源,雖然其中的人物仍然保留,但是故事的內容和人物的性格卻早已大相徑庭。事實上,大部分文學作品本身就已經是一個較為圓滿的狀態,其中的故事情節、人物心理等細膩細節也經過了作者的充分打磨。過分偏離原著的文學改編,不僅會造成其中精華的喪失,甚至還會出現較大的紕漏。
2012年,茅盾文學獎獲獎名著《白鹿原》被改編成電影。作為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的高峰之一,《白鹿原》將白家與鹿家上下三代人之間的恩怨情仇置于社會大變革的時代背景之下進行展現。原著不僅情節表現手法細膩,而且整體構思大氣磅礴,堪稱當代文學最重要的史詩之一。從改編技術上來看,將原著近五十萬字的龐大篇幅較為完整的納入一部影片之中難度固然極大,但是電影作品忽略原著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情節、只將一個配角(田小娥)的部分故事拿來講述的方法也實在令人難以認同。這這部作品中,白家與鹿家兩代人之間截然不同的人生選擇以及每個人物身上復雜的情感關系都沒能完整地表達出來。盡管導演王全安的目的是想要通過展現原著中的一個片段來折射整部文學作品的基調,但是影片《白鹿原》的這種“通俗化”的改編幾乎可以說是不成功的。相比之下,電視劇《白鹿原》的改編相對比較成功。其運用七十七集的巨幅篇章來呈現原著的細節與精髓,既保留了文學作品的原汁原味,同時也將不適合電視表現的段落進行了合理化改造,因此才能達到現象級的傳播效果。由此可見,文學作品在依照“通俗化”和“奇觀化”進行改編的過程中,首先要克服的就是極易出現的“極端化”趨勢。這種趨勢不僅容易一發而不可收拾,它還會影響觀眾對于改編作品內容的理解——尤其是對于歷史劇而言。鐘大豐教授曾經說過,“觀眾對歷史解釋的接受程度往往取決于對作品歷史表現符碼的認同程度。……人們在消費那直觀、生動的藝術形象的同時,也在接受作者所賦予的對歷史的解釋”。①鐘大豐:《作為敘事和表象的歷史——歷史寫作與歷史題材創作》,《北京電影學院學報》1991年第2期。改編作品的內容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顯然,文學作品的改編并非可以恣意妄為,它既需要對原始文學作品進行權衡,又受制于主流文化價值觀的核心理念。因此,只有將文學作品的改編放在主流文化價值觀的指導之下來進行,才能創作出符合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內涵和當前國情的優秀作品。
三、文學改編:審美獨特性與價值重構
從單純的文學作品到被改編成為具有影視藝術屬性的劇本,看似只是經歷了一個形態上的改造,即表述方式上的改變。但是從文學作品所謂內在屬性上來看,這種形態上的改造還對文學作品的審美獨特性造成了影響。概而言之,“通俗化”和“奇觀化”是文學作品改編的必然選擇,但同時文學作品在影視化潮流中也要為此付出一定的代價。
作為人類審美的對象,藝術在被受眾欣賞時,每一個單獨的受眾都會產生不同的審美經驗。這種審美經驗是“在審美主客體‘相遇’的審美活動中產生的,實際上它也是一種審美活動,是一切審美活動的最基本的形態”②曾繁仁:《文藝美學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1頁。。美國實用主義美學家理查德?舒斯特曼也曾經說過,“實用主義美學最重視的就是審美經驗”。③彭鋒:《新實用主義美學的新視野:舒斯特曼訪談》,《哲學動態》2008年第1期。由于文學作品只能依靠文字來提供信息,因此在對文學作品進行欣賞時,讀者需要運用自己的想象將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故事場景等還原在自己的思維之中。然而,鑒于每個人的生活閱歷、教育背景乃至成長環境都有所不同,每個讀者所還原出的文學作品信息也就千差萬別。所以,每一位讀者以及讀者的每一次閱讀都會產生不同的審美經驗。這些截然不同的審美經驗只存在于每一位讀者的想象之中,從而構成了個人的總體審美經驗。而當文學作品被改編成為影視作品之后,由于影視藝術的形象性和綜合性等特質,這種訴諸于“通俗化”和“奇觀化”的文化工業所生產的作品便會將一種單一的文學想象呈現在所有受眾面前。這種單一的文學想象來自于編劇、導演、演員等影視藝術創作者的綜合構思,一旦被制作成為具體的藝術作品,這種文學想象便被固化下來。而當受眾欣賞了這些影視藝術作品之后,這些文學想象也會隨之成為受眾的審美經驗。它不僅會占據受眾的想象空間,而且很難再被改變。誠然,受眾由于自身成長與教育因素的不同,其在欣賞影視作品時也會產生不同的審美經驗。但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審美經驗是建立在他人審美經驗之上的二次審美體驗,其可能產生的審美差別與欣賞文學作品所產生的審美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
盡管文學作品的改編為受眾提供了較為同質的審美經驗,文學作品閱讀的傳統體驗似乎也難以找回。或許正如作家李唯所言,文學作品的改編是“被迫向電視受眾的低層次審美進行趨同化的大踏步后退”。①唐加文:《從文學到影視,是拯救嗎?》,《人民日報》(海外版),2012年10月24日。然而,改編自文學作品的影視作品在“通俗化”和“奇觀化”的策略之下卻達到了文學作品難以企及的傳播廣度。仍然是以電視劇《瑯琊榜》為例。在電視劇播出結束一周之后,各大視頻網站的播放次數累計已經超過了35億,而由電視劇的熱播所引發的原著小說的銷量也隨之提升了33倍。這樣的數量級增長不僅再一次驗證了作為大眾文化產品的影視劇的影響力之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人們對于文學作品改編的詬病。誠然,為了達到影視作品最終的傳播效果,文學作品的改編要在一定程度上放棄原著中精彩卻不適應影視藝術表現的部分故事情節、人物描寫和抒情論述等片段,甚至要為創造“通俗化”和“奇觀化”的藝術效果而對原著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改造。但是,文學作品要想在這個充斥著現代媒介技術的年代再獲生機甚至重新找回昔日的榮光,那么其與影視藝術的媾和也就不可避免。否則,一味地與文化工業激烈對峙,對于文學來說不僅不明智,而且很有可能會傷及自身的發展。
事實上,無論是文學還是影視,都是眾多藝術門類中的一種,它們之間并無高下之分。盡管影視藝術在高雅與通俗之間尚有爭議,但無論是陽春白雪還是下里巴人,只要不墮落為庸俗藝術,它們就都有存在的合理性。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文學中也存在著網絡小說等通俗作品,而影視中也不乏藝術電影等高雅成分。因此,雖然文學與影視的審美取向不同,但它們都為受眾提供了較有價值的審美體驗。盡管文學作品的改編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審美經驗的多樣性,但是這種改編不僅為更多人提供了審美體驗,還讓這種由文學作品所承載的審美體驗又疊加了影視藝術的維度。這既代表了未來文學與影視的發展趨勢,同時也象征著大眾文化在當代社會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況且,這種“處于文化復調時代的大眾文化,其生長空間是無限廣闊的,……大眾文化較之其他文化形態都有著無法比擬的優勢”。②鄒廣文:《當代中國大眾文化及其生成背景》,《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因此,恰當處理文學作品的改編并使之與其他藝術形式和諧共存,將對文藝作品的生產、傳播和接受產生深刻影響。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daptation of Literary Work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WANG Chuan-ling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Liaocheng University,Liaocheng 252059, China)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Popularization”and“spectacularization”, as two “path-dependent”strategies in the adaption of literary works, are working toward the same direction through different paths, that is, to elevate the esthetic value of films and television programs. Modern film-television art integrates pictures, sounds, special effects and other elements together, so it has its preponderance of propagation which is far more beyond than literary works can reach. And therefore, though the strategies of“popularization”and the“spectacularization”in the adaption of literary work are somewhat buttoneddown, it,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modern cultural industry, aligns most with aesthetics of the audience and is the optimal choice to maximally improve the disseminating effect of films and television works.“Pop ularization”and“spectacularization”are inevitable choices for the adaptation of literary works, but, at the same time, literary works will pay certain price in the trend of being transformed to films and television programs, such as sacrificing the diversit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Therefore, the adaptation of literary works should avoid the extreme creation trap.
new media;mass culture; literary work; adaptation path; aesthetic experience
[責任編輯 唐音]
I06
A
1672-1217(2017)06-0021-06
2017-09-16
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17CZWJ11):移動互聯網時代文藝傳播機制嬗變研究;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點項目(16AA002):網絡文藝發展研究。
王傳領(1987-),男,山東聊城人,聊城大學傳媒技術學院講師,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