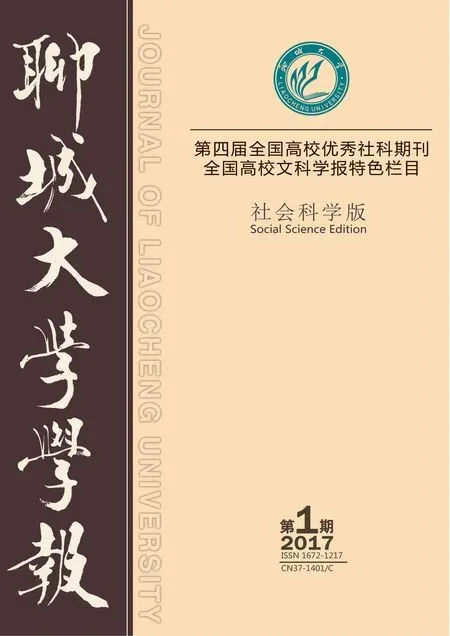民國時期胡適、張東蓀對科學與哲學關系的不同觀點
王敬華
(聊城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山東 聊城 252059)
民國時期胡適、張東蓀對科學與哲學關系的不同觀點
王敬華
(聊城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山東 聊城 252059)
科學與哲學的關系問題在20世紀之初的中國學界備受關注。“科學派”代表人物胡適提出“科學已蠶食了哲學”,“科學最終將取代哲學”,“哲學沒有將來”。張東蓀從學理的角度認為,科學不能代替哲學,科學與哲學各有特質,二者不但無抗爭而且相得益彰、共同發展,哲學是文化的本質與核心,哲學問題具有永久性,對“科學派”的主張予以回應。胡適與張東蓀關于科學與哲學關系的討論,屬于20世紀初期“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和“中西方文化論戰”中所討論的內容之一。正確理解哲學與科學的關系,對于推動哲學與科學的良性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胡適;張東蓀;科學;哲學
科學與哲學的關系問題在20世紀之初的中國學界備受關注,也是20世紀初期“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和“中西方文化論戰”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在“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對于“科學派”代表人物胡適等提出的“科學已蠶食了哲學”,“哲學將最終被科學所取代”之觀點,張東蓀從學理的角度,認為哲學問題具有永久性,哲學不可能被科學所取代,科學與哲學各有其自己的特質,二者是相得益彰的,是不存在抗爭的,對“科學派”的主張予以回應。在學術界,關于胡適的科學觀和哲學觀,或張東蓀的科學與哲學關系的思想,已經分別有過著述,但將兩位學者的觀點結合起來研究,比較其異同,或許更具學術價值。
一、哲學“破產”論:科學將“蠶食替代”哲學
20世紀初期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和“中西方文化論戰”所爭論的核心問題,即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關系問題。從哲學的層面看,焦點是自由意志與決定論孰是孰非的問題。胡適作為“科學派”的代表人物,明確指出:“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和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①張君勱等:《科學與人生觀》,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頁。。
(一)哲學是“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的學問
胡適在1919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指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②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1頁。胡適以善惡為例,對哲學的定義予以解讀。他認為,善惡是人生的一個切要問題,平常人對這個問題的解決,如勸人行善去惡、賞善罰惡等,都不算是根本的解決。根本解決主要是指,善與惡的基本內涵,“人的善惡還是天生的呢,還是學得來的呢;我們何以知道善惡的分別,……善何以當為,惡何以不當為;還是因為善事有利所以當為,惡事有害所以不當為呢;還是只論善惡,不論利害呢。這些都是善惡問題的根本方面。”①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1頁。哲學是將人生的切要問題從形而上的理性的角度去著想,尋求一個根本解決的方法的學問。
1923年11月,胡適在上海商科大學做“哲學與人生”演講,為進一步明確他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所下的哲學定義中的“根本”兩個字的意義,認為哲學對人生切要問題的研究,是“從意義上著想,去找一個比較可普遍適用的意義。”②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81頁,第281-282頁,第285頁,第286頁,第294頁。胡適指出:“哲學的起點是由于人生切要的問題,哲學的結果,是對于人生的適用。人生離了哲學,是無意義的人生;哲學離了人生,是想入非非的哲學。”③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81頁,第281-282頁,第285頁,第286頁,第294頁。胡適以人生為研究對象為哲學下的定義,體現了中國哲學的價值取向。
1925年5月17日,胡適在北京大學做的“從歷史上看哲學是什么”的演講中說:“一方面要修正我在中國哲學史上卷里所下哲學的定義,一方面要指示給學哲學的人一條大的方向,引起大家研究的興味。”④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81頁,第281-282頁,第285頁,第286頁,第294頁。胡適根據杜威的觀點,提出正統哲學應該具備的三大特點:“(1)調和新舊思想,替舊思想舊信仰辯護,帶一點不老實的樣子。(2)產生辨證的方法,造成論理的系統,其目的在護法衛道。(3)主張二元的世界觀,一個是經驗世界,一個是超經驗的世界,在現實世界里不能活動的,盡可以在理想的世界里玩把戲。”⑤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81頁,第281-282頁,第285頁,第286頁,第294頁。在這里,胡適對哲學特點的概括,明顯帶有實驗主義、科學主義的色彩。
(二)“科學的文明是求真理的唯一法門”
1926年7月,胡適在《現代評論》上發表的《我對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中認為,科學是西洋近代文明在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科學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務實,探究真理,只有真理才能使人自由、強大、聰明圣智。求知是人類天生的一種精神上的最大要求。“東方的舊文明對于這個要求,不但不想滿足他,并且常想裁制他,斷絕他。所以東方古圣人勸人要‘無知’,要‘絕圣棄智’,要‘斷思惟’,要‘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這是畏難,這是懶惰。……真理是深藏在事物之中的;你不去尋求探討,他決不會露面。科學的文明是求真理的唯一法門。”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4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6頁,第7頁,第7頁,第8頁。胡適看到了東西方文化的不同特點,但它高估乃至神話了西方文化和科學的作用。
胡適認為,近世文明有他的新宗教與新道德,這種新宗教的特點是:第一,新宗教的“理智化”,即“拿證據來”的態度。“科學的發達提高了人類的知識,使人們求知的方法更精密了,評判的能力也更進步了,所以舊宗教的迷信部分漸漸被淘汰到最低限度。”⑦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4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6頁,第7頁,第7頁,第8頁。第二,新宗教的“人化”。“近世文明仗著科學的武器,開辟了許多新世界,發現了無數新真理,征服了自然界的無數勢力,叫電氣趕車,叫‘以太’送信,真個作出種種動地掀天的大事業來。”⑧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4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6頁,第7頁,第7頁,第8頁。第三,新宗教產生的“社會化的新道德”。“物質享受的增加使人有余力可以顧到別人的需要與痛苦。擴大了的同情心加上擴大了的能力,遂產生了一個空前的社會化的新道德。”⑨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4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6頁,第7頁,第7頁,第8頁。
(三)哲學終將會因科學的“蠶食替代”而破產
1929年6月3日,胡適在上海大同中學作了“哲學的將來”的演講,具體闡述了他的哲學與科學關系的基本觀點。胡適認為,“過去的哲學只是幼稚的、錯誤的或失敗了的科學。……過去的哲學學派只可在人類知識史與思想史上占一個位置,如此而已。”⑩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81頁,第281-282頁,第285頁,第286頁,第294頁。在胡適看來,科學應該比哲學居于更高的地位。他說:“最早的元子論既可以在哲學史上占地位,何以近世發明九十元子的化學家,與偉大的Mendelief的元子周期律不能在哲學史上占更高的地位?最早亂談陰陽的古代哲人既列在哲學史,何以三四十年來發現陰電子(Electron)的Thomson與發明陽電子(Proton)的Rutherford不能算作更偉大的哲學家?最早亂談性善性惡的孟子、荀子既可算是哲學家,何以近世創立遺傳學的George J.Mendel不能在哲學史上占一個更高的地位?”①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94頁,第295頁,第295頁。胡適認為,歷史上哲學家的地位和作用遠不如科學家,所以科學應該比哲學處于更高的地位。
關于哲學的將來,胡適說:“科學不能解決的,哲學也休想解決。即使提出解決,也不過是一個待證的假設,不足于取信現代的人。故哲學家自然消滅,變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在生活的各個方面,自然總不免有理論家繼續出來,批評已有的理論或解釋已發現的事實,或指摘其長短得失,或溝通其沖突矛盾,或提出新的解釋,請求專家的試驗與證實。這種人都可稱為思想家,或理論家。自然科學有自然科學的理論學,這種人便是將來的哲學家。”②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94頁,第295頁,第295頁。由此,胡適得出結論:“將來只有一種知識,科學知識。將來只有一種知識思想的方法,科學證實方法。將來只有思想家,而無哲學家:他們的思想,已證實的便成為科學的一部分,未證實的叫做待證的假設(Hypothesis)。”③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94頁,第295頁,第295頁。即哲學是沒有將來的,哲學終將會因科學的“蠶食替代”而破產。
在科學與哲學的關系問題上,胡適與科學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丁文江的觀點具有一致性。丁文江在1923年發表的《玄學與科學》一文中認為:“科學的目的是要屏除個人主觀的成見,……求人人所能共認的真理。科學的方法是辨別事實的真偽,把真事實取出來詳細的分類,然后求他們的秩序關系,想一種最單簡明了的話來概括他。所以,科學的萬能,科學的普遍,科學的貫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④張君勱等:《科學與人生觀》,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9頁,第49-50頁。同時,科學也是“教育同修養最好的工具,因為天天求真理,時時想破除成見,……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種種的關系,才能夠真知道生活的樂趣。”⑤張君勱等:《科學與人生觀》,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9頁,第49-50頁。因而科學教育對人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響作用。
二、相得益彰:哲學與科學發展演變中的二者關系
1929年,張東蓀的《哲學ABC》出版,1930年,張東蓀針對胡適的演講,在《哲學評論》上發表了“將來之哲學”一文,1937年又在《東方雜志》上發表了題為《哲學究竟是什么》的文章。為了回應“哲學取消論”的科學主義思潮,張東蓀對胡適的觀點進行了批評,對哲學與科學的關系做出了深入分析。他認為,科學再發達也不能代替和包辦哲學,科學與哲學有著不同的性質和研究范圍,哲學總有其生存和發展的一席之地。
(一)哲學是一種追本溯源、窮根究底、唯真是求的精神
張東蓀通過對哲學和科學的發展演變的考察來分析兩者的關系。他認為,哲學是一種追本溯源、窮根究底、唯真是求的精神。哲學本是philosophy的意譯。希臘的字是philosophos或philosophia,譯為中文,是“冥索”或“思索”。“就是說對于一件事從思想上求有以徹底了解他。這一種追求的努力乃是思索上的功夫。所以凡是思索上努力求有以辨明一件事物的性質,求知其所以然之故,這都可以說是菲羅索菲。可見哲學的初起只是一種廣泛的求知。”⑥張東蓀:《哲學ABC》,上海:世界書局,1929年,第9頁,第10-11頁。所謂“冥索”只能算是哲學在“胎內”的時代。
后來蘇格拉底出來,使philosophy有了“愛智”的涵義。“他實在以為世人的求智不是真的求智。世人所有的知識不是真的知識。世人所有的學問不是真的學問。他想要于這種假的求智以外另立有真的求智。他想要于這種假的知識另立有真的知識。……這種求真知識,便是哲學的誕生。”⑦張東蓀:《哲學ABC》,上海:世界書局,1929年,第9頁,第10-11頁。哲學即從世人的普通知識之外求真的知識。
張東蓀認為,“哲學的誕生就帶來了一個極大的使命。這個使命是根據于求真知識而來,就是唯真是求。求到一層尚不能算為滿足,必定再更進一層以求之;再進了一層尚不能滿足必須又追進一層。如此窮求沒有間斷,必直達‘最后’(Ultimate)為止。所以我們從哲學的使命來看,可以說哲學就是追求最后的真理,或最終的真理,或無上的原理。用俗話來說,可以說是一種追根問底。……哲學識其他學術所研究的都是中層的真理,而不是最后的真理。惟有哲學是研究這個最后的真理。”①②③張東蓀:《哲學ABC》,上海:世界書局,1929年,第11-12頁,第12-13頁,第16頁。
哲學的誕生是由于蘇格拉底,但其始祖則是泰勒斯,他提出了“萬物根源是水”的主張,即萬物都是由水變化以成。張東蓀認為,這一主張包含有兩重意義:“第一種意義是在表明萬物都有根源。這樣一說起來便不啻把萬物與其根源看作兩個互相對待的東西了。萬物由其根源而變成,又可以復歸于其根源。于是這兩個相對待的東西,便形成兩種相對待的概念:一個名曰現象(appearanee),一個名曰本體(reality)。”②張東蓀:《哲學ABC》,上海:世界書局,1929年,第11-12頁,第12-13頁,第16頁。第二種意義是哲學“打起求真知識的旗幟,出來和迷信宣戰”③張東蓀:《哲學ABC》,上海:世界書局,1929年,第11-12頁,第12-13頁,第16頁。,與宗教分道揚鑣。
(二)近代哲學的認識論和價值論轉向
張東蓀認為,到了近代,哲學發生了認識論轉向,就是要問我們有無知道萬物本體的能力,即對我們的知識能力發生了疑問。就好比我們要切木頭,就必須用刀。但我們不可專研究把木頭切成什么形狀,而應該先問一問我們的刀究竟銳利不銳利,有無切割的能力。這種轉向的原因之一是根據于哲學求真知識的態度和追根問底的精神。原因之二是由于環境所迫,即后來天文、物理、心理、化學等科學紛紛從哲學母體里獨立出去并迅速發展,從而瓜分了哲學的全部領地。這時哲學不得不取消從前的包辦態度而退到自己的老巢,即知識問題,而科學是不愿意去涉及這個高深的先決問題的。所以這一時期“愛智”的哲學承擔了對知識、科學自身的研究。張東蓀說:近代“以后的哲學只限于認識論,因為認識論是科學所不能奪去的,所以和科學沒有沖突。可見哲學自己的變化不僅是對于科學有所讓步,并且是對于科學相求調和。”④張東蓀:《科學與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57頁,第158頁,第159頁,第160頁。
張東蓀認為,哲學發生了認識論變化之后又繼起一個小變化,就是由知識論而轉化為價值論,以價值論為中心的哲學為哲學發展的第三時期。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因為知識問題成為哲學的研究對象之后,那么知識是什么?知識的來源、知識與客觀事物的關系、知識的可靠性等問題都成為哲學家研究的對象了。“一問知識的可靠不可靠,便不啻研究知識的‘妥當’(Geltung)究竟有無了。……妥當與否是屬于價值上的觀念,然而價值究竟是什么。有了這種疑問,對于價值問題又發生了極密切的感情,至是,價值論又成為哲學家研究的對象了。”⑤張東蓀:《價值哲學》,上海:世界書局,1934年,第2頁。
張東蓀認為,哲學不是研究“純粹存在”的學問,是研究“意謂中的存在”。價值就是“價值自身”,是一個獨立的范圍,既不屬于客觀又不屬于主觀。屬于主觀的是“評價”,不是價值;屬于客觀的是“財物”,也不是價值。“價值是在主觀的評價與客觀的財物以外的一種非現實的東西,則科學決不能以此為對象;于是對這個范圍來下研究便是哲學的任務了。”⑥張東蓀:《科學與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57頁,第158頁,第159頁,第160頁。因此,文德爾班認為哲學是“普遍妥當的價值批判”之學。
(三)科學與哲學不是“蠶食替代”,而是“相得益彰”
通過對哲學發展演變的考察,張東蓀認為,科學與哲學自身同有變遷,“哲學從表面上看來似變化甚大,而根本上卻是其中心點未曾移動。科學不然,在表面上變化甚微,而其中心概念卻漸漸自己改動了。……科學的自身變化是暗中移動,哲學的自身變化是層層剝蕉。”⑦張東蓀:《科學與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57頁,第158頁,第159頁,第160頁。哲學的這種剝蕉式的變化就是把外層蕉葉一層層剝去,而最后便看到了其中的卷心。或者說,即剝去外皮而只留中心。這個中心離了其外層而卻未曾改變。張東蓀認為,“哲學的中心在最初是深藏在許多枝葉的當中,不容易辨別出來;自科學的誕生以后,基于分工的原則,于是便把各種事實之經驗的現象分門別類以歸于各科學聽其說明,而獨留此中心問題的‘先驗的妥當性’由哲學自己專門擔任了。”⑧⑧張東蓀:《科學與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57頁,第158頁,第159頁,第160頁。這個中心只有隱顯之別而無大小之異。
繼之,張東蓀以研究自然界的兩種不同態度為例,精辟地分析了哲學與科學的根本不同。“科學以為只有自然界,一切都在自然界以內,除了自然界以外別無所有。而哲學則以為自然界只是我們心上的所對,好像鏡中的花與水中的月,雖確是花,卻必在鏡中,雖確是月,卻必在水中;設若離了鏡與水,則花與月亦就不能成其為花月了。……所以哲學亦以自然界為題材,但他總把自然界認為是在思想以內的,在認識以內的,而不是超越的與自己獨立的。這便是哲學與科學根本不同的所在了。”①所以他認為,提出所謂“哲學破產論”的人,沒有搞明白科學和哲學的性質。
那么,科學的發展又是怎樣的呢?張東蓀以“科學中的成年人”——物理學作科學的代表,以物理學的變遷來分析科學的變遷歷史。他認為,物理學的科學方法經歷了三個時期:第一時期偏重于建立“假說”;第二時期可以說是“實驗的”;第三時期可以說是“數理的”或“測量的”,就是說只能用數理去推測,而已經超出實驗了。第一期與第二期的分別是在態度上,就是由粗浮而進入踏實。到了第三期,實驗的意義已經不大了,或者說實驗已經不夠用了,科學的方法漸側重于數理,而數理只是邏輯而已。科學的工具既然以邏輯為主而以實驗為副,則科學在方法上已趨于接近哲學。因此,張東蓀得出結論說:“(1)科學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有其沿革;(2)且其變化又是較接近于哲學。根據此二項結論我們便可知道主張科學蠶食哲學的人們對于科學先就沒有認識清楚。”②從張東蓀對哲學與科學的歷史沿革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科學與哲學不是蠶食替代,而是相互補充,共同發展的。
三、哲學問題的永久性:哲學是文化的本質與核心
將來的哲學是什么樣子的?張東蓀認為,在過去哲學沒有被科學所侵略,根據這個事實可以說即使在未來哲學也未必被科學蠶食,不會有生存危險,也不會被消滅。哲學問題與哲學的大部分學說是具有永久性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哲學本身就是文化,是文化中最根本的部分。
(一)“文化就是變化人類本性而使其向上的”
什么是文化?張東蓀在其《人生觀ABC》中說:“文化的本義是從素樸的或赤裸的上添些上去。我們今試按這個添上去究作何解釋,我以為不是別的,就是變化本能,使其向豐富優美和諧的方面去發揮。所以文化的所由出就是因為人類若率其本來面目的本能而行必不能成功。于是不得不設法利導之,抑遏之于此,則趨赴之于彼,節制之于彼,則引導之于此。其最大目的在使人與人之間不僅能調和而不沖突,并且能增長互相的利益,使各人的欲望更得一層滿足。”③張耀南編:《知識與文化——張東蓀文化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第398頁,第401頁。張東蓀認為,“文化就是變化人類本性而使其向上的。所以我們止有修補文化使其更有效。并且務使其沒有漏洞,不致使已淘汰的野性仍從破綻中重復闖出來作崇。”④張耀南編:《知識與文化——張東蓀文化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第398頁,第401頁。
從認識論的角度講,素樸就是外界,造成者與解釋則都是文化,通常被稱為概念。“我以為凡是概念,其功用都在于對付我們自己。詳言之,即概念所代表的并不是對象的自身,乃只是我們對于對象的觀察,亦就是我們對付他的態度。須知這些態度就是所謂文化。”⑤張東蓀:《科學與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60頁,第150頁,第182頁,第183頁,第183頁。哲學就是所謂理論概念,而理念只是代表我們的態度,“則概念的功用亦必在于能變更我們的態度,換言之,即哲學只能對于文化有作用。”⑥張東蓀:《科學與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60頁,第150頁,第182頁,第183頁,第183頁。一切形而上學都只是對人生哲學的形上解讀,形而上學必須歸結到人生哲學,作用于自己的人類。“所以宇宙觀與人生觀是分不開的。換言之,即形而上學在暗中本具有人生哲學的性質是不必諱言的。”⑦張東蓀:《科學與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60頁,第150頁,第182頁,第183頁,第183頁。中國哲學就以人生觀為中心來解決人生哲學問題。哲學的功用就在于變更文化,因為其本身就是文化。正如黑格爾所言:“思維使靈魂(禽獸也是賦有靈魂的)首先成為精神。哲學只是對于這種內容、精神和精神的真理的意識,不過是意識到精神在使人異于禽獸并使宗教可能的本質性的形態里。那消沉的令人心情嚴重的宗教情緒,必須揚棄它的悲觀苦悶、頹喪絕望之情,使之轉變為構成它的新生的主要成分。”①[德]黑格爾:《小邏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13頁。
(二)哲學文化與科學文化的關系
張東蓀還從文化上看哲學,即把哲學當作文化的組成部分,以說明哲學的永久性。
張東蓀認為,哲學與科學同屬于文化,兩者不同之處在于,“科學的研究在于細微與精確,所以科學的真理比較上單純些,換言之,即異說少些;哲學反之,在于求會通,求整全,求徹底,則自可容許各種不同的觀點。”②張東蓀:《科學與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85頁,第177頁,第177頁,第178頁,第179頁,第179頁。張東蓀稱之為“哲學的忍容”,并認為這種“忍容”不同于普通的忍容,普通的忍容只是關于態度。哲學的忍容則不僅關于態度,必須在學理上承認異說存在的可能性。
哲學的問題沒有一個不可由科學來窺測,但哲學產生以來,確實有傳統的哲學問題,“這些問題有時候可以變一個形式再出現,但卻不能化為無有。所以卡拿帕派要把哲學問題認為 ‘不成問題’,這實是由于不明哲學的性質。”③張東蓀:《科學與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85頁,第177頁,第177頁,第178頁,第179頁,第179頁。你可以不承認這些哲學問題,但不能說沒有這些問題。張東蓀認為,哲學問題是不斷增加的,哲學上的新問題層出不窮,構成了哲學的發展史。“至于有人以為非把問題解決不能得安慰,這便是不甚了解哲學的任務。因為哲學的功用不在于能解決問題,而在于能提出問題。”④張東蓀:《科學與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85頁,第177頁,第177頁,第178頁,第179頁,第179頁。哲學內容增加和豐富的表現就是哲學新問題的不斷提出,哲學上的“豐富”代表著哲學上的“進步”,也代表著隨著科學的發展,哲學會不斷拓展其研究領域。
(三)“文化基型”與哲學問題的永久性
為什么哲學問題具有永久性?張東蓀認為,這是由于特定的哲學概念都是特定文化中最根本的概念。“把這些概念抽去了,則這個文明必須隨之而倒。”⑤張東蓀:《科學與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85頁,第177頁,第177頁,第178頁,第179頁,第179頁。張東蓀以西洋哲學為例,認為雖然西方文明可以分為希臘文化、羅馬文化以及希伯來文化等等,但西洋哲學就是整個西方文明的代表。例如西洋哲學上的“本質”觀念、“因果”等等都是西方文化的基本概念,離開了這些就不會有西方文化。
張東蓀還用文化人類學上的“文化基型”來說明哲學問題的永久性。“大抵文化基型之意義是說一種文化中有一個根本觀念或形式能使此文化中所有的一切都染了他的色彩。但我在此處卻訓為文化中之最根本最基礎的方式。每一種文化都有其文化基型。……西洋哲學上的問題與西洋哲學上大部分學說就是西方文化基型的表現。有時一種文化且可有復雜的基型。”⑥張東蓀:《科學與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85頁,第177頁,第177頁,第178頁,第179頁,第179頁。反觀中國文化亦是如此。因此張東蓀的得出結論:“哲學問題與哲學上大部分學說所以有永久性的緣故,就是因為這些乃是關于那一種文化中的基型的。”⑦張東蓀:《科學與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85頁,第177頁,第177頁,第178頁,第179頁,第179頁。
張東蓀認為,科學與哲學的關系就是技術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對立統一關系,既然哲學問題具有永久性,是文化的本質和核心概念,是文化基型,則哲學對科學就必然具有指導、規范作用。“如果不使科學來與問理想,則科學在社會便純變為技術,供人使用而已。如果不使社會思想來指導科學,則這種技術知識只為現狀作奴隸罷了。而同時社會理想如不化為常識,在大家心中則亦決不會實現。……我們必以形而上的知識系統來規定理想;以科學的知識系統為方法而研究其所以實現之方與改良之道。又把他化為觀念形態,變為通行的文化。”⑧張耀南編:《知識與文化——張東蓀文化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第443頁。所以,必須有負責解放之使命的科學與代表理想的哲學相提攜,才能推動文化的創新。
四、結語
胡適與張東蓀關于科學與哲學關系的討論,屬于20世紀初期“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和“中西方文化論戰”中所討論的內容之一。毋容置疑,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聲勢浩大的“科學派”引領了向西方學習和救治中國之弊的時代大趨勢。同時,科學派主張重實證、重實驗、重證據,反對傳統思維、重估一切價值,在20世紀之初的思想轉換中發揮了重要啟蒙作用。但是在學術上卻導致了科學至上的傾向,胡適在哲學和科學的關系上,主張以科學蠶食、替代哲學,把哲學變成科學的附屬品或某種形態的“科學”,“哲學破產論”等,正是科學主義在學術上的反映。
在這個問題上,張東蓀的觀點顯得更為深刻和全面。我們從其著述中可以看到張東蓀只是不認同科學派以科學統一一切,將哲學歸結為科學的主張,并沒有抵制科學和西洋文明的目的,他從純學理的角度對哲學與科學的關系作了自己的思索。目的是為了使科學與哲學各安其位,相得益彰,共同發展。嚴格意義上的科學理性是真、善、美的統一,不是單純求真的片面的技術理性,絕不是純工具性學問。因此,張東蓀提出的哲學是文化的本質與核心,它可以為人們提供一種安身立命之本等觀點對于理解哲學與科學的關系,推動哲學與科學的良性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責任編輯 常偉]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Hu Shi and Zhang Dongsu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NG Jing-hua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representative personage of“science faction”, Hu Shi proposed that“Science is encroaching on philosophy and will replace it eventually”; “There is no future for philosophy”. Zhang Dongsun responded to “science faction”. He thinks that science can’t replace the philosophy. He thinks science and philosophy has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y can even benefit mutually and develop together. He also points out that philosophy is the essence and center of the culture and will exist permanently. The argument between Hu Shi and Zhang up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belongs to the campaigns between science and view of life, as well as the campaign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The appropri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is important for the proper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Hu Shi; Zhang Dongsun; science; philosophy
B261
A
1672-1217(2017)01-0090-07
2016-11-11
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15CWHJ14):朱熹《四書集注》政治倫理思想研究;
聊城大學科研基金項目(Y1002028):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王敬華(1959-),男,山東高唐人,聊城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