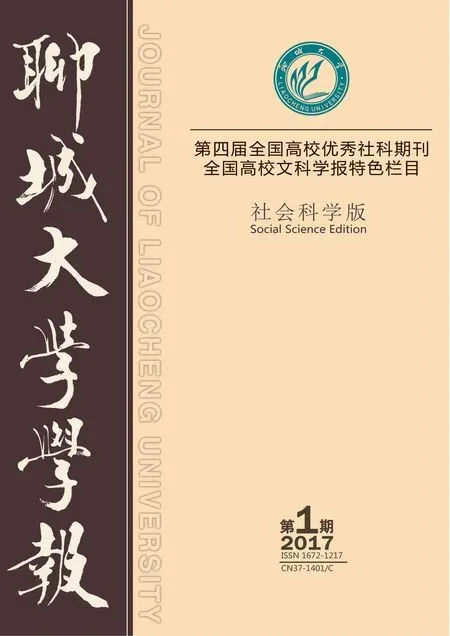蘇聯模式與中國社會主義改造
秦正為
(聊城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山東 聊城 252059)
蘇聯模式與中國社會主義改造
秦正為
(聊城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山東 聊城 252059)
蘇聯模式是蘇聯在社會主義探索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具有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特征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由于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因而其社會主義建設模式具有很大的模板性和導向性。加之蘇聯大國大黨主義的逐漸膨脹,這種模式不可避免地在國際上得到推廣。盡管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中國社會自主發展的必經階段,但它的開展進行也有著較為明顯的世界社會主義迅速發展和蘇聯模式推廣的國際大背景,因而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體制,既具有明顯的中國特色,也具有嚴重弊端,給中國以后的發展造成了雙重影響。
蘇聯模式;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體制
關于蘇聯模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系問題,是個老問題。但是,人們的視角較多集中在中國社會主義全面建設后的比較。實際上,在中國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這一問題就已經存在。蘇聯模式是蘇聯在社會主義探索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具有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特征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由于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因而其社會主義建設模式具有很大的模板性和導向性。加之蘇聯大國大黨主義的逐漸膨脹,這種模式不可避免地在國際上得到推廣。盡管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中國社會自主發展的必經階段,但它的開展進行也有著較為明顯的世界社會主義迅速發展和蘇聯模式推廣的國際大背景,因而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體制也具有兩面性,造成了雙重影響,成為中國以后正反兩方面發展的起點。
一、蘇聯模式在國際上的推廣
蘇聯模式形成于斯大林時期,因而又稱為斯大林模式。在此之前,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不認為乃至反對社會主義存在一定的模式。如馬克思恩格斯一直堅持認為:“在將來某個特定的時刻應該做些什么,應該馬上做些什么,這當然完全取決于人們將不得不在其中活動的那個既定的歷史環境。”①為此,恩格斯在晚年對于未來社會的特征問題沒有再系統地去加以研究,同時面對工人領袖的一再請教,他也一再闡述了如下思想:“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3頁,第693頁。關于如何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無論如何應當聲明,我所在的黨并沒有任何一勞永逸的現成方案。”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19-420頁。十月革命后,列寧曾經一度將特殊時期的“戰時共產主義”特殊政策作為向社會主義“直接過渡”的途徑和社會主義的建設模式,后來面對引發的政治經濟危機不得不承認“干了蠢事”,因而盡管他也羅列過幾種公式,但在新經濟政策的提出和探索上則是一直保持著高度謹慎的。列寧一方面堅持蘇聯一定要根據現實根本改變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而不要拘泥于書本知識和字眼詞句,另一方面也主張其他各國要根據自己的情況探索、試驗和確定自己的發展道路,而堅決反對推廣和照搬所謂的“發展模式”。但是,斯大林在戰勝了反對派之后,卻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這些基本原則,完全改變了較為靈活、頗具成效且已經初步證明是正確的新經濟政策,逐漸形成了固定不變、僵化難移的斯大林模式或蘇聯模式。
蘇聯模式,是伴隨著高速重工業化、農業全盤集體化和大清洗運動形成的,也是以此為基礎的。“優先發展重工業”并將其作為社會主義的基礎,并不是斯大林首先發明的。對于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資料的增長,馬克思恩格斯都曾給予了很多關注和論述。列寧在研究《資本論》時進一步予以發揮,提出“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理論”,并且在十月革命勝利后多次講述了發展重工業的意義和作用,認為重工業正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和主要基礎。同時,對于這一觀點,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也都有著大致的共識。對此,斯大林不僅有更為深刻的認識,而且還把發展重工業視為與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的根本區別,視為國家和社會主義制度興亡的重要標準。正是急于改變蘇聯的落后面貌、避免“落后挨打”的歷史,斯大林越來越強調工業發展的速度,并形成發展為所謂的“趕超戰略”,即盡可能快地趕上并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斯大林的領導下,1925年的聯共(布)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工業化方針,全國上下開始開足馬力發展重工業。與此相適應,1930年代又開展了如火如荼的斯達漢諾夫運動,工業化獲得了空前的高漲和高速發展。由此,經過兩個半五年計劃的高速發展,蘇聯建立起了基礎的重工業、基本上實現了工業化。與此同時,斯大林認為,要鞏固蘇維埃制度,并使社會主義建設獲得完全的勝利,單是工業的重工業化和社會主義化是完全不夠的,為此還必須實現農業的集體化和社會主義化。因此,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集體化,不但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內容,而且是鞏固社會主義國家的必要條件。根據斯大林的報告,1927年聯共(布)十五大確定了農業集體化的方針。斯大林一直堅持認為,集體農莊作為一種經濟因素基本上是農村發展的新道路,和富農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相反,這是農村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為此,斯大林一再指出,社會主義只能是“國家的即全民的所有制以及合作社集體農莊的所有制。”①《斯大林文選》(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6-77頁。農業全盤集體化從1929年下半年開始,經過四年多的時間,到1933年基本上完成。在此過程之中,大清洗運動也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大清洗運動旨在清除潛在的破壞分子、間諜分子和“第五縱隊”,以1934年基洛夫被害為開端,以三次莫斯科公審為高潮,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仍在持續。大清洗運動不但清除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拉狄克、布哈林等主要反對派,而且由黨內清洗、軍隊清洗擴展到社會清洗,形成一場規模宏大的政治鎮壓和迫害運動。三大運動既是蘇聯模式形成的重要推動力,也是蘇聯模式的重要組成和具體體現。
蘇聯模式,通過三大運動而建立,因而具有了鮮明的政治經濟文化特征,同時也產生了正反兩方面的重大影響。在經濟上,實行高度的計劃經濟體制。消滅私有制,實行單一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優先發展重工業,忽視乃至犧牲輕工業和農業,比例嚴重失調,經濟畸形發展;實行高度的指令性和計劃性,經濟管理政企不分,管理權與經營權高度統一;取消商品貿易,否認商品貨幣關系,排斥市場和價值規律。在政治上,實行高度集權的政治管理體制。過度強調國家的專政和鎮壓功能,通過大肅反、大清洗等運動,國家安全機關占據特殊地位、擁有特殊權力;黨委決定一切,黨政不分、以黨代政,蘇維埃實際成為表決機器、橡皮圖章;地方權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中央高度集權,地方無權,聯邦制國家實際上成為單一制國家;個人集權嚴重,領導體制形成金字塔型,總書記集黨、政、軍最高權力于一身,個人獨裁形成,個人崇拜流行,干部委派制、領導終身制和官僚集團逐漸形成;監督機制逐漸弱化,司法機關有法不依,或有法難依,民主法治破壞殆盡。在文化上,實行嚴格統一的思想文化控制體制。文化思想高度意識形態化,硬貼標簽,文藝科學均以政治為標準;學術是非由領導言論來衡量,主觀臆斷,科學研究均受官方意志裁定;實行高度嚴格的書報檢查制度和文化思想管理體系,一花獨放,進行思想壟斷和文化鉗制;輿論高度統一化、標準化,講求劃一,口號、標語滿天飛,標榜自我、貶低他人盛行,浮夸虛妄,資、社對立嚴重,暗流涌動。總之,蘇聯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高度集中、行政管理、領袖意志,并且覆蓋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各個環節。蘇聯模式,作為世界社會主義的第一個社會發展模式,一方面顯示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生命力。通過這種模式,20世紀30年代蘇聯實現了工業的高速發展,在短期內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與農業化,建立起了國民經濟發展的堅實基礎,使蘇聯由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并且建立起了強大的國防體系,為蘇聯衛國戰爭乃至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準備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但另一方面,也損害了社會主義的形象和持續發展。高度集權、個人崇拜,忽視民主、破壞法制,告密成風、清洗不斷,思想鉗制、文化壁壘,不但違背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成為西方攻擊和污蔑社會主義的口實,而且也給蘇聯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官僚集團成為腐敗的滋生地和保護傘,犧牲農業造成整個國民經濟的長期不振,大清洗成為二戰初期蘇聯失利的重要原因,大國大黨主義造成了民族分裂和社會主義陣營的破裂,更為嚴重的是種種弊端的積累最終造成了蘇聯的解體,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發展嚴重受挫。
蘇聯模式形成和定型的過程,也是這一模式在國際上不斷推廣的過程。隨著二戰的勝利進行和結束,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迅速誕生。這些國家在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同時,基本上都與蘇聯建立了密切的關系,并在國家建設上基本上都照搬了蘇聯的政治經濟文化模式。在政治上,東歐等各國基本上也實行了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個人崇拜、任職終身、大清洗等等,與蘇聯高度保持一致。在經濟上,東歐等各國也是實行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高速重工業化、農業全盤集體化,否認市場、商品、貨幣和價值規律等等,與蘇聯基本如出一轍。在文化上,東歐等各國也都實行了嚴格統一的思想文化控制體制。標語口號、輿論一致,書報檢查、思想控制等等,與蘇聯完全毫無二致。東亞和拉美的社會主義國家,也都普遍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即使最先突破蘇聯模式的南斯拉夫,力求尋求適合本國特色的“自治社會主義”,但由于國內外各種條件的限制,最終也未能完全擺脫蘇聯模式的影響。
蘇聯模式在國際上的推廣,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蘇聯模式在國際上得到推廣,一方面是這些國家別無選擇,因為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事業,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其建設經驗自然會得到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視和效仿。另一方面是這些國家不能選擇,因為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本身就受到了蘇聯的重要影響或控制,同時更由于蘇聯自認為作為社會主義的開創者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基地,其社會主義經驗具有普遍性和國際意義,從而也表現出了強行推廣的大黨大國主義,順之則昌、逆之則“壓”。加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立,使發展模式問題本身就成為檢驗社會性質和陣營立場的分水嶺。因而,蘇聯模式在國際上的推廣,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結合的結果。蘇聯模式在國際上的推廣,正如這一模式對蘇聯的影響一樣,也對這些國家產生了雙重的影響。一方面,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能夠迅速集中人力物力財力,使這些國家很快改變落后局面。東歐歷史上一直是歐洲最落后的地區,匈牙利曾被稱之為三百萬乞丐的國家,羅馬尼亞人均收入曾歐洲倒數第一,保加利亞則被稱作巴爾干的“果菜園”。但二戰以后,東歐在各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濟社會迅速發展,東德成為福利國家,匈牙利則被西方記者譽為“東歐小巴黎”和“消費者的天堂”。但另一方面,蘇聯模式的各種問題也同樣出現在東歐各國。社會發展逐漸放慢甚至停滯,出現了嚴重的困難和危機,以致積重難返、終成悲劇。
由此可見,蘇聯模式在國際上的推廣是一個較為長期的過程。盡管新中國的建立,相對東歐等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要晚,但其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卻是類似的。不過,由于中國共產黨的獨立自主性更強一些,因而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就呈現出更多的中國特色。
二、中國社會主義改造
在人民民主專政獲得鞏固、國民經濟逐漸恢復的情況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認為:“當一個任務完成了的時候,就要趕快提出新的任務,以免松懈下來。”①《周恩來選集》(下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6頁。在此原則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開始醞釀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設想。1952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統戰部起草的一個文件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②《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1頁。9月,在討論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談到: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開始過渡。③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220頁。這可以說是醞釀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開始。10月,受毛澤東的委托,劉少奇在出訪蘇聯期間給斯大林寫信,就這一想法向斯大林征求意見。對此,斯大林予以贊同,認為這一想法是對的。1952年底和1953年初,毛澤東又多次談論從現在起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1953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正式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并說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12月,中共中央批轉了由中央宣傳部編寫、經毛澤東修改的《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斗爭——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正式提出、公布和闡述了總路線的內容。1954年2月,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正式批準了這條總路線。
《宣傳提綱》指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④《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700-701頁。最為值得一提的是,這條總路線的主要內容被概括為“一化三改”,其基本戰略是“一體兩翼”。“一化”即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特別是發展重工業,這是“主體”;“三改”即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兩翼”。“一化”是發展生產力,增加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三改”是變革生產關系,改私有制為公有制,兩者同時并舉,相互促進,體現了社會主義建設與社會主義改造的有機結合、同時共進。過渡時期總路線與此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構想,既有共同點,也有相異之處。相同之處在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向是一致的,不同的是過渡的時間、步驟、方式、方法等有所變化。時間上,由先經歷相當長的新民主主義時期改為現在就開始過渡。步驟上,由先工業化后改造改為二者同時并舉,由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先限制利用后改造改為同時進行,由對農業的先機械化后集體化改為先集體化后機械化,等等。
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及其對原來構想的改變,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第一,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要求進行“一化三改”。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均是國家獨立、富強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條件,國民經濟恢復的完成自然要求將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提上日程。而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就必須對個體經濟和私營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因為小農經濟的分散低效難以適應工業化對糧食和工業原料迅速增長的需求,在新形勢下私營企業與國營企業、資本家與職工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也越來越明顯,要改變這種局面只有實行改造的方法。第二,國營經濟的迅速發展為社會主義改造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官僚資本曾占現代工業固定資產的80%,國家通過沒收的方式不但將其變為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經濟,而且實際上已經開啟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進程。到1952年,國營工業產值和商業營業額的比重已經占到全國總量的56%和60%。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迅速增長,使國家有能力、有條件對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第三,經濟恢復和調整探索出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在同私人資本主義進行限制反限制的斗爭中,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合理調整的過程中,黨和政府創造了諸如加工訂貨、經銷代銷、統購包銷、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通過這些措施,不但加強了私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聯系,而且引起了它們在生產關系上的不同變化,成為對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最初步驟。第四,國際形勢的變化也為社會主義改造提供了歷史機遇。兩大陣營的對立、西方國家中國的封鎖包圍,使新中國最終“一邊倒”,倒向社會主義。抗美援朝、鎮反運動和土地改革三大運動的完成,使“一化三改”具備了相對穩定的國內外環境。當時資本主義很不景氣,與之相反,社會主義國家則欣欣向榮,特別是蘇聯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顯示了巨大的社會主義優越性,促使毛澤東考慮盡早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中國是個農業國家,實現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化必須首先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引導農民實行互助合作,也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早在建國前夕,毛澤東就曾明確指出:“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向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權。”①《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2頁。因此,在建國后不久,毛澤東就不斷在探討農業合作化的問題。1951年春,毛澤東明確支持中共山西省委關于將互助組提高到合作社的意見。9月,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中共中央召開了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制定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較為系統地提出了黨對個體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政策。在此之后,特別是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后,毛澤東又進一步闡述了這一思想。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國家幫助的原則,堅持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采取循序漸進的步驟,以互助合作的優越性吸引農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改造大體經歷了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三個階段。互助組由農民自愿組成,生產資料仍歸農民個人所有,但在生產上則互幫互助,因而具有社會主義萌芽的性質。初級社實行土地入股,在生產上統一經營、集體勞動,產品分配則采取按勞分配和土地入股分紅相結合,耕畜和大農具也給予相應的報酬,因而具有半社會主義的性質。高級社則實行生產資料農民集體所有,具有完全社會主義的性質。經過努力,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農民已達1.17億戶,更為重要的是其中加入高級社的農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87.8%,這就標志著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
在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也對個體手工業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由于個體手工業與個體農業都屬于個體經濟,具有類似的特點,因而對個體手工業的改造也采取了與改造個體農業相類似的逐步過渡的方法。當然,由于個體手工業與個體農業畢竟有著很大的不同,因而在具體方針政策上也有所區別。對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黨和政府堅持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采取了說服教育、示范和國家幫助的方法,以及循序漸進的步驟。改造也經歷了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的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供銷小組,即生產資料仍然私有,但由國家或供銷合作社供給原料、包銷產品,因而具有社會主義萌芽的性質。第二階段是供銷合作社,即部分生產資料公有,在生產上合作社也進行一定的干預,因而具有半社會主義的性質。第三個階段是生產合作社,即生產資料全部歸集體所有,統一經營、集體勞動,實行按勞分配,因而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到1956年底,經過努力,全國共組織了10萬個手工業合作社,更為重要的是,入社社員占全部手工業從業人員的92%以上,這就標志著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
幾乎與此同時,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在順利進行。值得一提的是,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上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采取了和平贖買的方式。對于如何剝奪“剝奪者”,馬克思恩格斯曾設想過采取暴力沒收與和平贖買兩種方式,并表示如果能夠實現和平贖買,“那對于我們最便宜不過了。”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3頁。在此基礎上,十月革命后,列寧也曾經提出對那些愿意接受國家資本主義的資本家可以謀求妥協,實行贖買,但由于俄國資產階級的拒絕乃至反抗而未能實現。與此不同,在中國,黨和政府之所以能夠對資產階級進行和平贖買,在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和中國共產黨政策的正確性。民族資產階級一方面剝削工人取得利潤,屬于“剝奪者”,另一方面也擁護憲法、愿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對此,中國共產黨利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和雄厚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影響力,慎重地采取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逐步引導資本主義工商業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的,并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它主要地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存在,而是為了供應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存在……這種新式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帶著很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是對工人和國家有利的。”①《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2頁,第291頁,第432頁。因此,“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較健全和方法和辦法……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和逐步完成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經之路。”②《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2頁,第291頁,第432頁。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經歷了三個步驟。第一步,主要是實行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即在私營工業中實行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在私營商業中實行委托經銷、代銷等,將其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企業利潤則按照“四馬分肥”,即按國家所得稅、企業公積金、工人福利費、資方紅利進行分配,資方紅利大體占四分之一。資本剝削受到限制,企業因而具有了社會主義因素。第二步,主要是實行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即由國家向企業投資入股,委派干部(公方代表)會同工人、資本家(私方代表)共同管理和改造企業并起領導作用,企業利潤仍實行“四馬分肥”,企業因而具有半社會主義性質。第三步,最終實行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到1956年底,經過努力,全國99%的工業企業和82%的商業企業實行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這就標志著全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在此過程中,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還實現了改造企業和改造資本家相結合。國家對資本家及其代理人實行了“包下來”的政策,并根據“量才使用、適當照顧”的原則,對其進行政治保障、工作安排、生活照顧,通過改造階級成分達到整體上消滅資產階級的目的。通過改造,資本家由原來的“剝奪者”逐漸變成為自食其力的社會主義勞動者。
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也出現了一些失誤和偏差。社會主義改造的實質是社會主義革命,因而使中國社會開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也包含了社會主義建設,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開端。對此毛澤東曾經指出:“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于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③《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2頁,第291頁,第432頁。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同時并舉,不但實現了社會制度的重大變革,而且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保持了社會的穩定,促進了社會的進步。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體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萌芽和開端,對個體經濟的積極引導、典型示范和逐步過渡體現了改革力度、發展速度和社會可接受程度的有機結合,對私營經濟的和平贖買則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創舉,這些都體現了“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的基本原則和發展理念。同時,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是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重大貢獻。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不但是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高潮的背景下展開的,是這一高潮的重要組成和具體體現,是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在國際上推廣的迎合和創造,而且是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極大推動,對他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重大的啟發意義。當然,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出現了一些失誤和錯誤,其基本表現是“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化一”④《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50頁。。這些失誤的出現,有對社會主義認識上的偏差,即對什么是社會主義還沒有完全搞清楚,也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行政手段、大轟大嗡等現象極其相似。正因如此,社會主義改造之后中國的社會主義框架基本上屬于蘇聯模式。當然,由于認識到蘇聯模式的弊端,毛澤東也開始提出“以蘇為鑒”,力求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三、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和體制的特征及影響
經過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得以確立,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組成和具體體現。正因如此,中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從一建立就具有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呈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和強大的生命力。在此基礎上,中國逐漸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但是由于受到蘇聯模式的束縛和影響,這些體制也帶有嚴重弊端,造成了不良影響。
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其實質是無產階級專政,同時體現出較為廣泛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把民族資產階級納入人民的行列,創造性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上的首創。因而,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既不同于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專政,也不同于蘇聯等國的無產階級專政。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組織形式,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現了民主集中原則上的人民當家作主,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既不同于西方的兩院制,也不同于蘇聯的蘇維埃制度。中國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也是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和統一戰線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它不同于西方的兩黨制、多黨制,也不同于蘇聯的一黨制。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也是歷史形成的。這不但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建設,而且有利于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推進。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在中國實行的新型政治制度,實現了民族統一和民族自治、中央領導和地方自治的有機結合。這一制度也是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既不同于純粹的單一制,也不同于聯邦制或邦聯制,而是在中國的歷史傳統和現實狀況下實現國家統一、民族平等團結、共同繁榮發展的最佳制度。中國政治制度的基本特點是民主集中制。由于歷史傳統、時代背景以及蘇聯模式的影響,中國在進行民主建設的同時,也出現了較長時間內的高度集中的傾向。這種高度集中,有利于在特殊環境中集中人力物力財力辦大事。但隨著時代條件的變化,也帶來了許多弊端,因而有必要進行變革。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特點,體現在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兩個主體”和計劃性上,這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中國的公有制經濟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有制經濟一樣,采取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但是由于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方式和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水平的特殊性,中國的公有制并沒有采取蘇聯那樣的單一的公有制,而是實行了公有制為主體、其他所有制共存的形式。實行公有制為主體,決定了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而允許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則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和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在分配形式上,中國社會主義也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在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總原則下,保留了民族資本家的股分紅利、個體勞動者的自我勞動和自留地所得等非按勞分配的形式。實行按勞分配,體現了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的社會主義原則,從而與按資分配的剝削制度根本對立;允許非按勞分配形式的存在,則符合中國的生產力狀況和社會主義所有制狀況,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實行計劃經濟,是傳統社會主義與傳統資本主義的重要區別,有利于減輕和避免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隨著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建立,中國經濟的計劃性也得以確立。計劃經濟,有利于在特殊的情況下集中人力武力財力和進行宏觀調控,也是在一定條件下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重要體現。中國的“一五”計劃的建設成就即是證明。但是,同樣由于受到蘇聯的影響和囿于對傳統社會主義的認識,中國也一度向單一的公有制和按勞分配過渡,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運動,并且逐漸形成了長期存在的單一的計劃經濟。這種局面,不但破壞了生產力,阻礙了社會的發展,而且限制了企業的活力,影響了人們的積極性,也影響了社會主義的形象,因而成為中國改革的必破之冰。
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制度,是通過一系列的文化事業的發展方針、政策體現出來的。其中,最為突出的、最為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中的指導地位。首先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標志和基本原則,在這一點上中國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是一致的。而作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并列為指導思想,又是中國文化的特色。在此基礎上,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要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等,是中國教育、文化發展的基本指針。同時,中國共產黨充分發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政治優勢和思想優勢,最大限度地團結全國人民,充分調動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并與以“為人民服務”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相結合,共同推進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文化體制,極大地改變了中國文化教育落后的局面,促進了中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不過,由于國內外環境的影響和認識上的偏差,中國的文化教育也受到政治運動的沖擊,出現了意識形態化的傾向,給中國文化教育的發展和精神文明建設造成了極大的損失乃至災難。
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社會主義體制,既具有中國特色,又具有蘇聯模式的基本框架,因而既是中國探索自己道路的起點,也是中國發展道路曲折的淵源。
[責任編輯 常偉]
The Soviet Model and the China’s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QIN Zheng-we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China)
The Soviet model is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mode with the highly centraliz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during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ist explore.Since the Soviet Union is the world’s first socialist countries, and therefore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model has a great template type and orientation. Coupled with the gradual expansion of the Soviet Union’s Congress Party, this model is inevitable in the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Although China’s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is a necessary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but it carried out the more obvious the world socialist rapid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the Soviet model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and therefore on this basis established 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the system, Thu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the system, both with distinc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has serious drawbacks, and caused a double impact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
Soviet model; China;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socialist system
F325.7
A
1672-1217(2017)01-0097-08
2016-11-17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3BKS02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研究;
山東省社科基金項目(14CXJJ21):習近平國家利益觀研究。
秦正為(1973-),男,山東陽谷人,聊城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世界共運研究所、廉政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學博士,中共中央編譯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