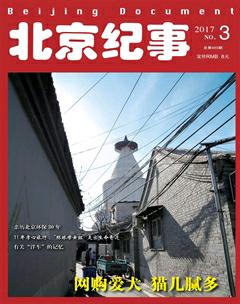卅年聚首
我是1977年插隊后進入海軍后勤部汽車修理廠,1981年離開的,大概在離開的10年左右我回去過一次,以后與那里失去聯系,偶爾還能聽到關于汽修廠同事的片語只言。

我在汽車修理廠唯一的好友,是多年來頻繁接觸的古垣(因有段時間我們住在一個小區),后來我搬離這個小區,接觸少了。
事情因古垣而起,去年7月份我的第一本著作《圓明園景觀志略》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拿到書后給古垣送書時(古垣為此書鐫刻極其精美之印章),他當時并沒有任何得病的跡象,我與他聊了有兩個小時之久,沒想到那次相別,古垣竟然住院了。我得到這個消息時,他的肝已經長了10厘米的瘤子,因為肝上沒有神經,感覺不適時已經是癌癥的晚期了。我到醫院去看望他,第一次去時他愛人告訴我,垣子的癌細胞已經擴散到肺,只是瞞著他。看到最好的朋友受病魔的肆虐,我束手無策,欲哭無淚,我多次鼓勵他頑強地戰勝病魔。他曾告訴我,倘若他能活著出去,一定與我看看祖國的大好河山。我鼓勵他,等著接他出院。
然而現實是殘酷的,僅僅3個月的時光,古垣就撒手棄我而去,為此我失聲痛哭。我責怪自己沒有在垣子生命的最后時刻守在他的身旁,送他最后一程,這是我終生的遺憾。我為古垣唯一能做的就是祭奠他的在天之靈,念我與他30多年兄弟情誼。我是接到噩耗的當天,懷著悲痛的心情開始寫作的,古垣的音容笑貌歷歷在目,多年來的友誼傾注于筆端,淚水伴著我寫完祭文,洋洋五千言,記述了我與古垣的友誼與追求……參加了古垣葬禮后,直至將古垣送到他插隊附近的陵園。我是海軍汽車修理廠的唯一代表,直至古垣入土為安。
我將《祭古垣》一文,網傳給《北京晚報》鄭勇編輯,很快便以《老友古垣》的題目刊登在12月14日的62版。發表后我是在孔祥澤老先生家看到的,孔老告訴我,見到你寫的祭文,便剪下保存起來。我趕快拿出復印了幾張。
很快便接到古垣的愛人打來的電話,她看到了該文,并代表逝去的古垣感謝我。這是我為古垣應該做的,我想讓更多的人了解古垣,了解古垣熱愛的祖國的傳統文化及他短暫的一生對篆刻藝術的癡愛;了解他為人的熱情忠厚以及對文化生活的向往……
我突然接到汽車修理廠原好友徐社的電話,我們有30年沒有聯系了,很是吃驚!他說是通過報社得到我的聯系方式的。是他最先見到紀念古垣的文章,文中提到海軍后勤部汽車修理廠,他深知作者和逝者肯定是一起參加工作的人,可是金鑒是誰?古垣又是誰呢?這兩人與參加工作的人姓名對不上號(金鑒、古垣均為筆名),因此反復給報社打電話,終于在一個星期以后與編輯聯系上,才得到我的聯系方式。
其時,海后汽修廠的職工,正在聯系30年后的聚會,而古垣的去世更促成了這次30年后的聚首。時間選在臘月十三(1月7日),不知為何那天紛紛揚揚地下起了雪,難道是老天叫我們借著紛紛揚揚的雪來懷念戰友——古垣嗎?這難道是巧合嗎?我想只有天知道……那時歡蹦亂跳的我們,如同初生牛犢,剛剛走上工作崗位,對人生充滿著希冀。1977年全國第一次高考舉行,我們的戰友中有黃艾和另一位男同學考上了大學,我們高興地歡送他們的場面,時至今日依然記憶猶新……
我們是汽修廠的新一代,用雙手去八達嶺山溝搬石頭,運回工廠擴建廠房,辛勤的汗水換來了新的廠貌。我們設計汽車大修的流水線,安裝天車,調試設備。總之創業的過程是十分艱苦的,但是我們沒有一人退縮……
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少職工逐漸地調回了城內(第一批招的職工幾乎都是海淀區八大學院的子弟),從此我們便失去聯系,在各自的崗位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不少人在工作上取得了優異的成績,為祖國默默無聞地工作,貢獻著智慧與力量!
30年啊!人生有幾個30年呢?我們由滿頭青絲到兩鬢染霜,女同志大多退休在家,男同志已經接近退休的年齡。不少人已經有了第三代,成了祖父母輩的人了。接到聚會的電話,深感組織者用心良苦,不僅是通知人參加,更重要的是尋找這些分散在京城沒有任何音信的戰友,實在是難上加難啊!好在組織者是我們其中的一員,他用不懈的耐心,終于通知到30余位戰友。為何稱戰友不稱朋友呢?經過“文革”的人,似乎稱朋友不解氣,不能彰顯出我們這代人經歷過的共和國歷史上的坎坷。
聚會選在香山以東紅旗村的新開地食府,汽修廠的戰友陸續到來了,見到時每位戰友的臉上,竟然是一時的驚訝!你是馬桂茹!你是李秀珍!啊!變化多大啊!有些朋友見面不僅僅是握手,而是張開雙臂熱烈地擁抱!是啊!30年啦,歲月的滄桑已經深深地刻在我們的頭顱,而古垣已經離我們而去,大家深深感到聚會來得晚了些,又慶幸今天終于聚首了!接著便是述說著離別之情,回首30年前在汽修廠度過的我們人生那段最美好的時光。可以自豪地說,我們把青春獻給了汽修廠,獻給了祖國的軍工事業。雖然有些人一時還記不起名字,但是看到那熟悉的面容,便會勾起我們年輕時的思索,當一報出自己的名字,便喚醒年輕時的記憶……
李英瑞是我們中的大哥,這次是由他做東把大家召集在一起,為此他付出了不少辛苦,大家感謝他,為大家辦了件大好事。他首開祝酒詞,得到熱烈的贊揚。
我見到現在汽修廠的廠長,我們鉗工班的王志剛,我對他的印象很深,聊得很投機。他向大家發出邀請,春天杏花開了的時候,邀請我們回家看看,大家欣然接受了邀請。將我剛剛從海淀史志得到的書——《圓明園景觀志略》送給他,書的扉頁上寫著:獻給海軍后勤部汽車修理廠的戰友們!并署名,在書首頁上鈐蓋了古垣為我鐫刻的八枚閑章與大家共賞,閑章是:千古絕唱、氣壯山河、系日求索、敝帚自珍、金鑒鑒賞、金鑒珍藏、天穹齋、鏡心八方閑章。
聚會的戰友大多知道古垣已經不在了,有些人是剛剛知道的這個消息,都為他過早地離開我們而嘆息!吳洪燕還回憶起在西三旗花卉市場見到古垣的情形,古垣也和我談起過那次意外的見面。北京如此之大,30年來我們幾乎就沒有見面的機會,可能是我們總走一條線路,日復一日地重復,因而沒有交集,雖然居住在同一座城市,竟然沒有見面的機會。

干杯!
飯菜是豐盛的,是30年來的手足情誼、戰友之情,使得大家竟然忘記了菜肴的可口,每個人的嘴都在述說著,臉上洋溢著豐富的表情,或是打聽著其中沒有來的人的情況,溝通與交流是幾個小時的主流……原來豪爽的人依舊豪爽、原來剛烈的人依然剛烈、原來感情細膩的人依然細膩、原來滔滔不絕的人依然如故。大聲地說話、大口地喝酒,我們的性情原來如此豪放,我們的命運原來如此息息相關,我們的心曾緊緊地依偎在一起……
我們雖然經歷過那場“史無前例”的動蕩年代,甚至沒有學到我們應該學到的知識,但是我們這代人有遠大的志向,在實踐中補充我們理論中的不足,難道不是嗎?祖國今日的繁榮昌盛是與我們的努力分不開的,我們依然是祖國各個行業的棟梁。正如杜甫所說的“安得廣廈千萬間”的廣廈是由我們這代人撐著,我們創造了共和國歷史上曾經沒有的輝煌,我們用辛勤的雙手和智慧,迎來了祖國歷史上的昌盛時代,高科技的衛星對接,中國人讓世界刮目相看。由我們開始,我們是祖國富強的鋪路石子……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最讓人痛快的是嘴,是溝通、是交流、是愉悅,我們其樂融融,攝影師手中的相機不時地把我們的風姿定格在數碼相機里。為了記載這30年后的聚首,攝影師竟然拍了7張,為這難得的聚首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愿珍重我們的友誼,保重我們的身體,我們要多活幾年,好好地享受祖國昌盛給我們帶來的福分。
(編輯·宋冰華)
ice705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