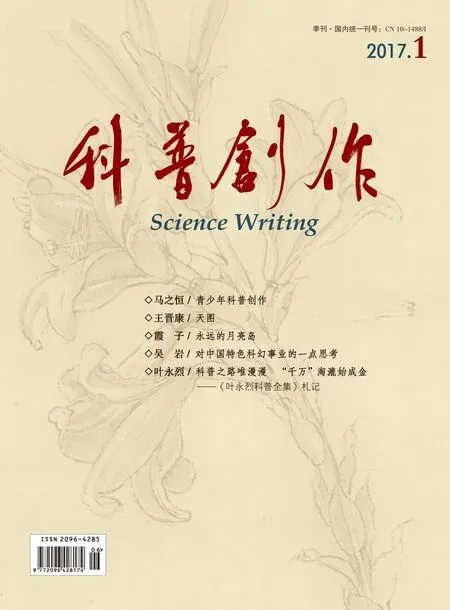他鄉布道 異國傳經
——洋教授戴偉在中國的科普之路
馬俊鋒

戴偉,原名David G. Evans,英國人,化學教授,畢業于英國牛津大學,獲博士學位,曾在英國埃克塞特大學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后到北京化工大學進行合作研究,現為北京化工大學特聘教授。由于思維的慣性,初次聽到“戴偉”這個名字時以為應該寫作“大衛”或“戴維”等帶點兒洋味兒的譯名,當看到名片上寫道“戴偉”二字時以為是寫錯了。看來,戴偉當時可能對中國文化已經比較了解,所以才有意識地給自己起了一個很中國化的名字。
戴偉熱心科研,成果豐碩,先后在國內外化學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200余篇,被英國皇家化學會聘為會士,并被選為英國皇家化學會北京地區分會主席,2017年又被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評為“2016年度中國石油與化工行業影響力人物”。他還熱心于中英兩國的科技合作交流,曾獲國家外國專家局頒發的“友誼獎”(2001年)和“功勛外教”(2014年)、國家“國際科技合作獎”(2005年)、英國皇室頒發的官佐勛章等諸多榮譽。最值得一提的是,除科研與中英科技合作交流外,戴偉還熱心于中國的科普事業,勤勉于向中國青少年普及化學知識,致力于培養學生們求真的科學精神和嚴謹的科學態度。2014年戴偉被聘為“北京化工大學知名學者科普報告宣講團”組員,2016年又被聘為“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科普聯盟”專家委員會委員。在網絡搜索引擎中輸入“北京化工大學戴偉”后,可以查到許多相關新聞報道和照片。同一個形象,胖胖圓圓的身材,短短的黃白的頭發,戴著護目鏡,穿著白大褂,頻繁出現在不同的地方,或北京、或安徽、或內蒙、或山西,大江南北,戴偉到處給青少年學生講授化學知識,演示化學實驗,向孩子們心中播撒科學的種子。2016年12月,戴偉被中國科協主辦的“典贊·2016科普中國”活動評選為“科普中國特別貢獻者”。由于在科普事業上的杰出貢獻,戴偉還受到過溫家寶、劉延東等中國國家領導人的表彰。
一個洋教授,何以和中國結緣,又在中國的科普之路上走出了這諸多精彩,獲得了那么多榮譽呢?
鐘情化學,緣自試驗
戴偉并非出生在化學世家,祖父是一名煤礦工人,生活在威爾士,后遷居到英格蘭的伯明翰,父親是一名初中數學老師,母親及其他家人也沒有從事與化學相關的工作。戴偉初次接觸到化學實驗是在學校的化學課堂上。十一二歲的他看到了化學老師的精彩演示后,便對化學實驗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運用學習到的有限的化學知識,戴偉開始自己做實驗,越做興趣越濃。漸漸地,化學課程上的實驗已經滿足不了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了,于是他就開始自己購買相關的儀器和化學藥品在自家廚房里做了起來。由于經常把廚房弄得又亂又臟,父親就把家中花園里的一個小棚子騰出來,專供他做實驗用。
有了自己獨立的小棚子“實驗室”后,戴偉更加沉迷于化學實驗了,放學后、周末、假期,只要一有空閑時間,他就把自己關在小棚子忙碌起來。在很多人看來,化學是無聊的、危險的,化學分子式很復雜,化學物質有毒有害,化學反應猛烈駭人,而在少年戴偉的眼中,化學是有趣的,能給人帶來無限快樂。
化學實驗中兩種不同的物質發生反應,可以產生新的物質,有時還會伴著猛烈的反應,這是戴偉對化學癡迷的原因。當時也有一些同學和他有共同愛好,他們時常會聚在小棚子里一起做實驗。在戴偉購買的化學藥品中,有一些危險性較高的物品,如腐蝕性極強的濃硫酸、易燃易爆的金屬物質等。十幾歲的少年,對各種新生的、有刺激性的事物充滿好奇,化學實驗恰恰迎合了他們的好奇之心,但因為年紀尚輕,化學知識有限,對化學實驗的危險性認識不足,所以也常常會有爆炸、起火等實驗“事故”發生。幸運的是,這些實驗“事故”并沒有引起大的火災。父母對此有些但心,雖然并沒有公開反對他做實驗,但也不很開心。戴偉在談及少年時的這段往事時說:“當時只掌握了一點點化學知識,知道如何做實驗,卻不知道實驗有多危險。現在掌握的知識多了,知道了危險,所以有些當時做的實驗我現在不敢做。”
進入高中后,隨著化學知識的增加,戴偉可做的實驗也越來越多,同時也遇到了人生中的良師。當時英國高中的課程比較少,只有化學、物理、數學三門課,上課時間非常短,學生有許多空閑時間可以自由支配。戴偉的高中老師看到他對化學實驗有濃厚的興趣,就讓他在課余時間用實驗室的儀器做一些自己喜歡或想做的實驗。這樣,戴偉就有大量的時間可以用來做實驗。化學老師開的這一“小灶”,仿佛給戴偉求知的小船掛上了帆,使他加速駛向化學的汪洋大海。
喜歡上化學實驗后,戴偉很早就決定將來上大學一定要申請化學專業。濃厚的興趣,勤奮的鉆研,反復的實驗,為他打下了堅實的化學基礎,并使他順利考上了英國最知名的高等學府—牛津大學。進入大學后的戴偉更是如一塊投入水中的海綿,肆意地汲取著化學知識的養分。英國大學本科的課程設置與中國、美國等國家不同,比較傾向于追求專業的深度。就牛津大學化學專業來說,學生在大學一年級時有1/4的課程是數學,其余3/4的課程全部是化學,大學二、三、四年級基本就不再學其他課程,全部都是化學專業課程。當時牛津大學每年有200多個化學專業的本科生,分布在30多個學院里,戴偉所在的學院每年級有8個化學專業的學生。學院里的輔導課堂上老師只需面對2個學生進行授課。戴偉說,當時老師在課堂上并非只講授化學知識,更多的是講授思考問題、分析問題的方式和方法。每次課上,老師先提出問題,然后學生針對問題進行討論,并試著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種“授人以漁”的教學方式,對戴偉日后的工作和教學有很深的影響,同時也使他在學術的山峰上越攀越高。1980年,戴偉獲得牛津大學學士學位,1984年又順利博士畢業,獲牛津大學化學博士學位。1984—1985年在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做了一年的博士后,隨后進入英國埃克塞特大學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
結緣中國,始于少年
戴偉少年時有兩個愛好,一個是對化學感興趣,另一個是對中國感興趣。當被問及為何喜歡中國時,他略顯驕傲地說:“已經過去幾十年了,真的記不得當時喜歡中國的理由了,但這一愛好和喜歡化學的愛好一樣,一直堅持了下來,直到現在。”
戴偉年少的時候,美蘇爭霸進行得如火如荼,中國也正處于風雨如晦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基本沒有什么人到英國留學或生活,所以當時戴偉的生活環境中很少有中國人出現。或許是冥冥之中的緣分,從來沒有接觸過中國人的戴偉在姥姥家里看到了一份中國出版的英文雜志—《北京周報》。《北京周報》是一份英文新聞周刊,1958年3月創刊于北京,主要報道中國的政治經濟現狀,介紹中國政府對內對外的重大方針政策,是當時中國進行對外宣傳的重要刊物之一。戴偉在談到《北京周報》時說:“這是一份小雜志,紙很薄,每年訂閱,從中國駐英國的大使館寄來,每個月都會收到。”戴偉認為這個雜志傳遞的信息顯示當時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比英國人還高,這顯然是不對的。不過他并沒有因此對中國產生什么不好的印象,反而興趣更濃。對他來說,中國就像化學一樣,充滿了神秘和未知。
大學時代,戴偉在牛津大學校園內雖然見到過一些赴英國留學的香港人的身影,但并沒有什么接觸,到了攻讀博士學位時,才第一次正式接觸到中國人—與戴偉同在一個實驗室學習的香港人賀子森(現任香港大學副校長)。1981年,受賀子森的邀請,戴偉第一次來到香港過中國最隆重的傳統節日—春節。那是戴偉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他很是興奮,當站在落馬洲瞭望臺眺望遠方時,少年時代讀到的關于中國的種種描述在他心頭頻頻閃現,那充滿著神秘和未知的國度,就在眼前。
1987年,戴偉受邀參加在中國南京召開的第25屆國際配位化學會議。當時,他親眼見到的中國與年少時在雜志中讀到的中國有諸多錯位和落差,但戴偉依然興趣很濃,想在會議后到處轉轉。原本會議主辦方在會后安排了游玩項目,可戴偉不打算跟著由許多外國人組成的旅行團一起走馬觀花似的游覽,而是想一個人到處走走轉轉,了解一下真實的中國。戴偉到南京參會時,他攻讀博士學位時的香港同學賀子森已經到新加坡國立大學工作。巧合的是,與這位同學認識的一個來自中國的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生,其父親正是該次國際配位化學會議副主席、南京大學化學系副主任陳懿教授。得益于這位同學的牽線搭橋,戴偉受到了陳懿教授的熱心幫助。會議結束后,戴偉向陳懿教授表達了想單獨出游的想法。聽到戴偉不會說中文,也不認識漢字,一個人出行很不安全,出于安全考慮,陳教授找了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科院上海有機所)、蘇州大學、杭州大學等幾個地方的同行幫忙照顧,還專門花了一下午時間給他安排游玩路程和食宿。陳懿教授的熱情讓戴偉很受感動:“陳教授學術水平很高,當時是南京大學化學系主任、知名學者,而我只是一個年輕的化學老師,最主要的是作為會議的主辦者,陳教授當時非常忙,可他還是抽出一下午時間給我安排好住宿,這讓我很感動,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國人是那么熱情。”在陳懿教授的幫助下,戴偉順利實現了游歷上海、蘇州、杭州等地的計劃。
戴偉知道,少年時在《北京周報》上讀到的中國并非真實的中國,那只是出于宣傳需要,真實的中國并不是那個樣子。那時的中國正處于改革開放初期,經濟改革也只處于起步階段,商業氛圍尚未形成,企業員工普遍沒有服務意識。當時,給戴偉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個漢語詞就是“沒有”。在上海,戴偉住的是中科院上海有機所的招待所,離市區繁華地段有些距離,能吃飯的地方不多,而且晚餐供應時間是五點至五點半。這對于初到中國的外國人來說,用餐時間顯然有些過早。當戴偉以為自己去吃晚餐的時間還挺早時,食堂已經什么都沒有了。所以問服務員有什么吃的時,得到的回答都是“沒有”兩個字。提及此,戴偉還講了一個當時在來華外國人中間普遍存在的情況:當時來華的外國人在中國學會的第一個漢語詞匯不是“你好”“謝謝”“再見”等之類的日常寒暄語,而是“沒有”,問有沒有吃的、有沒有房間,得到的回答最多的就是“沒有”!還有一件事情也讓戴偉印象深刻。在杭州西湖租了一輛自行車游玩時,他遇到了兩個熱心的粗通英語的年輕人。連說帶比畫,三人之間勉強可以交流。這兩個年輕“導游”花了大半天時間陪戴偉游覽西湖,給他講解了許多關于西湖的有趣故事和歷史知識。為表示感謝,戴偉邀請他們到自己下榻的酒店吃晚飯,到酒店后卻被告知兩個年輕人不能進入。在中國,這些中國人自己經營的四星、五星級豪華酒店卻只對外賓開放,只收外幣或外匯兌換券,拿著人民幣的中國人卻不能消費,當時這讓戴偉很不理解。不過,給戴偉印象最深的還是中國人的熱情,不管是學術造詣深厚的陳懿教授,還是西子湖畔陌生卻熱情的年輕“導游”,都讓他感動。從那時起,戴偉決定以后要經常來中國,并開始學習中文。
自1987年參加過第25屆國際配位化學會議后至1996年到中國工作的十年間,戴偉幾乎每年暑期都會到中國來,或參加會議,或在幾所大學做學術報告。戴偉最初學習中文時比較有趣,他每次來中國之前,都提前一兩個月拿出字典、磁帶開始學習中文,以便到中國后可以應用,但回到英國后又疏于復習鞏固,就慢慢忘掉了,第二年同一時間又會重復這一過程。1994年,戴偉結識了北京化工大學的段雪老師,并開始進行合作研究。1996年,戴偉接受了北京化工大學的邀請,辭去英國埃克塞特大學的工作,正式成為北京化工大學的一名老師,并定居北京。談及當時的決定,戴偉說:“如果1996年是我第一次來中國,我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但我是從1987年到1996年每年都到中國來,我看到了中國的發展變化,雖然發展有些慢,不如現在這么快,但卻有巨大的發展潛力。我覺得這對我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如果我不來中國,不來北京,也許我會后悔的,所以我決定來中國。”戴偉的決定在其英國朋友和同事眼中稱得上是“瘋狂”的舉動。當時中國的改革開放雖然也進行了一些年,但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并沒有太大變化,國外媒體及科學界并不重視中國。而且現實情況也是如此,那時戴偉在北京化工大學的工資僅有在英國時的1/10,工作條件和科研水平也不及埃克賽特大學。戴偉的一些英國朋友對他的舉動很不理解。“有禮貌的說我勇敢,不太禮貌的就說我瘋了。”戴偉的回答是,“你不明白,中國的發展前途無量,下次你來看我時,就會明白了。”戴偉還開玩笑地說:“一年一次回到英國,不會感覺到它有什么大的變化,而只要幾個月,甚至十幾天不在北京,回北京后就會感到又有了新變化。”成為北京化工大學的老師,戴偉感到很開心,他說:“剛來的時候,段雪教授的實驗室里只有兩個年輕老師,我是第三個,現在段雪教授的實驗室有40多個人。他們都比我來得晚。”在中國定居后,戴偉生活在漢語環境中,漢語水平進步很快。一轉眼20年過去了,現在他的漢語已經基本褪去了外國味,非常流利,像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
戴偉很喜歡中國的春節,第一次到中國的時候就剛好是春節。聽朋友說中國的農村很有傳統春節的氣氛,戴偉就經常跟朋友一起到中國的農村過年。春節期間,在外打工的人都回到家里,看到一個外國人在村里過年很是新奇,于是就表現出了十二分的熱情,經常是東家請完西家請。戴偉在村子里一家接一家地吃酒,很是滿足。戴偉坦言:“其實他們并不會因為招待我而顯得麻煩,我去不去他們都一樣,都是要吃那么多肉,喝那么多酒。”絲毫沒把自己當外人,儼然就是中國農民中的一員。他因此結識了很多農民朋友,也經常接到來自這些農民朋友的邀請電話:“什么時候再來呀,我們一起喝啤酒!”戴偉曾跟朋友去過安徽的一個小山村過春節,這個小村子全村一共才300多人,村里人在生活當中也從未見過外國人,所以聽說村里來了外國人,幾乎整個村子的人都跑去看他。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還瞪大了眼睛看著他說:“你就是孫悟空吧?”
邂逅科普,一往情深
早在英國埃克塞特大學工作時,戴偉就曾從事過化學科普活動。英國中學生的課程比較少,自由時間很充裕,所以學校會經常組織學生到附近的大學聽課,戴偉也常常接待這樣的學生,給他們講授化學知識和演示化學實驗。來到中國后,戴偉最初主要是從事化學研究和教學工作,一些偶然的機會使戴偉走上了化學科普之路,一往而情深。
1999年,中國實施大學擴招政策,當時各高校學生人數急增,面對這一情況,如何培養良好的校園文化成為各大學考慮的重要問題,北京大學也不例外。北京大學化學化工學院在考慮學生人數急增后的校園文化建設時認為,北京大學的很多學生將來很可能成為國家的管理人員,他們有必要了解化工、認識化工、知道化工對人類的意義,因此要求開設化學公選課,讓化學成為校園文化的一部分。最終這一任務落在了科研一線的寇元教授頭上。2002年,寇元教授開設了《魅力化學》的公選課,邀請許多科研一線的知名科學家來給學生講授化學。2004年9月,北京大學化學化工學院與國際知名企業德國巴斯夫集團開展合作,將巴斯夫的科普經驗引入到《魅力化學》的課程中,開辦了《北京大學化學化工學院—巴斯夫魅力化學》課,邀請許多知名科學家主講,戴偉當時就是被邀請的科學家中的一員。在給北京大學非化學專業的學生上了一堂精彩生動的化學實驗課后,戴偉喜歡上了這個課程,此后經常到《魅力化學》的課堂上給學生們講授化學知識和演示化學實驗。
在英國埃克賽特大學工作時教當地的中學生化學也好,在北京大學《魅力化學》課堂上為非化學專業的學生上化學課也好,這些都只是戴偉走上化學科普之路前的“小試牛刀”,真正投入大量精力和時間從事化學科普,是從2011年開始的。這一年有兩件事情促使戴偉走上了化學科普的道路,其一是戴偉的英國朋友Helen Boyle邀請他給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的學生上化學課,其二是英國皇家化學學會提供了1000英鎊的公益活動資金。
Helen Boyle原本是一位老師,在英國工作,女兒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留學。他來北京看望女兒時偶然發現,中國的打工子弟學校的辦學條件很差,于是就產生了幫助他們的想法。Helen Boyle辭去了英國的工作,并在英國申請成立了一個慈善會(Migrant Childrens Foundation,MCF),然后來到中國的打工子弟學校,幫助這些學生學習。剛開始只是教授英語,認識戴偉后,Helen Boyle就邀請他為打工子弟學校的學生們講授化學知識。恰好,2011年是國際化學年,英國皇家化學主席David Phillips教授會給每個分會1000英鎊作為舉辦國際化學年紀念活動或公益活動的資金。作為英國皇家化學會北京分會的主席,戴偉利用這些錢買了許多藥品、試劑和實驗設備,開始給打工子弟學校的學生上化學實驗課。戴偉在打工子弟學校的化學實驗課被英國皇家化學會評為當年所有分會活動中最優秀的三個活動之一,并獲得了1萬英鎊的支持。從此戴偉就把給打工子弟學校的學生上化學實驗課當作一個長期活動堅持下來。
只要有時間,戴偉每個月都會去北京周邊的打工子弟學校給學生們演示化學實驗。每次化學實驗課大約一個半小時,但課前準備器材,配制藥品就得花去一個多小時,課程結束后收拾器材,也需要同樣多的時間,再加上往返搬運器材和路上的時間,所以每次活動都要花費大半天的時間。因為經常去給打工子弟們上課,許多學生都記得戴偉,每次只要他一下車,原本玩鬧的學生就都向他聚攏過來,戴偉就用他流利的漢語和學生們你一句我一句地調侃。戴偉就這么被學生簇擁著,向教室走去。
進教室后,戴偉就在學生志愿者的幫助下開始準備實驗器材,配備實驗藥品。作為一個科學家,戴偉時時表現出了認真細致的工作態度和嚴謹的做事風格。他給學生們準備的實驗器材全部都是塑料的,以防學生不小心打破實驗器皿割破手指,另外還給他們準備了白大褂、眼鏡等,實驗中需要的東西,一樣也不能少。實驗中,他不僅讓學生體驗到了化學實驗的樂趣,還要培養學生樹立嚴謹的科學態度,引導學生養成積極思考的習慣。比如,實驗中他會拿出一個“空空如也”的容器問學生:“這個容器是空的嗎?”學生有的回答“是”,有的回答“不是”,戴偉就引導學生說:“不要輕易下結論,我們來驗證一下!”于是就拿一個帶火星的木條放進容器,看到木條迅速燃燒起來后又說:“木條迅速燃燒起來了,說明里面是什么?”學生思考一下異口同聲地回答:“氧氣!”在這一問一答中,學生們就會慢慢形成嚴謹的做事態度和積極思考的習慣。
戴偉不僅自己熱心科普,還主動帶研究生參與科普活動。或許是來中國太久了,他對中國大學生的就業情況非常了解。談及帶研究生做科普時,戴偉說:“讓研究生做科普也是雙贏的,因為現在的學生畢業找工作時,一般的用人單位對你研究什么方向不感興趣,他們不需要這樣的技能,而是其他的技能,比如溝通能力、團隊協作能力、協調能力等。學生通過參加科普活動,也培養了許多用人單位需要的技能。除非要做研究工作,否則一直在實驗室也不可以。”戴偉的科普團隊以北京化工大學里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研究生為主,包括碩士、博士,甚至還有學校的教師。每年新生開學時科普團隊都會招納新隊員,將那些對科普感興趣又有意愿參與的學生納入到團隊中來。有個別科普隊員畢業后留校了,成為北京化工大學的教師,但仍然愿意留在科普團隊中跟著戴偉繼續做科普。
2014年10月,戴偉被聘為北京化工大學知名學者科普報告宣講團成員,開始赴全國各地開展化學科普活動。他親自設計了獨特的《雙氧水豐富多彩的化學反應》,向中學生演示變色反應、時鐘反應、振蕩反應和歧化反應等五組十個化學實驗的神奇效果。奇妙有趣的實驗,通俗易懂的講解,循循善誘的引導,再加上戴偉風趣幽默的語言和憨態可掬的容貌,給各地聽報告的中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極大地激發了他們對學習化學的濃厚興趣。每次兩個多小時的報告中,現場座無虛席,聽眾掌聲不斷。戴偉不僅給學生講化學,還給一些中學化學老師講化學。2015年,北京化工大學開始舉辦暑期化學教師研修班。在每一期的研修班上,戴偉用嚴謹的實驗態度和方法、有趣的化學反應,為中學化學教師做了一堂堂生動的化學講座,在化學教學方法改革與創新方面給中學化學老師們帶來了許多啟發。戴偉也因此收到許多來自全國各地中學教師的熱情邀請,希望他能走進這些學校為師生做報告。
除在學校給學生做科普外,戴偉還積極組織科普沙龍活動,邀請各個領域的科學家給社會人員做科普講座。科普沙龍活動有一個很漂亮的中文名字“懂”,對應它的英文名稱是“Understanding Science”,由英國皇家化學會、英國物理學會和國際空間科學研究所北京分部合作主辦,每月一次,一般在五道口的橋咖啡館或三里屯的老書蟲咖啡館舉行。演講嘉賓由活動組織者邀請,一般外國學者居多,對象主要是一般公眾,純英語演講。活動形式很隨意,被邀嘉賓可以邊喝酒邊講,聽眾可以邊吃東西邊聽。內容主要是被邀嘉賓自己正在進行的科研內容:為什么要做這方面的研究,研究動機是什么,研究目標是什么,研究成果如何呈現,是短期內就可以對社會發展有貢獻,還是會促進科學理論知識的發展等。每次活動內容都不同,涉及納米材料、火星探索等許多領域。嘉賓演講一般約30、40分鐘,之后是互動環節,大家針對演講內容自由提問,嘉賓一一回答,20分鐘左右。對活動感興趣的人在活動結束時可留下自己的郵箱,方便下次活動時通知。因為是在咖啡館,又是純英文演講,所以無形中限制了受眾的規模。但也正是因為這樣,科普的效果非常好,不大的咖啡館常常座無虛席。聽眾邊品味美酒咖啡,邊聆聽科學知識,咖啡美酒的醇香縈繞鼻尖,趣味橫生的科學知識流入耳膜,甚是風雅。
此外,戴偉還經常參加科技部、中國科協、北京市科協等單位組織的一些城市科學節、科技活動周、科學嘉年華等活動。
通過科普活動,戴偉在許多中小學生心里撒下了化學的種子,點燃了他們的科學夢。四五年前曾有一個小學生宋大有參加了戴偉的科普活動,并由此喜歡上了化學。隨后他自己就網購了許多化學實驗器材和藥品,開始自己做實驗。宋大有的母親經常打電話咨詢戴偉,問他一些藥品能不能買、是否危險。一次,宋大有買了許多金屬鈉,放在家里很危險。母親向戴偉咨詢后,就把這些金屬鈉全扔了。宋大有對化學實驗的熱愛和執著讓戴偉想起了少年時代的自己,那時的戴偉對化學也充滿了熱愛和執著。后來,戴偉就讓他進自己的科普團隊做了一名志愿者。現在,他已經是東直門中學的一名初三學生,個子高了,化學知識更豐富了,所以在戴偉的科普活動上,有些小學生以為他是研究生志愿者,甚至有人喊他“叔叔”,鬧出了不少有趣的事情。宋大有不僅在家里做實驗,還將化學實驗當作表演做給同學們看。每次學校組織的文娛活動中,其他同學都是表演唱歌、跳舞、彈奏樂器,他卻將舞臺當實驗室,把自己的實驗器材和藥品搬上去大方地做起化學實驗來。不難想象,宋大有未來很有可能從事與化學相關的工作,甚至有可能成為一名化學家,為人類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化學似乎是神秘莫測、復雜、甚至是非常危險的一門學問。戴偉從事化學科普,就是為了要消除大眾對化學的這種認識,樹立化學的正面形象。戴偉說:“化學危險嗎?先不說化學,就說開車,開車危不危險?如果你經常酒駕,開車當然危險,如果你很注意安全駕駛,開車一點也不危險。化學也一樣,化學危不危險,要看人是如何使用化學的。如果尊重科學,遵循自然規律,化學不危險,如果只注重經濟利益,無視科學規律,化學當然是危險的。”
近代以來,西方的傳教士不遠萬里來到東方,雖然是為了傳經布道,但也間接地播撒了文明,尤其是他們那歷千險而不悔的決心,涉萬難而不輟毅力,值得學習。如他們一樣,戴偉辭去了待遇豐厚、科研條件優越的英國大學教職,只身來到中國,到條件簡陋的打工子弟學校、到中國的大江南北,給學生們講化學,做實驗,傳播科學。通過科普活動,戴偉不但播撒了科學的種子,更傳播了一種求真的科學精神、一種認真嚴謹的科學態度、一種積極思考的科學思維、一種為興趣和夢想持之以恒的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