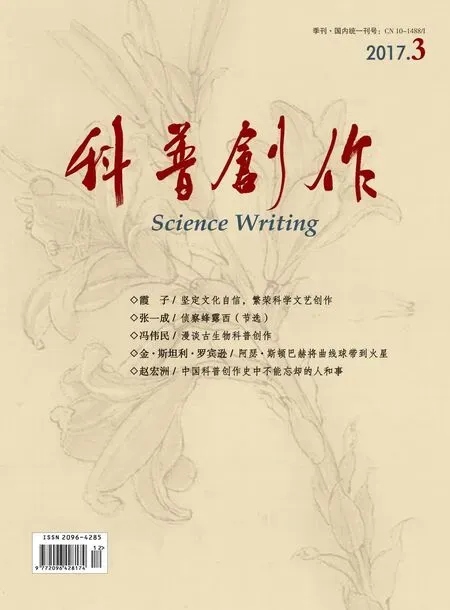《微觀世界歷險記》打磨記
晃眼間,《微觀世界歷險記》從首次出版到再版已4年有余,回首當(dāng)初的創(chuàng)作思路,也有了更多感悟。

圖1 《微觀世界歷險記》(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2015 年)
趕鴨子上架
5年前,《我們愛科學(xué)》的雜志主編讓我寫一套科普書,我欣然答應(yīng)。然而幾天后,她說,這套書是面向小學(xué)一二年級的。
我頓時傻眼,連連擺手,急忙推脫。
如何去給那么小的孩子講科普?我心目中那些無比有趣的科普知識,應(yīng)該適合小學(xué)高年級乃至初中生才是。
也許,正是最初的這種沒信心,讓我在寫這套書的過程中,時刻提醒自己:
注意難度!注意知識的難度!
注意使用到的每一個字,它是否生僻?筆畫是否過多?
注意使用的每一個詞,它對于孩子們是否陌生?
……
出版后,我從各種渠道了解到,這套書不僅既有小學(xué)低年級和高年級的讀者,更有不少初中生。而可能的原因,愚以為主要是兩點:故事和知識。
故事很重要
若是一篇1000字的文章,我們使用故事的手法進(jìn)行科普,則難度超大。因為你的故事還沒展開,字?jǐn)?shù)就用完了。
而對一套15萬字以上的科普叢書來說,如果都是科普知識而無故事,則孩子們難以從頭到尾讀完。
于是,使用故事便是一種較好的方式。就像一部吸引人的連續(xù)劇,很少有人看到一半,然后就不看另一半了。
毫無疑問,科普知識很有趣,但我們還需讓它更有趣,因為這不是20世紀(jì)70、80年代,只要是紙張上有字,大家都會去讀一讀。現(xiàn)代社會,不僅有各種有趣的動畫片,還有孩子們拿起就放不下的iPad游戲。
然而現(xiàn)實是,科普作者并非編劇出身,他們的大腦里全是一些有趣且自認(rèn)為很震撼的科普知識。你讓他們?nèi)ブv故事,他們會不屑。5年前的我,也這般幼稚。
幸運的是,當(dāng)年的我得到了《我們愛科學(xué)》編輯部多位前輩的很多反饋和指點,這讓我越發(fā)意識到:一個好的科普作者,他應(yīng)該同時是一個好編劇。
必須講故事,這又是另一種形式的趕鴨子上架。
《微觀世界歷險記》并非先有故事,才有里面的科普知識。那時的我,癡迷于原子世界的各種神奇,以及內(nèi)部蘊藏著的魔鬼力量。
而家里的兩歲男寶寶,他不喜歡大街上的藍(lán)色寶馬車,卻異常癡迷于滿身泥巴的挖掘機,原因很簡單:挖掘機大,很大。
喜歡大,這可能是人類的本能心理之一。而要把原子世界的這種巨大能量告訴孩子們,就要講核裂變和核聚變,就要涉及質(zhì)能轉(zhuǎn)換,以及電子、質(zhì)子、中子等知識,對小學(xué)生來說,這太難了。
幸運的是,我可以慢慢來,至少有15萬字可以掌控。
原子→原子核→質(zhì)子、中子→夸克……
無疑,這是一個從大到小的過程。
于是,故事就這樣定了,我要把5個主人公不斷地從大變小,先是跳蚤、螨蟲級別,接著是塵埃級別,再是細(xì)菌級別……就這樣一路變小,直到光子。
如果孩子們喜歡那種從地面不斷鉆入、直到地心的故事,顯然,他們一定也喜歡這種主人公不斷變小的故事——這是孩子們從出生就帶著的本能喜好。
故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我從事科普寫作11年,越發(fā)認(rèn)識到,文章的優(yōu)劣不在于你在其中科普了多少知識,而在于有多少讀者愿意沉浸在你的科普文章里。
百科全書式的書籍頁頁都是知識,但少有孩子在非需要時主動去讀它。《哈利·波特》里面哪怕只有極少的一部分涉及正確的科學(xué)知識,但因為孩子們愿意看,也看懂了,學(xué)會了,那么,僅從科普的意義上來說,《哈利·波特》就大于那些百科式的書籍。因為,《哈利·波特》的讀者太多了。
幽默有趣
幽默搞笑隸屬于故事的范疇,因其重要,分開來說一下。
不少家長聯(lián)系我,說他們的孩子特別喜歡“微觀系列”,前后看了幾遍,常常是看著看著就大笑起來。
家長的反饋讓人欣慰。而現(xiàn)在的問題是,如何讓科普故事變得幽默有趣?阿西莫夫給了我們答案。
在阿西莫夫的自傳中,他這樣說道:
“……我有這些想法是因為最近有一個好朋友,也是一個科學(xué)小說的作家,他的作品我非常的敬佩,在談話中,他很尷尬地提出一個問題:‘你的好主意都是怎么來的?’
“……我很誠摯地回答:‘我怎么得到我的主意?思考,思考,不斷地思考直到我?guī)缀跸胍獜拇翱谔鋈ァ!?/p>
“‘你也一樣?’他說,明顯地松了一口氣。”
是的,就是這樣。為了讓孩子們能一口氣讀完《微觀世界歷險記》,并在讀的過程中發(fā)笑那么幾次,記得那時的我,有時早晨一睜開眼,就會進(jìn)入構(gòu)思狀態(tài)。
舉一個文中的例子,為了穿插“動量守恒”這個知識點,我設(shè)置了這樣一個情節(jié),說的是師徒四人變成塵埃般大小,并在某個屋子里飄浮時:
家里塵埃太多,留在家里很危險,所以我們決定到野外去。
怎么出去呢?這是個問題。
八戒說:“窗戶在南面,我們可以背對窗戶,朝北面大口吹氣。然后我們就能飄向窗戶了。”
“嗯,這是一個好辦法。”
悟空說:“寒老師,我們還可以用雙手滑動空氣,像仰游似的,游向窗邊。”
“不錯,我們現(xiàn)在兩個方法一起用!”
于是,我們5人都拼命地滑動雙手,同時還大口地吹氣,不一會兒,我們5人開始慢慢地向窗邊移動……
突然,轟的一聲巨響,然后,我們幾個又開始慢慢地遠(yuǎn)離窗戶了。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八戒,你是不是放屁了?”小唐同學(xué)問。
“師父,我不是故意的。”八戒小心翼翼地說。
他一手緊緊拉著期盼富裕的千百萬果農(nóng),一手握著瞬息萬變的果汁飲料市場;也有人說,他之所以從當(dāng)年一個窮山溝的農(nóng)民走到今天,能夠走這么遠(yuǎn),這么成功,憑借的是他的才干,更靠著他樸實可敬的個人品質(zhì)。
八戒剛說完,就被小唐同學(xué)揪住了耳朵:“我們幾人大口大口地吹氣,吹得我們頭暈眼花。可因為你這一個屁,全白費了。請問你放的是大象屁嗎?”
“師父,你別揪了。”八戒低著頭,一臉慚愧,“如果下次還放,我保證會轉(zhuǎn)過身放,助大家一臂之力。”
“哈,咱們的飛行,又多了一種動力。” 悟空一臉高興。
……
通俗的知識
對于孩子們來說,不存在哪些知識適合普及、哪些知識不適合普及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找到一種合適的方式將它普及。
基于這種想法,在《微觀世界歷險記》撰寫過程中,遇到高深的知識時雖會有忐忑,但我更多的還是想辦法采用一些形象化的方式將其處理好。對于孩子們來說,如果一個段落讀起來沒有畫面感,這就不是一個好段落。
比如這套書中,下面的段落愚以為是很有畫面感的。
戰(zhàn)場上的聯(lián)絡(luò)兵——樹突狀細(xì)胞
樹突狀細(xì)胞是人體中一種非常重要的白細(xì)胞。平時,它們就像巡邏兵一樣,在身體各處到處轉(zhuǎn)悠。如果發(fā)現(xiàn)病毒,它們就會撲上去,吞掉這個病毒,并在體內(nèi)對這個病毒進(jìn)行加工,提取病毒的特征“碎片”,并把這個碎片扛在自己肩上,然后,它們開始長途跋涉,去尋找并聯(lián)絡(luò)可以對付這種病毒的T細(xì)胞。
科普的核心之一是通俗,而能有多通俗,這通常取決于我們愿意為此付出多大的代價。《微觀世界歷險記》中,其中有一冊專門講述身體內(nèi)的各種白細(xì)胞,如T細(xì)胞、B細(xì)胞、記憶細(xì)胞、自然殺傷細(xì)胞等。如果我只是簡單地查閱各種細(xì)胞的大概功能,然后就匆忙動筆寫,整個故事無疑將失去生動。顯然,如果認(rèn)識得不夠透徹,我就不可能在故事中大膽地駕馭它們,編織它們。萬一錯了呢?
有的科學(xué)知識過于復(fù)雜,需要很多的基礎(chǔ)知識才能看懂,此時,實在是難以用一種形象化的手法將其講述。沒有關(guān)系,跳過去便是。不在于這套科普書涉及了多少知識,而在于孩子們讀懂了里面的多少知識。
換個角度
給孩子們介紹科普知識時,如果都是采取說明文的形式,則孩子們接受程度就會較低。此時,如果可以的話,變換角度,讓科普的東西自說自話,則更吸引小孩子一些。比如《微觀世界歷險記》中,有一個標(biāo)題為《水分子的抱怨》的知識板塊,我是這樣處理的:
是的,我叫水分子。我有一個西瓜模樣的大腦袋,還有兩只蘋果一樣的小圓腳。丑?那是你眼光有問題!實際上,我可愛得就像米老鼠。不信你把我倒過來瞧一瞧,你看,我像不像米老鼠?
如果你們允許我說一句話,那么我只想說:“我很委屈!我們分子很委屈!”
你聽你聽——“動植物都是由細(xì)胞構(gòu)成的!”
有沒有搞錯?好像沒有我們分子什么事似的。但你可知道,所有細(xì)胞都是由分子構(gòu)成的!
……
綜上,就是《微觀世界歷險記》的基本寫作思路。回首這套書,它有不足和遺憾,當(dāng)初對故事的重視程度還不夠,這種從大到小的故事架構(gòu),其實還可以更引人入勝一些,當(dāng)然,這也會耗費更多的篇幅。而里面的科學(xué)知識,其實還可以再少那么一些些,密度不要那么大。
孩子們還小,匆忙地告訴他們更多,與讓他們對科學(xué)更感興趣比起來,后者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