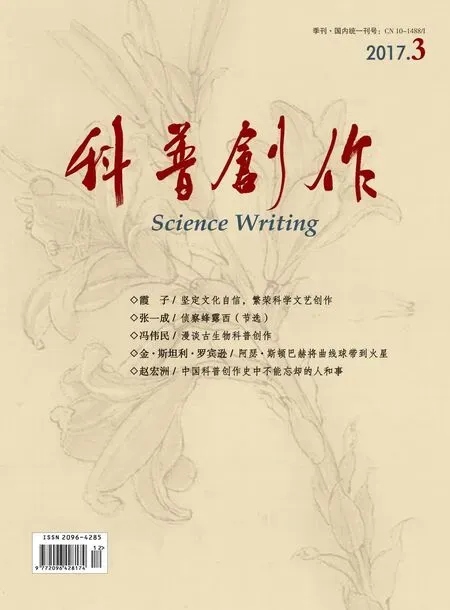中國科普創作史中不能忘卻的人和事
多年來,我陸續閱讀中國科普創作方面的資料。發現其中一些人物迄今在我國科普創作史上或聲名不彰或根本未提及,而實際上其在中國科普創作領域曾起過重大作用。這些有著不可磨滅貢獻的人或事引起我的關注。董仁威先生主編《科普創作通覽》一書時,作為編委的我曾去信告知我的意見,并列舉部分事例,董先生完全同意并在書中加以體現。但那只是匆匆瀏覽的結果,非常初步,在后來閱讀中我又發現了一些過去不了解的人和事,我感到這些人和事對于中國科普創作史來說是不能忘卻的。
近代自然科學起始于16世紀,即文藝復興運動后。16世紀末,利瑪竇等人初入中國,近代科學技術也隨之開始傳入中國。回顧中國近代科技的科普發展歷程,正是從明清傳教士開始,現代意義上的科普才真正起步,以徐光啟為代表的當時少數高層知識分子作為現代科普的創始人是不應被忘卻的。徐光啟作為明代著名科學家、政治家,畢生致力于數學、天文、歷法、水利等方面的研究,著譯頗豐。但人們似乎并沒有把他與科普創作聯系起來,一些資料中也查不到他在科普創作方面的貢獻。我以為,一部他和利瑪竇合作翻譯出版的公元前3世紀左右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的著作《幾何原本》,就應該確立他在現代科普創作史上的地位。至于《幾何原本》,我想引用愛因斯坦的說法,近代科學的發展依靠兩個基礎:實證方法和形式邏輯體系,愛氏說:“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的),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有可能找出因果關系(在文藝復興時期)。”徐光啟從近代科學基礎入手來科普,其眼光見識無疑是超時代的。《幾何原本》前六卷正式出版,馬上引起巨大的反響,成為明末從事數學工作人士的一部必讀書,對我國近代數學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翻譯是科普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沒有翻譯,也就沒有現代意義的科普。現代意義上的科普歷程就是以傳播普及西方近代以來的科學技術為主要內容的過程。也就是說,西學東漸過程中的自然科學部分的引進就是科普的過程,這個過程一直延續至今。比如1998年年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哲人石叢書”,就是把國外各種類型的科學名著引進中國,介紹給中國讀者,其中的策劃人是卞毓麟和潘濤先生。這套書立足當代科學前沿,彰顯當代科技名家,介紹當代科學思想,激揚科技創新精神,多角度、全方位地勾勒出一個多彩的科學世界。這套系列叢書的出版無疑是當今一項重大的科普工程。這套叢書的不同系列也多次在全國優秀科普作品評選中獲獎。
在西學東漸過程中,有這樣一個人憑借一己之力在做同樣的事,他就是科學編譯家杜亞泉(1873—1934)。
杜亞泉創辦了國內第一份完全由中國人創辦的科學雜志《亞泉雜志》,最早向國人介紹化學元素周期率,介紹當時化學新元素的發現和化學領域的新成就,并為新發現的一批化學元素確定了中文命名。他首創的化學元素中文名稱許多沿用至今。從20世紀初到30年代,杜亞泉在主持《東方雜志》編務和作為商務印書館自然科學編譯工作的主要組織者期間,翻譯出版大量介紹自然科學的文章和教材,使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自然科學方面書籍占到全國總數的近半,他還主編了《植物學大辭典》《動物學大辭典》等大型科技工具書,毫無疑問,杜亞泉應是中國科普的先驅者之一。遺憾的是回顧科普創作的資料中幾乎沒有看到任何有關杜亞泉的介紹。
在科普創作史上沒有提到的著名人物還有胡適。胡適(1891—1962)作為我國現代學術文化名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有著如雷貫耳的名聲。可他在我國科普創作史上的貢獻卻鮮見提及。過去在評價“五四”新文化運動時,雖然也提到“民主”和“科學”,但主要是從思想史層面上提到,如果涉及具體,更強調的是“民主”。而事實上,以陳獨秀、胡適為代表人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在當年掀起了科學大普及的高潮,其標志就是張君勱與丁文江的科學和玄學的論爭,這次論爭時間長達半年之久,國內一些思想學術界名流紛紛加入論戰。胡適作為科學派的主將和陳獨秀一起,分別為由這次論戰文章編成的25萬字的《科學與人生觀》一書寫了序言,闡釋了他們對科學的認識。今天重讀胡適先生的《科學與人生觀》,發現其對科學的介紹幾乎是全方位的。例如,“根據天文學和物理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空間的無限之大。根據地質學及古生物學的知識,叫人知道時間的無窮之長。根據一切科學,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萬物的運行變遷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著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根據生物學的科學知識,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競爭的浪費與殘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設是不能成立的”,等等。有這么一位名人寫作的序言,本身就是一篇精彩的科普創作。但在有關科普創作史資料中卻不見了這位名人的身影。
科普創作有諸多方式,在當年的氛圍中,大討論無疑是一種好方式,曾影響了許多國人的觀念,這要比一般的出本書更具影響力。1930年,胡適又作了《科學與人生觀》的講演,進一步對科學理念進行了普及。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科技工作者從20世紀初起陸續成立許多科技社團,如中國科學社等,研究學術普及知識。中國現代不少著名科學家也是受胡適先生等影響或直接指導下成長起來的。
這里順帶提到另一位科普創作史上不見記錄的我國著名地質學家丁文江(1887—1936)。丁文江先生是中國現代地質事業和地質科學的主要創始人。他少年負笈東瀛、輾轉英倫、學成歸國后,以“天生能辦事”的行政才干和組織能力,與章鴻釗、翁文灝一起創辦了中國最早的地質調查所、地質研究所,發起、創建中國地質學會,推動中國地質科學于20世紀20、30年代躋身世界先進水平,被譽為中國地質科學的開山大師、地學之父,贏得了世界級聲譽。早年他在地質考察和地理旅行期間,在雜志上發表了大量游記,像徐霞客一樣介紹地理知識。他從流失國外的資料中發掘考訂,為已經失傳的《天工開物》作者宋應星做略傳,向大眾介紹中國古代科技人物。前面提到他曾挑起科學與玄學的論爭,都可以視為他在科普創作上的貢獻。2008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文江文集》第一卷科學評論中如:《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系》《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玄學與科學——答張君勱》《玄學與科學的討論的余興》《赫胥黎的偉大》等就現在來看也屬于優秀的科普作品。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丁文江這位中國現代地質科學的開拓者、著名的地質學家很少被提及,更遑論他在科普創作史上的貢獻。
如果說上述諸位沒被提及是年代久遠的原因,那么新中國成立后,仍有一些在科普創作領域有影響的人和事被直接忽略。我在翻閱有關科普創作歷史資料時,看到過被譽為中國科普拓荒年代的“四大天王”的名字,嚴復(1853—1921)、陶行知(1891—1946)、任鴻雋(1886—1961)和王云五(1888—1979)。看到過新中國“科普七賢”的名字,他們是竺可楨(1890—1974)、茅以升(1896—1989)、賈祖璋(1901—1988)、顧均正(1902—1980)、董純才(1905—1990)、高士其(1905—1988)和溫濟澤(1914—2000)。再有就是記住了鄭文光、葉永烈、童恩正等少數幾個人。好像除了他們之外,科普大家就沒有了。以至每當我看到一位曾經產生過重大影響的科普作家都會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大吃一驚,朱冼就是其中一位。
朱冼(1900—1962),中國細胞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但我們怎么也不可想象他是一位高產的科普作家。據介紹,早在20世紀30年代朱冼就開始了科普創作,他從法國回來后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他一邊繼續做無尾類(蛙、蟾蜍)孤雌生殖研究,一邊與同事張作人合作,根據法文教科書編譯成《動物學》上、中、下三冊,該書印制精美,曾長期作為國內動物學教材。同時期,他還創作出版了科普著作《科學的生老病死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朱冼回國后和好友巴金、陸蠡等創辦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大家談到要出版一套現代科學叢書,朱冼提議編寫《現代生物學叢書》,因為他在法國時就有這個計劃。他在初版“總序”中寫道:“本叢書編輯的目的是要使學術大眾化,要把那些深藏于實驗室、專門著作、圖書館和博物館里的生物知識,循著發展的次序,由淺而深,由簡而繁,用暢達明確的文筆,寫成系統叢書,可作青年學生的課外讀物,亦為其他科學所不可少的參考書。”《現代生物學叢書》第一輯6冊是在抗日戰爭烽火中完成的。第6冊《愛情的來源》1945年著成,1946年7月出版。在戰時的惡劣環境下,朱冼堅持完成一百數十萬字的撰寫計劃,這是何等毅力!
《現代生物學叢書》不是根據通俗讀物或教科書寫的,而是根據原始文獻和專著書寫的,這是第一等手眼,非學識極深極專,無以致此。鐘少華在《科普──中國現代化的先導》一文中評價朱冼:“中國近代百年的科普作品桂冠,筆者認為應獻給中研院朱冼院士。”朱冼去世后,著名胚胎學家童第周撰文說:“有人估計自清朝末年以來,我國科學家用本國文字所寫的科學書冊最多的是朱先生,寫通俗科普讀物最多的也是朱先生。這并非過分之言。”
我曾經參觀共和國第一任林墾(林業)部長梁希紀念館。從中得知作為九三學社的創始人梁希(1883—1958)不僅是杰出的社會活動家和教育家,也是中國現代化林業科學的開拓者之一,著名的林學專家。
他有一段民主與科學關系的語錄:“民主是科學的土壤,民主是科學的肥料,民主是科學的溫床……所以,吾們需要科學,便不得不需要民主。”很好地闡釋了他人生的追求和實踐。讓我意想不到的是,他還是一位科普大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他就從事科普活動,發表科普文章,宣傳普及有關林業、森林的知識。1940年他兼任過《新華日報》的《自然科學》副刊編輯,1948年負責出版《科學工作者》會刊。這些刊物都是帶有科普性質的進步刊物。1950年,梁希被推選為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主席,也是中國科協的前身之一。為了紀念梁希在科普領域的貢獻,經科技部批準,由中國林學會申請設立了面向全國、代表我國林業行業最高科技水平的獎項梁希科學技術獎,其中就包括梁希科普獎,至今已經評選六屆。
相比自然科學領域的人士,人文社科領域從事科普創作而沒有被科普創作界提及的人和事就更多了。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徐遲、黃宗英等。10年前,我在給董仁威先生主編的《科普創作通覽》中提了這么一條:“在20世紀70年代末第二個科學春天到來之際,徐遲、黃宗英和黃鋼等一批著名作家加入了科普創作隊伍,他們的作品在當時的《人民日報》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上刊登播出,在全國造成很大影響。可以說以《哥德巴赫猜想》為代表的科學人物傳記作品,在全國掀起了新的科普創作浪潮。”其中最有代表的是著名報告文學家徐遲(1914—1996),他對科學有著濃厚的興趣,寫了一系列關于科學和科學家的報告文學,起到了廣泛的科普效果。特別是寫陳景潤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發表后,在全國特別是青少年中產生了很大影響。此后,徐遲相繼推出了《生命之樹常綠》《地質之光》《祁連山下》等一系列為科學家立傳的力作。徐遲對科學的熱愛是一般人難以想象的,他曾與人談到:“科學博大精深,科學能改變人類生活。我每天清晨兩點,一醒來就鉆研深奧的科學,鉆研理論物理學,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研究‘夸克’,研究物質世界的構成,研究基本粒子、電子、質子、中子、原子,即使有些地方看不懂,興趣也很大。”他認為:“科學使幻想變成現實。過不了多久,地球和月球之間會開通TAXI,人也可能到火星上去。人們乘著飛舟,天上地下,來往穿梭,像搭公交車那樣,十分方便。再過七八年,就進入21世紀了。猶如過了一夜到了清晨,過了一歲到了新年那樣,新世紀會帶給我們許多嶄新的、現在難以想象的東西。目前的情況是許多文學家不懂科學,許多科學家(錢學森例外)不懂文學。科學家如果懂文學,文學家如果懂科學,他們就能用美麗、形象的文字把科學通俗化,讓廣大人民看得懂……”
我在閱讀梁衡創作的國內唯一以章回小說形式演繹世界科學歷程的《數理化通俗演義》時又大吃了一驚。梁衡先生是著名學者、新聞理論家、作家。他擔任過我國新聞出版界領導。我在傳媒界工作時,曾讀過不少他撰寫的新聞業務書籍,受益匪淺。他除了新聞作品外,也創作了大量散文作品,作品并入選大、中、小學語文教材,也獲得過不少大獎。讓我想不到的是他會進行科普創作,在我讀過為數不多的中外科技史類作品中,寫得如此好看的書真不多,其中洋溢著濃郁的人文色彩。真是名家出手,果然不凡。這本書30年間再版36次,獲得過中國科普作品一等獎。這次新版還是由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作序推薦的。
另外一位讓我大吃一驚的是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金克木先生(1912—2000),他是中國著名文學家,翻譯家,梵學研究、印度文化研究家。在文化界,金克木先生絕對是一位知識淵博、中外融通的大師級人物。我也非常喜歡他的作品,買過、讀過他的許多書。但我不知道他竟然翻譯了美國作家西蒙·紐康的《通俗天文學》,要知道這本書從1923年至今,重印上千次,全球銷量過億。他翻譯這本書還是在1938年,不久他又翻譯了天文學著作《流轉的星辰》。我了解到金克木先生早年對天文學有特別的興趣,不僅翻譯過天文學的著作,還發表過天文學的專業文章。20世紀30年代,戴望舒非常欣賞金克木的作品,硬是將當時癡迷天文學的先生從天文學拉回文學。對此,金克木還頗有遺憾,曾在一篇隨筆中,悵然道:“離地下越來越近,離天上越來越遠。”數學也一直為金先生所好,他曾很有興趣地鉆研過費馬大定理,臨終前寫的一篇文章中還涉及高等數學的問題。先生早年即同數學大家華羅庚很談得來,華先生也是文理兼通。他還曾和著名數學家江澤涵教授在未名湖畔邊散步,邊討論拓撲學的問題。由此再次證明科普創作、科學傳播絕不僅僅是科學界的事情。
以上所舉之例,屈指可數,僅僅是我平時不經意地瀏覽中注意到的幾件人和事,我想連冰山一角也算不上吧!為什么在科普創作史上會有那么多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和事被遺忘?這些應該濃墨重彩在科普創作史上書上一筆的人和事為什么很少看到?我想這也不是無緣無故的,其中客觀有以往科普創作資料方面的缺失,毫無疑問這種缺失必然影響到我們對科普創作史的全面認識。也不排除那些有意無意的因素,比如科普創作研究界的主觀看法和偏見等因素。
比如有意識形態上的原因。這里我想到和上述人物有關聯的一件事或可幫助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在“五四”時期,杜亞泉曾受到胡適、陳獨秀的激烈批判。一位自然科學家,一位以科普工作為己任的作家,一個充滿理性的自由主義者,怎么竟然走到了“五四”學人的對立面,以致名聲湮沒多年長期無人提及?我看到一些論者從思想史的角度對之進行剖析,感到很有啟示意義。這里牽涉到激進與保守、偏激與寬容的態度和立場;也關系到自然科學工作者是否具備科學精神和科學思想的問題。或者往大里說,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相互關系的處理,還有就是西方文化和傳統文化之間的體用問題。比如同為崇尚科學之人,有論者就提出杜亞泉堅持的中體西用其實還停留在洋務派的認知階段,事實上當時這條路已經被證明行不通。所以只有科學的知識與方法,沒有科學的思想和精神只能是新瓶裝舊酒,骨子里還是保守派。也有論者認為,陳獨秀和胡適都是崇尚民主之人,可是當時他們對杜亞泉的批判完全有語言專制的嫌疑,況且杜亞泉對法制社會的期待、對理性精神的崇尚等理論觀點,也應是陳、胡等人一直所追求的,即便在當今社會也是很超前的。這在樊洪業先生有關科學史的文章中談及李四光與丁文江的關系時也可見到端倪。
比如與科普創作的界定有關。我以為從科普創作最終目的是為了提高公眾的科學素養出發,我們的科普創作至少應該包括下列范圍:一是人物的宣傳,亦即如席澤宗院士所說的那樣,通過科學家、科技工作者的介紹來引導青年一代熱愛科學、獻身科學事業。這已經成為廣大科普作家的共識。二是史的疏理,以此讓人們了解科技發展的源流,從而更深入理解科學文化。三是當今重大科學發現和科技成果的報道,這些將影響到今后人們生活和社會走向的重大事件,是吸引人們了解科學、理解科學文化的最好辦法。四是科學理性的傳播,通過人文社科的角度解讀科學,反思科學,弘揚科學精神,培養理性思維。而不僅僅是實用的科技知識介紹,把許多科普創作應該承擔的義務劃到圈子外去,不承認這些人和事屬于科普創作范疇,等等。
我想,不忘初心,就是不要忘記科普創作為了什么?這樣我們就不會畫地為牢,為了我們的使命和擔當而對當下的科普創作進行一次全面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