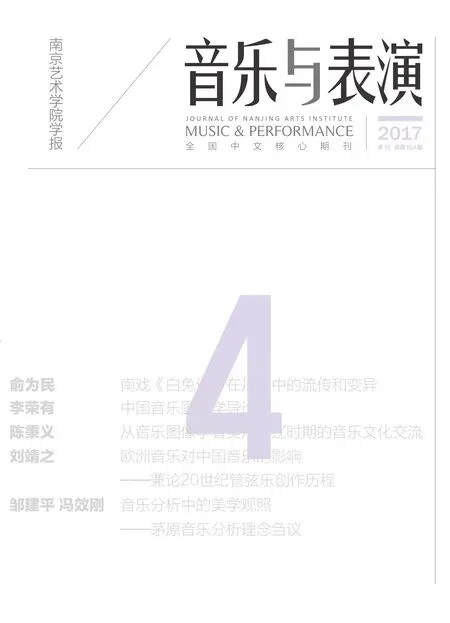音樂分析中的美學觀照
—— 茅原音樂分析理念芻議
鄒建平(南京藝術學院 音樂學院,江蘇 南京 210013)
馮效剛(南京藝術學院 音樂學院,江蘇 南京 210013)
茅原教授是新中國成長起來的第一批音樂理論家之一,他從1956年開始在中央音樂學院“蘇聯專家班”學習,期間隨姚錦新教授系統學習了曲式與作品分析課程。他一生在諸多領域奉獻了卓有見地的研究成果,作品分析是其中重要的領域之一,展現了他獨特的研究風格和音樂分析理念。雖其代表作《曲式與作品分析》[1]是本科教材,然而他的思考是建立在對音樂本質規律基礎上的。那么,我們應當怎樣理解茅原教授對音樂內容與形式之間關系的認知呢?筆者認為,探尋茅原教授的音樂分析理念需要結合他對音樂美學的文章來解讀。
一、對音樂內容與形式的闡析
與國內同類音樂作品分析教材相比較,茅原教授的不同理念在于,將音樂的技術分析與美學分析有機結合。他在“教材”的《緒言》中寫道:“作品分析是把樂曲的形式與內容聯系起來進行研究的一門課程,必須處理好技術分析與美學分析的關系。”“技術分析”包括曲式、和聲、復調、配器等,“美學分析,指的是把內容與形式、現象與本質統一起來進行的分析。這涉及音樂與生活,社會、人生的關系、音樂中所體現出來的美學思想觀念”。“二者的關系是,美學分析指導技術分析,技術分析支持美學分析。”他強調技術分析的重要性,但同時認為技術與“一定的內容存在著有機聯系”,提出,單純的技術分析如果“不上升到美學高度”,很難如實反映作品的真實內涵。[1]1
音樂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是藝術研究領域常議常新的話題,特別是對于內容究竟應當怎樣理解一直存在著爭議。
(一)音樂內容
由于音樂藝術的特殊性,音樂能否客觀地反映現實社會生活歷來是爭執的焦點之一。的確,音樂與其它藝術(特別是繪畫、戲劇與影視等)相比,其反映客觀現實的手段非常有限,并且往往“是主觀化了的,是通過人的精神面貌反映出來的”[2]40。所以許多人認為,音樂的內容主要是反映人的思想感情。早在1983年,茅原教授通過對馬克思《巴黎手稿》的解讀后認為,音樂內容“是通過現實中的人的精神狀態反映出來的”。他曾撰文提出:
承認音樂是一種特殊的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產物,承認音樂也是一種人化的自然,那么,把音樂的內容理解為在音樂中反映出來的現實的人的精神狀態(面貌),可能是比較恰當的。[2]40
既然如此,音樂內容在作品中是如何顯現出來的呢?茅原教授結合具體分析,將作品中的音樂內容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作品具有反映的是什么對象、反映的是什么思想、感情、精神氣質等多方面的特征。第二類作品僅只具有感情、情緒和精神氣質的特征。第三類作品連情緒特征也很難說,只有一種精神氣質特征。[3]110
如:貝多芬《第三》和《第五》、柴可夫斯基《第六》交響曲、李斯特《b小調鋼琴奏鳴曲》以及《二泉映月》,在“思想、感情”和“精神氣質”方面凸顯出作曲家對社會生活的感悟,屬于第一類作品;柴可夫斯基的鋼琴套曲《四季》,僅僅反映出他那“優柔寡斷的氣質”,屬于第二類作品;而“從《平湖秋月》《寄生草》這樣的音樂作品中”,我們恐怕“只能感受到一種平靜、柔和、優美、溫文爾雅的精神氣質”了。[2]40-41
事實上,人們從不同的音樂作品中往往能夠感受到作曲家千差萬別的性格和氣質,這說明音樂作品存在共性的同時,“更多的是存在著內容的個性特征”[2]41。那么,音樂內容具有普遍性嗎?如果這種普遍性存在,其規律是什么?反之,人們又是如何從千差萬別的“個性特征”中感受到相同(或相似)的音樂內容呢?也就是說,在具體的音樂作品中,作曲家的個性是如何融入共性中,他是如何表現出符合規律性的音樂內容的呢?
茅原認為:“沒有內容的形式是不存在的,沒有形式的內容也是不存在的”。音樂本身就有其“自己的內容和形式”,“作品所反映的思想、感情、藝術家的個人藝術氣質,屬于內容的范疇”[3]111,而音樂形式本身,存在著不同的規律。
(二)音樂形式
茅原教授從馬克思“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觀念出發,對音樂形式美進行了深入研究,探討了音樂“具體的形式律”,闡述了“整齊一律、平衡對比、符合規律、和諧”等在音樂“作品結構中的表現形態”。他認為:
“整齊一律”體現在音樂作品“節拍的規范化”、“樂段(或初級復合單位)”的結構上,主要表現在“服從于統一樂思的表現手段”相對統一。
“平衡對稱”有三種形態,第一種是“為反映一事物的不同側面或一對形象或兩組形象服務的”“對比并置曲式原則”,如“樂段、單二、三部曲式,復二、三部曲式”等;第二種是“為反映一系列不同的生活面服務的”“組曲原則”,各結構之間在對比中形成一定的“呼應關系”,從而“構成平衡感”;第二種是“回旋原則”,盡管非中心段落的每一部分之間形成對比,同時“又與中心段落構成主要對比”,但這是為了反映“一系列不同的生活面”中“有一個主要的中心”,被隔開段落之間的平衡由中心段落來實現,仍有“隔段平衡的趨向”,“體現了對立面的交替”,這種結構特征服從于“對立形象”“交替運動”的內容。
“符合規律”體現了對立面的并存,表現為變奏原則,“是為反映事物發展的不同階段而服務的”。其中,或旋律保持一致,而節奏各異;或旋律、節奏都一致,而和聲、織體各異;……總之,“與事物發展不同階段之間內容上的相互關系是一致的”。
“和諧”“是為反映對立統一的復雜事物發展的不同階段服務的”,“奏鳴原則”中集中體現了相同與相異的互相滲透,其結構圖式①茅原說:“A代表主部主題,B代表副部主題,T表示主調性,D代表副調性,T D表示在矛盾中呈示,T T1表示在統一中得到歸宿,中間則是展開階段,呈示部與發展部中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發展部與再現部以至呈示部與再現部之間亦復如此,這里與變奏的區別就在于,相同面和相異性不再十分清楚地加以區別,雖然二者都存在,卻互相融合,互相滲透。甚至某些作品,主部副部之間也互相滲透。”(茅原.人化的自然和音樂的耳朵——《巴黎手稿》與音樂美學[J].樂府新聲(沈陽音樂學院學報),1983,(03):42.)為:

茅原認為,形式律是古典美學家對所處時代音樂創作實踐富有指導意義的總結,但是,“所有的形式律都不能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完全符合形式律,比如最平衡對稱的音樂反而是不美的?”他根據馬克思“創造是一個很難從人民意識中排除的觀念”(全集42卷129頁)解釋了這一疑問:“要真正實現形式美,不僅僅是要借鑒形式律(前人的經驗),而且要體現創造性!”音樂家的“智慧、才能、技術、深入認識對象的程度、自由自覺的創造能力和在勞動上花的功夫不同”,產生出的結果大相徑庭:“包括好的演唱演奏的聲音素質,也是在正確指導下經過一定積累而獲得的訓練成果”;并且提出:“歷史既然還在發展,人們就會去創造更新的形式律”[2]42-43的觀點。由此出發,茅原教授進入了音樂語言的解析中。
二、對音樂語言的解析
茅原教授首先提出,音樂語言是一個借用來的名詞,其中既含有“語言”的本質屬性,又必須考慮到音樂表現形式的特殊性。他寫道:
……斯大林把語言稱為思維的形式。但是,從邏輯上來分析,形式是類概念,語言是低一級的、范圍更小一些的種概念,語言與形式的關系類似于整體結構和局部材料的關系,或者說表現手段的體系和個別表現手段的關系。形式是由音樂語言的體系構成的,二者相互聯系,卻各自具有不同的內涵和外延。[2]41
茅原教授引用了馬克思的原話:“思維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現的要素,即語言,是感性的自然界”[4]129,并進一步解析道:
音樂語言這個借用意義上的語言,也是人類交流認識的信息,與本來意義上的語言的區別,就在于音樂的信息是一種抽象的具象。……所謂“抽象”就是抓住主要特征,舍棄次要特征,所作的概括。[2]41
茅原教授通過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所舉“魚的形象的例子”,解析了藝術抽象的過程,并以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主題旋律的產生為例,解析了作曲家音樂創作中進行藝術抽象的過程。越劇中不論是對“賢妹妹”“充滿深情的呼喚”,還是用“叫頭”喊“賢妹”都還不是音樂,只有當“我想你,哪天不想你到天明”(譜例略)的唱段出現時才具有音樂的屬性。然而,此時作曲家還要舍棄歌詞(次要屬性),深化感情,從而產生出小提琴協奏曲《梁祝》中的愛情主題(譜例略)。當然,在這個主題中,已聽不到賢妹妹了,可是它抓住了思念賢妹的情緒,進一步作了發揮,它的具象也抽象化了。[2]41
這段旋律更為深刻而充分地揭示出深深的思念之情。由此了解符合實際的“音樂語言”產生的特殊規律,從而揭示了音樂內容與形式關系的本質屬性:在音樂藝術中,內容與形式不可分割的同時,形式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他把音樂語言界定為基本(或局部)的某一方面的表現手段;把音樂形式界定為整體的表現手段。
雖然我們從以上解析中已經可以感受到茅原教授縝密的邏輯性以及入木三分的音樂分析功力。但他并未就此止步,提出了音樂語言與“生活音調”的關系問題。他以實事求是的自我批評精神反思了自己以前觀念的局限:
我曾長期相信和宣傳過一種理論:生活音調;進入音樂邏輯,形成音樂音調。這種理論,固然有其一定的合理因素,但是,有許多問題,它不能自圓其說。
隨后,他的一系列追問發人深省:
……生活音調難道不是人的思想感情的反映嗎?難道不是第二性的嗎?它能與現實生活等同起來嗎?如果說生活音調與音樂音調都是人的思想感情的反映,只是在不同范疇內以不同方式作出的反映,這二者之間的關系,就需重新加以研究。音樂音調的根據就應當到人的思想感情中去尋找,而人的思想感情的根據則應該到人和環境的關系中去尋找。[2]42
接著,茅原教授繼續問道:
為什么生活音調的變化在歷史發展中相對緩慢,而音樂音調的變化卻相對迅速得多呢?人類的哭聲和笑聲幾百年之內,能有多大變化呢?音樂上卻早已千變萬化了,這難道只是作曲家主觀加工的差異引起的嗎?這主觀加工的差異又是如何引起的呢?
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顯現出他對馬克思哲學精要的理解,凸顯出新中國第一代音樂理論家求實精神。在人們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社會現實和音樂文化”的關系之間存在著這樣一個問題:“音樂隨時向社會吸取什么,又給予社會什么”?毋庸置疑,“物質與精神”“社會和音樂”的發展是各自獨立的,如此,兩條線索在發展中之間互相發生反饋嗎?事實證明,“音樂傳統中隱伏著無數的生活與音樂之間的中間環節,它們對音樂創作所起的作用必須給予重視。”于是,新的問題產生了:
是否任何音樂必須從對生活音調的加工開始呢?為什么許多音樂是找不到它的生活音調的呢?如果不能直接找到生活音調,是否音樂就不反映現實了呢?是否音樂就純粹由作曲家的主觀噫造而產生,就不受物質制約精神這一規律的支配了呢?
茅原教授從馬克思“人的第一個對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4]129出發,闡述了“人的感情和整個內心世界,都存在著運動的特性”這一基本規律。這一點突出地反映在樂音運動與人“心理(主要是感情)”運動的相似性方面:
……這樣,我們就可以說:音樂不是生活音調的反映,而是現實生活中的人(自然)的心理運動的反映。
然而,“在音樂作品中,有時確實有明顯的生活音調的痕跡,這是怎么回事呢?”茅原教授認為:“能夠反映人的心理狀態的生活音調,是一種現實生活之中的反映形態,音樂音調則是藝術中的人的心理狀態的反映形態,因而,二者能互為參考系或參照系 (參照架 )。”
而事實上也正是如此。當然,不是“任何音樂作品都必須處處以生活音調”為參照,“即使在以具體生活音調作為參照系的情況下”,還有作曲家一系列的抽象過程參與其中,不僅僅是“去粗取精”,而且“帶有作者的理解(理智因素的表現)和愛憎(感情因素的表現)”;“在這個抽象過程中,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利用音樂傳統中不知多少代人積累下來的經驗,就是說,在前人所作抽象的基礎上再作進一步的發展,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不能在音樂作品中到處找到生活音調的痕跡,即使發現了這類痕跡,它們也是隨著社會生活和音樂傳統的發展和個人獨創性的貢獻而采取千姿百態的原因。”所以,“無論是直接地反映人(自然的一部分),還是以生活音調為參照系來反映人的心理狀態,這些反映現實生活的手段,即音樂語言,總歸是人化的自然,即經去人的主觀過濾所反映的自然的映象。”
正是因為音樂創作中存在著抽象的過程,因而
“無論就音樂與心理,音樂與傳統,音樂與生活音調各方面的關系來說”,在具體加工(抓住本質特征而揚棄許多次要屬性)的過程中展現出各種可能性,“這也就給音樂的概括性、具體性、確定性、不確定性等問題提出了研究課題。”[2]42
三、論音樂內容與形式的關系
由此,他展開了對音樂內容與形式關系的分析。為了清晰地說明這個問題,茅原教授從更為廣闊的視野談到藝術的普遍規律。他首先解析了拉波泡泡爾特對藝術內容①茅原說:“在1987年出版的《音樂美學原理》(楊洸譯)中,拉波泡泡爾特把藝術的內容分為三個方面:一、實物方面,二、感情方面,三、思想方面。”([1],第111頁)的看法,認為:
他的第一方面大體相當于我所說的第一方面,他的第二、三方面相當于我所說的第二方面。他沒提到的就是我所說的第三方面——藝術家的個人藝術氣質。至于有的作品三個層次都反映得比較明顯,有的作品只反映到一、兩個層次,那是具體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與廣度上的差別。[2]111
進而,茅原分析了斯坦尼戲劇理論“角色中的自我和自我中的角色”以及我國戲曲藝術中“我演我、我亦非我。演非我,非我有我”兩種說法,提出“演員是第一自我,角色是第二自我”,表演中“深入角色、深入環境”是一個演員必須要達到的“無我”境地;然而,如果沉入角色之中不能自拔,必然無法控制自己,也不可能充分發揮其“創造者的才能”,演員要控制自己,時刻保持“有我”的清醒狀態;“破壞了二者之間的有機聯系”,則不能很好地“反映對象”,就會“導致藝術上的失敗”。“艾德華·布洛的《心理距離論》……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某些看法上是相當接近的”:
進入角色,出不來,心理距離就太近了;根本不能進入角色,心理距離就太遠了。兩種情況,都是偏頗。朱光潛先生說:“藝術的理想是距離近而卻不至于消滅”。我以為,是有道理的,這正是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之間應當保持的心理距離。
茅原教授從作曲、演唱和欣賞三個方面分析道:作曲家在創作中如果“一味感情傾瀉,不能控制自己……可能是高潮基礎上再加高潮,十個八度的音域也不夠用,結構也會散亂無章,飛翔無度,難于成功。”反之,如果作曲家十分冷靜,往往容易“不動感情”,雖然 “結構處理可能有條有理,音樂卻不感動人”。“要使二者有機統一,應當在深入環境的同時,保持一定心理距離,角色中有自我,自我中有角色,在體臉中,充分施展表現的才能。”演唱者也是一樣,“情緒高度激動,失去控制,荒腔走板”在所難免,假如“絲毫無動于衷,可能音色純正,板眼準確”,但常常會“不感動人”。“欣賞也是如此,忘記了是在欣賞藝術,才會發生觀眾向演員砸石頭的事,心理距離太近了;反之,過于冷眼旁觀,根本不為藝術所吸引,心理距離太遠了,也得不到美感享受。”[2]42-43這都是沒有把握好心理距離:“心理距離太近了,會導致藝術上的失敗”,“心理距離太遠了”,“冷若冰霜,根本不能深入環境”,同樣也會失敗。他以著名陜北說書藝術家韓起祥1953年在全國民間音樂舞蹈會演期間介紹演唱《劉巧團園》經驗時的一個細節為例來說明,“忠實于反映客體對象和表現主體創造才能的有機統一,是藝術成功不可缺少的條件”。
劉巧聽說她將要被迫嫁給包辦婚姻所指定的從未見過面的男人時(她不知道這正是她自由戀愛選擇的那個對象),十分傷心,連唱了多少“直哭得……”,達到高潮時,是“直哭得……鳥無聲”。他解釋說(大意):為什么伴奏突然強奏呢?因為演員哭了很長時間了,聽眾已經很難過了,再哭下去,就不再有藝術效果了。他用三弦喚醒聽眾:“你是在聽說書呢!”聽眾松一口氣,再聽下去,才能繼續接受演員的表演。可見,他在深入角色同時,始終控制著自己,這難道不正符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的要求嗎?[2]43
以上所有論述都給我們指出了回答這個問題的思路:“面對著同樣的客體對象,藝術家高于平庸的藝術工作者之處,難道不就在于藝術家本身的素養和才能嗎?”[2]44
由此可見,在茅原教授看來,音樂內容、音樂語言、音樂形式是既有區別又相互聯系的概念。他說,黑格爾稱方法為“形式的一般者”,認為方法同樣是手段,那么,音樂手段中就包含著音樂語言和形式。然而,作為“個別的、局部的、某一方面”表現手段的音樂語言和作為“作品整體結構”表現手段的音樂形式是什么關系呢?
音樂語言與音樂形式的關系,好比建筑材料與建筑物整體結構的關系。音樂語言比如鋼骨水泥等建筑材料,當它們被組建成長江大橋時,就發生了一次飛躍,我們就不再把這一建筑物的整體叫做鋼骨水泥,而叫做長江大橋了。[3]110
在此基礎上,茅原教授又提出音樂內容與形式是什么關系的問題。有人說,音樂中的“內容和形式可以相分離”[5],并以黑格爾的話“形式就是內容”和“同一個東西即內容,作為發展了的形式”為據。不錯,這兩句話都是黑格爾說的。但“這里有兩個問題,一是黑格爾的語言是否準確?二是擁護這說法的人在觀點上是否與黑格爾真正一致?”黑格爾還說過:“因為形式在這種同一性中,它就被當作本質性的持存,所以,形式就是內容”。
首先,黑格爾在這里并不是談“音樂的特殊性”問題;其次,黑格爾說:“辯證法永遠把同一的東西與差別的東西、主觀的東西與客觀的東西、有限的東西與無限的東西、靈魂與肉體分離和區別開來”。“而一旦分離,就成了兩個東西了”。黑格爾“永遠把矛盾雙方分離和區別開來”。[3]110也就是說,黑格爾從哲學的角度來看,事物的內容與形式處于統一體中,形式是“內容得以保持和存在的物質載體”,并沒有當作內容與形式關系的全部結論。可見,就此認為內容和形式可以分離是“形而上學”的結論。但是,“為什么這個人、這一次寫出來的音樂非常美,而另一個人、另一次寫出來的音樂就不美呢?”關于這個問題,茅原先生認為,這是“音樂在差異中存在”,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這差異中存在著同一性”[3]110也是客觀事實,我們需要探尋的正是這種“同一性”符合實際的存在方式。正如茅原先生借維特根斯坦所說,這是“部分相似和一種交叉相似的網狀形態”。音樂作品大致處于這一范圍內,就是同一個東西,內容和形式就沒有分離[3]110。
由此可見,茅原教授的音樂分析理念是建立在作曲技術和美學分析基礎之上的綜合性分析。
……美學分析如脫離了具體音樂現象,就很難說是有根據的分析,美學分析需要技術分析提供的數據。……在這一點上,正是技術分析證實了美學分析。[1]1
目前,茅原教授的這本教材還沒有在專業音樂院校被普遍使用,“對于學習音樂的任何一個學生來說,音樂作品分析是一門關系到他能否真正懂得音樂的基礎課。學音樂就必須懂得前人的藝術創造,才談得到自己的藝術創造。”音樂專業的學生增強技術修養固然重要,但“一定的美學思想的指導是不可缺少的。”[1]1
[1]茅原.莊曜. 曲式與作品分析(上、下冊)[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6.
[2]茅原.人化的自然和音樂的耳朵——《巴黎手稿》與音樂美學[J].樂府新聲(沈陽音樂學院學報),1983,(03):38-45.
[3]茅原.音樂的內容與形式的關系[J].中國音樂學,1988,(04):110-119.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29.
[5]王寧一.簡論音樂的內容與形式的相互關系——兼對某些成說的質疑[J].中國音樂學,1986,(02):108-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