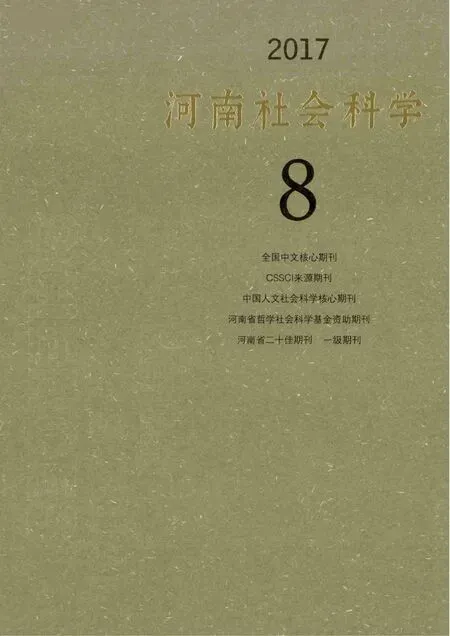論侵權法上的損害賠償酌減規則
張玉東
(煙臺大學 法學院,山東 煙臺 264005)
論侵權法上的損害賠償酌減規則
張玉東
(煙臺大學 法學院,山東 煙臺 264005)
一、問題的提出
所謂侵權法上的損害賠償酌減規則,是指在例外情況下,如令侵權責任人承擔全部賠償責任,將對其構成極為沉重的負擔時,法院可根據雙方當事人的經濟狀況及其他相關事由,減輕責任人一方的損害賠償責任①。損害賠償酌減規則是對侵權人在正常情況下所應承擔的損害賠償責任的減輕。因此,在侵權法以責任構成論及責任承擔論(或損害賠償論)為基本構建框架的前提下,損害賠償酌減規則屬損害賠償論范疇。在損害賠償論中,現代侵權法以完全賠償為基本原則。在此意義上,損害賠償酌減規則是對完全賠償原則的偏離。
在歐洲法上,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為瑞士法所首創,明確設置這一規則的國家還有丹麥、芬蘭、荷蘭、挪威、波蘭、葡萄牙、西班牙及瑞典等。同時,在新近起草的《歐洲侵權法原則》《奧地利損害賠償法草案》《瑞士責任法草案》《歐洲示范民法典草案》中,該規則也被明確加以規定②。此外,即便在法典中未對此規則設有明文的國家,也在司法實踐中通過解釋權利不得濫用原則而對其加以適用③。盡管如此,對損害賠償酌減規則持反對態度的國家和學者仍不鮮見④。
盡管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第218條及《澳門民法典》第487條對損害賠償酌減規則有所規定,我國大陸現行法并未對其進行規定;但學界一直不乏主張確立該規則的呼聲。此種主張,不僅體現在相關學者的論述中⑤,也體現在諸多與侵權法相關的學者建議稿中⑥。如此,認為我國法上應對損害賠償酌減規則予以確認的觀點似乎已占主流。但此種觀點卻并未為司法實踐所采納。同時,在我國承認完全賠償原則的情形下,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畢竟是對完全賠償原則的偏離。而此種偏離是否具有足夠的正當性基礎,即是否公平和合理,還需詳細論證。此外,在我國學者相關草案關于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的規定上,仍存不小差異。故而,在我國現已重啟民法典編纂的背景之下,于未來民法典中應否設置這一規則以及如何設置這一規則,值得認真思考。盡管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的確認涉及整個損害賠償法體系,但限于篇幅,本文僅就侵權法上的損害賠償酌減規則進行探討。
二、承認損害賠償酌減規則之必要性
筆者認為,我國法上應否承認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總體上應從理論層面和現實層面兩個角度展開分析。在理論層面,由于損害賠償的確定以完全賠償原則為主導性原則,而損害賠償酌減規則是對該原則的偏離,因此,如欲承認損害賠償酌減規則,則必須證成此種偏離具備足夠充分的理論基礎。在現實層面,首先,應確定我國現實生活中是否存在可由損害賠償酌減規則調整的案件,如無此類案件的發生,自無設置該規則的必要;其次,應考察我國法上是否存在足以替代損害賠償酌減規則所欲實現目的的其他制度,如依其他相關制度已足以解決損害賠償酌減規則所欲解決的問題,則也無需再行設置該規則;再次,應評估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的制度運行風險,如該規則的運行會導致難以承受的負面效果,則也不應對其予以確認。
(一)理論層面的分析
1.比例原則
損害賠償酌減規則可從憲法上的比例原則理念中獲得正當性基礎。比例原則起源于公法,但在私法領域也有其適用空間⑦。比例原則強調“禁止過度”。就損害賠償酌減規則而言,比例原則體現為在保護受害人的同時,不能要求致害人承擔對其而言過重的負擔,從而影響其生存及發展。對此,卡納里斯強調,損害賠償酌減必須是可能的,否則在特殊情況下,會對致害方造成毀滅性的后果。過度的損害賠償義務,不僅影響行為人的自由,而且也影響到其憲法上應受保護的人格權。受害人僅在依賴損害賠償支付的情形下,尋求完全賠償才是正當的。相反,在受害人能夠不通過損害賠償而滿足其需求,且損害賠償的支付將給致害方的余生帶來毀滅性后果的情形下,致害方的損害賠償就應被減少。基本權利與憲法上比例原則相結合,要求侵權法對致害方也應給予保護,以避免對其造成不成比例的不利影響⑧。盡管我國憲法并沒有如德國基本法、日本憲法、加拿大憲法那樣規定可推導出比例原則的條款,但我國現行《憲法》第三十三條第三款以及《立法法》第六條可有限度地為比例原則提供憲法規范依據⑨。同時,將比例原則作為制度構建或解釋的正當性基礎,也并不必須以憲法中存在規定為前提。只是在憲法中存在規定的情況下,相關制度的構建或解釋會獲得更為直接的依據。
2.社會正義區分原則
基于社會正義區分原則,窮人和富人、強者和弱者的區分在法律適用中也應被加以考量。此種思想,在民法的制度變遷中反映為民事主體“從法的人格的平等轉變到不平等的人”“從抽象的法的人格轉變到具體的人”⑩。對于區分原則的合理性,各國法律也給予充分的回應,尤其體現在對弱勢群體一方的特別保護,如對消費者的保護,對婦女、兒童及老年人的保護,對雇員的保護等。相應地,在侵權損害賠償制度中,應體現為考慮受害方與致害方的經濟狀況,在致害方無力承擔全部損害責任且會因此而陷入生活困境時,也應對其提供相應的保護。因此,社會正義區分原則也為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的合理性提供了正當的基礎。
3.歸責基礎與賠償范圍相關聯理論
歸責基礎與賠償范圍相關聯理論,來自自然法思想。在自然法學者看來,行為人的主觀過錯程度應與其損害賠償范圍成正比。尤其在加害人僅具有輕微過失的情況下,法官有權減輕其損害賠償責任?。但隨著過錯責任的衰落及對受害人救濟的強調,此種理念逐漸式微。這尤其體現在部分國家的侵權法中,對過錯程度的區分僅于責任構成論上具有意義,而在損害賠償論中,損害賠償的確定與過錯程度不再具有內在關聯。損害賠償的確定原則上取決于損失的大小而與過錯程度無關。這被認為是對完全賠償原則的貫徹?。但在損害賠償法中,致害方的歸責基礎是存在強弱區分的。因此,在考量損害賠償責任范圍的時候,基于公平的原因,就應對歸責基礎的強弱予以考量,否則一些重要的不同就會被忽視?。責任基礎本來是損害賠償效果發生之基礎,而賠償范圍卻又完全隔離于請求權基礎的特征,這樣出爾反爾,必將導致價值實現的斷裂?。因此,在承認損害賠償酌減制度的國家,行為人的過錯程度為法官考量是否酌減的重要因素。在我國侵權法上,一般認為,基于完全賠償原則,行為人的過錯程度原則上不會對其賠償范圍產生影響,總體上與德國法類似而與奧地利法和瑞士法有別。但是,是否在任何情形下均不考慮行為人的過錯程度而令其承擔全部損害賠償責任,尤其在行為人因極小過失而造成他人重大損害的案件中,值得考慮。筆者認為,即便出于對完全賠償原則的維護,從而認為僅僅基于過錯程度因素并不足以酌減致害方的賠償責任,但當其他支持酌減因素(如經濟狀況)與過失程度因素相結合并構成支持酌減的足夠理由時,應認為在例外情形下過失程度因素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損害賠償的范圍。此種例外情形下的適用,并不會從根本上削弱對完全賠償原則的堅持。
4.損害發生的偶然性理論
比德林斯基教授認為,在損害事件的發生與否及造成何種類型的損害上,大致來說是一個偶然情形的問題。如此,某人的經濟生活不能為其所遭受的損害而被毀,但同樣也不能因其承擔過重的賠償責任而被毀?。對此,可將其概括為損害發生的偶然性理論。該理論的合理之處在于,損害的發生與否及所造成損失的大小,致害方并不具有完全的控制力。對此,反對觀點可能認為,如果行為人對于損害的發生存在過錯,就不能認為損害的發生不在其控制之下。但一個不能忽略的事實是,只要是人就會犯錯。同時,也并不能因為其犯錯就令其承擔完全無法承擔的責任,甚至在有些情況下損害的規模也遠非其所能預見。當然,也不能認為因人都會犯錯而在一切情形下均可減輕其賠償責任。合理的解釋應該是,如果行為人對于損害的發生存在故意,其對損害的發生具有完全的控制力,此時不應酌減其損害賠償責任。因此,將損害發生的偶然性作為酌減理由,應是直接排除了行為人對損害的發生存在故意的情形。
5.權利不得濫用原則
我國《民法總則》第一百三十二條規定:“民事主體不得濫用民事權利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權利不得濫用原則是對民事主體行使民事權利的一定限制,通過限制民事主體不得濫用權利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達到民事權利與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權益的平衡。”?權利濫用不僅表現為無理取鬧行為,也表現為一方行使權利的獲益與因此而受影響的他方負擔之間的嚴重不成比例?。因此,在受害人主張損害賠償時,應考量雙方的經濟狀況,以平衡雙方的利益。
6.公平原則
公平原則作為民法上的基本原則,為《民法通則》第四條所規定,《民法總則》第六條以單條的形式對其再次加以確認。公平原則不僅要求公正、平允、合理地確定各方民事主體的權利義務,也要求民事主體合理地承擔民事責任?。基于公平原則,我國《侵權責任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了公平分擔損失規則。根據該規則,即便行為人對于損害的發生沒有過錯,考量經濟狀況及其他因素,也可令其承擔一定的賠償責任。同理,在因行為人構成侵權而應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時,則也應考量其經濟狀況及其他因素而例外地減輕其賠償責任。此兩種情形在公平原則的貫徹上具有內在的一致性。
綜上,筆者認為,比例原則、社會正義區分原則、歸責基礎與賠償范圍相關聯理論、損害發生的偶然性理論、權利不得濫用原則及公平原則,均為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的承認提供了相當的理論基礎。盡管個別理論(如歸責基礎與賠償范圍相關聯理論)因存在與其相反的價值判斷(如完全賠償原則)而無法單獨作為承認酌減規則的充分理由,但將上述理由結合起來,應認為酌減規則的確立具有充分的理論正當性。這些理由也將決定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的具體設定。
(二)現實層面的分析
1.現實案件
關于損害賠償酌減的適用案件,比較法上多有論述?,在我國則突出地反映為多地發生的碰撞豪車天價賠償案。在此類案件中,致害方因過失而造成他人豪車受損,而豪車的維修費用極為高昂,致害方對此往往無力承擔。盡管在現實生活中,有的車主因對方無力賠償而主動免除了其責任,但此種情形的發生終究屬于特例。在多數情形下,致害方不得不接受“不小心撞豪車,只能毀其一生”的后果。但是,如果一個人自愿將價值極高的物品置于高度交通危險中,卻因他人的輕微過失而能獲得全部賠償,也是很難令人接受的?。此外,未成年人致害案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對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的需求?。當然,由于我國法在未成年人致害案件的處理上采監護人替代責任模式,與比較法上的監護人承擔過錯推定責任且承認未成年人責任能力的制度相比,在處理結果上對未成年人的影響相對較小。但即便由監護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其也同樣會面臨無力承擔巨額賠償的情形。因此,在監護人因負擔巨額賠償責任而陷于經濟困境時,也并非無損害賠償酌減規則適用的余地。
2.替代性制度
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的承認,主要目的在于避免致害人因承擔巨額損害賠償責任而陷于困境。但此種目的的實現,卻也并非僅限于損害賠償酌減規則這一種途徑。從制度構造上看,責任保險、破產制度及執行程序中的保留必要生活費用制度,均為實現致害方保護的路徑。
責任保險制度的存在,無疑對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的確認產生重大影響。因為,在致害人投有責任保險的情況下,其損害賠償責任實際上已由保險公司承擔。但若論及責任保險對酌減規則的完全替代,則必須存在兩項必要性前提:其一,全社會的潛在賠償義務人均購買了責任保險;其二,保險公司所給予的賠償額度能夠滿足賠償責任人的需求。但顯然,在現實生活中,并不能確保在一切情形下均具備這兩項前提。因為,除去法律規定潛在賠償義務人須購買強制責任保險的情形,是否購買責任保險應由行為人自己決定;同時,即便是在行為人購買了責任保險的情況下,其保險賠償額度也存在限制,并不能確保在一切情形下均能滿足致害人的賠償需求。因此,責任保險制度并不能完全替代損害賠償酌減規則,但二者間會呈現此消彼長的態勢,即在責任保險被廣為應用的情形下,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的適用可能性會變得更小或即便適用酌減規則也會使得酌減額相應降低?。就我國當前的情況而言,絕大部分民眾并未為自身可能的致害行為購買責任保險,或者即便是購買了責任保險也會存在保險賠償的上限(如車輛責任保險),這無疑為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的適用提供了空間。
破產制度的存在,也可為致害方提供相應的保護,但會因適用主體的不同而存在差異。在破產者為自然人的情形下,自然人破產之后,無需對其破產之前所負擔的債務進行清償。而在破產者為法人的情形下,盡管其于破產后也無需清償破產之前所承擔的債務,但因破產結果為企業注銷,而在企業法人因注銷而消滅的情況下,已無保護的必要。因此,破產制度對企業法人的保護,并不體現為企業法人因破產而無需償付其無力承擔的債務,而僅體現為破產法中的重整制度和和解制度。如此,問題的關鍵在于,除去重整制度和和解制度對企業法人所提供的保護之外,是否還應承認損害賠償酌減規則以避免企業破產。筆者認為,對此不能一概而論,而應該考慮企業的存在價值。如企業的存在對于地區經濟發展、民眾就業及其所在領域的行業發展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則可有酌減條款適用的空間,以維持其運行。反之,則不應承認酌減條款的適用。因此,損害賠償酌減規則也可適用于企業法人。同時,根據我國《破產法》第二條的規定,破產制度僅適用于企業法人。如此,在自然人負擔過于沉重的賠償責任的情況下,破產制度無法為其提供保護。綜合上述情形,在我國法上并不能完全通過破產制度實現對致害方的保護。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一款和第二百四十四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在執行中應保留被執行人及其所扶養家屬的生活必需費用和生活必需品。此規定對致害方的生活維持提供了必要的保護。但訴訟法上所提供的保護,與損害賠償酌減規則所提供的保護仍有不同:其一,在保留生活必需費用的情形下,致害方仍須承擔全部賠償責任;而在酌減的情況下,致害方則無需再承擔因酌減而減輕的責任。其二,基于利益衡量而對行為人賠償責任的酌減,能夠留給行為人高于必要生活費用的財產,由此,行為人仍舊存在利用此財產發展的可能性?。
3.運行風險
一項規則的設定,不應僅著眼于其所能實現的功能,同時也應對其運行所可能引發的負面效應予以考慮。由于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為衡平規則,其在具體適用中須由法官自由裁量,因此必然會引發人們對法律適用確定性及司法腐敗可能性的擔憂。同時,由于損害賠償酌減規則須考量致害方的經濟狀況,而在誠信度不高的社會環境中,致害方極有可能通過隱藏或轉移財產,向法院主張自己無力賠償,從而規避本應由其承擔的責任。
必須承認,上述制度運行風險,都是有可能存在的,但這并不構成否定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的根本理由。首先,法律適用的確定性與自由裁量之間確實構成矛盾關系,但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其根本目的在于使法官可基于不同的案件情況作出妥當的判決。現實生活千差萬別,法律不可能對所有情形均作出細致而明確的規定。因此,自由裁量在法律的適用中不可避免。于是,問題的關鍵在于法律適用的不確定性是否在可容忍的限度內。對此,可通過明確法官于裁量時應考量的因素及要求法官在判決中寫明裁判的依據及理由,將酌減規則適用的不確定性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圍之內。從比較法上看,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的適用,既未給法官造成過重的負擔,也未導致法律的不穩定性?。其次,司法腐敗的滋生在根本上并不取決于裁量權的賦予,而取決于法官管理機制等相關制度,更何況裁量權的賦予也并非為損害賠償酌減規則所獨有。再次,盡管在我國當下,并不排除在該規則的適用中會出現行為人通過轉移或隱匿財產而主張自己無能力承擔責任的情形,但也同樣不能排除致害人因巨額賠償而確實會陷入生活困境的情況。對此,法官須在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的適用上,對致害人無力賠償的證據進行更為嚴格的審查。
三、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的具體構建
(一)承認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的路徑選擇
關于損害賠償酌減制度的承認,有兩條路徑可循:其一,通過解釋《民法總則》第六條公平原則條款或第一百三十二條權利不得濫用條款確認損害賠償酌減規則;其二,在未來民法典中明確設置損害賠償酌減條款。第一條路徑的優點在于其時效性強,即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的承認依據對現有空白條款的解釋即可實現,無需等待未來立法。但相比于第二條路徑而言,其也存在不足:第一,法律適用確定性的減弱。損害賠償酌減規則本身是一種衡平規則,其適用自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法律的不確定性。因此,在其適用上,必然要求盡量減少此種不確定性。但權利不得濫用原則及公平原則規定本身就極為概括,與明確規定法官具體考量因素的損害賠償酌減條款相比,其并未規定具體的適用條件,會加大法律適用的不確定性。第二,法官適用法律負擔的增加。相比于條文中明確規定適用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的裁量因素,權利不得濫用條款及公平原則條款中卻無相關指引。在此情形下,也會增加法官裁量的難度和負擔。第三,與我國司法現狀不符。在我國現有的法官考核體制上,上級法院是否改判下級法院的判決為一項重要的參照指標。由于法官的知識背景及判斷偏好有所不同,下級法院引用空白條款而進行判決,極有可能因為上級法院法官的不同理解而改判。如此,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并不愿意援引過于抽象的一般條款進行裁判,而更偏向于尋找為其裁判提供基礎的具體性規定。
綜上,盡管我國當下可通過解釋空白條款而承認損害賠償酌減規則,但于未來民法典中明確設置損害賠償酌減條款能更好地實現制度設置的目的。
(二)設置損害賠償酌減條款的要求
1.條文設置的基本要求
比較法的研究表明,通常情況下,法典條文的設置既不能過于概括,也不能過于僵化。過于概括的規定會因其對司法實踐的指引力不足,而使法院不得不承擔起本應由立法機關承擔的價值判斷職能;而過于僵化的規定會使立法過度限制法院的行動自由,最后的結果只能適得其反:法院遍尋突破口,大大削弱制定法對法院的約束力?。因此,就損害賠償酌減條款這一具有衡平性質的規定而言,要盡量避免在其中使用過于抽象化的語詞,且應更為明確地規定得以指引法官進行合理裁量的因素。此種條文設置要求,總體上遵照了動態系統論思想。盡管學界對動態系統論的適用價值提出了質疑,但就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的設定而言,動態系統論思想是適合的。在此意義上,以過于概括的方式規定損害賠償酌減規則?,或在損害賠償酌減條款中使用“公平”“合理”或“公平原則”等用語?,均不甚妥當。
2.考量因素的確定
如上所述,在損害賠償酌減條款中應盡可能明確羅列法官得考量的因素。而何種因素得被加以考量與損害賠償酌減制度存在的理論基礎、欲實現的目的以及我國現有制度的整體構造密切相關。
由于損害賠償酌減制度的目的在于避免致害方因承擔過重的損害賠償責任而影響其生存及發展,因此,在該規則的構建上就需考慮致害方的損害賠償承受能力。就此,致害方的經濟狀況為損害賠償酌減規則中的必備因素。而關于致害方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能力的不足,并不僅僅體現為其喪失勞動能力或因退休而無力承擔對其而言的高額賠償。因為,即便致害方未喪失勞動能力或并未退休,相比于其正常收入,高額的賠償同樣可使其陷于生活困境。故而,現有部分草案中以喪失勞動能力或退休為損害賠償酌減適用前提的規定,失之過狹。同時,盡管在經濟狀況的考量上,應首先考慮致害方的經濟承受能力,但受害方的經濟承受能力也應一并考慮。因為,就受害方而言,其生存與發展可能同樣依賴于致害方損害賠償的支付。在此情況下,也并不能酌減致害方的損害賠償責任或在比較雙方的經濟狀況后僅能在極小的程度上減輕致害方的損害賠償責任。因此,在損害賠償酌減條款中,應規定需同時考量雙方的經濟狀況。對此,《歐洲侵權法原則》第10:401條、《奧地利損害賠償法草案》第1318條的規定,堪稱妥當?。當然,由于致害方是否投有責任保險,會影響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能力,因此,在經濟因素的考量上也應將該因素納入其中。
致害人的過錯程度也是損害賠償酌減規則中的重要考量因素,但此處所言的過錯應排除故意情形?。因為,在故意侵權的情形下,致害方對于損害的發生具有完全的控制力,與損害發生的偶然性理論不相契合。同時,將故意情形排除在適用范圍之外,也能夠更好地實現侵權法的預防功能。需要考慮的是,重大過失是否也應排除在酌減規則的適用范圍之外。對此,《瑞士債務法》第44條第2款及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第218條,均將重大過失排除在酌減規則適用范圍之外。筆者認為,將重大過失侵權排除在損害賠償酌減范圍之外的做法并不妥當。盡管在侵權法上常將重大過失等同于故意,但二者仍存在區別。相比于故意,重大過失體現了致害方對損害發生控制力的降低,故應在價值判斷上對二者進行區分。但是,即便不否認重大過失情形下適用酌減規則的可能性,但于個案中在決定是否酌減及酌減的額度上,重大過失所具有的權重無疑要小于一般過失。
除經濟狀況和過錯之外,酌減條款中應同時承認其他應考量的因素。原因在于,其他考量因素雖不似經濟因素一般為決定性因素,但與過失程度因素一樣是對歸責要素與損害賠償范圍內在關聯性的承認,具有理論基礎上的正當性。關于其他影響酌減規則因素的規定,《葡萄牙民法典》第494條及受其影響的我國《澳門民法典》第487條采取了概括規定的模式,即“有關事件之其他情況”。而《歐洲侵權法原則》第10:401條則采取了不完全列舉模式,即“判斷是否降低損害賠償的數額,應尤其考慮責任的基礎,法益的保護范圍以及損害的大小”。筆者認為,為提高法律適用的確定性,應對其他因素進行不完全列舉,從而為法官裁量提供明確指引。
此外,因企業法人對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的適用需特別考量其存在價值,故應將此在條文中一并規定。
3.適用機制的表達
在損害賠償酌減條款中,也應對其適用機制進行規定。對此,應明確損害賠償酌減規則須經致害方向法院申請才能適用,法院不得主動援引。因為,酌減規則的適用僅涉及雙方當事人的私人利益,與國家利益及公共利益無關。同時,為避免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的濫用,須在條文中表明損害賠償酌減規則應是在例外情況下得以適用。
(三)損害賠償酌減條款的具體表述
基于上述關于損害賠償酌減規則設置的要求,我國法上的損害賠償酌減條款應具體表述為:“在特殊情況下,如令致害方承擔全部損害賠償責任將對其構成過于沉重的負擔時,可經其申請,由法院酌定損害賠償責任的減免。損害賠償責任應否減免,取決于雙方當事人的經濟狀況、致害方的過錯程度、致害原因的危險性、受法律保護的權益位階、損害的大小、損害與預防該損害所采取措施費用的比例、責任保險的有無及致害主體的存在價值等。但致害方為故意侵權的,不適用本條規定。”
注釋:
①損害賠償酌減規則的英文表述為Reduction of Damages或 Reduction of Liability,德文表述為Reduktionsklausel。對此,有學者將其翻譯為責任減輕條款或減低條款,也有學者稱之為生計酌減制度。
②參見《歐洲侵權法原則》第10:401條,《奧地利損害賠償法草案》第1318條,《瑞士責任法草案》第52條,《歐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6-6:202條。
③參見 Helmut Koziol,Basic Questions of Tort Law:from a Gemanic Perspective,Jan Sramek Verlag,2012,p.304.
④具體介紹參見[德]克雷斯蒂安·馮·巴爾:《歐洲比較侵權行為法》,焦美華譯,張新寶審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頁;European Group on Tort Law,Principles of European Tort Law:Text and Commentary,SpringerWienNew York,2005,p.180;[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債法總論》,杜景林、盧諶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31頁。
⑤參見鄧輝、李昊:《論我國生計酌減制度的構建》,《研究生法學》2015年第3期;徐銀波:《論侵權損害完全賠償原則之緩和》,《法商研究》2013年第3期。
⑥具體參見,第2035條,王利明主編:《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及說明》,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頁;第58條,于敏、李昊等:《中國民法典侵權行為編規則》,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610頁;第167條,楊立新:《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草案建議稿及說明》,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頁;第1707條,梁慧星:《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附理由:侵權行為編》,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頁。
⑦關于比例原則在私法上適用的論述,參見鄭曉劍:《比例原則在民法上的適用及展開》,《中國法學》2016年第2期;紀海龍:《比例原則在私法中的普適性及其例證》,《政法論壇》2016年第3期。
⑧關于卡納里斯教授觀點的詳細介紹,參見Helmut Koziol,BasicQuestionsofTortLaw:from a Gemanic Perspective,Jan Sramek Verlag,2012,p.304.
⑨參見門中敬:《比例原則的憲法地位與規范依據》,《法學論壇》2014年第5期。
⑩參見[日]星野英一:《現代民法基本問題》,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78頁。
?參見[德]布呂格邁耶爾、朱巖:《中國侵權責任法:學者建議稿及其立法理由》,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頁。
?參見 U.Magnus(ed.),Unification of Tort Law:Damages,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1,p.91.
?參見 Helmut Koziol,Basic Questions of Tort Law:from a Gemanic Perspective,Jan Sramek Verlag,2012,p.305.
?葉金強:《論侵權損害賠償范圍的確定》,《中外法學》2012年第1期。
?具體論述,參見 Helmut Koziol,Basic Questions of Tort Law:from a Gemanic Perspective,Jan Sramek Verlag,2012,p.305.
?參見李適時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釋義》,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407頁。
?具體論述參見 Helmut Koziol,Basic Questions of Tort Law:from a Gemanic Perspective,Jan Sramek Verlag,2012,pp.304—305.
?參見李適時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釋義》,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1—23頁。
?比較法上的例證,參見European Group on Tort Law,Principles of European Tort Law:Text and Commentary,SpringerWien New York,2005,p.181;Christian von Bar,No-Contractual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Damage Caused to Another,Sellier.Europen Law Publishers, Bruylant, Staempfli Publishers Ltd.Berne,2009,pp.971—972.
?參見[德]克雷斯蒂安·馮·巴爾:《歐洲比較侵權行為法》,焦美華譯,張新寶審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頁。
?參見徐銀波:《論侵權損害完全賠償原則之緩和》,《法商研究》2013年第3期。
?對此,瑞士法提供了有力證明。在瑞士,因為大部分賠償義務人投有責任保險,向受害人承擔賠償責任后,侵權人得依據保險合同從保險公司獲得賠償,因而不存在“經濟生活困難之可能”。故而,《瑞士債務法》第44條第2款規定的責任減免事由的實踐意義已經非常有限。參見[瑞]海因茨·雷伊:《瑞士侵權責任法》,賀栩栩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頁。
?參見 Helmut Koziol,Basic Questions of Tort Law:from a Gemanic Perspective,Jan Sramek Verlag,2012,p.305.
?參見[德]克雷斯蒂安·馮·巴爾:《歐洲比較侵權行為法》,焦美華譯,張新寶審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頁。
?參見赫爾穆特·柯啟爾:《論法典化對法的塑造力》,史夢宵、邸楠譯,載《中德法學論壇》第10輯,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頁。
?如《中國侵權責任法建議稿》第6:108條第一款規定:非故意侵權的,法院基于特殊事由,出于公平考慮,可以減輕特別高額的損害賠償責任。參見[德]布呂格邁耶爾、朱巖:《中國侵權責任法:學者建議稿及其立法理由》,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頁。
?如《歐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6-6:202條所規定的“公平合理的情形下”,參見歐洲民法典研究組、歐盟現行司法研究組:《歐洲示范民法典草案:歐洲私法的原則、定義和示范規則》,高圣平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25頁;《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侵權行為編》第1707條中規定了“違反民法公平原則的要求并且違反公序良俗的”,參見梁慧星:《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附理由:侵權行為編》,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頁。
?《歐洲侵權法原則》第10:401條規定,在極為特殊的情況下,考慮到雙方當事人的經濟狀況,全額賠償將給被告造成沉重負擔的,可降低損害賠償的數額。判斷是否降低損害賠償的數額,應尤其考慮責任的基礎,法益的保護范圍以及損害的大小。《奧地利損害賠償法草案》第1318條規定,賠償義務對于加害人嚴重不當且造成巨大壓力,并且受害人只能夠期待部分賠償的,在例外情況下可以減輕損害賠償的義務。在此應考慮歸責事由的輕重程度、受害人和加害人經濟上的狀態以及加害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
?此為通行觀點。從正面排除故意侵權的規定,參見王利明主編:《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及說明》,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頁;梁慧星:《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附理由:侵權行為編》,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頁;楊立新:《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草案建議稿及說明》,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頁;等等。通過反面規定排除故意侵權的條文,參見《葡萄牙民法典》,唐曉晴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頁;中國政法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澳門政府法律翻譯辦公室編:《澳門民法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頁。
Tort Liability Law:Monographic Study on the Legislation of Tort Liability
With a focus on the infringement upon property,On the Tort Liability for Infringement upon Property differentiates between infringement upon property and property rights.The essay underscores that there are three forms of infringement upon property—embezzlement,damage and destruction and three corresponding forms of tort liability—restitution of property,restoration and compensation for loss.Based on a contrast analysis of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Property Law,Tort Liability Law and Contract Law,the essay seeks to outline the tort liability and its application.
On the Logical Approach to Determine the Scope of Compensation for Damage to Property Tort reveals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property damage compensation.The essay underscores that the key to differentiate the principle of total compensa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limited compensati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whether the factors of determining property damage compensation are mono-basic or poly-basic.A total property damage compensation(system)chain is composed of damage theory and damage compensation theory,which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identification of damage,limitation of damage and a ruling on damage.The laws of the world tend to be the same in the identification stage,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legal concept.For the limitation of damage,there are two main types of damage:self-limiting type and interest restriction.In view of the central position and existing practice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ivil legal relationship,China’s law should limit the scope of damage to the extent of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In the discretion phase of the damages compensation,the scope of the compensation should be determined in terms of causality,profit and loss,and negligence.
On the Discretionary Rreduction of Tort Law undersco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 theory that the legislation should clearly stipulate the law on damages.It should be acknowledged from amulti-angle perspective of proportion principle,the principle of social justice,imputation basis and relevant theory of compensation scope,prohibition of abuse of rights principle and equity principle that discretionary reduction is of profou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lity,the existing system can not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inflictor is in serious trouble due to total compensation.The risk of applying the discretionary reduction is within a controllable range and its application is helpful in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This rule should be defined in the future Civil Code,and the factors that need to be considered should be enumerated incompletely,which should be made explicit so as to realize the certainty of applicable law to a large extent.
TortLiability;Infringementupon Property;Damage Compensation; TotalDamage Compensation;Discretionary Rreduction of Tort Liability
2017-05-20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FL14R03);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16JJD820015)
張玉東,男,煙臺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煙臺大學中歐侵權法研究院研究員,歐洲侵權法與保險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主要從事民商法學研究。
編輯 潭 影 王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