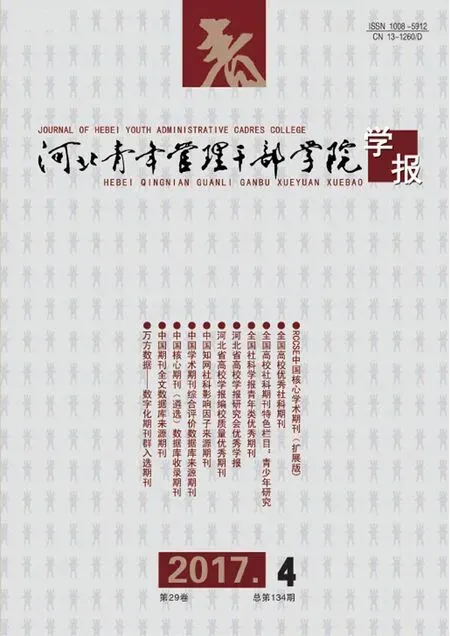佐哈爾:為翻譯文學(xué)正名
李天楊
(廣東外語外貿(mào)大學(xué) 高級(jí)翻譯學(xué)院, 廣東 廣州 510420)
佐哈爾:為翻譯文學(xué)正名
李天楊
(廣東外語外貿(mào)大學(xué) 高級(jí)翻譯學(xué)院, 廣東 廣州 510420)
以色列學(xué)者伊塔馬·埃文·佐哈爾(Itam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統(tǒng)論把翻譯研究從語言學(xué)領(lǐng)域帶入文化領(lǐng)域,他認(rèn)為,翻譯不再是本質(zhì)和界線一成不變的現(xiàn)象,而是一種與特定文化系統(tǒng)有千絲萬縷關(guān)系的活動(dòng)。他的多元系統(tǒng)論對(duì)翻譯學(xué)影響巨大,其價(jià)值在于拓展了翻譯學(xué)研究的廣度和深度,為翻譯學(xué)研究打開了一個(gè)新思路。
佐哈爾; 文學(xué)多元系統(tǒng); 翻譯文學(xué)系統(tǒng); 翻譯策略
引言
雖然“文化轉(zhuǎn)向”這個(gè)詞是英國(guó)華威大學(xué)(Warwick University)教授蘇姍·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首先提出來的,但是以色列學(xué)者伊塔馬·埃文·佐哈爾(Itammar Even-Zohar)是將翻譯研究從語言學(xué)視角帶入文化的奠基人,描寫派主力[1]。佐哈爾對(duì)俄國(guó)形式主義和捷克結(jié)構(gòu)主義進(jìn)行了多年研究,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一套全新的理論——多元系統(tǒng)化。他提出的多元系統(tǒng)化,不僅對(duì)翻譯學(xué)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而且對(duì)文學(xué)也具有很大影響。以“佐哈爾”為關(guān)鍵詞在中國(guó)知網(wǎng)上進(jìn)行檢索,按照“被引”排列檢索結(jié)果可以發(fā)現(xiàn),我國(guó)許多著名翻譯研究者都對(duì)佐哈爾及其理論進(jìn)行過研究并發(fā)表過相關(guān)論文;而按照“發(fā)表時(shí)間”排列檢索結(jié)果可以發(fā)現(xiàn),直到現(xiàn)在還有許多翻譯研究者使用多元系統(tǒng)理論進(jìn)行翻譯研究,還有很多學(xué)者對(duì)該理論本身進(jìn)行研究。佐哈爾和他的多元系統(tǒng)理論也是一代代翻譯新人初入翻譯研究領(lǐng)域時(shí)絕不會(huì)錯(cuò)過的。本文將對(duì)多元系統(tǒng)理論進(jìn)行闡述,以期對(duì)“該理論為何經(jīng)久不衰”這個(gè)問題作出一些回答。
一、問題的提出
筆者認(rèn)為,多元系統(tǒng)理論的提出緣起于文學(xué)翻譯和翻譯文學(xué)的區(qū)別。文學(xué)翻譯即忠實(shí)于原創(chuàng)的全翻譯,而翻譯文學(xué)是指采取適應(yīng)本國(guó)文化背景的翻譯策略、語言特點(diǎn)所產(chǎn)出的翻譯作品。佐哈爾將翻譯文學(xué)稱為向創(chuàng)作靠攏的“半翻譯”和“準(zhǔn)翻譯”(semi- and quasi-translations)。文學(xué)翻譯和翻譯文學(xué)的區(qū)別就在于對(duì)該社會(huì)、文化等產(chǎn)生的影響。翻譯文學(xué)對(duì)社會(huì)、文化的影響要遠(yuǎn)大于文學(xué)翻譯。所以,佐哈爾不同意形式主義者傳統(tǒng)的美學(xué)標(biāo)準(zhǔn),絕不以價(jià)值判斷為準(zhǔn)則來預(yù)先選擇研究對(duì)象[2]。他認(rèn)為兒童文學(xué)、恐怖文學(xué)以及翻譯文學(xué)等文學(xué)形式不是邊緣化的,而是具有文學(xué)造詣、社會(huì)作用和研究?jī)r(jià)值的。佐哈爾在他的《歷史詩(shī)學(xué)論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中第一次提出“多元系統(tǒng)”這個(gè)概念,他分別在1979年、1990年和1997年發(fā)表三篇文章對(duì)多元系統(tǒng)理論進(jìn)行論述。本文是對(duì)其1979年文章的翻譯和闡述,該文現(xiàn)收錄在Venuti教授的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中,篇名為《翻譯文學(xué)系統(tǒng)在文學(xué)多元系統(tǒng)中的位置》(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二、基本概念
在翻譯和闡述之前,筆者認(rèn)為有幾個(gè)基本概念是讀者需要知道的。第一,什么是多元系統(tǒng)?佐哈爾概括為:社會(huì)符號(hào)系統(tǒng)并非單一的系統(tǒng),而是多元系統(tǒng),也就是由若干不同的系統(tǒng)組成的系統(tǒng)。各個(gè)系統(tǒng)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有些子系統(tǒng)處于多元系統(tǒng)的中心位置,而有些則處于邊緣位置。第二,文學(xué)多元系統(tǒng)內(nèi)部是怎樣的?佐哈爾把他的研究定位在文學(xué)多元系統(tǒng),文學(xué)多元系統(tǒng)簡(jiǎn)單舉例來看是這樣的:第一層按地區(qū)國(guó)別來分類,我們有亞洲的中國(guó);第二層按文學(xué)類型來分類,我們有中國(guó)的詩(shī)、成人文學(xué)、兒童文學(xué)、恐怖文學(xué),等等;第三層按是否翻譯來分類,我們有翻譯的兒童文學(xué)和原創(chuàng)的非翻譯的兒童文學(xué);第四層按譯自哪國(guó)來分類,我們有分別譯自法國(guó)、美國(guó)、俄羅斯、拉美國(guó)家或者其他國(guó)家的兒童文學(xué)。第三,什么是形式庫(kù)?形式庫(kù)(repertoire)是支配文本制作的規(guī)律和元素(可能是單個(gè)的元素或者整體的模式)的集成體[3]。佐哈爾認(rèn)為,任何系統(tǒng)產(chǎn)品的制造和使用方式都由形式庫(kù)控制[3]。探討文學(xué)和翻譯,“形式庫(kù)”是讀者必須知道的概念。
三、主要觀點(diǎn)
以下是筆者對(duì)原文進(jìn)行的翻譯和闡述,原文分五部分,以數(shù)字分隔,均沒有標(biāo)題,筆者根據(jù)自己的理解對(duì)各部分主要內(nèi)容進(jìn)行了概括,并加上了標(biāo)題。
(一)關(guān)于翻譯文學(xué)系統(tǒng)的存在和建立
作者首先指出,通過對(duì)各種史料的研究,史學(xué)家有一個(gè)共識(shí),那就是翻譯對(duì)一個(gè)國(guó)家文化的形成和發(fā)展起著重要作用,是塑造民族文化以至世界文化的一股重要力量,比如佛經(jīng)翻譯對(duì)中國(guó)文化形成和發(fā)展有重要影響,但很少有學(xué)者談及這個(gè)問題。也很少有學(xué)者談及翻譯文學(xué)在文學(xué)多元系統(tǒng)中的具體作用和地位。因此,作者在這里設(shè)問,翻譯文學(xué)的背后是不是也存在著像原創(chuàng)文學(xué)中一樣的文化和語言關(guān)系的網(wǎng)絡(luò)進(jìn)而能夠形成系統(tǒng)呢?作者指出,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gè)方面來看這個(gè)問題,即選擇方面和借用方面。第一方面即選擇方面,筆者在這里用楊憲益先生的一段話來說明,“不幸的是,我倆(還有其夫人戴乃迭)實(shí)際上只是受雇的翻譯匠而已,該翻譯什么不由我們做主,而負(fù)責(zé)選定作品的往往是對(duì)中國(guó)文學(xué)所知不多的幾位年輕的中國(guó)編輯,中選的作品又必須適應(yīng)當(dāng)時(shí)的政治氣候和一時(shí)的口味,我們翻譯的很多這類作品并不值得我們?yōu)樗速M(fèi)時(shí)間。”[2]通過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在楊先生所描述的那個(gè)年代,被選中的翻譯文學(xué)都帶有極強(qiáng)的與文化和語言有關(guān)的共同點(diǎn),比如都受當(dāng)時(shí)的政治氣候影響,因目的語(我們將有關(guān)的環(huán)境如楊先生所處的時(shí)代,人如楊先生描述的編輯等因素在這里通稱為目的語)的選擇,這些共同點(diǎn)使各個(gè)獨(dú)立的翻譯文學(xué)作品形成文化和語言的網(wǎng)絡(luò),進(jìn)而形成系統(tǒng)。第二方面即借用方面,筆者用一個(gè)例子來說明,清末民初我國(guó)現(xiàn)代小說形式庫(kù)的形成和發(fā)展很大程度上來源于翻譯,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語言、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方面都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對(duì)當(dāng)時(shí)青年、學(xué)者的思想觀念、理論、行為甚至產(chǎn)生了顛覆性的作用,這些影響是實(shí)實(shí)在在存在過的,這些影響具有共同的特點(diǎn),那么從影響這個(gè)角度來看,翻譯文學(xué)系統(tǒng)也應(yīng)該是存在。這兩點(diǎn)共同告訴我們,翻譯文學(xué)系統(tǒng)也是存在的,是有其文化和語言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的。證明了翻譯文學(xué)系統(tǒng)的存在,那這個(gè)系統(tǒng)在文學(xué)多元系統(tǒng)中的地位和作用又是怎樣的?是中心的還是邊緣的?是創(chuàng)新突破的還是保守陳舊的?是基本的還是次要的?在這里,作者用了一個(gè)比喻來引導(dǎo)我們對(duì)這些問題的看法,他并沒有直接回答這些問題,而是說無數(shù)個(gè)多元系統(tǒng)就好比星群(constellation),這些問題的答案是由翻譯文學(xué)系統(tǒng)與這個(gè)星群的關(guān)系決定的。
(二)關(guān)于翻譯文學(xué)系統(tǒng)的位置和發(fā)展演進(jìn)
作者首先討論了翻譯文學(xué)系統(tǒng)處在中心位置時(shí)的幾個(gè)問題。為系統(tǒng)走向中心位置出力的翻譯家,作者稱他們?yōu)橄蠕h,筆者認(rèn)為處在中心位置的系統(tǒng)便可以稱為先鋒。這個(gè)位置是與文學(xué)史上的情況(由諸多事件組成)相融合的,這些事件決定了翻譯文學(xué)系統(tǒng)的能力和前景。作者說,在三種情況下,翻譯文學(xué)系統(tǒng)將處在中心位置。其一,文學(xué)系統(tǒng)尚未形成還很年輕(when a polysystem has not yet been crystallized, that is to say, when a literature is “young”,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established),中國(guó)清末民初時(shí)的翻譯文學(xué)便是一個(gè)較好的例證。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還處于“細(xì)嫩”狀態(tài),我國(guó)作家自己創(chuàng)作的現(xiàn)代意義上的小說還沒有出現(xiàn),白話詩(shī)有待探索,話劇則連影子都沒有,于是翻譯文學(xué)便成了滿足當(dāng)時(shí)新興市民階層的文化需求的最主要來源,翻譯小說占當(dāng)時(shí)出版發(fā)表的小說的五分之四[2],翻譯文學(xué)豐富了我國(guó)現(xiàn)代小說、白話詩(shī)、話劇等文學(xué)形式的形式庫(kù)。其二,某個(gè)文學(xué)系統(tǒng)在文學(xué)多元系統(tǒng)處在邊緣或虛弱狀態(tài)(when a literature is either “peripheral” (within a large group of correlated literatures) or “weak” or both),“文化大革命” 時(shí)期的翻譯文學(xué)是一個(gè)較好的例證。由于特定歷史、政治、文化條件的制約,原本資源非常豐富且在歷史上一直是周邊國(guó)家(東亞及東南亞國(guó)家日本、朝鮮、越南等)的文學(xué)資源的中國(guó)文學(xué),此時(shí)卻處于“弱勢(shì)”和“邊緣”地位,而蘇聯(lián)(高爾基的《母親》)、越南、朝鮮、 阿爾巴尼亞等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的文學(xué)作品,連同日本無產(chǎn)階級(jí)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的作品, 在當(dāng)時(shí)都被翻譯引進(jìn)國(guó)內(nèi),產(chǎn)生了不小的影響[2]。其三,轉(zhuǎn)折點(diǎn)、危機(jī)或文學(xué)真空期的出現(xiàn)(when there are turning points, crises, or literary vacuums in a literature),“五四”時(shí)期的文學(xué)翻譯可以較好地印證這一點(diǎn)。這些情況下的翻譯和原創(chuàng)很接近[2],創(chuàng)作的成分很少。
在這一部分,作者還特別強(qiáng)調(diào)了三點(diǎn):其一,“虛弱”的文學(xué)系統(tǒng)帶來創(chuàng)新的能力定不如那些強(qiáng)大的或處于中心的文學(xué)系統(tǒng),在“文革”時(shí)期,譯自越南社會(huì)主義文學(xué)的翻譯文學(xué),我們當(dāng)然要肯定它們的作用,但是這個(gè)本來就較為弱小的系統(tǒng)帶來的創(chuàng)新及影響力,不如譯自處在中心位置的蘇聯(lián)文學(xué)的翻譯文學(xué)帶來的影響力。其二,有些文學(xué)多元系統(tǒng)的等級(jí)在其形成伊始便已較為堅(jiān)固,比如在歐洲文學(xué)中出現(xiàn)了以上三種情況的一種或多種時(shí),其受到的影響就可能不會(huì)像中國(guó)文學(xué)那么大。其三,翻譯文學(xué)帶來了原創(chuàng)文學(xué)形式庫(kù)的創(chuàng)新,也使得原創(chuàng)文學(xué)系統(tǒng)內(nèi)部獲得重新洗牌的機(jī)會(huì)以及許多其他的新的可能。
當(dāng)翻譯文學(xué)系統(tǒng)處在邊緣位置時(shí),就是一種保守的情況,此時(shí)在進(jìn)行文學(xué)翻譯時(shí),絕大多數(shù)情況都要求(有時(shí)甚至是必須)使用目的語原有的詞匯和表達(dá)(當(dāng)然這些原有的原創(chuàng)的詞匯表達(dá)本身也在發(fā)展),與目的語稍有偏差,即被視為罪過[3]。在這種情況下便形成了一個(gè)關(guān)乎翻譯本身的引入和保守的矛盾,那就是:進(jìn)行翻譯,一個(gè)很大作用就在于引入新的表達(dá)、新的思想,而處在邊緣位置的翻譯文學(xué)系統(tǒng)只能保守舊有的表達(dá)和思想,這當(dāng)然不利于翻譯文學(xué)系統(tǒng)走向中心去。
討論了兩種位置問題,作者簡(jiǎn)要提及了兩點(diǎn)有關(guān)系統(tǒng)發(fā)展的問題。作者說,隨著系統(tǒng)的不斷發(fā)展,曾經(jīng)在中心位置的系統(tǒng)也會(huì)保守起來,以此來保護(hù)這個(gè)系統(tǒng)所帶來的形式庫(kù),如嚴(yán)復(fù)的理論原是個(gè)一級(jí)模式 但走進(jìn)中心之后,固定下來,就變成了二級(jí)模式,形成了新的保守主義,阻礙了翻譯研究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4]。還有一種情況是,處在次級(jí)的系統(tǒng)甚至?xí)褐聘渭?jí)的系統(tǒng)。
(三)關(guān)于翻譯文學(xué)系統(tǒng)的分層和正名
作者認(rèn)為,翻譯文學(xué)系統(tǒng)內(nèi)部也是分層的,他以二戰(zhàn)時(shí)期的希伯來文學(xué)為例對(duì)這個(gè)問題進(jìn)行了說明。相較英、德、波等語言的翻譯文學(xué),蘇聯(lián)翻譯文學(xué)在當(dāng)時(shí)的希伯來文學(xué)中占據(jù)著無可置疑的中心地位,希伯來文學(xué)形式庫(kù)所引入的最具創(chuàng)新精神的詞匯和表達(dá)皆從俄語翻譯文學(xué)而來,其他引入詞匯和表達(dá)都是英、德、波等次級(jí)語言翻譯文學(xué)通力合作的結(jié)果,它們的影響力遠(yuǎn)不及蘇聯(lián)翻譯文學(xué)。
討論到這里,筆者認(rèn)為,為翻譯文學(xué)正名的問題就正式出現(xiàn)了〔作者并沒有在原文中表達(dá)正名的意思,該正名是筆者通過原文(以下原文筆者未做改動(dòng))對(duì)作者意圖的猜想〕。作者說目前的研究還不能確保翻譯文學(xué)有特別的地位,或者說中心地位,翻譯文學(xué)還是邊緣的,尤其是考慮到不同國(guó)家、地區(qū)的文學(xué)多元系統(tǒng)的特點(diǎn),比如法國(guó)文學(xué)多元系統(tǒng)內(nèi)部就是十分堅(jiān)固的,翻譯文學(xué)很難有所作為,而法國(guó)文學(xué)對(duì)整個(gè)歐洲文學(xué)影響十分深遠(yuǎn),但隨著翻譯文學(xué)系統(tǒng)自己的發(fā)展以及各種新情況的發(fā)生,處在邊緣地位的翻譯文學(xué)系統(tǒng)就有發(fā)展到中心地位的可能性,就有發(fā)揮作用的可能。筆者認(rèn)為,我們不需要也不可能要求翻譯文學(xué)系統(tǒng)時(shí)時(shí)處在中心,但翻譯文學(xué)系統(tǒng)處在中心位置的可能性及其相應(yīng)的影響是我們必須看到的,這大概就是作者想要為翻譯文學(xué)正的名。
(四)關(guān)于在兩種不同位置下翻譯者的不同翻譯策略
在翻譯文學(xué)系統(tǒng)處在中心位置時(shí),作者認(rèn)為此時(shí)的翻譯模式是一級(jí)創(chuàng)造模式,簡(jiǎn)單來說就是去引入新的詞匯和表達(dá)形式,打破目的語原有的、固定的詞匯和表達(dá)形式,這個(gè)作用還是產(chǎn)生在目的語形式庫(kù)中的。作者在這里特別強(qiáng)調(diào),在進(jìn)行引入和打破的創(chuàng)造過程中、在與目的語自身文學(xué)系統(tǒng)的競(jìng)爭(zhēng)過程中,一旦因?yàn)榉g文學(xué)系統(tǒng)太過于具有原語的特點(diǎn)、太過于革命而失敗的話,它將再無東山再起之日。
在翻譯文學(xué)系統(tǒng)處在邊緣位置時(shí),作者認(rèn)為此時(shí)的翻譯模式是二級(jí)保守模式,翻譯者只得套用目的語中原有的、固定的詞匯和表達(dá),這種模式下的翻譯多是不充分的,只是可接受的。
以上這些策略手段絕不是一個(gè)涇渭分明的問題,一級(jí)創(chuàng)造模式下不是肆意可以打破的,二級(jí)保守模式下也不是沒有引入和創(chuàng)新,到底采取什么樣的策略和手段還是要看目的語本身文學(xué)系統(tǒng)的允許程度、開放程度和官方認(rèn)可程度。
最后作者用這樣一句話結(jié)束了全文:翻譯不再是本質(zhì)和界線一成不變的現(xiàn)象,而是一種和特定文化系統(tǒng)有千絲萬縷關(guān)系的活動(dòng)。
四、評(píng)價(jià)
首先是根茨勒(Gentzler)教授說佐哈爾的多系統(tǒng)理論使翻譯研究不再只是孤立的語言學(xué)研究,帶來了描述性的翻譯研究和文化轉(zhuǎn)向,這也與佐哈爾在第一部分中“星群”的觀點(diǎn)相呼應(yīng)。當(dāng)然,佐哈爾的觀點(diǎn)也有缺點(diǎn),根茨勒教授總結(jié)如下:其一,佐哈爾的理論實(shí)際例子太少。其二,關(guān)于多元系統(tǒng)理論,大部分都是佐哈爾自己的邏輯,自己的假說。這種理想化的模型缺乏對(duì)現(xiàn)實(shí)中真實(shí)存在的各種情況的考慮,尤其是沒有考慮各種束縛條件和缺少對(duì)譯者本身的關(guān)照。其三,佐哈爾說多元系統(tǒng)是科學(xué)的模型,這個(gè)模型真的客觀嗎[5]192-197?
謝天振教授對(duì)佐哈爾多元系統(tǒng)論給予很高的評(píng)價(jià),其一,“多元系統(tǒng)理論把翻譯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它把翻譯與譯作與所產(chǎn)生和被閱讀的文化語境、社會(huì)條件、政治等許多因素結(jié)合了起來,為翻譯研究開拓了一個(gè)相當(dāng)廣闊的研究領(lǐng)域。”[2]其二,使人們能從更廣泛的范圍來看待翻譯問題,以把握它的真正本質(zhì),可以使人們不再糾纏于原文和譯文間的對(duì)等問題,而把譯本看作是存在于目標(biāo)系統(tǒng)中的一個(gè)實(shí)體,來研究它的各種性質(zhì)。正是這一點(diǎn)后來發(fā)展成了 Toury 的“目標(biāo)側(cè)重翻譯理論”(Target- oriented approach)。其三,既然譯文并不只是在幾種現(xiàn)成的語言學(xué)模式里作出選擇,而是受多種系統(tǒng)的制約,那么就可以從更廣泛的系統(tǒng)間傳遞的角度來認(rèn)識(shí)翻譯現(xiàn)象。”[2]
根茨勒教授和謝天振教授的評(píng)價(jià),筆者認(rèn)為是對(duì)其他許多研究者評(píng)價(jià)的概括和總結(jié),較具有參考意義,限于篇幅,筆者不再轉(zhuǎn)引其他學(xué)者的評(píng)價(jià)。
五、思考
研讀原文幾遍,且看過一些評(píng)論后,筆者自己有兩點(diǎn)想法。其一,佐哈爾的多元系統(tǒng)理論的價(jià)值是巨大的,多元系統(tǒng)理論把翻譯學(xué)從語言學(xué)研究帶入了文化學(xué)研究領(lǐng)域,其研究成果極大地推動(dòng)了翻譯學(xué)的發(fā)展,拓展了翻譯家的視角,讓很多研究者從更高更廣的層次認(rèn)識(shí)翻譯學(xué)、研究翻譯學(xué)。或許這也正是“這一理論經(jīng)久不衰”的原因。作者在上文中論述的每一部分都可以單獨(dú)拿出作為各種不同研究的理論依據(jù),或者對(duì)各部分的理論本身進(jìn)行研究、深挖和發(fā)展。這也是本文開頭說該理論是經(jīng)典理論的原因之一。其二,作者關(guān)于翻譯文學(xué)系統(tǒng)的觀點(diǎn)是不是可以推廣到其他類型的翻譯呢?比如科技翻譯。筆者認(rèn)為,答案應(yīng)該是肯定的。
[1] 林克難. 翻譯研究:從規(guī)范走向描寫[J]. 中國(guó)翻譯,2001(6):43-45.
[2] 謝天振. 多元系統(tǒng)理論:翻譯研究領(lǐng)域的拓展[J]. 外國(guó)語,2003(4):59-66.
[3] [以色列]伊塔馬·埃文·佐哈爾.多元系統(tǒng)論[J]. 張南峰譯.中國(guó)翻譯,2002(4):21-27.
[4] 張南峰. 從邊緣走向中心——從多元系統(tǒng)論的角度看中國(guó)翻譯研究的過去與未來[J]. 外國(guó)語,2001(4):61-69.
[5] [美]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M].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編輯:劉小明
2017-02-16
李天楊(1992—),男,廣東外語外貿(mào)大學(xué)高級(jí)翻譯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美國(guó)明德大學(xué)蒙特雷國(guó)際研究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譯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