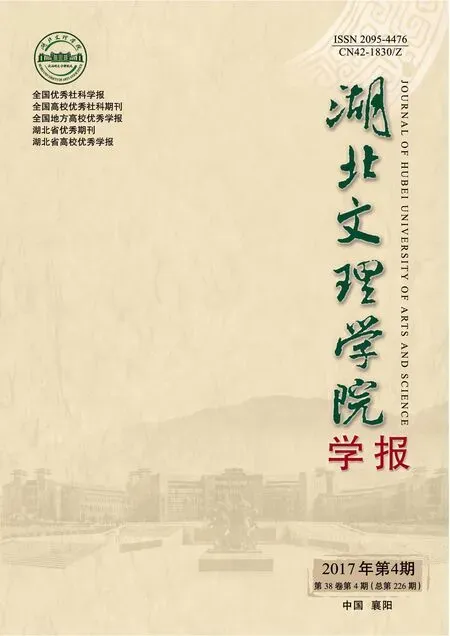人的道德位格之淪落
——斯密道德規則的內蘊
郭敏科
(首都師范大學 政法學院,北京 100048)
政治、經濟學研究
人的道德位格之淪落
——斯密道德規則的內蘊
郭敏科
(首都師范大學 政法學院,北京 100048)
亞當·斯密以自己獨到的經濟學視野闡釋了一個道德規則:主觀為己,客觀為人。這一特定時期的道德規則包含了四個方面的內容,即人和人的關系、物質地位與精神地位的關系、道德追求的崇高性和知行關系。這四個方面集中體現了人的道德位格的降低,人們對向神而生的道德追求的輕視和對物質需要的過分追逐,作為人的特殊性的德性地位開始下降,人們對物質的要求超過對其自身德性的要求并慢慢呈現占據上風的趨勢。主觀為己,客觀為人這一道德規則內蘊的多種可能性,不僅要求追求人自身價值的特殊性即德性,同時也迫切的昭示需要一種外部的正義原則來調節道德和利益面臨的正面交鋒。
亞當·斯密;道德規則;道德位格
一、背景與內涵
主觀為己,客觀為人的道德規則最早比較充分的體現在亞當·斯密的思想中。它是工業革命背景下人們對市場經濟與道德倫理的關系的處理中促生的。18世紀中期,英國市場經濟已經興起,工場手工業極為發達,中世紀被禁錮的人身自由在致富動力的推動下得以釋放,個人追求自身權益的沖動和愿望在經濟力量增強的同時變得十分迫切。與此同時,圍繞如何看待和處理市場經濟與道德倫理的關系這個嶄新的歷史性課題,出現了截然不同的思潮和主張:一種堅持傳統基督教以“仁慈”為核心的道德哲學體系,譴責當下社會的種種丑行和弊端,甚至懷疑市場經濟之路的正確性;另一種主張迎合市場經濟之勢,推崇極端利己主義——孟德維爾的“私人惡行即公利”;還有一種主張走中庸之道,既要肯定市場工商業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和進步性,又要肯定堅持和發展傳統美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斯密的重要思想正是在這一時代課題下得以建立的。
同時這一規則也是斯密卓越的經濟思想和道德哲學思想相結合的產物。亞當·斯密的卓越思想不僅體現在經濟學,同樣也體現在倫理學中。經濟學專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文譯本作《國富論》)和倫理學專著《道德情操論》,是斯密著稱于世的兩部經典著作。他注意到道德領域和經濟領域所蘊涵的不同規則,同時也為此建立了兩個截然不同的體系,于是有了眾所周知的“斯密問題”,即在經濟視野中,他以人性自私為邏輯起點,闡述了“經濟人”行為的利己性;而他在《道德情操論》的道德視野中,以人性的同情為起點,強調了“道德人”行為的利他性。
斯密將經濟領域的規則應用于道德領域才產生了這一道德語言形式。他說,“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的促進社會的利益。”[1]27
“按照斯密的思想,‘經濟人’行為的動機雖是個人私利,且追求的目標是個人利益最大化,但‘經濟人’的這種自利傾向,在‘看不見的手’的指導下,其行為結果非但不損人,反而更有益于他人,即主觀為己客觀為人。”[2]243
每一種道德語言規則的出現和演變都與其所處的時代特征相對應,主觀為己,客觀為人的道德規則的出現不僅意味著不同時代道德語言形式的變遷,同時也從內部折射出人的道德維度的多層次性拓展,這一道德規則不僅內嵌于人們對人性本質認識的深化,同時也反映了人們生活的道德實質的內容在四個方面的重要變化,這集中體現了一個令我們憂慮的核心問題:在道德領域人的位格的降低。
二、人和人的關系
人和人之間的相互關系變遷影響了道德規則的變化。人和人相互的需要催生了社會共同體的產生和發展。為了維持和發展自己與他人共同的利益,不僅需要外在的法律上剛性的明確保障,同時也需要內在的柔性的道德規則加以勸導,主觀為己客觀為人正是與這一關系相對應的產物。
這一規則是建立在人和人的相互關系之上的,這一關系在斯密的理論中有如下說明:
第一,交易及相互需要的關系,這一關系因之于人類的利己心。斯密認為,分工協作、互通有無、互相交易的傾向,是人類共有的性能,也是人類特有的性能。“他如果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訴他們,給他做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論是誰,如果他要與旁人做買賣,他首先就要這樣提議:請給我以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1]13利己心是行為的動力,是關系的紐帶,這一道德規則正是人們交往方式的體現。
這一交往方式內在的自我調節動力和機制也是由于利己心的作用,他說,“個人的利害關系與情欲,自然會使他們把資本投在通常最有利于社會的用途。但若由于這種自然的傾向,他們把過多的資本投在此等用途,那么這些用途利潤的降落,和其他各用途利潤的提高,立即會使他們改變這種錯誤的分配。用不著法律干涉,個人的利害關系與情欲,自然會引導人們把社會資本,盡可能按照最適合于全社會利害關系的比例,分配到國內一切不同用途。”[1]14
第二,利己心是人的情感判斷的標準和行為選擇的原則。利己心是“支配個人的一切行動,使其在某一問題上根據利害觀點選擇某一行動的原則”。[3]這一利己心是人類社會得以發展的動力,尤其是在經濟領域,每個人在不違反法律的前提下,讓每個人自由的去追逐他最大的利潤,社會就會自然而然的合理分配資本,增進社會的公共福利。由此,個人私利和公共利益經過自然的平衡和調解,是不會相互對立的。每個人由利己出發,最終能夠利他。“每個人在滿足自己的利益的同時,就包含著對社會公共福利的增進。這就是所謂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斯密命題”。
第三,如何保證這一道德規則的實施問題也就是如何處理市場經濟與道德倫理的關系問題。這一規則預設了重要的前提條件,即自然的公正秩序,只有處在合理的公正的透明的競爭秩序之中,人類的利己心才能夠和利他的利益相統一。斯密時代的這種秩序就是他所說的“看不見的手”,它能夠“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的促進社會的利益。”[1]27他認為這是基于自利的商品交換規律的作用,以一種不依人們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法則的力量。
這種自然的公正秩序不僅在經濟領域同時也在道德領域有著同樣的要求。所以,斯密的這一論題體現出經濟和道德兩個不同領域的適用規則的差異性,同時也體現出人類規則內部與外部兩種不同的秩序,即內在的道德秩序與外在的使道德秩序得以存在和踐行的外部公正制度。保證和實施這一道德規則并使之有益于我們社會的關鍵點就在于,營造一種接近于自然公正秩序的外部制度,以使利己心最終與利他心在動機和結果上達成一致,以此既保證了道德動機的首發性和自主性,同時也使人和自己、人與人、個人與社會在三者關系上實現統一,既解決了道德的動機問題,又解決了道德的回報問題,這是我們可以借鑒的地方。
第四,這一道德規則的出現在歷史維度中體現出一種人的道德標準的內部流變。這是從古希臘、中世紀到近代這一經濟基礎的根本變革所推動的,道德規則與道德的基礎、社會的經濟狀況和政治狀況和時代需要是一一對應的。當社會生產力低下的時候,自給自足的經濟狀況對應的就是簡單素樸的內在的自我幸福,人和人的聯結關系呈現出弱化的特征,最直接的表現就是不依靠別人我們也能生活下去,人的社會性并未被完全發掘出來,人還沒有成長為現代意義上完整的人,人的本質由于經濟基礎和時代條件的限制并未完全體現。當人們并沒有更多的利益交鋒的時候,就缺少道德沖突的條件,道德沖突的條件被限制在自我之內的時候,追求自我的幸福就較可能成為德性的幸福的第一追求。自我實現的意義雖然離不開社會,但是社會條件在此刻不是充分必要的條件,而是不充分也不必要的條件,人和人的關系的弱聯系就引導人和社會的關系并不是多么強烈,人們有條件在社會之外去尋求到另外一種幸福。在近代工業化以前,人口數量較少,人類的拓展空間范圍卻很大。我們對于幸福的定義和選擇在社會層面并不必然,道德踐履和自我實現在自我之內就能實現,不需要迫切的完全進入社會之中。社會實現的選擇項位于我們所有備選項的較低層次,因而人們有條件也傾向于追求內在的自我幸福實現。
人和人的關系是人和社會的關系得以存在的基礎和前提。人們關系的弱聯系,利益沖突的減少,與之相對應的道德規則是呈現出黃金律“愛人如己”的形式。但是隨著人們關系的加強,利益沖突的增多,與之相對應的道德規則出現新的形式,即要像別人愛你那樣愛別人,直到呈現為主觀為己客觀為人的道德規則。
這種道德規則的演變是有本質區別的。前者是無條件的推己及人,后者是有條件的行善,行善不再是完全的個人的主動行為和不求回報,而是含有被動的條件交換和利益平衡。
人和人關系的演變是等價交換道德規則的一個內部特征,與之相對應的還有產生這一道德規則的經濟基礎所呈現的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等價交換原則。“斯密的這個思想就是后來被黑格爾所指由主觀利己心轉化為對其他人有利的那種‘辯證運動’,這個理論是以市場經濟的等價交換原則為基礎的,它正是在市場經濟關系中包含著的合理利己主義和互利的道德原則。”[2]340而我們所憂慮的,正是人們在對道德多維度和深層次的認識過程之中,將道德的最低標準和最高追求的混淆運用,將道德的崇高性作為一種以經濟利益為目標的手段去交換,人的道德位格在此呈現出一種衰落。
三、物質地位與精神地位
斯密所處的時代,正處于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初級階段,斯密利用個人的知識背景和時代背景的雙重結合,將經濟活動領域的運行規則運用于倫理領域,以人性自私為起點,以等價交換的原則為基礎,共同催生了這一道德規則的出現,“請給我以我所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需要的東西。”[1]20
“在斯密的心里,人同時有著‘經濟人’和‘道德人’兩種特性或身份,因而人的生活世界也有著經濟與道德、物質與精神或者靈與肉之兩面,就像金和銀可能同時成為一面盾牌的兩面一樣。”[4]主觀為己客觀為人這一道德規則正是合宜的處理自身生活和行為的一種表達,也是人在經濟關系和道德關系中的展現。經濟基礎影響人們的物質需要層次,同時,也影響著人們的精神需要和物質需要二者的關系和地位,也將涉及人類社會所要面臨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關系問題。
同時,經濟領域的等價交換原則催生了人的道德領域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平等性,完全主動的自我道德之律轉變為以自我需求和自我主動作為共同的結合體的道德律。人的道德追求的降低,帶來人的道德本質屬性的降低,人的道德位格在這一程度淪落了。
亞里士多德認為真正的德性是完全的精神層面的自得,是作為德性的自我幸福,是自我的價值體現和愉悅的情感舒張,是我們自我意識的內在幸福。現在,對于道德的要求涉及了精神層面與物質層面雙重領域,道德要求被作為回報的德性,是物質層面的利益滿足和精神層面的情感需求的共同考量,是內在幸福與外在需求的二者合一,這是時代和人的共同發展促生的。但是某種程度上將道德作為發展和滿足物質需要的手段,卻使人在道德上的向往,由純凈的神性位格向神而生的狀態,開始轉變為與利益駁雜而生的回報道德向物看齊的狀態,人的道德性和神性位格在失去了對道德崇高的向往之時,因而變得渺小了。
四、道德追求之君子不器
孔子說,“君子不器。”[5]基本含義是君子不應該像器物一樣,這里我們可以用一個衍伸意義,即人不能和物一樣。人不能像物一樣,作為物質的本質特征就是需要,滿足人的某種特定的需要,這是物的特性。而精神需求,是作為人的特性。人的身體屬性及與他存在的限定性的物質組成層面,我們在此有著同樣的構造和同樣呼吸。在物性之中并不能體現出人的差異和價值屬性,人的價值屬性正是在特殊性之中所體現的,這一特殊性對應的就是人的精神屬性。
而作為特殊性的另一個認識就是,特殊性比普遍性更加接近事物的價值和意義所在。普遍性作為一種客觀事實,特殊性才體現出事物的價值屬性。換句話說,特殊性才是價值這個詞語的核心意蘊,而需要是低層次的滿足層面。主觀為己客觀為人這一規則不應該也不能夠表現道德生活的全部內容和最高根據,而且對它的誤用都易于喪失道德的絕對性價值,而“道德的至上價值就在于它能夠滿足作為主體的人的需要”。[6]
同時,人與物的區別也體現在目的的追求之中,人以其理性決定為目的。阿奎那說,“有理智者追求一個目的,是把這個目的決定為自己的,而自然物追求一個目的,就不是把這個目的自己決定為一個目的,因為它們不知道這個目的的本性。”[7]而且,人的價值是自身賦予的,“事物的價值是我們的意識給它們的”[8],物質需要的多樣性是我們生活的內容,但是物質的價值卻是應該服務人于人的,德性作為人的一種價值屬性也不應當被用作滿足物質需要的手段。
某種程度上,人向物的過渡和沉淪就意味著物的有限性和被動型也將更多的深深地體現在我們的生活烙印之中,也就意味著我們將淪為被機器取代的機器,被工具取代的工具,主體理性生命和人類自身價值和存在意義的消亡。
五、知行關系之道德的崇高性
從愛人如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規則到主觀為己客觀為人的道德規則的轉變折射出道德內容的變遷,也是特殊性價值在知行關系領域的拓展。
這也表現在等價交換的道德規則和不損害他人的最低要求之上。道德內蘊兩種實現形式,理論認知的層面和實踐的層面,即知行兩個不同的層面。
道德的核心屬性和最高追求恰恰體現在理論認知的高度和不可到達的完美屬性上,即道德追求神域,我們應向神而生。在這一意義上,最高的知應該成為實際行動的最終目標和價值規定性,道德實踐只有符合至善的追求,才能稱之為善。恰恰是主觀為己客觀為人的道德規則之內,人的向往要求的降低,將把我們引向物而不是神的發展方向。所以,這一道德規則缺陷性就在于將道德的知的最高意義貶低了,實質上,它以行動的最低要求作為了我們的道德原則。
道德認知要確立一個最高的價值和意義,這是道德認知的一個特有要求和屬性,那么在道德實踐的層面,即行的層面,我們的要求恰恰和知是相反的,對于行的要求恰恰應該是最低的,而不是最高的。對于這種道德要求的演變,我們必須警惕的一點和全面看待的一點就是,知行兩個層面的完整客觀看待,即在知的層面,保持道德的最高價值屬性,在行的層面,保證切實可行,從低要求而不是從高。
主觀的出發點對應最高道德的標準,客觀利他是行動的最低標準,這也應作為重要的限制而作為我們道德秩序的一部分,因為“沒有限制的自由肯定是不存在的;脫離了社會秩序就沒有人的存在,人只能通過社會秩序來發展自己的個性,并且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9]
這二者應該明確,行動的最低標準不能作為道德的最高價值,這就會淪為物性的從屬,純粹的以功利化為目的的人;道德的最高價值如果脫離了實踐的行動源泉和可行性,那也將變為空洞無物的說教。我們不僅要在知行關系中去理解人的道德規則,同時要“把‘個性’的多種可能性看作理解世界和生活的鑰匙”[10]。康德強調的道德行為本身的無條件是對這一道德規則的最佳勸誡,“這樣的善良意志不是因快樂而善,因幸福而善,或因功利而善,而是因其自身而善的道德善。”[11]
亞當·斯密的這一道德規則內蘊著時代的內容和多維度的方向,我們應該全面的看待其在當時的影響和當今的借鑒意義。
它的一種可能性就是,人們可能慢慢地輕視道德要求。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力量的均等的事實需要我們人類自身理性對自我更多的掌控力,以免使人們忽視道德在社會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以物質需要為主導可能會讓德性成為附庸,精神需要服從于物質需要。這種轉變的可能性預示著人的內在的特殊的道德規定性到物的普遍規定性的轉移。
同時,道德可能成為滿足物質需要的手段。道德是為人所特有的特殊性,而特殊性才是事物存在的根本價值和意義所在。我們不能喪失自己獨有的特性能力而淪落為物的有限性和規定性的層面。人應該做人應該做的事。這種可能性就是,機器可能與人平等,而在拋開自己優勢的這一領域,我們終將被物擊敗,成為物的奴隸,被機器所奴役。作為人的自由何在!物應當是使人發展的手段,我們不能用我們發展的東西最后毀滅了我們自己。
因此,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德性應當是人的第一屬性和最終意義和價值歸宿,“只有那由自身而被選取,而永不為他物的目的才是最后的。”[12]作為人的價值屬性,它應當成為最后的目的,人畢竟不僅僅屬于自然物,道德追求才能體現他應有的崇高。道德人格的價值存在于德性之中,尤其最完全的展現在對崇高的追求之中的,如康德所說,一個斯多亞派哲學家“在痛風劇烈發作時喊道:疼痛,你盡可以如此厲害的折磨我,我仍然將永不承認你是一種惡的東西;人們可以笑話他,但他的確是對的。他感覺到這里是一種禍害,而他的叫喊就吐露了這一點;但是,他沒有理由承認,惡因此就附著他了;因為疼痛絲毫不降低他人格的價值,而只是降低了他境況的價值。”[13]
君子不器,人物有別。我們不僅需要自己對自己的內在的掌控力,同時也要在外部制定一種正義的規則來平衡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關系,以外在的理性規約來防止我們滑向肆意情感的深淵,人應該做人應該做的事,應該追求人所追求的。我們所拋棄的自身的最閃耀的部分,恰恰是我們偉大的先賢最自豪的部分,亞里士多德對此深情的說道,“如果努斯是與人的東西不同的神性的東西,這種生活就是與人的生活不同的神性的生活。不要理會有人說,人就要想人的事,有死的存在就要想有死的存在的事。應當努力追求不朽的東西,過一種與我們身上最好的部分相適合的生活。因為這個部分雖然很小,它的能力與榮耀卻遠遠超過身體的其他部分”。[14]
[1]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2] 宋希仁.西方倫理思想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3] 坎 南.亞當·斯密關于法律、警察、歲入和軍備的講演[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4] 羅衛東.情感秩序美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5] 朱 熹.四書章句集注[M].長沙:岳麓書社,2008.
[6] 李亞彬.道德哲學之維——孟子荀子人性論比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7] ANTON C PEGIS.The Basic Writings of Thomas Aquinas[M].New York: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c,1995.
[8] 蒙 田.蒙田隨筆[M].梁宗岱,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9] 查爾斯·霍頓·庫利.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10] 鮑迪爾拉夫.德意志史[M].柏林:迪特爾·拉夫出版社,1985.
[11] 康 德.道德形而上學原理[M].苗力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2] 苗力田.亞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13] 康 德.實踐理性批判[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
[14] 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M].廖申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The Falling of Man’s Moral Position:Connotation of Smith’s Moral Rules
GUO Minke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China)
Adam Smith in his own economic perspective explains a moral rule that is subjective for oneself and objective for others.The moral rule of this particular period contains four aspects,that i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huma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 status and spiritual status,the sublime of moral pursuit,knowledge and action.The four aspects reflect a trend that people gradually ignore the lofty and people began to pursue material needs too much.The moral rule contains many possibilities.It not only requires us to pursue our virtue but also reminds us that there should be a principle of justice to keep a balance between the conflict of morality and interest.
Adam smith;moral rules;moral position
F091.33
A
2095-4476(2017)04-0026-05
(責任編輯:徐 杰)
2017-03-03;
:2017-03-30
郭敏科(1992—),男,寧夏銀川人,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