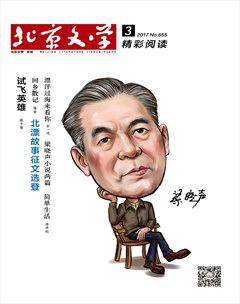張麗小小說兩篇
失獨
初冬難得的晴日,藍天沉在池塘的水底,幾朵云彩被粼粼的波光清洗著,白得晃眼。
進村第二家是英子的娘家,三十年前我就熟了。從小學到初中,我和英子是最要好的同學、姐妹,連英子媽都說,她家就是我家。英子家很溫暖,爸媽和善,房子又是我們老家最好的紅磚墻。還有三間厚實的木樓,冬天暖和,夏天陰涼。我和英子在她的房間吃柿子、柿餅,躺著咬耳朵說悄悄話,趴著做作業。總在我們玩累的時候,傳來英子媽的喊聲:“伢們,快出來吃飯。” 這次,也是午飯時分,只是隔了三十年,還少了一個人。是的,少了英子。我是一個人回來看英子媽,也是我的干媽的。
英子屋后的銀杏樹光禿禿,散落的黃葉被風吹得七零八落。那棵柿子樹向蒼天伸著無助的枝干,托著幾個紅紅的小燈籠。都冬天了,竟然還有沒被寒霜打落的柿子。柿子可是英子最愛吃的啊,如果……我不敢想,鼻子發酸,腳步發軟。拐了個彎,就看見坐在太陽下的英子媽。才一年不見,她更瘦小了,頭發全白了,像罩著一團水洗的白云。曾幾何時,我和英子搶著在她頭上涂抹洗發水,揉搓出一把把白色的泡沫,跳著笑著歡叫,媽媽是個白頭翁,媽媽成了老奶奶!英子媽真的成了老奶奶。我都走到她跟前了,還不見一點動靜。趴在她腳邊的黃狗,叫了一聲,懶懶地仰頭看我。
我喊了聲“干媽”,沒有回應。便走到她面前,她看著我,表情呆呆的,似乎面對一個陌生人。
干媽,您不認識我啊?我是蘭蘭,英子的好朋友啊!我拉過她的手說。
英子?英兒——干媽機械地念叨著英子,手拍懷里的小棉被,身子一下下搖動。椅子很扎實,是上世紀70年代家家有的圓椅,椅靠大半圓,彎到前方空著,孩子坐進去后,用木棍穿過彎靠洞眼,以防孩子掉下來。這種圓椅是為小孩制作的,大人一般坐不進去。干媽坐的顯然是英子小時候的圓椅。
不是啊,干媽,我是蘭蘭,蘭蘭!我擁著干媽作無力的申辯——她已經不認識我了,甚至腦子不清醒。風吹進我酸澀的雙眼,強忍的淚珠在池塘道道波光的映射下,顆顆滴落。
怕干媽看見,便趕緊擦了眼淚找英子爸爸。
進門又是白,先是一院子的白棉絮,再是干爸的白發白胡子。
干爸拍著我的背,說,過去了,伢,莫哭,哭也哭不回。
我捂住嘴,忍住不哭,可干爸的眼睛分明是紅的。他嘆了口氣,唉,英兒走了,真的走了,可她媽就是不相信哪!
干爸帶我去英子的房間,那是我和英子的閨房啊!一切還是過去的模樣——床靠墻擺著,書桌上擺放的柿子軟塌塌的,起了黑斑。床上鋪著床單,厚厚的被子是綢緞被面,條紋被里,摸上去柔軟溫暖。干爸打開衣柜,除了英子的衣服,全是棉絮。
英兒從小怕冷,她媽年年給她種棉花,打棉絮。太陽出來就抱出來曬。干爸說。
我走到院子里,把臉埋進吸飽了溫暖的棉絮,陽光的味道撲鼻而來,一股溫熱順著我的雙眼、鼻翼,緩緩流下。
自從英兒一走,你干媽腦子糊涂了。天天坐在那個圓椅里。那椅子,唉,是英子爸留下的。
怎么可能?您是說——英子不是你們的孩子?我覺得干爸也開始犯糊涂。
蘭蘭,你忘了嗎?小時候你倆問過我們的,為啥椅子底板上的名字不是我們的。
是的,我記得。底板上的名字是阮清華,我們村方圓幾十里沒有姓阮的。
英兒媽不能生,我們才抱養的她。把她當寶貝養大,哪曉得她年紀輕輕得了肺癌,才活到四十歲——就要我倆老,白發人送她……干爸的話在風中顫抖:她爸是山里的木匠,伢養多了不耐活。英兒小沒人帶,丟在圓椅里不愿意,哭死哭活的,爸媽哪忍心——我們抱她過來,她爸媽送了圓椅,說是個念想,還有那小包被……
干媽還在陽光下,手拍小包被念叨著什么。英子稚氣的話又在我耳邊響起:蘭蘭,你有一群兄弟姐妹,我為啥是獨苗啊?
獨苗吃獨食,你看,滿樹的柿子都是你一個人的!站在樹下,我喃喃著當年的話語。
池塘的水泛著清冷的白光。“啪”,一個柿子落到地面,鮮紅的汁液,血一般飛濺。
過年之后是來年
車駛入老家熟悉的水泥路,他的視線穿過行道樹掃向那片麥田。麥子一筷子高了,綠得像一片海。都要過年了,還不見雪花的影子。這要是在十幾年前,早就是大雪紛飛,四野茫茫了。“今冬麥蓋三層被,來年枕著饅頭睡”,寒冬里,潔白溫潤的雪花,才是麥苗的滋養品呀。兒時母親教他念農諺,他迫不及待地想吃饅頭,問啥時候是來年。母親說,過了年之后才是來年。“來年”——他若有所思地念叨著,打定主意,一定要把母親接到城里,全家人共赴來年。
母親在院子里扎草把子,突然聽到他的喊聲,愣了愣才轉身。“進兒,是你!”她一手攥緊稻草把子,一手拉身后的椅子。“熱椅子,快坐,我去拿開水。”顯然,母親對他回家是驚喜的,也是驚慌的,完全不像她做農事那么麻利。他追隨母親急急的身影,看到了零星的白發和還算挺直的背。
母親給他加了開水,就忙著準備午飯。他把院子里草把子搬到灶屋說,媽,咱家路邊的那塊田,麥苗長得蠻好的!母親用打火機點燃草把子塞進土灶,應聲說,好是好,也長了不少苦草,苦草圍著麥子長,麥子難出頭,得趕緊除掉。他想問,咋不用除草劑呢?覺得問了也是白搭。就像他無法阻止母親回到鄉下,無數次阻止母親種田,田里還是麥苗青青。
對于母親的執拗,他曾經很惱火。他一個堂堂的城建局局長,把年近花甲的老母丟在鄉下,不說同僚們嘲笑,就是族人會怎么看?可是好話說盡,母親說走就走。那還是前年春節,來送禮的下屬剛走,母親就數落“吃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軟”,非要他趕緊退還。身在官場,他深知人脈的重要,人情似網,有些禮不是一個退字能解決的。他寧愿母親賭氣離去,也不能讓人情網撕裂一個缺口。
吃罷飯,母親拿起小凳和鏟子對他說,進兒,你睡會兒,有太陽,我去扯草。母親是在回避他,根本沒有去城里的意思,他哪里睡得著?他順手拿起個小凳說,不走了,我也去。還是那塊田,十多歲的時候他就跟著母親扯草;還是那種苦草,和麥苗相似,細長的葉,白皙的莖,蓬松的根,綠得比麥苗淺,長得比麥苗嬌嫩,卻比麥苗躥得快。最初他分不清哪是麥苗哪是苦草,母親讓他多長個眼睛,莫被苦草的障眼法迷住,好壞不分。現在,他當然分得清苦草和麥苗,可母親不說草。母親說,兒吶,媽不是不會享福,在農村做了一生,我不做事過不得。趁現在身體好種點口糧,送你們吃,我心里舒坦。他急著分辯,您兒子當局長,想吃啥還愁嗎?您這大把年紀,一個人在農村種田,不是摑兒的臉?叫我么樣見人?母親嘆了口氣,伢呀,兒當官媽不跟著享福,外人不會道長短,要說也會說咱家人本分。媽跟你住,看人家送東西來就睡不著。住在鄉下,牽住兒的心,你就可以推掉應酬多回來,看一下我,接下地氣。他覺得母親的心思太瑣碎又不無道理,就說,我哪能時時看您?不在您身邊的時候,我怎能心安?母親笑了,媽的身體骨好得很。雖說我人不在你身邊,心思可在哪。聽說你們又在搞大工程,拆林場建小區,是真的么?聽母親關心他的工作,他馬上來了精神,像兒時得了獎狀那樣炫耀起來:是的,林場離城里近,有山有水,建個小區,栽花種樹修草坪,整體規劃的,要多好看有多好看,要多自在有多自在,來年您去住一套……
我才不去咧!母親打斷了他的話,有些生氣地說,好好的林場改小區,該砍多少樹,不是作孽么?
作孽——他沒想到母親是這樣認為,便解釋說,安居工程是政府行為,是為老百姓造福。
母親扯起一把苦草問,這苦草有你們種在草坪的草好看吧——實際上它叫麥苗草,長得和麥苗一樣,我們農民可分得清,叫它苦草,因為它壞事,把麥苗害苦了,有它在,麥苗難得活——算了,房子都做起來了,我一個農村婆操啥閑心呢!改建也有改建的好處,我是舍不得那些樹。進兒,把房子做好些,可不能耍花架子,搞草包工程……
母親的嘮叨攪得他心緒不寧,手里的草也像一根根綠箭扎人。他點燃一支煙吸了一口,抬頭看見不遠處小學外墻上“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紅標語。這些標語母親都爛熟于心,自己怎么熟視無睹呢?在升騰的煙霧里,他仿佛看見機器張牙舞爪,林場的樹一排排倒下。樹林在后退,退一片,樓房豎起一棟。一退再退,房子雨后春筍般生長,比苦草的勢頭兇猛無數倍。苦草靠擠壓爭盤奪地,樓房靠抹殺顛覆而矗立,這一場場不動聲色的殺戮與官場你死我活的爭斗何異?
——過年之后是來年。想要有和諧太平的來年,真的該好好考慮了!他想。